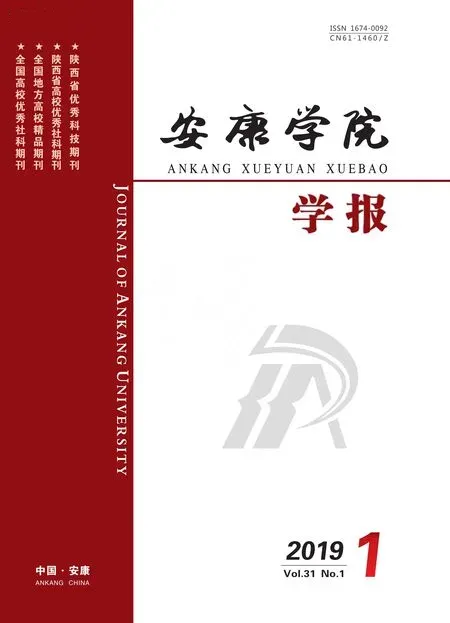论电影隐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以电影《湮灭》 《降临》为例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隐喻作为历史生成的人类文化特定形式,广泛地存在于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作为隐喻艺术”的电影,其隐喻又与一般的文学隐喻迥然不同,因为电影的直观画面性决定了其隐喻的转换过程与文学的差异。它省略了从抽象符号到意象的这一文学喻义转化环节,而直接进入画面、场景的意义隐喻性转换层面。电影的摄影特性使影像隐喻应用更为广泛和普遍,在一定意义上,它规定了电影叙事的特性,较之文学的文字隐喻更为丰富、生动和自由。然而电影隐喻的自由灵活,也导致了隐喻意义呈现出不确定性和松散性,造成了人们对其识别上的困难,使得识别主体产生意义分歧,从而出现了同一电影隐喻有不同意义解读的现象。本文拟以科幻电影《湮灭》和《降临》为例,对电影隐喻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深入探讨,以期丰富和充实电影隐喻这一领域的研究阵图。
一、视觉隐喻及其图像表达
随着“视觉文化”的到来并渐渐盛行,在这样一个以“看”为主的视觉主导世界里,视觉隐喻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视觉隐喻的关注点是从图像开始的,对图像隐喻的解读是影视文化接受的基本途径。视觉隐喻解读需要相应的前理解为基础,这种前理解正如潘诺夫斯基关于图像阐释理论的第二与第三个阶段解析涉及的论域。在阐释的第二阶段——“图像志分析”阶段,阐释的对象是第二性或习俗主题,即根据传统知识分析、解释作品图像中的故事和寓言,观众由此进一步分辨其中的故事或人物。解释者需要“熟悉特定的主题和概念”,具备一定的文献知识。第三阶段是“图像学阐释”阶段,即发现艺术品的深层意义和人类心灵的基本倾向,“揭示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宗教信念和哲学主张的基本立场”。研究者必须具备综合直觉和“对人类心灵基本倾向的了解”[1]。在这一阶段中对图像隐喻的阐释是最具争议且最难把握的,其解读所依赖的因素非常庞杂,不只是具有基础文献知识这么简单,还包含一定的个人阅历、经验和对文化、人性、宗教等的感悟和理解。
(一)衔尾蛇与灯塔
在电影《湮灭》中,衔尾蛇图像作为队员自生自长的文身多次出现,其蕴含的意义与西方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衔尾蛇作为中世纪教堂建筑常见的雕塑符号,大致形象为一条蛇(或龙)正在吞食自己的尾巴,结果形成一个圆环或一个数字“8”的形状(如图1所示)。在中世纪炼会术中它是重要的徽记,其含义为“自我吞食者”(self-devourer)。

图1 衔尾蛇图像
在西方文化中,这个图像一直有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无穷”或“循环”等意义。衔尾蛇不断咬啮、吞食着自己的尾巴,体现着生命与死亡的轮回交替。从生态角度分析,大蛇需要吃掉尾巴才能生存,自己的尾巴为它带来无限的食物,而自我吞食随时交织着的是死亡与再生的存在悖论,这是一种生与灭的永恒循环模式。
这一图像在《湮灭》中是以队员左臂上的自生自长文身出现的,并且是在他们进入“闪光”(shimmer)之后慢慢生长出来的。可以理解为是在棱镜环境下的一种基因折射引起的突变,但突变的文身可以有很多样式,为何在这里是衔尾蛇?首先,这里需要理解何为“湮灭”?这是一个物理学概念,简单的理解,就是电子与反电子(电荷相反)被“无中生有”的过程,被称为粒子—反粒子偶的产生[2]。反方向的过程同样存在:当一个电子与反电子相遇时,它们发生湮灭,它们的质量变回能量,在一瞬间变成光。所以湮灭又称互毁、相消、对消灭。电影《湮灭》中外星不明物体坠落在美国国家公园的海岸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如“泡泡”一般的能量场,这个能量场在不断地一天天变大,凡是进入能量场的人都未能生还,而在能量场之中的人或物都产生了基因突变。由于整个“闪光”是一个棱镜而非屏障,它不仅折射了光和无线电,更在折射其中一切生物的DNA,人类、植物、动物的DNA互相折射产生了很多奇异的现象,比如:树枝上会结满水晶、植物会生长成人体的形态、人的手臂会生发出花草。所以,进入“闪光”的人都在“闪光”中产生了基因折射,并形成了各自不同形式的“湮灭”。看似是死亡,但经历这样自我吞噬后回馈的就是新形式的永生。同时,“闪光”中X区域的动植物都是以基因复制的形式循环往复地生存,比如女主角和她的丈夫,都被如同曼德勃罗集合一般的“能量团”复制出另一个自己,而真正的自己则被“湮灭”。所以,整部电影所呈现的就是一种变异、解构和重生,就是一种自我的湮灭。因此不难看出,衔尾蛇所体现的是一种宇宙循环观的理念,即一种建构与破坏的循环往复。
《湮灭》中灯塔的图像隐喻意义在于预示。灯塔原有指引、希望等含义。外星不明能量场坠落在灯塔旁,是一种预示,它暗示着在外星的高级文明面前,人类那些引以为傲的文明和进化史,在浩瀚的宇宙中可能渺小到不值一提。所以,高阶的外星文明在收集到女主角和她丈夫的基因序列后,掌握了人类男、女基因的“能量团”,已经完成了立足地球的第一步,并创造出了能完美适应地球环境的生命载体。这时,曾经的“闪光”犹如实验室的保护膜一样失去了意义,所以选择在灯塔自我毁灭,也预示着外星文明犹如灯塔一般,指引和带领接下来的人类文明的走向与发展。
(二)笼中鸟与七肢桶
“笼中鸟”在电影《降临》中反复出现,不禁让人联想到希区柯克在电影《鸟》中试图传达的“笼”中之“鸟”与“笼”中之“人”的隐喻关系。故事以“鸟”被关在“鸟笼”中开始,以“人”为躲避鸟的袭击而把自己关在电话亭、房屋等近似“笼”的东西里面而结束。“人”与“鸟”之间的隐喻关系,通过叙事得以转换。希区柯克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观众在“人”与“鸟”的隐喻关系中感悟世界,思考人类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3]。在《降临》中,笼中鸟的用途是检测外星飞船中氧气含量是否适合人类接近,而对于外星生物来说,笼中之鸟也就如同我们被困在线性时间内无法超脱。这个“时间”即禁锢我们的笼子,在笼中“歌唱”的我们引以为傲的科学与文明,其实在外星生物眼中不值一提,而我们不过就像这笼中鸟一般。人类将自己封闭在自以为安全的“笼中”,对外星生物友好的帮助也恶意揣测并无端制造恐慌,人类彼此之间也不愿相互分享和帮助,如同这笼中之鸟一样孤立无助、自私自负。进入外星飞船的人类,都包裹在厚重的如同鸟笼一般的层层防辐射服之下。笼中鸟还出现在女主角女儿的画中,画中爸爸妈妈的中间是笼中鸟,这笼中鸟也是一种隐喻,女儿如同笼中之鸟一般,只能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七肢桶(heptapods)的触角如章鱼一般,同时还有大象一样粗糙皱褶的表皮、鲸鱼一样庞大的身躯,整体具有很原始的非拟人形态。导演尼斯·维伦纽夫表示:“我想打造出一个具有超现实的外星生物,它们来自一个梦幻与噩梦的世界,它们是颠覆人们认知想象的……”[4]影片在展现七肢桶的时候,并没有将其全貌毫无保留地直接拍摄出来,而是当七肢桶出现时一定会有一种白色烟雾与之相随。幽暗浓雾下的黑白色彩,使得影像的视觉效果显现出缥渺和无形来。没有完整的形象,需要观众去臆测,它带来的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未知感体验。因无法洞悉浓雾背后的主体,遂使影片也隐含了一种不确定和不安的情绪。
七肢桶的文字带有浓厚的东方水墨文化意蕴,这是一种可以书写在玻璃墙体上的墨色闭环或半开环文字。外星的环形文字代替了语言交流,借图形化的文字推动叙事,圆形文字可以拆分成12个基本部分,字符组合拼接不同形状的墨迹斑点,表达不同的句子和含义,这样的文字设定,具有强烈的陌生感和神秘感。女主角在学习七肢桶的文字时,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从西方向东方的反向文化融入过程。其文字的每一种墨迹斑点和形状,都隐含着语素和叙事的信息,在其落笔时已能预知将要表达的内容,而预言命运的每一步其实都是通往既定目标的过程。在已预知未来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重新体验生命的完整过程,从而形象化地隐喻了影片中非线性时空观念这一命题,即时间可以如同圆环一般,它是一种轮回。这也就最终诠释了影片对生命的理解和对宇宙的感悟。
二、类型隐喻及其叙事模式
类型电影是在电影工业体制下所产生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好莱坞电影工业体制中。正如达德利·安德鲁所说:“类型在电影总体机构中有明确的功能,这个机构包括一个工业,一种信息生产的社会需求,一大批人类主题,一个技术系统和一套表述惯例。”[5]而类型的本质是“形构的稳定性”与“文化的凝聚性”,类型的发生与发展是文本在“形”与“质”方面所求的和,而类型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形式的稳定性获得文化的凝聚性,是“互文性”的扩散[6]114。
托本·格罗达尔则认为:“尽管一个成形了的类型在精神与身体上具有一定的原则,这个原则也不是本质的东西,但和其他的类型选项相比,它获得自身的一个特殊的效果,一个建立在情感反应基础上的类型体系和一个类型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致,这是以一个既定环境里选择故事的观众为基础。关于支配性的情绪冲击的类型期待,能够更深入地在观众对一个先在的影片的重构中起到重要作用。”[7]所以,观众接受的重要基础是情绪,电影隐喻的传达也是靠观众在一种想象性的情绪中完成的。在类型电影中,观众的情绪是建立在一种与视觉相似性的基础之上的。例如科幻类电影,观众的情绪是建立在外星飞船、外星生物、茫茫宇宙、超前科技等这些相似物的联通关系之上的,从而奠定了观众感知的一种情绪基础,即这一类事物的复现就会产生一种意义上的关联,从而为类型隐喻奠定基础。在《湮灭》和《降临》中的外星生物,一个没有具体形象,另一个则是具象的,但在科幻电影中,外星生物这一事物的复现,造成了观众的一种感知的联通性,即外星生物出现,观众便会有侵略或反侵略的情绪认知。无论这部电影所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这种情绪都会导致这样的类型期待。
在众多相似性的图像隐喻的复现中,也存在着核心隐喻图像的复现。电影《降临》中的外星飞船的出现方式和电影《独立日》中外星飞船的出现方式具有一定的相似点,即都是多艘外星飞船分别降落在地球上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上空。但不同的是,《降临》中的外星生物是来帮助人类,同时请求人类帮助的,而《独立日》中的外星生物则是要侵占地球,所以这种图像复现所对应的语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20世纪末,人类对于自身安全和领土安全,普遍存在着一种危机意识,遂将这种危机意识艺术化地投入到外星生物的入侵与人类勇敢反抗并取得胜利的电影叙事中,歌颂人类不畏强权勇敢反击的抗争精神。当今人类更推崇和平而非战争,在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下,新的时代主题彰显的是和谐与共赢、沟通与合作、交流与互进。所以图像的复现,最终指向的,还是一种文化语境,而非只是图像的本身。
除了图像的复现以外,类型电影还存在着相似的叙事模式,这其中包括“核心的叙事隐喻模式”。这是决定电影类型中叙事隐喻的关键要素,是叙事模式中归纳出来的一套被认可的经典隐喻模式。由于核心叙事隐喻模式的存在,单独的文本叙事结构就有了比对的参照系,当单独的一部文本在叙事上出现的独特性与这个核心模式出现差异时,就会产生隐喻效果[6]125。同属于“外星生物侵略”模式的《湮灭》和《降临》,即与传统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湮灭》中外星生物制造的“闪光”,其实就相当于一种外星飞船,一种实验舱。在《湮灭》和《降临》中,外星生物来到地球,人类都对其目的表示疑惑和担忧,都试图进入“飞船”一探究竟。《降临》中人类不但与外星生物友好交流,还学会了外星文字。虽然其间曾存在误解,但最后还是实现了和平解决,人类互帮互助,外星生物也达到了帮助人类的目的而离开。与传统的“外星生物侵略”模式不同的是,电影所传达出来的一种大爱、博爱与和平的主题。片中反复提到的“非零和博弈”,即“游戏中双方的互利”。这一词的反复出现,也隐喻了国际关系与星际关系在本质上的某种相通,即应推崇和平合作、交流沟通。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下,东西方文化相互包容理解,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交流与互进,促成了世界文化繁荣时代的降临。而《湮灭》虽然还是沿袭了外星生物侵略地球这一模式,但片中并没有激烈的星际大战,也没有血腥的屠杀,而只是经过折射人类和动植物DNA造成变异而完成电影叙事。这更像是一种生物战争,没有硝烟但是威力十足。最后《湮灭》也没有遵从旧有模式,外星生物夺取了这次无声无息的战争的胜利,造就了完美的人类复制体。隐喻当下人类应时刻保持一种危机意识,在未知的外星高级文明面前,人类或许根本不堪一击。
三、生存母题及现实诉求
类型隐喻是文本与文本之间意义连接的重要通道,它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互文性”隐喻场,而“原型”是隐喻场中的核心支点。依据诺斯罗普·弗莱的观点,原型是“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形象”,是一种可“交流的象征手段”。对原型的关注主要是“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交流模式”,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程序和体裁的研究”,“力图把个别的”纳入“全部的整体”[8]。但是,原型只是一种“原初形象”,无法形成一种主导,因而被文化母题所结构。反观科幻电影这一类型,我们发现无论题材是太空探险、星际侵略,还是时空旅行、人工智能等,科幻类型电影的题材都存在一种共性,即表面看起来脱离人类实际生活,但其内在深层意蕴却仍在探讨人类的生存、发展、本体价值等根本性问题。科幻电影旨在通过一系列被陌生化了的形象,来对生命、时间、哲理、伦理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可以说,对人类与外星生命或先进科技如何相处的探讨,即为科幻电影的文化原型。这样“生存”这一母题就成为科幻电影的无意识归纳,它关注的是人类文明与外星或高阶文明、人类文明与自身之间如何相处和生存所显现的同质化的文化和心理映像。所以,如果说若干类似的原形指向一个同一化母体的话,那么科幻电影类型隐喻的特质与指向就是对“生存”母题的表征。
作为科幻电影的母题,“生存”也体现在科幻电影的叙事文本中。许多科幻电影喜欢表现外星生物入侵地球,抑或是外星高阶科技入侵地球,也有人类入侵外星文明,或是人类自身与未来文明的对抗等等。无论表现的主题是哪一种,必然是对人类或外星文明的生存探讨。如电影《湮灭》在外星生物入侵地球之后,并没有展开大肆地杀戮,而是制造了一个宛如梦幻泡泡一般的“闪光”,“闪光”一天天的变大,并一点一点蚕食地球,这样的蚕食是通过折射改变人类和动植物基因序列来实现的,并没有杀死任何生物,而是将生物基因变异。由于生物不同的基因序列,自然产生了不同的变异体。当女主进入“闪光”之后,发现自己已经被基因折射和改造,她的反应并不是单纯的惊慌,而是惊慌中带有一丝敬畏和好奇。所以,在外星文明入侵地球后,这样的基因改造是否会让地球变得更“好”?高阶的基因改造是否是人类文明承续和发展下去的另一条道路?这场无声的侵略战到底是人类文明同化了外星文明,还是外星文明改造了我们?谁才是最后生存下来的赢家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引发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一遍又一遍地呼应“生存”这一母题。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社会戏剧的阶段性结构并不是本能的产物,而是行为者头脑中所带有的模式和隐喻。”[9]这里,维克多·特纳把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和社会事件视为一场戏剧,并用戏剧的方式对其进行考察,但是他所指出的隐喻及其在社会性戏剧中的作用,对电影也是同样适用的。
四、结语
总之,隐喻在电影的表意结构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它是构成电影镜像语言和叙事技巧的重要手段和基本要素。意大利电影理论家帕索里尼就明确指出:“电影靠隐喻而生存”[10],尽管这个结论是其针对“诗电影”的分析而得出的。罗伯特·斯坦姆也曾指出:“电影理论的历史也可以是关于创作电影的隐喻的历史‘电影眼睛’‘电影麻药’‘电影魔术’‘摄影机与自来水笔’‘电影语言’‘电影之梦’以及‘电影镜子’等等。”[11]所以说,“电影,作为隐喻的艺术”一点也不为过,它早已深嵌在电影文本的方方面面,成为电影表意的有效机制。因此,持续深入地研究和探索电影隐喻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对当下电影理论创新和体系建构,以及电影创作美学品格的提升,无疑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