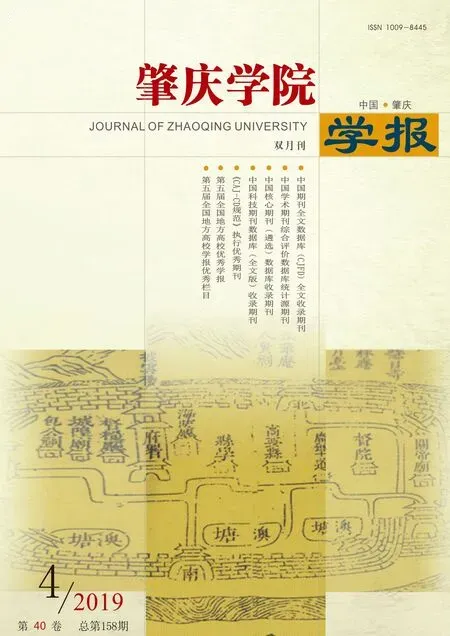现场:一种集体沉浸式空间
——20世纪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表达
肖 平,李 冉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2.上海自道精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 201203)
一、“不约而同”:因素与诉求
最早提出新纪录片运动概念的吕新雨在界定这一中国纪录片独立而又独特的影像创作现象时,对于独立纪录片及其运动,采用了“不约而同”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纪录片导演把眼光转向民间,将创作者自身与拍摄对象置于同层面,即平民化的视角与视点建立起独立纪录片导演共同的趋向,“纪录片的作者怎么去看待他生存的这个社会,他怎么去建立和这个社会的联系”成为不约而“同”的核心,据此,独立书写与共同关注才能形成书写并作为现象级次的创作风潮和趋势。
(一)开端的意义:《流浪北京》
吕新雨在讨论新纪录片运动时提出:“新纪录片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开始的。”[1]41这是因为纪录片《流浪北京》给予观看者一个全新的创作者与创作对象之间的关系,吴文光关注到何为现场,颠覆了传统的专题片那种权威的、全知的和引领的视角,其开端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反叛,研究中国纪录片发展就必须注意到《流浪北京》这一新纪录片运动的“重要文本”[1]41,尤其是纪录片导演的认知权力和纪录片对象的原状形态,决定了新纪录片运动的不约而同。
《流浪北京》纪录了五位青年新艺术“流浪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段北京生活。其中文学的张慈、摄影的高波、绘画的张大力和张夏平、先锋戏剧导演牟森等。五位流浪艺术青年作为纪录片中的人物来自云南、四川、黑龙江等地。他们有的是放弃在老家的工作来到北京寻找理想和生存方式,有的是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五个人物个性独立,境遇不同,因为有着共同的追求而成为纪录片中色彩各异的纪录片对象。王慰慈在研究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时针对《流浪北京》的创作指出之所以成为新纪录片运动的开篇之作,是导演吴文光不仅仅要反叛传统专题片的虚构,还要将自身对于当时社会的观察采纪录片的方式呈现给社会观看,因此,《流浪北京》“除了表达流浪艺术家的心灵本质外,还隐密地反映了现在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企图从主流意识形态中自我放逐,游离在现行体制的边缘”[2]93,这应当是《流浪北京》作为开端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流浪北京》作为开端的价值及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创作者层面来看,后面有着一批“不约而同”的导演出现;二是题材对象由高大全的题材统治观看并建构观看,变为平民化趋向张扬个人认知的民间话语与现场。
吴文光在谈到当时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群体时的状态,认为当时的创作者有表达的愿望,能够豁出去,无所畏惧,大家创作的唯一愿望和冲动是真实,共同认定纪录片创作是一种纯粹个人写作的方式,忠实还原最初的精神和个人的冲动成为一种导演自觉,“不是带着一种非常的理念的、主题的肯定,才来选择哪些该拍,哪些不该拍”[2]107。吴文光关注那些社会的、没有规矩的和流浪状态的所谓街头生活,无论是面对独立性的青年先锋艺术工作者,还是走江湖的街头民间艺人及团体,非常着迷那种自然生活中呈现出来的一种人的生存状态。一言以蔽之,导演的自由选择与倾向使得创作者与民间态度形成高度一致性:导演生活即行走江湖。
追求真实和最有品质的素材即现场,成为众多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趋向,正如贾樟柯提倡的那样,“我们要欢呼一种业余电影时代的来临”[2]158,几乎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都体现出一种面对生活现实的实录精神。段锦川被公认为中国纪录片导演中屈指可数的追求内容与形式相一致的导演,他的纪录片创作特别强调自主选择与构成,明白摄影机的角度和立场怎样建立起其纪录片的真实,他认为“如果拍片时我大部分能够有很大的自主,我会把这样的东西叫做我的作品”[2]125。也就是说,段锦川认为独立纪录片的价值在于导演本身的自主性,能够选择并控制题材的方向,导演必须要具备发现并看到事件发生发展的眼光。尤其是这些独立纪录片导演,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纪录片创作上强调独立,脱离体制表达自我。
上世纪80年代末创作了《风》的导演郝志强也是一个关注时代并反省东西方文化差异问题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作者在那个独特的时代,内心生存着一个否定的因子,创作本能中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就决定了郝志强选择了独立纪录片,并采用冷静和客观的摄影机眼睛去观看并发现身边的原状生态,期待通过关注个体的人的生命存在,寻找真实的存在,纪录片《大树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实现其独立观察与现场建构。郝志强回顾当时进入到独立纪录片运动时的状态时说:“拉着当时拮据的吴文光、蒋樾一帮朋友做了几部这样的片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谈论一些纪录片的话题,我对纪录片的一些概念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于是开始想做一些跟台里没什么关系的片子”[3]10。作者把他的创作比作一个生活的速写,通过纪录一种生存状态,更多地表达自身的观看。郝志强认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与独立纪录片是重合的,所谓独立并非以是否在体制内外为标准,而是指创作者的角度和独立的思考为基础。作为一个需要独立表达的纪录片创作群体,独立是这一群体形成的核心,所谓独立就是期待在纪录片导演个人意志与意识层面形成一个完全属于个人的言说,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叙述方式上走出体制的专题片套路,而这种相对自如的表达空间是与当时社会主流思潮形成了价值与意识上的冲突,这一反叛与对抗本身就成为独立纪录片运动的驱动。
在《流浪北京》之后,聚集着一大批“不约而同”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及其创作。蒋樾以《彼岸》到此岸,从抛开传统开始;杨荔娜是在经过一个小区大墙时偶遇老头并以《老头》的名义加入到独立纪录片运动的“真实电影”行列;李红携《回到风凰桥》与杨荔娜形成反差,作为女性主义独立纪录片代表人物,创作意识与价值取向与吴文光形成了一个呼应,成为以女性视角把纪录片创作由群体价值观向个人主体意识回归的一个范例;杜海滨则是从《铁路沿线》开始取消传统的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以新生代纪录片导演的面貌自觉迎接独立纪录片运动的影像自由表达新时代;周浩的《厚街》则趁DV运动之潮,训练有素地记录与观察感知社会,并实现其独立纪录片的纪录与保存价值;与上述独立纪录片导演经历形成最大差异的是康建宁,在体制内有职有位的电视台专业记者的身份,抱着纪录片的灵魂——真实走向黄土高原,期待在现场寻找关于“脊梁”的真实,并以《阴阳》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独立纪录片面貌,成为这一独立纪录片运动的开拓者和标志。
《流浪北京》作为开端,与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所有纪录片导演共同开创了中国纪录片的纪元,康建宁的《阴阳》的创作则完成了探索一种中国本土文化、生态和立场中国纪录片导演的创作道路。从吴文光到康建宁等独立纪录片导演创作倾向与题材,无一不是从民间立场出发,以真实为纪录片的灵魂,所有纪录片导演在创作中呈现了作者个人对于所置身的生存社会的观看与思考,重要的是通过纪录片来建立起这一观看方式与社会的联系,这也是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称之为独立运动的根本原因。
(二)境遇的重叠:《铁路沿线》
麦克·雷毕格在论述纪录片导演创作时针对创作过程中面对素材问题时,谈到拍摄对象除了真实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导演认知的制作道德问题,“如果你希望你的作品被观众视为公正、观点平衡并且是客观的,你将需广泛地在真实的基础上掌握你的对象,掌握那令人置信并且可靠的村素,同时必须兼具勇气与洞察力地对于如何使用它们做出具解释性的判断”[4]27。纪录片导演如何判断并做出阐述对象也成为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的一个特征,所谓境遇的重叠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导演置身民间;另一方面是导演的观看形成了对民间社会的转向。
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的价值在于这一纪录片现场给予观看者一个“我们视线以外的风景”[5]137。首先,导演选择这一题材是偶然性遭遇。杜海滨是在选择虚构类型的剧情片题材时,遇到一群生存于陕西宝鸡市郑局宝段的铁路边的流浪儿,在毫无准备的时候接触并确定拍摄这一题材。从开始的陌生到后来的熟知无间,铁路沿线生存的流浪儿与导演的摄影机之间的距离逐渐消失,这使得导演第一次遭遇到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创作经历,作者无法预期即将发生的事件,同时又沉浸于这样一种不可控制不可预期的创作期待之中。导演并不掩饰摄影机的存在,以保持对拍摄对象的尊重与告知,从而获得了对象的原状生存形态:一种与我们正常生存状态和习惯决然不同的生存者。
吴文光在观看《铁路沿线》时就为创作者拍摄时与当事人相处生活的方式所打动,推崇导演不掩饰摄影机的存在和导演身份的存在。纪录片中流浪儿生存状态与场景呈现在观看者面前:野外支锅煮面、众人分食一个苹果、吃鸡、捉弄警察、摩丝抹发打扮、谈梦想、除夕夜围着火坑歌舞和修理玩具枪等事件,导演置身于流浪儿的生活中,聊天、倾听,这种“杜海滨的方式决定了这部片子完全是杜海滨式的,具体呈现就是我们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这样的一些被细致、充满耐心拍摄到的段落”[5]138。杜海滨在谈到《铁路沿线》时特别强调了流浪儿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是唯一吸引其关注这一题材的原因。尤其是关于保护当事人和创作现场的认知,杜海滨在拍摄《铁路沿线》时带着一个人进入现场,事后认为其他因素的介入会导致创作状态和创作对象的原状形态失去应有面貌,“刺激我的那种东西没有了,就变成一种姿态”[5]215。215因此,杜海滨在一开始就注意到纪录片导演除了摄影机与对象之间的有效距离外,还涉及到自身创作状态与当事人现场的形态保持问题。包括在拍摄时因巨大的火车冲击力导致的镜头不稳和家用录像带出现划痕等关于何为纪录片及现场的认知,都成为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过程中典范。
上述关于《铁路沿线》创作经历与片断的梳理,产生了三个层面的纪录片概念:镜头距离、现场和创作身份。尤其是作者身份的境遇重叠显示出纪录片与非纪录片的差异,吕新雨在分析中外纪录片差异时,以受到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影响而产生的电视栏目《生活空间》为例,认为无论是电视栏目还是独立纪录片都给当代中国用影像方式书写了一部民间的小人物历史,吕新雨认为这反映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精神。一方面,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题材对象在一开始就是城乡中的平民,如流浪青年、居民、游客、村民、残疾人、农民工、打工者、病患者、少数民族、贫困人和具有独立思想的文艺青年,等等。仅仅如此还不能构成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的核心,重要的是纪录片导演选择显示出趋向民间的纯粹个人化的表达。
林旭东在判断何为纪录片时提出:纪录片创作无论在导演与当事人之间是否有某种相互的感应;另外一个是现场感,这其实就是强调纪录片导演置身民间并尊重原状现场创作原则。这些创作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是在媒体边缘形成的”[5]464,一批与电视台媒体有着各种联系的导演依托其身份,环顾左右将视角圈定在处于边缘而弱势的“失语地位的”当事人群体。流浪者吴文光与反映新艺术青年的《流浪北京》;挣脱体制制约力求独立判断的郝志强以《大树乡》来尝试一个现场速写;段锦川站在广场和居委会的空间,以《八廓南街16号》实现了设定场景的直接电影理念;独立制作人蒋樾游离于电视栏目与地下剧场之间,穿行于《生活空间》和《彼岸》两种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脉络,演绎彼岸与此岸的联系;曾经的车间锅炉工朱传明不肯就范,感同身受《北京弹匠》中小人物的丰富性,触动了距离自身生活,又以最近最坚实的质感去触摸身边熟知的物质;租住在平民区的演员杨荔娜被“一串”在墙跟排排坐的老头吸引而成就其DV作品《老头》;李红由制作栏目节目编外人员,以《回到风凰桥》的女性关注成为新纪录片运动的女性代表等等。朱靖江以“乡愁”、“面孔”和“土地”三个层面划分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的发展脉络及其面貌,将纪录片导演的乡愁与边疆情绪联系起来,关注到城乡之间创作者与当事人的“流浪”面孔日记,坚持着导演创作与土地、农民的亲近,寻找到并建立起质朴的面孔和沉实的生命基调。一言以蔽之,独特的创作境遇与宿命般的生活境遇相互重叠,成就了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不约而同的因素与诉求。
麦克·雷毕格在论纪录片创作时认为导演创作不是一个神秘的过程,否则就无法突破与当事人的距离,摄影机因此只能是某种摆设,纪录片也无法呈现给观看某种只有这一现场才能具备的真情。所有创作都是由创作者与当事人相互面对并接受所达成的最近距离的某种重叠。在这个意义上说,纪录片导演并非描绘人类活动的活动影像,而是主动并具有现场感的纪录,导演本身是站在当事人中间的一个“主观诠释者”[4]28。
二、从独立到表达独立
20世纪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的形态在“不约而同”,这就是说,所谓独立纪录片运动,并非因为独立而成为纪录片运动,而是因为不约而同的共同趋向、价值和关注自然形成了一个别异于其他时期和影像方式的表达,从而构建起了当代中国真正意义层面的纪录片。
(一)《彼岸》:反省与展示
麦克·雷毕格在讨论独立纪录片导演与媒体纪录片导演的差异时,以艾略特和左拉关于人对于生活独立认知的论述进行比较。艾略特说:“所有艺术的功能,都是为了使我们对于生活的秩序有某种理解,因此它强加某种秩序在生活上”[4]29,艾略特强调的是艺术的功能对于生活的解释。自然主义观的左拉则是关注艺术与自然的联系,认为“一件艺术品乃是透过某种性质而看到的自然的一角”[4]29。麦克·雷毕格认为艾略特与左拉的观点是在主张个人在艺术创作中认知自然与生活的主导作用,而作者对于生活的认知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人格特质及良知”[4]29。
蒋樾说,《彼岸》就是此岸。这与他早期从事戏剧编剧工作有关,同时,这一经历也导致了蒋樾会敏感到牟森主导的话剧《彼岸》,并关注到牟森的先锋“戏剧车间”,这才有了独立纪录片《彼岸》的反省与展示。蒋樾的纪录片创作是从大学开始,从抛开传统开始,“我们完全抛开过去的传统,那时候西方的东西刚进来,对中国来说,文艺思潮都是从美术这里开始的,艺术界对人的思潮比较敏感”[2]157。作者早期热衷投身当时风起云涌的西方文艺思潮,尤其是美术界的思潮与运动使得他沉浸于当时中国艺术界和学界风靡一时的“荒诞戏剧”“贫困戏剧”“行为艺术”等,用蒋樾自己的话说,当时并不懂什么是纪录片,但用镜头面对在这一文艺思潮中搞所谓运动的人们。除了戏剧、美术的影响外,还有早期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影响,如张艺谋的《黄土地》。作者当时的身份类似于北漂族,即不是电视台的人,也不是单位的人,但是一个北京本地的漂流族。蒋樾读书时代北京流行着文化流浪者身份,身边的朋友在他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过着流浪生活,蒋樾也认定自己也是这一流浪族的人。这种生活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蒋樾跟随黄建中导演担任电影副导演两年后辞职,又追随着外流潮,前往西藏生活了两年。在西藏的两年时间,他开始思考过去经历的许多事情,“体现在我身上的是理想的破灭,开始觉得现实的思考是比较重要的”[2]161。此时,经历了上纪录八十年代中后期文艺思潮、实验戏剧活动和电影创作的蒋樾“希望有一种个人的创作”[2]162,从而与《流浪北京》的摄影卢旺平合作,关注煤矿工人的生活,开始接触中国最底层社会的人,与产业工人、农民、社会职员等的接触,使其对社会有一种重新的认识,这一认识主要是自身的审视,至此,作者回到最熟悉的北京,开始了独立纪录片《彼岸》的创作。
纪录片《彼岸》的题材对象是牟森的戏剧车间所排练的高行健的剧作。《彼岸》的拍摄对象就是这部先锋话剧的所有演职人员,作者拍摄时不仅关注到在这一戏剧车间牟森和他的学生们的排戏全过程,还关注到这些学员们的生活和想法。蒋樾回顾自身的创作历程时解释了为何选择这一题材的原因:“那时候牟森在办《彼岸》里拍的那个训练班。我一看他那种训练方式,包括青年人的那种躁动,我特激动,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当年的理想和那种青春的劲头”[1]147。《彼岸》的当事人是一群没有考上大学有志于表演的外地孩子。他们在北京电影学院进入到戏剧导演牟森的一个戏剧训练班。纪录片跟随这个培训班四个月时间,拍摄他们的排练和生活。三个月后蒋樾再次见到戏剧培训班和演出结束后的孩子们时,这些怀抱明星梦想的孩子们从舞台还原成高考落榜生那种没有掌声和鲜花的普通人生活中,“他们已经被那个瞬间粉碎的大梦扔回到残酷现实之中,流浪在北京城里”[1]165。蒋樾谈到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最困难的时候,与当事人同样处于某种茫然状态之中,导演用四个月时间,在戏剧车间拍摄“一群人跟着一个人排了一场戏,来了一群人,在那里看,很激动”,而纪录片所有的拍摄与当事人一样困守于那间有限空间的小剧场排练厅,与社会隔绝,仅仅属于某种精英式的封闭圈子的场景。
无论是纪录片的创作还是当事人的戏剧与生活困惑,本身给定了纪录片一个合理而且具有隐喻性的框架,从乌托邦式梦想的开始到梦想的破灭,使得当事人重新回到现实,“他们就在北京沉下来了,寻找各种方式来生存”,此时,蒋樾突然领悟到纪录片创作困境所在正是与拍摄对象的困境所在一样,如果仅仅是把摄影机架设于排戏厅的排戏过程,不能让当事人走出窄小的剧场空间走向社会,这个纪录片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与价值,正是戏剧的剧场空间的打开和戏剧梦想的破灭,使得当事人走向外部的社会,“‘彼岸’的意义也产生了”[3]21。如果把这一纪录片题材对象的戏剧车间活动作为一个展示的话,人物的戏剧生活展示就是期待当事人将“彼岸”当作此岸立足,由此形成了一巨大的当代反省:此岸即彼岸。
梳理蒋樾的《彼岸》创作历程,立足基础在于审视90年代独立纪录片运动中那种自我反省与回归的纪录精神和具有人文情怀的立场,朱靖江、梅冰在研究蒋樾的创作经历时总结到,蒋樾的《彼岸》是新纪录片运动的典范,经历这一历程,使得他开创了国家电视媒体的纪录片栏目《生活空间》,体现了民间立场与理想主义的态度,让纪录片纪录并发掘出掩藏于“贫困与卑微的尘埃之下的人性光辉”,由于导演自身独特的创作经历与影响,与段锦川、康建宁等纪录片导演相比,蒋樾的纪录片认知与风格是建立于时代与社会变迁这一巨大历史背景之中,由某一类型人群或者某一事件切入,展示并反省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命运。
“我在《彼岸》里面有这种隐喻,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消失了”[2]161。所谓《彼岸》即此岸,是说立足现实观看理想现实。作为旁观的戏剧人身份的蒋樾观看牟森的戏剧车间的活动,摄影机面对的排练舞台场景就如同当时中国特定时期的广场场景,所有的人以为就置身于彼岸,其实彼岸仅仅是一个名词,乌托邦的想象消失使得舞台上所有的戏剧表演者和戏剧人物本身在双重层面上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有的人表演与观看都被陌生化了,在这一自身置身并创造的场景中沉寂了。《彼岸》的作品力量即在此。
(二)《八廓南街16号》:构成直接电影的真实
罗伯特·C·艾伦在讨论美国真实电影的早期阶段时给直接电影或真实电影一个定义:“真实电影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利用同步声、无画外解说和无操纵剪辑尽可能忠实地呈现不加控制之事件的一种尝试”[6]77。这一定义中的不加控制成为纪录与虚构的区别。这是由上世纪60年代罗伯特·德鲁领导的一个纪录片摄制组,为电视台创作的纪录片节目给定无论是拍摄者还是当事人一种置身现场,即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而引发出的纪录电影方式。史蒂文·芒贝在《美国的真实电影》一书中也强调了纪录片创作中创作者自发而“不受约束”[6]77有专门一节关于直接电影与真理电影的创作分析与比较。应当说,流行于上世纪60年代的直接(真实)电影是对格里尔逊的创作性处理现实的、以解说取代事件并干预事件材料的反叛。单万里在两种电影创作观念历程基础上,概括出直接电影与真理电影的区别关键在于“纪录”与“虚构”两个核心概念的差异对抗。
直接电影观认为纪录片应当是对现实生活的纯粹纪录,采取旁观不干预和等待的方式,摄影机处于被动状态下纪录与保存原状现场;真理电影观则主张纪录片应当干预并促进事件的发生发展,以挖掘出事件背后深层面的事实,同时可以采用虚构策略并建立起影像的权威叙述视角。单万里梳理主要由美国和法国纪录片导演创作实践总结出的基本概念后分析界定两种创作主张和方式的差异:“从根本上说,‘真实电影’是一种反对虚构的电影,以至于‘非虚构影片’一词逐渐成为后格里尔逊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纪录电影定义,并且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甚至成了‘纪录电影’的代名词”[6]13。对真实电影观与真理电影观的发展与差异进行简单比较的目的,是基于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掀起的不同于以往传统专题片(纪录片)的认知方式与价值取向,尤其是以段锦川为代表的真实电影观的独立纪录片创作已经成为中国纪录片创作成熟的标志。从严格意义上说,90年代开始,中国才在影像表达方式和价值取向层面意义上具有独立纪录片。本节将重点以段锦川与怀斯曼之间的创作与联系开展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讨论。
段锦川毫不掩饰怀斯曼对其的影响。在题材层面,怀斯曼逐渐倾向了机构题材的纪录片,同样,段锦川与其他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创作的题材不同点就在于关注机构题材。怀斯曼认为在当时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病态声音”[7]77的影片,这些影片的当事人都是明星、黑人罪犯等,怀斯曼更加倾向于去纪录与表现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机构。如以《法律与秩序》《医院》《白杨商行》和《中央公园》等诸如社会福利院、疯人院、少年法庭、军队、中学和住房计划公共服务类型,等等,怀斯曼称其关注这一构成类型题材的纪录片是因为“这些机构对美国社会发生着重要作用”[7]77。段锦川在谈到纪录片《广场》时提到怀斯曼的影响,他说《广场》是直接受怀斯曼的《中央公园》影响:“我原来就想拍广场,只是无从下手,看完《中央公园》以后,我完全可以靠这样散点的结构来做一个片子”[1]108,因此,段锦川同样选择一个固定的具有某种语义的空间场景,如《八廓南街16号》《广场》和《拎起你的大舌头》等,“喜欢在一个公共的场合里面工作和拍摄,因为我觉得所有发生在这个地方的事件和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要解决”[2]134。他认为无论是广场还是居委会、派出所、村委会等固定场景都有着中国独特的政治语境,在这一场景的背后存在着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像物质,这是直接电影观所给定的一种开放的结构和场景。
段锦川的直接电影观的独立纪录片从《广场》开始,到《八廓南街16号》获得国际纪录片最高奖——1997法国真实电影节“真实电影奖”。《八廓南街16号》拍摄的地点就是西藏拉萨市的中心八廓南街。片名的“八廓南街16号”就是当地的一个居委会所在地,纪录片纪录的是这个居委会的日常工作。纪录片采用旁观的方式,片中场景与任何一个中国大陆的居委会的情况一样:调解家庭邻里纠纷、给相关人员开会、解决居委会街道中的各类琐事、吵架闹事、老人状告儿女、临时审问小偷、各类统计数据和完成上级各种事务,等等。作者在谈到这一纪录片的创作时特别强调了直接电影创作观的旁观态度和摄影机保持与当事人场景的距离,导演选择这一题材与场景本身就是将八廓南街16号当作一个具有某种政治和文化隐喻意义的舞台场景,认为“直接电影都拥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大量地、准确地使用‘隐喻’”[1]128——即政治与人的关系。段锦川期待直接电影观的开放、不干预与等待,可以使得当事人所置身的场景成为一个公共的舞台,当事人面对摄影机按照自身的形态表达,无意识地自然地扮演着自身的角色,“等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人都会被自己的行为吓一跳”[1]129。所谓积累即客观呈现并保持一系列导演认知的现场,显然,段锦川受到怀斯曼直接电影观的影响,怀斯曼在其《积累式的印象主观描述》的创作论中早已指出了段锦川关于影片与镜头积累的目的与价值:“我拍的影片都是关于美国机构的,我的想法是对当代美国社会进行积累式的印象化主观描述”[6]475。怀斯曼认为直接电影的不干预旁观的方式,本身就是依靠摄影机对现场生存状态持续保持的积累,通过积累的方式,一个机构就是一个现场印象,一部纪录片就是一个机构,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综合起来看,所有的纪录片现场都是相互关联的,即纪录与保存美国社会当时的生活形态。
怀斯曼的直接电影虽然属于非虚构的纪录片,是真实发生的不受导演控制与干预的真实事件,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是与怀斯曼对于直接电影构成的戏剧性认知紧密相联的,“在拍片过程中,很多精力都花在正确设计电影的结构上”[6]475。在怀斯曼来说,日常生活中充满着戏剧性,尤其是直接电影的导演必须具备“把它们从普通生活中分辨出来”[6]475的能力。怀斯曼把小说创作与纪录片创作进行比较,认为小说家是在进行一种虚构的创作,而纪录片导演则是在生活中对素材所含有的戏剧性元素将其分辨出来。段锦川喜欢古典戏剧的结构方式,在同一的时间、情节和地点的规定性,因此,段锦川的纪录片都非常注重结构合理,在叙事充分具有戏剧性,选择八廓南街16号这一居委会题材,是看到了这一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当事人的家庭生活、个人情趣及其历史传承等,都是怀斯曼式的戏剧性素材,段锦川处理这些素材的手段与怀斯曼一样,“用旁观的态度,通过一个事件来分析它带来的意义”[1]113。因此,段锦川经常在纪录片创作中强调“角色”的作用,认为在前期创作中发现或选择一个适合的角色可以决定一个纪录片的成败,尤其是采用直接电影观的方式的纪录片创作,“你要拍一个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你必须要去找一个正确的角色”[1]118。在段锦川的直接电影创作中,组织构成类型的题材所承担的公共话题价值决定了纪录片现场的历史形态,而戏剧性结构则是其直接电影创作的内存形式,作者认为直接电影的旁观态度亲减少了导演对现场的干预,建立起某种怀疑主义的开放性认知基础。
段锦川认为纪录片设定场景的结构问题其实就是关于纪录片场景与事件的完整性问题,不仅仅是纪录片语言,还体现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正如怀斯曼阐述自己的创作观时指出:“我是用我的电影来表明人类存在一些复杂问题,并以复杂方式来解释这些问题,而不仅仅对它们进行简单的意识形态阐释”[6]480。直接电影开放式结构强调了观看者的观看,摄影机的旁观性使得当事人的原状形态超越了摄影机的存在,展示出纪录片现场深刻而富有价值的复杂性。段锦川认为生活中不缺乏具有戏剧性的场景,“影片的结构是否合理,发展的动机是否合理,转折、冲突是否必要,人物关系、事件安排是否正确等等”[1]132,这些原状的非组织事件的选择与安排还是构成纪录片具有意味的根本。在此,作者所理解的戏剧性并非仅仅是戏剧层面的冲突,而是由各类现场非组织事件结构起来的整体性,这不仅仅是怀斯曼的影响,同时也巴赞的选择对象的真实,叙事结构的真实和时间空间的真实这一纪录片三大构成相吻合。
段锦川的直接电影观创作还体现在其对于题材对象的选择上。这里的选择并非指组织机构的题材类型,而是指这一直接电影观的纪录片创作,在题材对象确立后,导演面对摄影机对象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尊重当事人的告知性原则;二是尊重现场非组织事件原状形态。怀斯曼特别强调前期拍摄时对当事人的告知原则,无论是拍摄时还是后期制作阶段,摄影机公开自身的存在,“在拍片过程中,一般都告诉拍摄对象我所要拍的东西”[1]474。段锦川在《八廓南街16号》有一场在居委会中老人告子女的纠纷,当居委会调解完成后,当事人不希望进行保留时,作者就完全剪去拍摄了这一精彩段落。同时,每天拍摄完成后都要把当天的素材与当事人共同观看,导演与当事人“一起评论自己的行为,一起来理解拍片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1]119。这样公开告知的创作原则除了关于现场认知外,还在于纪录片体现出保持并尊重非组织事件的原状性。
怀斯曼在进行直接电影前期创作时,不主张做过多前期准备,在现场也反对干预事件的发生发展,他指出“如果我不带任何观念去拍摄的话,我的电影就会更加有趣,整个拍摄过程就像一个不断有新事物发生的旅程”[6]475。这种直接电影观的纪录片创作是强调前期非组织事件的积累作用。段锦川受其直接电影观的创作影响,也都采取了旁观的方式,“摄影机与被拍摄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介入,不干预,最好是把摄影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降低到最低,尽量完整地真实地表现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首先从技术的角度就尽力避免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1]43,段锦川认为这才是直接电影观最核心的理念。
比较不是目的,将段锦川的直接电影观纪录片创作与怀斯曼的直接电影观影响进行比较,是期待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中最具有价值,同时也最能呈现中国独立纪录片面貌与精神的创作进行梳理。显然,段锦川的纪录片创作给定了当时和现在纪录片在中国的一个明确界定与原则,这一原则通过纪录片运动及其创作展示出纪录片创作最根本的原则:现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