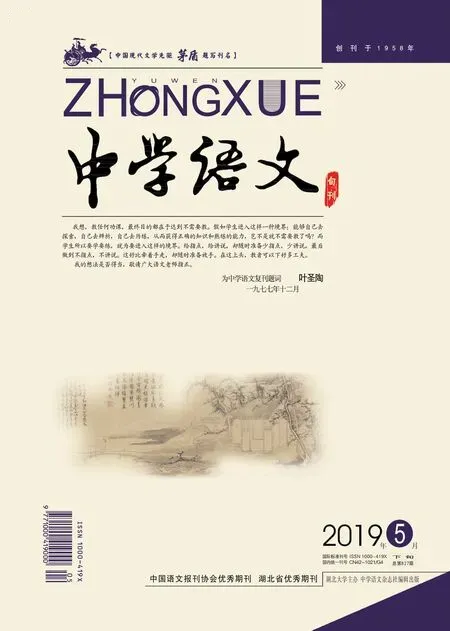《祝福》的思辨性阅读三题
江宗明
作品文本阐释即文本意义生产,体现出文本、作者和读者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文本意义、作者意图和读者会义三者,存在着某种张力关系。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相互制约,这种制约又反过来制约着读者会义的形成。正是三者的互动和制约关系决定了文本意义具有某种弹性。如此看来,一些阅读教学直接将教师乃至编者的读者会义当作文本意义,消解了文本意义的弹性及其阐释的张力,并让学生作为不成熟读者的主体性处于压抑与屈从状态。本文以《祝福》为例,谈谈其思辨性阅读三题,即《祝福》题目、“我”的逃离和鲁镇人的看戏心态,它们是理解祥林嫂悲剧人生的三个重要侧面,也是把握课文文本意义与作者写作意图并与之进行互文式对话的三个重要方面。
一、作品为何以“祝福”为题?
“祝福”作为小说呈现祥林嫂悲剧性命运的一个环境氛围,也是作品首尾呼应的一种写作技巧。作者将祥林嫂死亡这一悲惨性事件安排在旧历年底“祝福”这个喜庆性氛围中,从鲜明对比中强化作品的悲剧性主题,并构成强烈的反讽意义。它的确如王北平老师在《<祝福>教学设计》(第三课时)中指出的:“‘祝福’与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息息相关,是人物命运转变的契机和背景”,祥林嫂从勤劳能干到受歧视冷遇,再到变成木偶人被逐沦为乞丐,最终惨死雪夜的巨大变化,都和“祝福”事件与背景有关。但他认为“‘祝福’是鲁镇的一种封建迷信活动,充满了‘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色彩,‘祝福’之时也正是封建思想对人们影响和制约最深的时候,也是人们对祥林嫂歧视和迫害最甚的时候。封建势力通过祝福杀害了祥林嫂,祥林嫂又死于‘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祝福声中”,这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祝福”毕竟是一种地方民俗,而非封建迷信活动。
课文中有介绍:“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显然,“祝福”是旧中国辛勤劳作一年的人们美好生活追求的节庆仪式。据周作人考证,“祝福”作为一个节日可能是综合了吴“过年”和越“谢神祖”的内容而来,而二者又都是古代祭百神的“腊”的遗风。就是在当下,这种传统节日依然保留着。问题在于祥林嫂悲剧性命运与喜庆性氛围的对比与反讽,而不能由此得出“祝福”节日在鲁镇的鬼神观念统治和控制性质。“祝福”之时祥林嫂受到歧视和迫害最甚,源于鲁镇人头脑中认为,祥林嫂作为寡妇即使被迫再嫁也是“败坏风俗”与“不干不净”而致用人忌讳,以及作为一群看客对祥林嫂不幸遭遇的缺乏同情和麻木不仁,应该抨击的是人们的病态思想观念及其所引发的对待祥林嫂的荒谬行为态度,以及这个社会病象背后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而不能将棒子打在传统节日上。
二、“我”为什么要逃离鲁镇?
祥林嫂的悲剧人生叙事都直接源于“我”在鲁镇的见闻,“我”与祥林嫂、鲁镇和鲁镇人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其中蕴含着“我”之所以选择逃离鲁镇的重要线索。学者彭小燕曾指出,“《祝福》之‘我’隐喻着时至1924年初鲁迅自我生命的生存危机及其残酷自省。‘我’在祥林嫂、鲁四老爷、鲁镇人面前的矛盾,犹疑传递着‘我’对一个苦难世界的私欲关心、但又不敢、不能关心的隐情,这隐情不仅事关‘我’的道义良知、时代责任等等,更事关‘我’自身生存价值的有与无,事关‘我’如何消解、抑或变异‘我’之‘无聊—虚无人生的生存机密。’”但笔者以为,此文或许无关作者自我生命的生存危机,而是由于弥漫着鲁镇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与人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现状,让“我”深切地感到无力、无助和无奈;在这种现状面前,“我”不仅存在着难以言说或虽言说但难以被认同的解释困境,而且一旦表达与众不同的新见必将会遭到否定与批评的尴尬境地,作者想表达的是病态社会中清醒者的深重的内心孤独。
这从“我”刚回到鲁镇之初与鲁四老爷的照面叙述中可以看出,“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跟“讲理学”的鲁四老爷尚且“话不投机”,和没有文化的祥林嫂等鲁镇人又如何能敞开心扉呢?因此,“我”的孤独心境和压抑心理是隐含在字里行间的。祥林嫂选择祝福那天死亡是死得“不早不迟”,被鲁四老爷斥为“谬种”,给祝福的祥和美好氛围制造了不和谐音符,让“我”怀疑自己“不早不迟”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促使“我”决计要离开鲁镇进城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祥林嫂碰面后她关于魂灵与地狱的有无、人死后一家人能否见面等一系列追问。“我”本不信鬼神,但考虑到鲁镇人相信鬼神的传统尤其是祥林嫂的穷困潦倒,为了让末路的人心安起见,吞吞吐吐含糊其辞说“有”,在祥林嫂的不断追问下继而惴惴不安起来,于是改口“说不清”并仓皇逃回四叔家。其后不安心理和不详预感一直困扰着“我”,以致想到福兴楼价廉物美的清炖鱼翅是否涨价了,就是没有同游朋友自己一个人也要去享用,以此来排遣心中的压抑与担忧。换言之,与祥林嫂对话之后“我”的心里,是担心祥林嫂因他的话会选择非正常死亡,他因此要承担难以推卸的责任(事实也恰恰印证了他的担心和预料)。由上述两种情形决定,鲁镇于“我”而言,绝非一个可以久留之地。
三、作者为何要描绘鲁镇人的看戏心态?
作者叙述祥林嫂的悲剧人生,除了上述祝福热烈氛围里的凄凉和“我”的不安外,还有就是鲁镇人看客现象中的看戏心态。除了鲁四老爷、四婶、柳妈、祥林嫂的婆婆和卫老婆子等对祥林嫂的相近相关相同态度外,特别写到鲁镇男人、女人们、有些老女人作为一群看客对待祥林嫂讲述儿子阿毛悲惨故事的反应:“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祥林嫂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阿毛的故事早被大家厌弃后,作者又描绘了祥林嫂和柳妈聊天后鲁镇人捉弄她的看客现象:“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那个受大家嘲笑的以为耻辱的记号的伤疤。这种看客现象中包含着一种看戏心态,就像《药》中写到丁字街口“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而后就有康大叔、阿义和花白胡子等关于夏瑜被杀的聊天和评头论足。
这种“‘看客’现象的实质正是把实际生活过程艺术化、把理应引起正常伦理情感的自然反应扭曲为一种审美的反应。在‘看客效应’中,除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和灾难都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这实在是一种愚昧麻木民众的病态审美心理,高远东先生说:“‘看客’现象的症结并不在于人们由于缺乏现代觉醒所特有的愚昧、麻木及感觉思维的迟钝,而恰恰在于对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别人的不幸和痛苦称为他们用来慰藉乃至娱乐自己的东西。”笔者以为,看客现象的症结恰恰在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正是这种密切关联才能诠释鲁迅所批评的国民病态心理与灵魂劣根性。鲁镇人由于缺乏现代觉醒所特有的愚昧和麻木,因而在有关祥林嫂寡妇再嫁而“伤风败俗”和“不干不净”等问题上缺乏良知,才有对狼吃阿毛和祥林嫂额上伤疤的病态审美,他们的感觉思维只能对生活现实中的不幸和痛苦敏感并产生兴趣,而无法对思想精神中的不幸和痛苦敏感发生兴趣的。作者曾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就提倡文艺运动了。”然而创办《新生》杂志的失败,让作者感到寂寞与悲哀,转而钞古碑钻故纸堆了,《新青年》创办和钱玄同的邀请,作者才重生“唤醒熟睡人们和打破铁屋子”的意识和行动,但精神病痛的难以治愈,对此作者是有着深刻的体认的。“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为当时中国深刻的社会危机孤独而彷徨,期望得到疗救与改良是其目的。
——以《祝福》中三处细节描写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