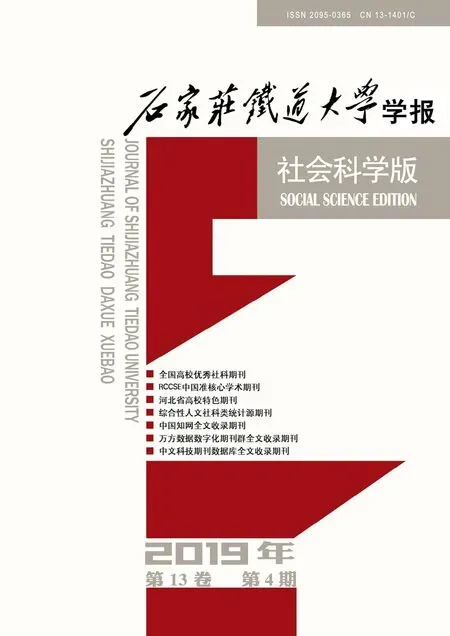纪昀小说中的清代新疆文化书写
吴 卉
(石家庄铁道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河间人纪昀曾被贬谪新疆,在长期孤寂的生活中,他利用诗文、志怪小说、随笔等记录了大量新疆当地的文化及日常生活。以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为中心,其中涉及新疆风貌、乌鲁木齐百姓生活的各个侧面,其书写内容虽尚未摆脱“拓荒”的范围,但客观上,却为当时的文人认识、了解边疆打开了窗口,又为后来的边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广泛的一手材料。
一、谪贬文官,寄意文辞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生于雍正二年(1724),逝于嘉庆十年(1805),直隶河间府献县(在博野、蠡县的东面近卫河,位处冀中平原)人。纪昀作为文学侍从之臣,自登科后就一直因学问优长而被乾隆留在朝中为官。除去乾隆二十八年有一次短暂的外放福建学政的经历外,纪昀另一次离京的经历则是乾隆三十三年秋因卢见曾案被贬乌鲁木齐,直至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才被赐环。纪昀在乌鲁木齐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也是其仕宦生涯中离京最远、在外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可以想见,乌鲁木齐之行势必对《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阅微草堂笔记》关于乌鲁木齐的记述中看出,从《滦阳消夏录》开始,除去十九与二十四两卷之外,每卷皆有关于乌鲁木齐之记载,共计七十八则之多。以所记述志怪发生的地点论,除去京师、河间府外,则属乌鲁木齐最多。
纪昀虽然是被贬到乌鲁木齐,但无论是《乌鲁木齐杂诗》还是《阅微草堂笔记》中关于乌鲁木齐的记载都很难找到怨望之词,反而像钱大昕说的那样“无郁轖愁苦之音,而有舂容混脱之趣。”(《纪晓岚文集》)之所以如此,固然与清代的文化专制政策有关,但也与当地官员对纪昀的优待以及乌鲁木齐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对纪晓岚内心愁苦的消解分不开。纪昀与时任乌鲁木齐提督的温福的关系十分融洽,《阅微草堂笔记》“张一科”条,就是温福在乌鲁木齐城西秀野亭宴请僚佐时,作为章京的纪昀在座间听到的。纪昀作为罪员却可以参与宴会,并在席间与温福谈论鬼怪之事,由此可见温福对他的优容。而温福由乌鲁木齐提督升任福建巡抚,恰逢纪昀在当地种的虞美人开花,他将这件事比为“如扬州芍药偶开金带围也”。扬州芍药的故事屡见于宋代笔记,今姑举一则,以明其义。“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者,名‘金腰带’……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数验。”[1]由此,也可看出纪昀对温福的感激及期待之情是何其深厚。虽然新疆、宁古塔、乌里雅苏台皆为清代贬谪官员、流放罪犯之地,但三地人文、自然条件却相去甚远。据《宁古塔山水记》“石城”条记载当地:“城方二里,磊石而成,垣城内居民寥寥数家。”[2]《乌里雅苏台志略》“城垣”条载乌里雅苏台“乾隆三十三年,创建木城一座,周围三里。”[3]可见两地人口之稀少与环境之萧条。至于乌鲁木齐,据《西域闻见录·卷一》“乌鲁木齐”条下记载:“(城中)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辐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4]纪昀虽被贬至此,而其地之繁华并不亚于内地,又值国家新近统一新疆,将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新疆的建设,所以乌鲁木齐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纪昀的愁苦之思与怨望之情。故而,在晚年创作《阅微草堂笔记》时,才会对乌鲁木齐的那段时光念念不忘,每每见诸笔端,几乎每一卷都留下有关乌鲁木齐志怪的记述。
关于乌鲁木齐志怪的记述,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记录乌鲁木齐奇异的自然风光及怪异之事。二是记录发生在当地将士、遣犯身上的怪异之事,发明因果报应之不爽。三是记录大量内地民众进入乌鲁木齐后引当地风俗之变化。四是考证汉唐遗留在乌鲁木齐及其周边的碑志、遗迹,并结合自身实际生活经历对汉唐志怪小说中记录的西域怪奇荒诞之事进行驳正。要之,这四类内容又体现出作者两方面的写作目的,其一即表达纪昀本人对塞外诸多奇观异景的认识或解释,其二是融合由汉入疆的各种风俗,试图以儒家文化传统整合边疆风俗信仰,使之与内地保持一致。
二、塞外风光,释异为常
乌鲁木齐地处塞外,意为水草丰美之地,其地耕牧两宜,故地理风貌与内地相比有着显著不同,这也引起了纪昀的注意,如《土鲁番大风》《乌鲁木齐多野牛》《古松皮》《西域瓜果》等则都对乌鲁木齐的自然风貌进行了描述,认为这种不同于内地的自然风貌是一种“异”,并试图对这种“异”的成因作出自己的解释。如在论述土鲁番多风时,他认为这是“盖气之所聚,因成斯异。犹火气聚于巴蜀,遂为火井,水脉偶聚于于阗,遂为河源云。”[5]张载就认为“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6]。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本。纪昀的解释明显受其影响,可见他是在试图用儒家的天地万物皆为“气”所聚集而成的理论对吐鲁番大风的成因进行解释。再如其奴吴玉保曾经得到一块古松的树皮,竟然拿来作床,作者从历史的角度指出“盖天山南北,如乌孙、突厥,古多行国,不需梁柱之才,故斧斤不至。”所以才会有古松“高出二三十丈”的奇观。无论是吐鲁番可以把人刮起来送到两百里之外的大风,还是生在山谷树冠够到山峰的古松树,都是一种内地看不到的奇异景观。可见,纪昀对于乌鲁木齐风物的记录是出于记异志怪的目的,所以除了乌鲁木齐奇特的自然风光外,他对乌鲁木齐本地发生的怪异之事也积极著录。纪昀所记录的乌鲁木齐之“怪”与内地之“怪”有着很大的不同,内地之“怪”更具“人性”,无论是狐狸还是花精、木怪,在成为“精怪”后都或多或少具有人的属性,可以用人类的逻辑对其行为进行推测、解释。而乌鲁木齐之“怪”则不可以常理度之,如刚朝荣遇到的“身毵毵有毛,或黄或绿”的野人,参将海起遇到的“山精”,吉木萨台军遇到的“面及手足皆黑毛”的山神,他们似乎都只有动物本能,害人也只是为了觅食,并非涉及前世的果报,也与被害之人是否犯有过错或触犯某种禁忌无关,由于这些怪异发生的地点都在乌鲁木齐周边的深山之中,是汉文明还没有触及到的地方,所以纪昀面对这些怪异进行描述后,只能对其性质进行猜测,难以给出明确的解释。记录乌鲁木齐的“怪”,除了记述异闻之外,还有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意图,即将清朝平定新疆的战争“神圣化”、“天命化”,指出清朝取得胜利是天命所归,非人力所能阻挡。如《乌什回部》[5]一则,乌什的的回部将要叛乱时,有人看到在其始祖墓上有巨人东向,若有所望,是知道部族将遭到从东面而来大祸。再如《和和乎通诺尔之战》一则,“巨人端拱东拜,意甚虔肃,知为山灵。”而对山灵东拜的解释是“窃意或此地当内属,故鬼神预东向耶。”[5]这两条都突出了鬼神拥有的“前知”、“预知”能力,同时也说明清朝平定新疆“事皆前定”,是人力无法更改的,从而使这场战争的胜利方——清朝——有了天命所归的神圣性和统治新疆的合法性。
纪昀记载发生在当地将士及遣犯身上的怪异的主要意图则是发明因果报应之不爽。清朝平定新疆的战事非常惨烈,将士难免心怀恐惧,而他则记述了许多将士因作战英勇,虽死于战事但终获善果的故事,如《滦阳消夏录》卷三记载“有厮养曰巴拉,从征时,遇贼每力战。”[5]后战死成为博克达山神部将。又如乌鲁木齐提督巴彦弼曾对纪晓岚说梦中曾至冥司,见到因不同原因死亡的人所登名册亦不同,而为国死难的将士大都“最上者为明神,最下者亦归善道。”所以巴弼彦说:“吾临阵每忆斯言,便觉捐身锋镝,轻若鸿毛。”这些故事一方面借因果报应之说消解了战争的残酷,另一方面又借死难将士的故事对因果报应之说作了阐释。
乌鲁木齐建城之后,大量的罪犯被流放到此,“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蓝帔青裙乌角簪,半操北语半南音。秋来多少流人妇,侨住城南小巷深”[5],就是描写大量罪犯被流放到乌鲁木齐后,城内房屋鳞次栉比,十分拥挤,住户来自各地所以北语南音交杂的情形。正是因为乌鲁木齐的住户成分主要是驻军及被流放到此地的遣犯,所以城内的秩序十分混乱,至于“冶荡者惟所欲为,官弗禁,亦弗能禁”,在这样的治安状况下各种“怪事”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纪昀之所以热衷于记录遣犯身上发生的怪异之事,原因还在于遣犯本来就是身上有罪之人,大多数也是品行不端之人,他们既热衷于作奸犯科,有机会就会想从戍地逃走,而乌鲁木齐周围地理条件极为恶劣,所以往往不能成功,被抓住后种种因果报应的传说就随之而起。比如《遣犯刘刚》一则就是极佳的例子,刘刚从戍地逃走,半路在大树树洞中睡着,结果被逻骑追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地故事,再加上刘刚自己曾经杀过人,一个被杀冤魂借机报仇的发明因果不诬的故事就这样成型了。再如刘允成,因为“逋负过多,迫而自缢”而他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的原因则是“为重利盘剥,逼死人命事”,在纪晓岚看来这正表明“天道乘除,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即应,有时缓应,亦有时示之以巧应”[5],正是这种报应的神秘莫测,更使人感到畏惧而不敢为非。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纪昀之所以记录发生在遣犯身上的怪异之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常常触犯禁令,做出违背常规之事,是“异”的一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遣犯天然就带有罪孽,运用因果报应之说可以极好地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异”,给他的记述带来极大方便,这也是其他故事中作者极好记述发生在仆妇、妓女等社会底层身上的“异”是一样的道理。
三、整齐风俗,以儒治疆
“小说”作者,在汉代大多是方士或儒生,其功用,在于干谒帝王,投其所好,以求功名。如王充在《论衡》中所言:“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7]游说君主,评议朝政。子部小说的发展与封建皇权的强化,实是不能分隔开来的线索。小说功能历经几朝而有所转变,从“王者欲知闾巷风俗”(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的载体到清代娱目逞心的游戏之作,而相反的,小说家的身份反而从稗官变为正式官员,甚至是京官,这就不能不影响着小说的创作功能和意义。
大量的汉族人从内地进入新疆,也将内地的风俗信仰带入乌鲁木齐,对这一情形,《阅微草堂笔记》也有所记载。关于乌鲁木齐的关帝信仰,在《滦阳消夏录三》和《滦阳续录二》里均有载述,并且认为其颇为灵异,如《乌鲁木齐杂诗》中“齐拜城南壮缪祠”即是此种信仰兴盛的证据。纪昀对汉人信仰进入新疆是十分高兴的,如昌吉之乱关帝显圣,他认为这是“国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于二万里外。”这也与他对当地风俗的不满有关,在《额鲁特寡妇》一则中,他认为额鲁特寡妇在丈夫过世后为公公养老送终是符合“孝”的,但后来又改嫁他人则是“惜其不贞”。
文人们热衷于小说家言,是和中国古代士人修齐治平的理想分不开的,正是志怪小说这一文体,为文人指了一条出路:似乎书写小说就可以参与经国治天下。“汉代的小说家尽管身份低微,却深受帝王的宠幸,他们要么是待诏之臣,要么是方士侍郎,而且像虞初还享受着黄衣、坐专车的待遇,参与国家重要活动。”孙少华认为“对政治得失的讨论与对儒家学说的称述,最终成为规定汉代诸子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同时也成为汉代诸子著书立说的两大基本主题。”[8]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中,个体的道德实践始终是和社会的政治体制相联系的,由内在的个人修为到重建社会政治秩序是士人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大限度实现“道”的理想的途径。即使遭遇流放,文人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文人写作小说,推崇德治,宣扬忠信,提倡报恩,体现出儒家的一种伦理道德思想,并且利用小说的讽谏功能,最终实现干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建设的目的。这种讽谏寄托了小说家的历史和家国责任感,余英时在《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中认为循吏在身为官吏的同时“又扮演了大传统的‘师’(teacher)的角色。”[9]故而,我们可以推测纪晓岚对额鲁特寡妇的不满也是出于儒家“整齐风俗”的传统,体现了纪昀作为官吏试图以儒家文化传统整合当地风俗信仰,使之与内地保持一致的意图。
新疆,早在汉唐时期便归属于中央政府统治之下,汉置西域都护府、唐置安西北庭都护府,各统治新疆达百年之久,故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而西域文明也不断沿丝绸之路渗入内地,如志怪小说中不断出现的西王母、昆仑、瑶池、火浣布、胡商等题材即是一证。自安史之乱后,西域与中原的联系便被切断,其中经历宋、元、明直至乾隆平定准噶尔部,西域作为新疆才重新被纳入版图。在乾嘉及道光时期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的交相作用下,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得以发展起来。嘉庆朝,尤其是道光后期,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由此所带来的国家危机和民族兴衰成了当时社会知识分子最关注的内容。在这一状况影响下,乾嘉、道、咸几朝的边疆研究呈现出兴盛期的特点,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西北边疆地区史地学的兴起。这一时期,举凡边疆政治、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军事、域外等领域,都出现了相当多的研究者,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许多不朽的著作得以产生,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状况都有了极大的呈现。这一热潮也反映在志怪小说的创作中。
纪昀在乌鲁木齐生活达两年之久,在奉命勘察地形、构筑军城之时见过许多汉唐时的碑铭、城池遗址,也见到了许多汉唐志怪中记载的西域异物。作为当时的学问大家,深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的儒家博学传统和汉学考证之风影响,纪昀自然要对这些遗迹、异物做一番考证。乾隆三十五年,纪昀两次奉命与当地驻军将领相度屯兵之地,在这两次外出考察时,他通过残碑认定“特纳格尔为唐金满县故地”,“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为清代统治新疆找到了历史依据。而对于汉唐志怪中对西域的记载,纪昀则认为很多都属虚妄无稽,“而所谓瑶池、悬圃、珠树、芝田,概未乎见,亦概未乎闻。”[5]像《古今注》里记载的“大如六升之瓠”的青田核,当地人说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再如《杜阳杂编》里记载的“芸香”,可能是一种叫“玛努”的草根,当地僧侣拿来供佛,也不像书里说的“香洁如白玉”,这些记载“均小说附会之词也。”这也体现了《阅微草堂笔记》对志怪小说博物传统的继承。
乌鲁木齐壮丽的自然风光,作为清帝国新疆土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风貌与当地丰富的文化历史遗迹,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纪昀心中的苦闷郁结之情,成为他谪居在外却心系国家福祚的凭籍,同时也扩展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志怪类型、故事题材,接续了志怪小说的博物传统,既使清代志怪小说的艺术风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也为当时及后学了解、研究边疆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