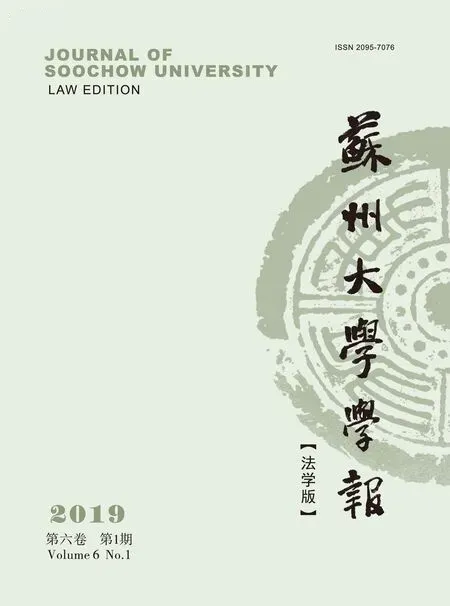民事诉讼中第三人权责不对称问题研究
——以我国参加效制度的缺失与构建为中心
陈晓彤
一、引言
民事诉讼的主体中,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我国法的语境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下简称“无独三”)始终是学者颇为关注的对象。与无独三直接相关的文章主要研究其诉讼地位、参加利益要件与类型划分等问题,[注]如肖建华:《论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重构》,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1期;赵信会、李祖军:《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内部冲突与制衡》,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张卫平:《“第三人”:类型划分及展开》,载《民事程序法研究》2004年第1辑;章武生:《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龙翼飞、杨建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载《法学家》2009年第4期;肖建国、刘东:《民事二审程序中的第三人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刘东:《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识别与确定——以“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类型化分析为中心》,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2期等。2012年后由于《民事诉讼法》修订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学者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展开了详细的研究,该制度的主体要件是可能成为第三人但未实际成为第三人(一个过去虚拟式的条件),故与对第三人的直接研究存在一定的距离。其中无独三可能被判决承担责任或随意被拉进诉讼导致其利益受损是促使学者们研究无独三制度的重要考虑,即为了防止不利“后果”,需对无独三的诉讼权利进行界定并对其范围予以限制。但作为这一研究思路的逻辑前提应是,无独三作为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主体,与当事人一样,其在诉讼中的权能与其应承担的后果具有对称性。然而,除规定无独三可被判决承担责任(意味着其直接承担判决的既判力)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缺乏一般性的无独三应承担何种后果的规定,这就造成我国民事诉讼中第三人权责不对称的问题。[注]由于立法规定的不完善和第三人可被判决承担责任,很容易导致第三人进入诉讼后的权与责在立法上不相对应,“有缺失程序保障之虞”,参见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作为解决该问题的一环,有学者主张应借鉴大陆法系的参加效制度,[注]参见刘文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效力研究》,载《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大陆法系参加效指的是裁判对辅助参加第三人产生的特殊拘束力。关于在我国是否有必要构建参加效的问题,还需考虑我国是否存在合理的替代性效力,如存在则无必要,否则应当构建。这在规范层面虽付之阙如,但实践中却存在一些“解决”问题的操作:法院常对未被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三适用既判力,或者适用事实预决效力。这意味着在考虑是否、如何构建我国的参加效制度时,必须对参加效与既判力或预决效力的关系进行研究。[注]关于无独三应承担的法律后果问题,我国学界的研究十分稀少,不过亦有学者对参加效与既判力的关系进行探讨,参见蒲一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判决效力范围》,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但该作者主要关注的是被判决承担责任的第三人承受既判力的问题。这样做有助于将外来的参加效知识与我国特有的无独三制度、实践进行对照,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探究在舶来的理念影响下和在本国特有的环境条件中,制度如何生成,在立法论和法解释论层面进行研究以使制度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与无独三相关的特殊问题领域中,就意味着尽可能妥当地实现第三人的权责对称。
鉴于以上问题,本文首先对我国参加效制度缺失的原因与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稍作分析,在民事诉讼的第三人之权与责应当对称这一体现了公平原则的基本层面,承认我国构建独立参加效制度的必要性。接下来,拟将如何构建我国语境下的参加效制度分解为三个小问题:第一,参加效与既判力存在何种关系,我国法院对未被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三适用既判力的不妥当性何在?第二,参加效与事实预决效力存在何种区别,二者之间应如何划清界限?第三,参加效还能适用于哪些情形,其法律后果能否类推适用?结合我国特殊的无独三参加诉讼制度与相关实践,对这三个小问题分别予以解答,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希望能够大体上明确我国参加效应具有的特征及其适用的范围。
二、我国参加效制度的缺失原因与必要性分析
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的规范与大陆法系国家类似的辅助参加制度进行对照,我国参加效的缺失较为明显,这有着历史渊源与现行制度实施等方面的原因。基于公平原则和主体的权与责应对称的原理,裁判对具有独特诉讼地位与权能的无独三应产生某种特别的效力,而法院实践并不能合理地解决该问题,故在我国亦有必要承认参加效。
(一)为何我国未规定参加效
我国未规定参加效,首先与无独三制度移植自前苏联有关,[注]参见蒲一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判决效力范围》,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辅助参加效主要是德日的制度,在我国未予规定是可想而知的。在体系层面上,前苏联是否承认裁判对参加诉讼的无独三产生某种效力,恰巧在其预决力的学理中能寻得答案。1964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55条规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某一民事案件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在审理由同样人参加的另一些民事案件时无须重新证明”,学者将这里的被判决认定的事实称为“预决事实”,这种效力称为“预决力”,预决力是不可推翻的,包括无独三在自己作为当事人的诉讼中应受自己参加过的诉讼中法院判决的拘束力。[注]参见[苏]多勃罗沃里斯基主编:《苏维埃民事诉讼》,李衍译,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由此可知,前苏联亦承认无独三应承受判决的拘束力,但将其作为预决力的一种情形。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中虽有与前苏联上述法条类似的规定,学者亦将其称为“预决效力”,但似乎仅在2001年以前不准许举证推翻,[注]我国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4项仅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与前苏联的规定相近。自2002年后就成为可举证推翻的效力。[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1款第4项虽延续了1992年司法解释的内容,但其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这一规定被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本文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3条所延续,仅在字句上有所变动。由此我国难以像前苏联那样以预决力来说明裁判对无独三产生的某种拘束力,若依据现今我国的预决效力规范,无独三仅承受一种可推翻的事实性影响。
然而,在司法实践看来,预决效力这种可推翻的事实性影响与既判力加起来似乎已经“够用”了。法律虽未特别规定裁判对无独三产生何种效力,法院在审判中仍不得不解决这一问题,法官有时对无独三适用既判力,即使未被判决承担责任也不例外;有时则对无独三适用非拘束性的预决效力。[注]这种做法亦受到现有规范体系的影响,因为法院作出裁判时必须援引相应的法律规范,而我国的法律规范中仅有对消极既判力和预决效力的规定。具体司法案件将在后文研究参加效与既判力、预决效力之关系时予以简介或列举。这种现象本身即足以说明无独三承受的裁判效力尚不清晰,但实务界人士或许已满足于这些替代性效力。在实践层面,既判力与参加效均属于拘束性效力,消极既判力遮断后诉,积极既判力保障前后诉判决的一致性,且大多数案件中后诉被遮断与后诉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实体后果相差无几。若法院适用预决效力就赋予相关主体进行争议的机会,方便无独三提出特殊事由,法院还可将其后诉的失败归结于其举证的不足,由此来规避风险。
在无独三那一方面,法院对其适用裁判效力之操作的混乱性,以及前诉法院违反处分权原则直接判决其承担责任(且不说由于参加利益要件较为抽象导致的滥列第三人等现象),均引发了无独三权益遭受不合理侵害的批评。对此,规范和学理上的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加强对第三人的保护、增设第三人的救济渠道。虽然2012年《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赋予本来可以成为第三人的主体以事后救济,而非直接对第三人的救济,但其亦体现了倾向于保护第三人的社会总体氛围。在这种将无独三视为“弱势群体”的气氛下,探究裁判对其产生某种拘束力,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做法。这或许增强了立法者拒绝规定参加效的倾向,也影响了学者对参加效问题的研究热情。对这个问题长期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使得未规定参加效引起的第三人权责不对称问题迟迟不能获得应有的注意。
(二)我国承认参加效的必要性
裁判对参加诉讼的无独三产生相应的效力,是第三人权责对称原理的要求,同时亦是公平原则的体现。无独三参加诉讼的过程,是与双方当事人一同实施诉讼行为、影响生效裁判结果的过程。当事人要承受裁判的各种效力(包括对后诉的既判力),若无独三无须承受裁判的任何效力,对于与其一同实施诉讼的主体来说就是不公平的。虽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裁判对无独三不产生任何效力并不现实,但适用既判力或预决效力的现状,仍有违第三人权责对称原理。
若法院判决无独三承担责任,这虽然有违处分原则,可能造成裁判突袭,亦与第三人权责对称原理不符,但考虑到事后的救济手段,将这样的无独三视为“转化”为当事人并承受判决的既判力,对其更为有利。对于未曾被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三,在其作为当事人的后诉中,若使其承受既判力,就意味着事实上将其等同于前诉的当事人,但其在前诉中并非当事人,与原被告这样的当事人所享有的诉讼地位和权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裁判效力环节却将其视同当事人,就有违程序保障原则。而在另一个极端,裁判对无独三不产生某种拘束性效力而仅有事实性影响的话,无独三就可能获得两次争执机会,他在前诉中已经争议过或有机会参与争议的事项,还可在后诉中“举证推翻”,对于前诉的当事人来说有不公平之虞。
更重要的是,实践中对于无独三究竟应承担何种裁判效力不存在统一的定论,这就使维持现状具有更突出的非正当性。除被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三,其他无独三对自己究竟是承担既判力还是不承受裁判的拘束力,无法获得明确的预期。既判力是裁判遮断后诉或拘束后诉的强制性效力,对相关主体的程序、实体权利均产生较强影响,因此应被限制在明确的范围内,使某些无独三(条件并不清晰)承受既判力就可能冲击既判力的边界,影响对既判力制度的正确理解;[注]值得一提的是,承认裁判对无独三产生参加效,也要解决参加效作为一种拘束力与既判力之间的差异问题,否则同样可能影响对既判力的正确理解。对另外一些情况同样不确定的无独三适用预决效力,亦会使预决效力的性质与内涵产生巨大的争议。[注]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后诉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未对该效力的性质予以明确澄清。但既然可举证推翻,就不同于既判力等拘束力,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法定证明效,但予以批判,认为仅应承认事实上的证明效,参见段文波:《预决力批判与事实性证明效展开:已决事实效力论》,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5期。但实践中预决效力适用的情形极其多样,有必要对这些案件进行类型化,在此基础上或可期待通过考察不同类型案件能否适用同一种效力进行逐步调整,以明确预决效力的性质。参见王亚新、陈晓彤:《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民诉法解释>第93条和第247条解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鉴于此,在我国有必要承认独立的参加效,使未被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三原则上均承受一种统一的裁判效力。这种效力应与当事人承受的既判力、一般案外人承受的事实证明效区别开来,与无独三在诉讼中享有的地位和权能相匹配,如此无独三的权与责才具有一致性。通过探讨参加效与相关裁判效力的差异,结合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地位与权能之状况,参加效在我国语境下的特征与范围能够逐渐得到澄清。
三、参加效与既判力的差异
作为我国的一项特殊制度,无独三可能被判决直接承担责任,此时其应承受判决的既判力。关于这一特殊状况中的既判力,本文亦表示赞同,[注]这样的无独三承受既判力亦可能存在争议,但争议的源头在于无独三被判决承担责任本就违反了处分原则,可能对无独三造成裁判突袭。因为他在参加诉讼时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要被判决承担责任,故不一定尽力防御,在判决阶段却成为直接承担责任之人,就缺乏合理的程序保障。对该制度的不合理之处,恐怕不得不期待立法将来能够予以修正,不论是采取保守路线禁止判决无独三承担责任,还是采取开放路线允许将这类无独三作为被告引入诉讼。接下来在考虑参加效与既判力的差异时所提及的无独三限于未被判决承担责任的第三人。根据前诉判决内容,这两种无独三之间区分较为明确,故这种分类具有可操作性。
无独三承受参加效,当事人承受既判力,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系统性的,不限于主体要件。不过二者之间在法律效果上存在相近之处,[注]参加效也是一种拘束效,与积极既判力的后果十分相似,且其制度目的亦在于禁止重复争议、定分止争。因此在学理中和实践中可能产生混淆或混同、合并的“趋势”。我国法院对无独三适用既判力的做法,与大陆法系国家学理与实践中存在的将参加效等同于既判力或将二者整合为一种效力的某些观点,一定程度上共享某种思维逻辑。接下来先对德日相关学说稍作介绍,再整理我国法院对无独三适用既判力的案件,利用案例分析的结论并结合其中涉及的我国无独三参加诉讼的程序特征,对我国参加效的要件进行研究。
(一)德日的辅助参加效及其与既判力的关系
德日通说均将辅助参加效理解为一种与既判力有别的效力,但始终存在着相当有力的将参加效与既判力联系起来的学说。虽然日本借鉴了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度,但在辅助参加效适用范围与适用方式等方面,两国存在较大差异,学理观点亦存在区别。
1.德国的规范与学说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在辅助参加人与被辅助当事人之间,辅助参加人不得主张前诉判决是错误的。第74条第3款规定,这一辅助参加的效力同样适用于第三人被诉讼告知的情形。
根据德国通说,参加效是一种特殊的判决效力。在主体范围方面,其仅适用于辅助参加人与被参加人之间,且仅能对辅助参加人不利。[注]BGH NJW 1997, 2385, 2386; BGHZ 100, 257, 260ff. = JZ 1987, 1033(Fenn); BGH NJW 1987, 2874= JZ 1987 1035(Fenn); Musielak/Weth, § 68 Rn. 5. 对此越来越多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Bork, Häsemeyer, W. Lüke, Stahl, Ziegert,因为辅助参加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保护被辅助人,还应通过防止矛盾判决维护公共利益,Vgl.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München 2010, S.260.在客体范围方面,参加效并不限于判决主文,与辅助参加人有关的判决理由,其在后诉中亦不得争议。在法律后果方面,辅助参加效意味着一种拘束力,但存在例外:如果辅助参加人由于参加诉讼时的状况(如时机)或由于被辅助当事人的主张或行为而受到妨碍、无法提出攻击防御手段以影响判决结果,或者他所不知道的攻击防御手段由于被辅助当事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在前诉中未提出,他就可以主张被辅助当事人的诉讼实施行为有瑕疵,自己不应承受参加效。[注]辅助参加人的这种抗辩具有古老的来源,即拙劣诉讼追行的抗辩(exceptio male gesti prozessus)。参见柏木邦良:《民事訴訟法要説》,リンパック有限会社2005年版,第508页。
与此相比,既判力有较大的不同。在主体范围方面,既判力原则上具有相对性,在既判力主观扩张的例外情形中,既判力通常发生在与一方当事人存在特定实体法律关系的案外人与该方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之间,如前诉一方当事人的继受人与该当事人在前诉中的对方当事人。作为“连接点”的案外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本身未经过前诉的审理,并不受判决的影响。在客体范围方面,既判力限于判决主文,虽然关于判决理由应否产生既判力存在诸多争议,[注]德国学者Zeuner提出意义关联学说扩张既判力的客观范围,Vgl.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München 2010,S.882. 日本学者借鉴美国争点排除效提出争点效理论,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92页。但原则上不妨碍在既判力与参加效之间作出区分。在法律后果方面,既判力不存在当事人拙劣的诉讼实施行为之例外,除非是既判力基准时后的新事由,或者存在再审事由可开启特殊救济渠道,既判力不可被推翻,这与参加效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参加效与既判力均为禁止重复争议的拘束效,服务于防止矛盾判决、实现法的安定性与节约资源的公共利益,二者都要求法院依职权予以注意。[注]BGHZ 96, 50, 51 = NJW 1986, 848; BGHZ 16, 228 = NJW 1955, 625. 有一段时间德国判例与学者均主张参加效之适用应取决于当事人的主张,如RG JW 1933, 1964 Nr. 16与RGZ 153, 271, 274,当时人们认为参加效主要是(甚至是唯一地)服务于私人的利益,而且参加效范围比既判力宽泛,并不限于判决主文中的结论,所以不应依职权使当事人承受这样的拘束。但现今德国通说与判例均不再支持这一观点,而是将参加效理解为与公共利益有关。Vgl.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München 2010,S.260.在法律后果方面,参加效与既判力均为判决对后诉产生的积极拘束力,参加人虽可提出特定的抗辩以摆脱参加效,但在实践中很少有成功的事例。[注]Vgl.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München 2010,S.259.因此,德国历史上的判例与文献多次将参加效表述为“既判力效力”(Rechtskraftwirkung)、“有限的既判力效力”(beschränkte Rechtskraftwirkung)、“既判力扩张”(Rechtskrafterstreckung)、“扩展了的既判力”(erweiterte Rechtskraft)、“既判力的特殊情形”(Sonderfall der Rechtrkraft)、“类既判力的效力”(rechtskraftähnliche Wirkung)等。有的学者主张参加效就是既判力;有的学者主张应在参加效与既判力之间建立起一种体系性的联系,理由是如果过分强调二者的区别反倒有可能加重理解参加效的困难。[注]Vgl. Kathrin Ziegert, Die Interventionswirkung, Tübingen 2003,S.3,21-22.将参加效理解为既判力的一种形式,意味着既判力的扩张,将二者联系起来意味着在拘束力层面的“统一”。
2.日本的规范与学说
日本参加效虽来自德国,但时至今日已有了较大的差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存在辅助参加的诉讼的裁判对辅助参加人也有效力,除非由于辅助参加时诉讼的程度导致辅助参加人不能实施某些诉讼行为;由于辅助参加人的行为与被参加人行为抵触而无效;由于被参加人的妨碍辅助参加人不能实施某些行为;被参加人由于故意或过失未实施辅助参加人不能实施的诉讼行为。
该规范字面表述是裁判对辅助参加人亦产生效力,故许多学者主张参加效就是既判力的主观扩张,这曾经成为有力说并被判例接受。[注]参见三月章:《民事訴訟法》,有斐阁1959年版,第239页。然而,参加效还适用于被诉讼告知人,仅诉讼告知就产生既判力扩张是不妥当的,且日本学者普遍主张法院不必依职权注意参加效,仅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用之,故今日日本通说将参加效视为与既判力不同的特殊裁判效力。[注]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67页。参加效的基础是责任分担,辅助参加人辅助主当事人共同实施了诉讼行为,基于公平的考虑其应与主当事人共同承担败诉责任,故参加效仅在参加人与主当事人之间产生。
不过,近来相当多学者主张,裁判在辅助参加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亦产生效力(既判力和争点效),其理由是辅助参加人在前诉中针对与自己法律地位相关的争点均享有主张和举证的机会,在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亦应禁止重复争议。这种观点被称为“新既判力说”,新既判力说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开始成为日本学理与判例的通说。[注]日本学者铃木重胜、住吉博、新堂幸司教授的主张大致都可以理解为这一类观点,参见三谷忠之:《民事訴訟法講義》,成文堂2011年版,第296页。关于新堂幸司教授的观点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68-569页。新既判力说并未直接冲击传统参加效理论,因其处理辅助参加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与处理辅助参加人与被辅助人之间关系的参加效并列。但这两种效力的根据是同一的,即辅助参加人在前诉中享有主张和举证的机会,因此“新既判力”和参加效实质上可联系起来考虑,且这种“新既判力”与一般的既判力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根据德日通说,参加效与既判力不同,但二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故可从体系性的角度出发将二者连接起来,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借助了既判力主客观扩张的工具,与一般的既判力存在不可小视的差别。
(二)我国法院对无独三适用既判力的实践
我国没有规定参加效,仅有消极既判力的规范,积极既判力比参加效稍微“幸运”,其或多或少得到了实践的承认。考虑到无独三虽未被判决承担责任,一般仍参加了前诉并有机会主张和举证,为了防止重复争议和矛盾判决,法院时常对无独三作为当事人的后诉适用某种裁判效力,有时语焉不详地适用一种拘束性效力,有时则直接适用既判力。
案例1:甲乙将某房屋出卖给丙,约定将出售款在甲、乙和丁之间进行分配,由乙作为丁的代表。房屋出售后,甲将获得的房款中属于乙、丁的部分交付给乙,乙未向丁给付。丁诉乙,将甲与丙作为第三人,请求分配房款。法院认为,乙应按照约定将丁应得数额交付给他,在诉讼中乙主张甲还有9万元未交付给自己因此自己无法交付给丁,甲则主张早已交付给乙,法院对证据进行审查后不支持乙的主张,判决乙将包括这9万元在内的房款与丁进行分配。随后乙诉甲请求给付9万元,后诉法院认为甲已交付9万元的事实已被前诉判决确认,乙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即便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亦非另行诉讼能够解决,故判决驳回乙的诉讼请求。[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696号民事判决书。前诉判决书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180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中,在前诉无独三与一方当事人之间,法院虽适用了预决效力规范,却认为即便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亦非另行诉讼能够解决,其言外之意就是当事人与无独三并不能在后诉中重复争议,这意味着前诉判决对后诉产生一种拘束效。本案中这种拘束性效力是有利于前诉无独三、拘束前诉当事人的效力。
基于公平的考虑,这种有利于无独三的拘束力是值得承认的。此外,我国无独三并不像大陆法系辅助参加人那样在参加诉讼时要表明自己支持何方当事人,因此将参加效限于无独三与一方当事人之间亦不现实。有利于无独三的参加效无损于其制度基础,参加效是基于公平与诚信原则禁止重复争议的效力,第三人参加诉讼仍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在诉讼地位上似乎不如当事人,但并不一定非要从属于固定的一方当事人。[注]在大陆法系国家,为防止辅助参加人与对方当事人潜在的重复争议,可通过对方当事人向辅助参加人告知诉讼、辅助参加人按照程序阶段决定改变其辅助的当事人来解决。这样的确有助于程序的安定,但在实质意义上并不应影响参加效的范围,否则太过机械。若这样考虑,参加效与既判力确实十分近似,但具体到本案可知,既判力客体对象是乙、丁之间是否应进行房款分配的判断,而参加效的客体是甲乙之间关于9万元是否已经交付的判断,仍存在差别。
案例2:甲租赁乙的房屋并将其转租给丙。乙要求终止合同,甲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赔偿损失,法院追加次承租人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过审理法院认为由于乙不愿继续履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故应将合同解除,乙应赔偿给甲造成的损失,丙的损失涉及转租关系不宜在本案处理,告知丙可另行起诉。丙诉甲乙请求继续履行转租合同,后诉法院认为前诉判决具有既判力,后诉法院不得作出相矛盾的判断,前诉判决解除租赁合同,次承租人亦不再享有占有使用租赁物的依据,故判决驳回丙的诉讼请求。[注]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2)江民一初字第2609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后诉法院直接适用“既判力”来处理前诉判决在无独三与前诉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效力。前诉判决对无独三不利,但关于主合同能否存续的问题,无独三参加了前诉并有机会进行争议,故应受前诉判决拘束,其在后诉中以该合同存续为基础提起的请求就不能得到支持。本案判决对后诉产生效力的内容是判决主文,前诉诉讼标的是后诉诉讼标的的先决条件,因此与积极既判力很容易产生混淆,但前后诉主体毕竟存在差异,与其将其理解为既判力,不如理解为与无独三有关的参加效。
案例3:甲业委会诉乙开发商,主张某房屋属于公建用房请求交付给全体业主无偿使用,由于该房屋已被乙出卖给丙,法院通知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过审理法院认为乙已提供足额面积的公建用房,对涉案房屋亦不存在特别约定,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甲再诉乙、丙主张二者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小区公建用房故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丙抗辩称甲不具备当事人适格且后诉请求与前诉判决矛盾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后诉经过两审与两次再审,法院最终认为甲与该房屋无直接利害关系故不具备当事人适格,且前诉判决有既判力,后诉构成重复起诉。[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99号裁定书。关于丙作为前诉第三人的信息,来自于该案的第一个再审裁定书,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民再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
本案后诉法院不仅提及前诉判决有既判力,还对后诉适用了消极既判力即禁止重复起诉的遮断效。但前后诉主体并不完全相同,且前诉判决仅仅是对乙是否有义务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业主使用作出的判断,并未对作为后诉请求的房屋转让合同效力作出判断,因此将后诉理解为重复起诉明显有误。不过,前诉判决已确定该房屋非公建用房,甲以公建用房为由提出的确认合同无效请求并不存在确认利益,其对该确认之诉不具备当事人适格,作为前诉被告的乙和作为前诉无独三的丙均能够援引前诉判决结论中的判断主张甲不具备当事人适格,甲通过提起后诉对是否属于公建用房这个问题进行重复争议的企图有违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由于主体身份不同,乙可主张积极既判力(前诉甲乙为对立当事人),丙则应主张参加效(丙为无独三)。与案例1类似,本案亦属判决对无独三产生有利效力的案件。
(三)与我国无独三制度相应的参加效之特征
我国的上述实践表明,对未被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三适用既判力是不妥当的,但应当对其适用一种略有差异的拘束力,将这种拘束力称为参加效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其与无独三参加诉讼的行为相对应。那么,我国的参加效特征亦应当与我国无独三参加诉讼的形态相照应,才符合主体的权责对称性原理。
首先,我国无独三参加诉讼时不需要明确表明态度自己是“支持”或“辅助”何方当事人,因此参加效并不像大陆法系通说那样限于参加人与被辅助人之间。在真实的诉讼中,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没有那么程式化,而是根据诉讼情况,有时与甲方为同一阵营,有时与乙方为同一阵营,若定要强制其因变换阵营而时时改变其参加诉讼的“辅助”关系,并且将其体现于参加效中,那么在确定参加效主体范围时将会极其复杂,可能出现对这一客体内容的判断在甲与第三人之间产生参加效,对那一客体内容的判断却在乙与第三人之间产生参加效的现象。与其如此,倒不如放弃这种支持/辅助关系的特定化,承认参加效可以在无独三与任何一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日本学者提出的“新既判力说”直观而言是主张无独三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既判力,然而这种“新既判力”在基础和例外事由方面更像参加效。在我国,既然本就不存在特定的辅助关系,那么参加效可产生于参加人与任意一方当事人之间。
第二,我国参加效应不限于对无独三不利的效力,亦应承认对其有利的效力。将参加效限于不利于无独三的效力的德国通说,不符合公平原则,已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参加效既然并非一种单纯保护当事人的效力,而是一项禁止重复争议、防止矛盾判决的制度,就不应在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区别对待。
第三,关于客体范围,如上述案例表明的那样,与无独三有关的裁判内容包含判决主文和判决理由。如是判决主文,法院可能倾向于适用积极既判力,其与积极既判力的作用方式确实相近,然而前后诉主体不同,与其将这种情形视为既判力(扩张),不如依据相关主体无独三的身份将其理解为参加效。如为判决理由,由于学理通说主张既判力仅限于判决主文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务界,法院很少直接对后诉适用积极既判力,下文将要介绍的诸多案件中法院对后诉适用可推翻的预决效力,但许多案件中无独三参加诉讼就是奔着某个判决理由而去,与当事人就该判决理由进行了充分的争议并直接影响判决结果,该判决理由的判断如不对后诉产生拘束力,实质上就是准许重复争议,并不合理。因此应当明确我国参加效客体范围包括判决主文和与无独三之法律地位有关的判决理由。
参加效与既判力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异,那就是例外事由的问题。这在德国实践中或许极其少见,但在我国很可能较为多见,即无独三事实上未能通过参加诉讼对裁判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换言之,他未在前诉获得充分的程序保障,此时使其承受裁判的拘束力反倒走向了不公平的方向。无独三经常未获得充分程序保障的现象,可能正是许多法院对无独三适用可推翻的预决效力之原因。但不确定的预决效力难以实现稳定的制度预期,在参加效的要件上确立相对明确合理的例外是更佳的方案。
四、参加效与预决效力的差异
预决效力在规范表述中是一种免证效力,但如不准许推翻,其实际拘束性不亚于既判力和参加效;如准许推翻,当事人就可在后诉中任意提出反证进行争执。我国的预决效力是一种可推翻的事实影响力,因此与既判力和参加效均不同。但是,预决效力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均存在多个层次:在后诉中重新出现的前诉裁判确认事实可能是判决理由中的主要事实、间接事实或辅助事实,甚至可能是判决主文中牵涉的事实;前后诉主体可能存在不同的牵连关系;预决效力对后诉法官的影响可能是较强的,需要提出较为充分的反证才可推翻,也可能影响较弱只要存在某种合理的反证就可推翻。与这种稍嫌不确定的性质相应,预决效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范围很广,案件类型多种多样。
无独三参加前诉的情形中,其与该诉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作为当事人的后诉与前诉之间牵连往往较紧密,故可推测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亦较强,何况无独三还参加了前诉,已获得事先的程序保障,以此为根据使无独三承受拘束性的参加效亦属合理。但若无独三实际上并未获得充分的事先程序保障,就不能绝对禁止其在后诉中争议,此时应适用可推翻的预决效力,否则无独三的利益就会遭到损害。
(一)参加效与预决效力在法律后果上的差异
参加效与预决效力在法律后果上的差异较为明显,一个是拘束性的,一个是非拘束性的。实践中我国法院经常对无独三适用非拘束性的预决效力。
案例4:甲乙协议离婚,后诉讼要求分割财产,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甲在丙公司的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二人均享有权利,法院据此作出调解书。丙对该调解书进行申诉,法院依职权再审并追加丙为第三人,再审认定甲是被任命担任丙公司职务,但不享有实际股权,因此该股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后来甲乙诉丙对丙主张股权,后诉法院认为前诉判决已认定甲对丙不享有股权,适用《民诉法解释》第93条判决驳回甲乙的诉讼请求。[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6)甘0102民初第2972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中,关于甲是否对丙公司享有股权的问题,在前诉中并非诉讼标的本身,但构成法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前提,并且与丙利害相关,丙作为无独三参加诉讼且与甲和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争议,法院作出判断并根据这一判断在甲乙之间作出前诉生效判决。假如允许甲乙在后诉举证推翻,就是准许其进行重复争议,对于丙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可推翻的预决效力不适于解决本案提出的问题。[注]不排除由于我国无参加效的规范,法院利用预决效力规范达到实质上禁止重复争议、实现判决协调性的目的。在实际意义上,即便赋予当事人在后诉中重新争执的机会,有时也很难推翻前诉判断。对于本案,应当适用拘束性的参加效。
(二)关于参加效的例外事由
法院对无独三适用预决效力,在一些例外情形中是合理的,即无独三虽然形式上参加了前诉,但基于某些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的程序保障,未能以自己的诉讼行为影响裁判结果。
案例5:甲银行向乙开立信用证,乙出具信托收据约定甲享有乙通过该信用证交易购买的一批大豆的所有权。乙未还款,故甲诉乙请求确认该批大豆属于自己所有,法院查封这批大豆。乙还曾通过置换协议将该批大豆换给丙,故丙向法院提出异议,法院通知丙作为甲乙诉讼的无独三参加诉讼。但由于乙对甲起诉的全部事实予以承认,法院作出相应的判决。然后丙诉乙,将甲作为第三人,请求法院确认同一批大豆属于自己,甲抗辩称前诉判决已确认大豆属于信托财产,后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后诉法院认为前后诉不具有同一性,至于前诉判决认定的事实,仅为已决事实故可推翻,乙在前后诉对大豆的权属存在矛盾表述,且信托收据不能对抗第三人,故大豆仍属乙所有,不属于甲。不过由于乙还未交付给丙,法院判决驳回丙的确权请求。[注]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四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中,虽然丙作为无独三参加了前诉,但由于被告对原告起诉的事实全部予以承认,丙所主张的自己才是大豆所有权人的这一问题,并未获得实质性的争议,对前诉判决的作出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前诉法院很可能是基于处分原则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注]虽然无独三丙提出异议,但可能是考虑到债权的相对性和不大可能是虚假诉讼,前诉法院未对被告的处分行为进行干预。后诉丙作为当事人,才有权对大豆权属进行充分争议,因此不能承认参加效的拘束。参加效是以无独三在前诉中获得了充分程序保障为基础的,假如无独三虽然在形式上参加了诉讼,但却实质上未能影响判决结果,他就不应受参加效拘束,否则可能导致裁判突袭,损害无独三的程序权利和实体利益。
本案是构成参加效例外的一个典型情形,此外,德国和日本辅助参加效的例外在我国的语境中亦可借鉴,如无独三由于参加诉讼的时机、与当事人行为抵触或受当事人妨碍未提出攻击防御手段等。但是我国无独三参加诉讼制度与大陆法系辅助参加存在差异,而且无独三在诉讼中究竟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受到当事人行为的何种制约,均存在一些模糊之处。根据相关规定,无独三无权提起管辖权异议、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申请撤诉,但仅被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三有权提起上诉,其他无独三无权上诉。管辖权异议、对诉讼请求本身的处分方面受到的限制,不影响无独三提出攻击防御手段。但无独三是否受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制约,无独三不能提起上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程序保障,均难以确定。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意或承认时,有的法院不考虑无独三的反对意见,有的法院则相反(结合上述案例4和5可知);有的法院不准许无独三单独提起上诉,[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终3130号民事裁定书。但有的法院却准许无独三上诉。[注]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0民终686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3民终1194号民事裁定书。一概不准许无独三上诉确实不合理,但若与当事人意愿相违时该如何处理亦是问题。这些情形都影响到我国参加效例外事由的确定,[注]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对无独三诉讼权能作出细致的合理规定,但另一方面,承认参加效及其例外反过来有助于促进第三人诉讼权能的规范化。在现阶段或许仅能停留在较为抽象的层面,即无独三在前诉中非因自身原因未能对前诉裁判结果产生影响。
(三)参加效与预决效力的关系
无独三虽应承受生效裁判的参加效,但在符合例外条件时,他可以对裁判中的判断进行争议,即像普通案外人那样仅承受非拘束性的预决效力的影响,这或许能够看作理解参加效与预决效力关系的一条线索。在某种程度上,参加效可被视为预决效力的一种“升格”,一种由于案外人获得了事先程序保障而在预决效力之上增加了拘束性的效力,且由于无独三实际上未获得充分程序保障而回归为一种可推翻的事实性影响。
这恰好与无独三在前诉中地位的“流动性”相对应,因此体现了诉讼中第三人权责对称的原理。无独三在前诉的地位正好居于当事人与一般案外人之间,其进入他人之间的诉讼,对自己法律地位有关的事项进行争议,由于这种事先程序保障其能享有几乎与当事人一样的争议机会,因此要承受裁判内容对其的拘束;然而若由于种种外在原因(除掉其自身的懈怠,懈怠不能成为摆脱参加效的正当事由),其未能实质影响裁判结果的,该第三人实际上与一般的案外人没什么两样,此时应像一般的案外人那样可以在后诉中再来争执。
由此,参加效还与既判力、预决效力处于一种联系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将参加效视为居于无例外地产生拘束的既判力和无例外地不产生拘束的预决效力之间的一种“状态”,即一种有例外的拘束力。在适用范围上,参加效也具有一种过渡性的特征,既不像既判力那样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也不像预决效力那样门槛极低。
五、关于参加效在前诉共同诉讼主体之间的类推适用
关于参加效能否类推适用的问题,曾有日本学者主张辅助参加人与当事人间关系与某些共同诉讼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极为近似,且即使共同诉讼主体之间未在形式上进行辅助参加(由于共同实施诉讼故无须诉讼告知),由于利益相互纠结,他们实际上会像辅助参加人一样实施相互“辅助/支持”的诉讼行为,此时可承认“当然的诉讼参加”,并将参加效在这些共同诉讼主体之间类推适用或进行扩张。这种学说曾经构成有力说,[注]兼子一教授的体系书对这种学说有所介绍,该学说在当时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见三月章:《民事訴訟法》,有斐阁1959年版,第241页。不过一些学者认为参加效应具有明确性,因此拒绝参加效的类推适用。[注]参见三月章:《民事訴訟法》,有斐阁1959年版,第241页。但是,这种类推适用在特定的情形中的确有助于实现公平。[注]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71页。
在我国,参加效在规范层面缺失,相关的学理研究也较少,对于参加效能否类推适用的问题自无明确答案。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前诉作为共同诉讼人的主体在后诉中成为对立当事人的情形极为常见。若前诉为必要共同诉讼,由于诉讼标的同一,裁判对共同诉讼人产生统一的既判力;[注]特别明显的就是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如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终713号民事判决书,本案涉及继承纠纷。若前诉为普通共同诉讼,裁判其实是多个独立的裁判,仅在存在诉讼请求的诉讼主体之间产生既判力,后诉不被遮断,且既判力不影响共同诉讼主体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国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本文限于篇幅不进行深入的探讨,但通过一般观察可知,多数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之间进行的对立的后诉不应被前诉裁判所遮断,因其并不符合重复起诉的定义与要求。此时,若共同诉讼人之一在前诉中对另一共同诉讼人的诉讼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符合成为第三人的要件,在我国并不存在相关的制度设计允许共同诉讼人再成为无独三,但共同诉讼人作为当事人本就有机会对相关问题进行充分的争议,并且很可能影响裁判结果,此时如在后诉中还准许他们重复争议,就没有必要且可能造成矛盾裁判。既然共同诉讼人彼此之间处于与无独三和当事人之间相同的利益状况之中,将参加效类推适用就是妥当的。
我国司法实践中,前诉(共同诉讼)裁判对共同诉讼人作为对立双方实施的后诉产生影响的案件极为常见。就像对待无独三一样,后诉法院经常适用既判力或预决效力,也不存在统一的标准。
案例6:甲向乙借款,丙为保证人,乙诉甲、丙分别请求偿还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法院判决支持乙的诉讼请求,并说明丙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甲追偿。丙诉甲,主张甲不偿还债务故法院扣押了丙对第三人的债权导致自己受损,请求法院判决甲向自己给付。后诉法院认为,丙的追偿权已由前诉判决予以确认,丙、甲之间的争议已经生效判决处理,法院和当事人均受前诉判决拘束,丙再次起诉缺乏法律依据,应驳回起诉。[注]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5民终388号民事裁定书。类似的案例还有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葫民终字第01614号民事裁定书。
本案法院将后诉视为重复起诉是不妥当的,因为追偿纠纷并不属于前诉诉讼标的。前诉法院仅仅顺带说明了保证人承担责任后可向主债务人追偿,其实是对相关规范的复述,是法律逻辑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并非对追偿权具体的确认。此外,在前诉判决作出时,追偿权尚未产生,能否产生以及具体的追偿数额等问题均不清楚。前后诉主体也并不真正同一,故不能认为前诉判决对后诉产生既判力。案例6法院的做法,就容易使保证人的利益受损。
案例7:甲向乙借款,丙以某栋房产为甲提供抵押担保,乙诉甲丙分别请求还债、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甲缺席,丙对担保债务进行了抗辩,法院认为三方签订的协议有效,甲、丙应承担债务,判决支持乙诉讼请求。丙向乙偿还借款后起诉甲追偿,法院受理,甲抗辩称借款关系实际发生于乙、丙之间,自己只是中间人,但法院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3条认为前诉判决已对主债务和担保债务进行了确认,担保人履行债务后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甲的抗辩与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不符,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判决支持丙诉讼请求。[注]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5民初10231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法院就未将后诉视为重复起诉。但本案中,主债务人前诉缺席,未对主债务成立与否进行充分的争议,因此后诉中应准许其举证推翻,法院对其适用非拘束性的预决效力是合理的。共同诉讼人与无独三毕竟存在差异,无独三参加诉讼或被通知参加诉讼的,他的目的是或制度期待他,利用参加诉讼的机会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争执,而共同诉讼人的攻击防御重点却往往是针对对方当事人的,如果共同诉讼人缺席还要类推适用参加效,就不合理了,因为不能期待共同诉讼人在前诉中必须与自己的“同伴”进行争议。
不过,一旦共同诉讼人之间确实就某个问题经过了实际的争议,法院作出判断并以此为据作出本诉判决的,就应将参加效类推适用于共同诉讼人之间。
案例8:甲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损和乙受伤。乙诉甲和该车的保险公司丙请求赔偿损失,丙抗辩称车辆超载,根据保险合同丙享有10%的免赔率,甲则主张丙对该免责条款未履行说明义务故该条款不生效,法院认为超载同时还是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保单对这一免责条款进行了加黑,因此甲的主张不能成立,支持丙享有10%免赔率的主张,由甲自己向乙赔偿这10%的损失。后甲以自己车损为由诉丙请求理赔,后诉争议焦点再次集中到关于超载的免责条款效力问题,法院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3条认为前诉判决已经确认丙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故该条款有效,甲关于该免责条款不生效的理由不成立,并据此作出判决。[注]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4民终1155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中,甲与丙之间针对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效力问题在前诉中已经进行过争议,并且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决定了法院如何作出终局判决:在确定丙享有10%免赔率后,这一部分的损失就由甲承担,不由丙承担。在甲与丙关于车损赔偿义务的诉讼中,免赔条款的效力同样决定终局判决的内容,构成前后诉共同的关键性前提条件。在这样的情形中,由于甲丙对同一问题已进行过充分的争议,在后诉中就不应当准许重复争议,否则就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对于前诉判决对其有利的当事人不公平。
将参加效类推适用于共同诉讼主体彼此之间,是因为在有些情形中共同诉讼人彼此之间的利益状况与参加诉讼的无独三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状况极为相近。如果不予类推适用,就意味着准许重复性的争议。但是考虑到共同诉讼制度与无独三参加诉讼制度的差异,不妨将这一类推适用限制在共同诉讼人实际上在前诉中进行过争议的案件,[注]将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参加效限于共同诉讼人在前诉中实际争议过的情形,与美国在类似情形中适用的争点排除效(一种拘束力)十分接近。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Judgments, vol.1, § 38 (1982). 美国争点排除效在我国学术界亦有一定的影响,但该效力内容较多,还包括判决对实质参加了诉讼的第三人产生的拘束力,这部分内容与大陆法系的参加效相近。这一限制条件正好直接对应着防止重复争议的目的并能够防止裁判突袭。
六、结语
在我国确立参加效制度,有利于解决民事诉讼中第三人权责不对称的问题。在将参加效与既判力、预决效力进行对比的过程中,既进一步佐证其作为一项裁判效力的独立性,又能为我国参加效制度的构建提供一个大致的基础与框架。在我国语境下,不妨承认参加效可产生于无独三与任意一方当事人之间,且不限于不利于无独三的效力,它可产生于判决主文和与无独三有关的判决理由,存在无独三未实质获得程序保障的例外事由,还可类推适用于实际进行过争议的共同诉讼人之间。在更精致的层面,究竟哪些判决理由产生参加效,取决于无独三与前诉的利害关系类型;参加效应存在哪些具体例外事由,应根据我国无独三在诉讼中的地位和诉讼权能来确定。对于这些问题的详细解答,需要回归到我国无独三参加诉讼制度的本身,本文限于篇幅难以展开,但将这些我国学界颇为关注的制度问题与判决效力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有助于从体系化的角度促进我国民事诉讼中第三人制度研究的深化,因此笔者今后的研究会继续朝这一方向努力,也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学界同仁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