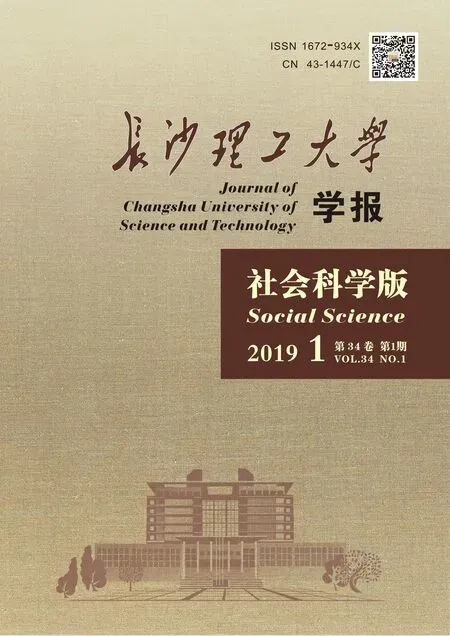社会生物学探求人性的方法论缺陷
——论菲利普·基切尔的社会生物学批判
郝 苑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社会生物学的人性探求引发广泛争议
在当代智识世界中,社会生物学是一个颇具影响而又充满争议的主题。早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那个时代,进化对行为的影响就引起了许多生物学家与哲学家的兴趣。不过,社会生物学主要是在20世纪获得了系统的发展。1948年,动物行为学家约翰·保罗·斯科特在一场关于遗传学与社会行为的学术会议上创造了“社会生物学”这个术语。20世纪60年代,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罗伯特·特里弗斯与威廉·汉密尔顿的相关研究,为社会生物学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让他们成为当代社会生物学思想的重要先驱。1975年,爱德华·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系统阐述了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思想,并将之推广到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研究之中,广泛激起了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兴趣与争辩。
根据威尔逊的定义,社会生物学致力于探究的是“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1],社会生物学并不仅仅满足于研究非人类的动物社会,而是力图将有关动物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与社会规律的诸多研究结论拓展到人类社会。社会生物学的一个核心主张是,生物群体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方式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这些行为方式服务于生物让自身的适应性最大化的目的。生物种群的特定行为方式在生物的遗传基础中有着深刻的根源,它们不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轻易发生变化。相应地,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行为方式与结构规律,是自然选择在漫长进化历史中挑选出来的有利于人类这个群体的适应性最大化的东西,这些盛行的行为方式与社会制度有着深刻的基因、遗传与生物基础。鉴于这些基础具有相当程度的固定性,不难得知,难以通过改变社会环境来更改人类的行为模式以及相关的制度。倘若忽视生物学提供的这些原理而强行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与相关的制度,“其损失是社会科学家们承担不起的”[2]。
应当说,就主观意图而言,威尔逊等著名社会生物学家未必都明确希望,让自身的理论来为各种宣扬阶级歧视、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极端政治立场做出辩护。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与社会生物学结成同盟的达尔文主义的人类学、人类行为生态学、进化心理学的通俗论著中,充斥着各种鼓吹政治偏见的观念论断,而那些致力于宣扬阶级压迫、性别歧视、种族隔离的新右翼分子,也利用社会生物学积极为自身的政治主张辩护。不难预料,社会生物学所蕴含的政治主张,激怒了一大批致力于推进社会平等与公正的左翼理论家与社会活动家,他们对社会生物学所蕴含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后果进行了猛烈抨击。不过这些批判经常负载着诸多源自学术左派的政治观点与政治修辞,社会生物学家就此抓住了反击的契机,他们在“科学自治”名义下表示,不应当根据在西方当代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先入为主地认为人性应该如何,然后再强行要求自然科学依照这种理想模式描绘人性。
必须承认,当代有相当一部分对社会生物学的批判确实主要侧重于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它们相对缺乏对这种科学理论及其蕴含的方法论本身的专业剖析。相较于这类从政治与文化的“局外人”视角进行的社会生物学批判,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 1947-)更多侧重于在方法论上对社会生物学进行内在的批判。基切尔凭借严谨的分析论证与过硬的专业知识,敏锐地揭露了社会生物学在探求人性的过程中所犯下的诸多方法论错误,进而敦促人们去反思社会生物学诸多谬误的深层思想根源。
二、社会生物学对“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的仓促判断
虽然基切尔对社会生物学的批判也带有他的政治动机,但基切尔并没有沉溺于流俗的政治修辞之中,而是明智地聚焦于方法论层面上的哲学批判。社会生物学在文化中的强大话语权来源于它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源于它所运用的方法的合理性。一旦在方法论上揭示了社会生物学的诸多问题与弊病,也就能从根基处撼动社会生物学的权威性与正当性。许多社会生物学家宣称,社会生物学是整合进化论的洞识与对动物行为的细致观察的产物,社会生物学方法的合理性,源于进化论的方法的合理性,任何不支持这个研究纲领的人就是在反对达尔文的理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当代哲学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方法论上的可靠性并不像这些社会生物学家所认为的那么普遍被哲学家认同。维特根斯坦在对比了达尔文的理论与某些物理学理论之后认为,进化论说服人们所借助的“根据极为微弱”,“到头来你对有关证实的每一个问题都忘得一干二净,你只知道去确信事情似乎一定是这样的”[3]。维特根斯坦质疑的是进化论的证实方式,而波普尔则怀疑进化论是不可证伪的。由于波普尔相信,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可证伪性,真正的科学是可以证伪的。因此,“达尔文主义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4],进化论在这种方法论的意义上是一种可疑的理论。
基切尔并不赞同上述哲学家的激进论断,按照他的观点,进化论在方法论上的合理性与可靠性,取决于它对于生物由来历史与自然选择历史的演变原因所构造的结构性叙事(基切尔将之称为“达尔文主义的历史”[5](P55))的合理性与可靠性。检验“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的方式,并不是绝对的证实或证伪,而是科学家依据生态学、遗传学、生理学等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构造出一系列相互竞争的“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然后再依据细致严谨的观察与实验逐步排除不合理的假设,进而确定迄今为止最合理的理论叙事。基切尔指出,在探寻“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理想的情况”,科学家依据背景知识构造出了一系列可能存在的进化历史假设,通过观察与实验提供的坚实的经验证据,科学家排除了其他的竞争性历史,只留下一种关于这段历史的假设。第二种情况是“不充分决定的情况”,即现有的经验证据不足以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竞争的历史假说之间进行取舍。第三种情况是科学家拥有一个详尽的达尔文主义的历史,但是,科学家在相关的背景知识上“过于无知”,导致了他们迄今没有能力去构造众多对于这段进化历史的竞争性解释[5](P71-72)。基切尔认为,科学家对于第一种情况的合理反应是相信这种历史,对于第二种情况的合理反应是承认自己的无知。造成困扰的是第三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貌似只存在一种对于这段进化历史的合理解释,但是,由于这种解释没有经过严酷的理论竞争,由于科学家在相关学科背景知识方面的欠缺,因此,并不能确保未来不会出现一种更好的解释来取代现有的理论。对于这种情况,不同的科学家将采纳不同的认知态度,谨慎的科学家会采纳怀疑的态度,将理论交付未来的进一步检验。野心勃勃的科学家则会主张大胆接受这种历史解释,并有可能在这种解释的基础上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研究事业。
在这种方法论哲学的观照下,进化论所构造的种种历史叙事的合理性与可靠性就有所不同,而不同科学家对待在第三种情况下的“达尔文主义的历史”所采纳的不同认知态度,也将深刻地影响他们自身发展的研究纲领的合理性与可靠性。在基切尔看来,社会生物学家在方法论上犯下的诸多错误,就与他们仓促接受一些颇成问题的“达尔文主义的历史”有关。在社会生物学家探究人性的整体论证思路中,他们青睐的是那些符合他们理论旨趣的适应主义历史。然而,基切尔通过细致严谨的理论分析表明,用来论证适应主义历史的“最优化证明”本身,总是过于轻易地忽略了诸多在进化历史中存在的重要可能性。社会生物学家所钟爱的适应主义历史,只是伏尔泰笔下的潘格洛斯博士的幼稚乐观主义在当代的改进版本,在生物进化历史的每个阶段中,受制于同时代诸多约束条件的最佳设计并非始终都会普遍存在。“在所有可能存在的建筑师中,进化并不是一位最好的建筑师。”[5](P226)通过方法论的哲学反思,不难看出,社会生物学的整体论证思路在根基处就是大成问题的。
三、社会生物学与最佳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差距
毋庸讳言,社会生物学家在其宏大理论抱负的诱惑下,在方法论层面犯下了诸多仓促与草率的错误。初看起来,社会生物学家努力从最好的自然科学中汲取最佳的理论方法,这些精致而严谨的科学理论方法有助于各种社会生物学理论在社会文化中提升自身的说服力、权威性与正当性。然而,基切尔并没有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以三个例证为切入点,精心比较了社会生物学与最佳科学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差距。
基切尔选取的第一个例证是开普勒对于火星运行轨道的计算。开普勒通过运用哥白尼的体系,计算出了火星运行轨道,计算结果与第谷积累的观察资料的符合程度在八分弧度之内。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第谷并没有将这八分弧度的差距作为“合理误差”,而是据此做出了重要的理论修正,从而为近代早期的天文学革命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基切尔进一步深入探究了社会生物学家对于粪蝇、灌丛鸦、狮群以及社会性昆虫的研究所采纳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相较于开普勒对于理论预期和观察资料的细微差异的重视,社会生物学家“遗漏了令人不安的事实并错误报告了动物行为研究者的发现”[5](P181),他们不仅经常没有对理论模型与观察资料之间的数值差距采纳必要的重视态度,而且不时会忽略诸多可能的竞争性解释。社会生物学家在方法论上的仓促态度,显然无益于他们进一步做出重要的理论发现与理论修正。
基切尔选取的第二个例证是牛顿在经典物理学中做出的“我不杜撰假说”这个著名声明。为了避免对于引力的诸多原因进行徒劳的争辩,牛顿坦然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并且主张,不去构造那些在实验哲学中没有地位的,并非现象推断出来的,在科学实践中并不能发挥实际效用的假说。基切尔在细致审视以理查德·亚历山大为代表的一批社会生物学家的研究规划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社会生物学家也宣称自己不做假设,但他们所假定的那个在人类之中广泛存在的计算广义适合度并据此限定人类行为的近似机制,在研究舅权制、斧战、弑婴与不同阶层的婚嫁现象时,既没有导出未曾预料到的新颖预测,也没有给出不可替代的有效解释。基切尔借助“进化的民间心理学”,能够同样好地对上述社会现象给出必要的解释。因此,基切尔认为,社会生物学提出的近似机制实际上并没有帮助人们加深对人性的理解,而是“将描述性的人类学与有关广义适合度的不相干咒语混在一起”[5](P329),而对于这种在探究人性与社会的科学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假说,人们完全可以像拉普拉斯那样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假说”。
相较于先前取自最佳科学实践的两个正面例证,基切尔的第三个例证则取自社会生物学的反面例证——拉姆斯登与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威尔逊早期版本的社会生物学因其在解释中没有恰当考虑人类的心灵与文化而饱受诟病,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拉姆斯登与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运用了大量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方程来解释诸多文化现象。在基切尔看来,拉姆斯登与威尔逊之所以采纳这样的方法,是因为他们想借助数学的权威来压制社会生物学的诸多批评者与诋毁者。恰如胡塞尔指出,在近代早期的科学革命中,“科学普遍性的新理念在数学的改造中有其起源”[6],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自然本身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这个哲学观念转变的过程对于现代科学的确定性与精密性的奠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研究范式下,复杂而严密的数学方法是优秀科学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基切尔强调,并非任何使用了貌似复杂而严密的数学方法的科学就必然是一门优秀的科学。数学在生物学中的成功应用“纠正了幼稚的预期, 将我们导向了新的问题, 并让我们意识到了先前没有被我们辨认出来的诸多假设”[5](P394)。然而,尽管拉姆斯登与威尔逊所发展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宣称要揭开心灵与文化的“面纱”,“透露人类起源的秘密”[7],但其运用的复杂数学方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玩弄数学技巧来达到他们既定的理论结论的,这既没有让他们的理论产生新颖的预测,也没有有效增加他们理论的解释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生物学所运用的许多数学方法,不过是一件用繁杂的数学方程式编织而成的“皇帝新衣”。拉姆斯登与威尔逊妄图借助这件“皇帝新衣”来维系自身在方法论上的权威,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社会生物学先前对人性、心灵与文化的狭隘理解。
通过对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文献与案例研究进行广泛的考察,基切尔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生物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一系列的错误与缺陷,但是,并没有某个单一的方法论谬误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生物学理论之中。因此,有必要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生物学理论。基切尔将社会生物学大致区分为两个类型:一种社会生物学主要研究的是非人类的社会性动物的行为规律与社会结构;另一种社会生物学则试图根据动物行为进化的研究成果来提出有关人类本性与社会制度的宏大论断。由于后一种社会生物学不仅在公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许多社会生物学家也有意无意地用这类研究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基切尔将之称为“流行的社会生物学”[5](P14-15)。基切尔指出,社会生物学拥有“两副面孔”,在研究非人类的动物行为时,它通常是谨慎而细致的,在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时,它为了获取公众的关注与社会的影响,就经常做出仓促而浮夸的论断[5](P435)。
社会生物学为了将有关动物社会行为的结论拓展到人类社会,往往无视或低估动物与人类的诸多差异,而这导致了社会生物学家频繁地运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动物与人类的社会行为。可是,人类不仅仅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也是精致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建构而成的存在者,他的行为动机与社会制度要比动物远为复杂。以“强暴”为例,动物之间发生的强迫性性行为或许能够增加强暴者后代的数目。然而,在人类社会中,由于强暴而产生的子女在未出生前就有可能被受害者堕胎,即便勉强出生后也有可能因为疏于照顾而夭折。由于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刑罚,强暴者会由于这种暴行而被长时间乃至终生剥夺自由,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他在一生中孕育后代的可能性。进而,人类的强暴行为还有可能发生于没有生育能力的幼女、老年妇女乃至同性身上,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类进行这种暴力行为的动机更多的是对受害者“施加痛苦与羞辱”,“所有这类行动对强暴者基因的传播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5](P187-188)。社会生物学家将人类的强暴行为与动物的强暴行为进行牵强的类比,恰恰遮蔽了人类行为动机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以相同的术语来描述人类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这反映了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预设乃至理论偏见,强烈地扭曲了他们对这些行为的观察。
当然,正如汉森、库恩与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指出的,“观察渗透理论”的现象即便在最好的科学当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有人据此主张,对于社会生物学这种看起来具有远大前景的科学理论来说,应当对之保持必要的宽容。即便这种科学理论在方法论上存在着诸多缺陷与错误,仍然不能过于仓促地将之彻底拒斥。基切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为自己在方法论上对社会生物学采纳的严格态度做出了如下辩护:在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里,现代政府经常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寻求指导。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与人类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人性问题、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社会生物学有关人性的诸多论断,将轻易影响社会政策的形成。若以社会生物学的某些论断作为政策依据,这些政策极有可能产生诸多不利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后果。恰如当一款新药品投放市场可能带来严重的危险后果时,药品制造商就会对于检验该药品的证据采纳更高的标准。“当社会生物学有可能在政治文化中带来威胁大量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发展的风险时,科学家与哲学家就应当以更高的方法论标准来要求这门学科给出更加严谨慎重的证明”[5](P9)。
四、社会生物学探求人性的“奢望”及其谬误根源
令人遗憾的是,社会生物学家并没有在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研究主题上保持必要的谨慎态度,他们虽然在非人类的社会生物学领域取得了不少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但他们就像麦克白一样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荣耀,野心勃勃地希望将他们的诸多结论拓展到人类社会。他们仓促地在方法论上犯下了诸多严重的过错,让他们探究人性与社会宏大理论的过高抱负沦为一种“奢望”。当然,基切尔丝毫无意于否定社会生物学在理解人性与社会的问题上做出理论贡献的可能性。这种严肃的社会生物学研究是在运用进化理论家、行为遗传学家、发育生物学家、发展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认知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巨大的理论综合,“当这个联盟的某些贡献者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时, 就难以实现这种综合”[5](P436-437)。
社会生物学在相关学科知识没有充分成熟的条件下仓促进行这样的理论综合,这反映的是一种在当代智识世界中颇为流行的科学主义的虚妄而又傲慢的态度。作为“分科之学”,现代科学孕育的是在诸多专业领域中的专家,这些专家在自身研究领域中的论断经常是严谨的与审慎的。然而,当这些专家试图超越自身的专业领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理论方法拓展到人性、社会与文化之上时,他们就有可能做出偏颇的论断。康德早在18世纪就告诫人们,“真正纯理论的知识永远不能拥有经验以外的对象”[8],当人类理性的认识试图超越经验的界限来认识物自体时,就将导致“二律背反”。如果说,在康德那个时代里,犯下超越理性界限错误的是缺乏经验根基的形而上学,那么,在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里,犯下这种错误的则是信奉科学万能或科学方法万能的科学主义。
海德格尔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科学也不只是人的一项文化活动。科学乃是一切存在之物借以向我们呈现(dar-stellen)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9]。当科学决定性地支配了事物向人类呈现出来的面貌时,它也就遮蔽了事物借由不同于科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其他面貌。独断的科学主义者相信,现代科学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提供了排他式的客观真理,只有科学真理才提供了符合这个世界的客观描述。独断的科学主义者陶醉于科学真理的客观性,而尼采的视角主义却早已对这种客观性进行了质疑。在尼采看来,被哲学家与科学家宣扬的客观性并非没有利益的沉思,而是“视角性的观看”与“视角性的认知”。尼采进而宣称,“我们能用来观察一个事物的眼光(不同的眼光)越多,我们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越全面”[10]。否认科学认知的视角性,只会让科学提供的客观真理变得片面与狭隘。在狭隘的科学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生物学家往往倾向于认为,他们提供了有关人性的全部真理。然而,借用王尔德的说法,有关人性的“真理很少纯粹,也绝不简单”,实际上,社会生物学家对于人性的理解是视角性的,他们仅仅提供了有关人性的部分真理。社会生物学家极力通过各种研究来将人类的行为关联于某种与进化或适应性有关的动机。不过,正如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西德尼·卡顿纯粹为了爱情而做出降低自身适合度的自我牺牲一样,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复杂多样的,并不能将这些行为动机完全还原为让自身适应性最大化的生物学动机。为了更加全面丰富地理解人性,就绝不应当忽视来自科学实践之外的其他人类实践所提供的诸多透视人性的视角。
社会生物学家无视于科学理性的局限性、科学真理的视角性与人类个性的复杂多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哲学的傲慢无知态度。根据一种流俗的观点,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而哲学仍然在一些古老的问题上举步不前。有一些关切哲学问题的科学家就据此主张,应当将哲学“科学化”,通过吸收诸多科学的理论成就和研究范式来推进哲学领域的实质性进步。社会生物学家也认为,他们试图利用社会生物学的诸多理论,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哲学的人性问题。应当说,科学家运用科学理论方法来推进哲学发展的做法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幸的是,恰如基切尔令人信服地表明:社会生物学家对诸多重要哲学传统的傲慢无知,让他们的许多理论观点重复了历史的错误。科学家若在无视哲学史与伟大哲学传统的情况下,将某门实证科学的范式生硬地强加于哲学研究之上,那么,这种“科学化”哲学的做法难免遗忘科学理论视角的局限性,从而催生出诸多乏味、平庸而又狭隘的人性理论。就人性问题而言,恰如海德格尔指出,“根本上,在任何时候,无论哪一门科学的结果都不可能直接地在哲学上获得应用”[11]。纵观世界哲学史,那些在人性问题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哲学家,都不是通过生硬地直接套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或视角来获得这种理论成就的,科学家有关人性的见解确实也帮助过哲学家,不过经常是来自反面——使他们能够批判、反思与超越在智识世界中先入为主的人性偏见。当代科学哲学乃至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或许是,“划定知识的极限,界定它自己的区域”[12],批判、反思与超越现代科学对自然的“祛魅”所导致的种种机械、平庸与乏味的人性观和文化观,在当代知识状况下重塑人性的尊严与高贵,重新点燃人们追求公正、平等与自由的政治理想的希望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