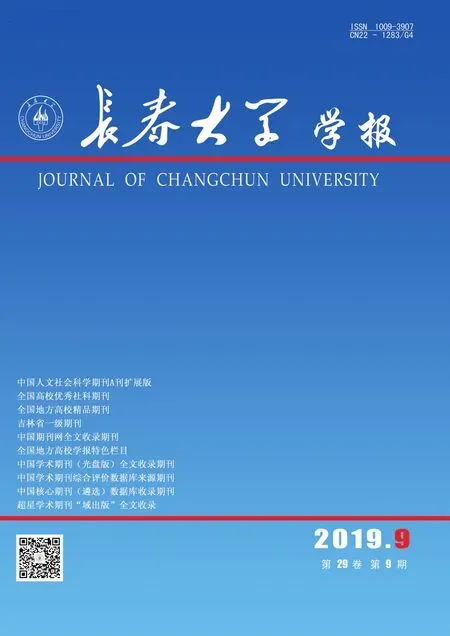空间视域下莫里森《天佑儿童》中的身份建构
郭丽峰,杨晓丽
(太原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太原 030024)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耆耄之年仍活跃于美国文学舞台。2015年,其第11部长篇小说《天佑儿童》(GodHelptheChild)一经面世,便广受赞誉。英国《卫报》称赞说“太好了……莫里森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不管她讲什么故事,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1];《纽约时报》赞誉“莫里森运用她的叙事魔法……这个故事既具有影响力,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既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又能引起强烈的反响”[2]。《天佑儿童》体现了莫里森一贯的主题和风格:以变换的叙事视角,外加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与怪诞,用西方惯用的成长小说模式,讲述了当代社会中黑人女孩布莱德(Bride)童年时期所受的创伤、创伤对其成年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布莱德走出创伤的成长故事,表达了对美国种族以及虐童等当代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近年来,研究者多关注小说中的创伤叙事与成长[3]107-113、身份异化[4]4-11、女性主体意识[5]32-39等主题,缺乏对其中空间与身份的关注。本文将从空间和场域的视角探讨《天佑儿童》中的身份问题,揭开空间与身份建构的互动关系。
1 空间理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文学和文化学研究迎来了空间转向,学者从空间视域探讨文学作品,将跨学科的方法应用到文学研究中。赫尔曼·比沃斯(Herman Beavers)在其2018年新作《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地理与政治想象》中,借用了场域创制、场域身份、场域依恋等多个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从空间与场域视角分析了莫里森的前10部小说,是“对莫里森作品空间研究的拓展与深化”[6]169。比沃斯提出幽闭空间(tight space)概念,指出“这种空间形式是莫里森小说人物所经历的集体和个人创伤的形式,标志着人物与社区在精神和情感上的隔阂和疏离,以及它抑制了人物维持与场域的有意义的联系方式”[7]6。幽闭空间会导致垂直性场域创制,“强调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暴力和屈从,是构成疏离的主要因素”[7]6。比沃斯指出,莫里森笔下的人物只有鄙弃垂直性场域创制,选择水平性场域创制,强调合作与协调,才能形成更加平等和开放的场所,摆脱幽闭空间束缚,形成更为真实的自我。顺着此思路去研究比沃斯尚未涉足的小说《天佑儿童》,可以更好地发掘该作品中的空间意义。
2 幽闭空间与自我身份断裂
莫里森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对空间的关注。空间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而是“人类主体意识、欲望、身份的投射”[6]170;空间及其所容纳的权力和社会规范,决定了人物的行为方式,“在所有社会中,空间、身体和两者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交织的互动——既不存在独立于社会印记的‘空间’,也不存在独立于社会印记的‘身体’”[8]。《天佑儿童》呈现了多个幽闭空间,包括家庭空间“甜甜”之家,工作空间西尔维娅化妆品公司,以及布莱德自己公寓所代表的个人空间和情感空间。
2.1 “甜甜”之家——种族操演下的幽闭空间
在母亲“甜甜”的忏悔和布莱德回忆的交织中,莫里森描述了“甜甜”之家这样一个幽闭空间。家本该是温馨、安全和庇护的所在,而卢拉·安(Lula Ann Bridewell,后改名为布莱德)所成长的家却沦为微型的种族主义操演的空间,一个有着病态的肤色等级的“家”。卢拉·安的外祖母卢拉·梅(Lula Mae)因肤色较浅,“被误认为白人”[9]3,从此隔绝了和子女的关系;卢拉·梅本可以蒙混过关,却选择了黑人身份,并“为这选择付出了代价”[9]4;卢拉·安的母亲“甜甜”(Sweetness)因肤色较浅很少受到歧视, 并不认同自己作为黑人后代的事实,认为浅肤色是“保留一点尊严”[9]4的资本。上世纪90年代,如“午夜一般”“苏丹人一般”[9]4漆黑的柏油娃娃卢拉·安的出生引起了浅肤色父母的相互猜疑,大打出手,乃至婚姻破裂。“她的肤色是她永远要背负的十字架”[9]7。
由于肤色,布莱德出生即遭到了亲生父亲的抛弃,母亲的歧视、鄙夷、漠视和冷暴力。女儿的深黑肤色让“甜甜”尴尬、困窘、疯狂,甚至一度试图用毯子将孩子闷死,或将孩子送孤儿院。因为良知和害怕而终止行为后,“甜甜”转为对女儿采用冷暴力和“黑人为奴”的奴化教育:尽力避免和女儿有身体的接触,拒绝母乳喂养;拒绝女儿称自己为“妈妈”,而称呼“甜甜”;教导女儿“如何行为举止,如何保持头低下,不惹麻烦”[9]7,远离白人小孩。母亲的漠视和鄙夷让卢拉·安对母亲的抚摸和爱产生了病态的渴望,她祈祷母亲“会扇我的脸或者打我的屁股,只为了感受她的抚摸”[9]31。为了“妈妈能拉我的手”,“用骄傲的眼神看我,哪怕一次”[9]153,在恐惧和顺从的支配下,在一起儿童猥亵案中,卢拉·安指证了无辜的幼儿园老师索菲亚,将其芳华葬送在狱中。这种负罪感和愧疚感更成了她成长过程中背负的十字架。为了保住自己居住的狭小住所,母亲禁止卢拉·安揭发房东性侵儿童一事,造成了卢拉·安所感受的“视觉创伤”[4]7,扭曲了她的是非观和正直感,让她“在面对不公正、罪恶的社会现象时采取了容忍和规避的态度”[4]7。
种族歧视和肤色权利扭曲了父母,异化了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而“父母的肤色歧视让黑肤色女孩子得不到任何尊严”[3]109和关爱,“让那些诅咒、欺凌像毒药、像致命的病毒一样在我(布莱德)的血脉中游走,没有解药”[9]57,让“我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免疫力,所以我只需要不成为一个‘黑鬼女孩’才能赢得比赛”[9]57。在布莱德的回忆中,母亲的卧室“似乎总是没有灯光的”[9]53;在母亲眼里,“我没办法透过黑色看清楚她是谁”[9]43。母亲的身份认同影响了孩子的身份认同,在母亲的冷暴力中,在依赖黑白种族符号的幽闭空间中,在对“黑鬼女孩”的反抗中长大的布莱德同样不知道自己是谁。她对家的感觉是疏离的,事业成功后的布莱德从不回家探望母亲,只给予母亲钱财上的帮助;她与社区和黑人文化是断裂的,这些都阻碍了她塑造连贯的自我的能力。高中毕业后,16岁的卢拉·安丢掉了那个“愚蠢的”“乡野气息的”[9]11名字,改名为Ann Bride,两年后去西尔维亚化妆品公司应聘销售岗位时,将名字缩减为Bride,“在那个令人难忘的音节之前或之后,没有人需要再说什么”[9]11。名字的更换象征了她跟之前的身份以及过去的生活的决裂,象征着她对“甜甜”之家所教授的黑人价值观的反抗。
2.2 西尔维娅化妆品公司——消费符码操控的工作空间
“甜甜”之家的幽闭空间造成了布莱德童年时期所受的创伤和身份的断裂,成年后的布莱德改了名字,隔断了和家庭以及过去的联系,成功地在西尔维娅化妆品公司谋求到一份工作。深黑肤色“既是诅咒,也是祝福”[10]。在西尔维娅,深黑肤色成为对布莱德的“祝福”,成为她在美容界成功的资本。深黑肤色从“诅咒”到“祝福”的转变,契合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以白为美”到“以黑为美”的文化转向,“以黑为美的流行文化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非洲文化寻根成为一种时尚,白人妇女追求深肤色,黑人超模成为时尚杂志和化妆品公司的宠儿”[11]。西尔维娅构成了布莱德的工作空间,成为布莱德离家后重建身份认同感的主要场所。“流行,一种消费艺术”[12]120主宰了该空间,使它成为一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支配下的幽闭空间。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被无限的物所包围,“社会行为举止和心理变化等都受到了物的影响和操纵”,“主体失去其主体性,成了被操纵的对象;物品失去了往日的使用价值,所呈现的更多是它的符码价值,明显地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地位的差异、身份的差异和声望的差异等”[13]39。
在西尔维娅,布莱德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以黑为美”的流行文化所带来的事业成功和虚荣之上的,“试图通过对外在浮华的追求来彰显自我的存在,但是不知不觉中她在流行文化里迷失了自我”[14]。布莱德的真正价值被忽视,她被珍视是因为拥有象征着大众流行文化符号的深黑肤色以及深黑肤色能给消费者所带来文化联想与幻觉,“好时(Hershey’s)糖浆”般的黑皮肤,总能“让人想到掼奶油和巧克力,是上等的、漂亮的”[9]33。“黑色畅销(Black sells),是文明的世界中最畅销的商品”[9]36。为了迎合这样的消费倾向,在造型师杰瑞(Jeri)的建议下,布莱德在穿衣上只穿白色以衬托自己的黑,营造“雪中黑豹”的外在形象。可以说,在工作场所,布莱德及其肤色已成为最具有符号价值的符码,成为了“被消费”的对象。
在日常消费行为中,“消费的性质日益与人的本性、文化和社会建构之间产生密切的关系”[13]41。跃身为化妆品行业的老板后,布莱德开豪车,消费奢侈品, 沉溺于购物所带来的快感与虚荣中,极力想通过购物来获得身份认同和自我满足,消费变为彰显她社会地位和等级的标志。布莱德所消费的“不仅仅是商品的物质性,而且还消费着商品的符号性,因为作为符号的商品能够为人们创作自我,建构身份”[13]43,其消费行为体现了消费社会中对物的符码价值的依赖。布莱德实现的认同实际上是对消费意识形态的认同,是被消费所控制的一种虚假身份的认同,而物的操纵和消费主义也影响了她的行为方式。在索菲亚获假释当晚,布莱德带着一沓机票打折券、一堆护肤品和5000美元(200美元每年,如果刑满)来看望索菲亚,企图用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诬告对索菲亚造成的伤害。正如周权在其文章中所说,“她的黑色身体其实变成了男人消费的对象,变成了一种物化的商品。布莱德被物化或者商品化了,她获得的只是一种虚假的主体”[5]35。布莱德在西尔维娅这一消费符码操纵的空间下所建构的身份认同,是虚假且虚幻的。
2.3 “公寓”所代表的个人情感空间
作为私人住所的“公寓”(Condo)是布莱德日常生活空间的另一重要部分,也成为布莱德与异性建立情感关系的主要空间,在她自我身份认同和构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柯尔特(Kort)认为,个人空间具有“治愈潜能”[15]73,能让人“摆脱社会分类和身份构建限定”[15]136,实现本真自我和自我的完整性。而布莱德的公寓并不具备成为这样的个人空间的可能性,而是消费主义在其个人生活空间内的延伸,构成了禁锢布莱德的另一重幽闭空间。
在消费社会中,“性欲被视为头等大事”[13]44,“个体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体,……必须使个体把自己当成物品,当成最美的物品,……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12]147。对于布莱德而言,身体和性无疑成了最具有交换价值的符码,最美的消费品,在异性关系上“似健怡可乐(Diet Coke)——表面甜蜜、营养全无”[9]36。布莱德并不明白什么是真爱,以为性才是爱情的全部,认为商业广告、杂志、音乐中所表现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在与各式男友的交往过程中,她始终保持一种情感的距离,只维持一种性关系,沉迷于外在美对男人的吸引力以及给自己带来的情感的安全性,而其男朋友们也是把占有她当作“一枚奖章,对他们的能力的一种闪亮而安静的见证”[9]36。在与布克的交往过程中,布莱德“真心觉得已找到我的男人”[9]62,“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每一次恐惧,伤害,成就,无论多渺小”[9]53,但对对方却知之甚少,“我从没有想过他人生中那些事,因为除了做爱和他完全懂我之外,我们关系的重点是一起玩乐”[9]61。只享受和布克的性爱和玩乐,布莱德对布克的了解仅限于对他身体和外貌的了解,“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美丽的男人,甚至是完美无缺的,除了上唇上的一个小小的伤疤和肩膀上的一个丑陋的伤疤”[9]10。布莱德与布克缺乏真正的交流,对爱人的成长经历、童年创伤一无所知,致使两人因为索菲亚之事发生了龃龉,激怒了布克,被他抛弃。可以说,布莱德公寓所代表的个人情感空间实际上是被性欲和“快感原则”支配的空间,是消费主义在她个人生活领域的延伸。在这样疏离的情感空间中,布莱德建构的情感安全性和身份也是虚幻缥缈的,缺乏真正的人际关系和对自己的真正认知。
3 空间流动与自我身份的重构
布莱德的男友布克因年少目睹了哥哥被性侵杀害后弃尸的惨状,对娈童者愤恨有加,因此无法理解布莱德去探望“猥亵”过儿童的索菲亚,留下一句“你不是我要的女人”后摔门而去。不顾男友反对,布莱德在索菲亚假释的日子来到监狱门口,试图用物质来弥补索菲亚15年的冤情,遭到了索菲亚的暴打。男友的抛弃使她失去了情感的安全性,生活支离破碎,“个人魅力,对一个令人兴奋甚至充满创造力的职业的控制力,性自由,这些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保护她不受尴尬或爱等任何过度强烈感觉影响的盾牌”[9]79,这些她曾经缝合好的东西再一次支离破碎。两件事中的懦弱和无助把这位成熟的女商人打回到童年时伤痕累累的黑人小女孩,让她从一个拥有完整、性感的身体的黑人女性萎缩成一个没有发育、没有胆量的黑人小姑娘。莫里森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布莱德身体变回小女孩的过程,第二性征之一的阴毛消失了,耳洞消失,乳房变得扁平,“布莱德身体的残缺是她之前建构的虚假的主体性瓦解的内心反映,是心理创伤的外化”[5]36。痛苦愤恨无助下,布莱德挺身而出,踏上了追寻布克之路,去勇敢地面对第一个让她掏心掏肺的男人。布莱德所追寻的不仅是爱人,她要找他当面问清楚为何她不是他想要的女人。因此这样的追寻就包含了两层含义:追寻爱情,追寻身份(自己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布莱德的追寻之路百转千回,从城市到乡村,从嬉皮士夫妇之家,到奎因(Queen)的小屋。
在寻爱之旅中,布莱德驾车冲出急拐弯,撞上了大树,遭遇车祸被困车中,后被白人小女孩雷恩(Rain)发现,被隐居于乡下的嬉皮士夫妇史蒂夫(Steve)和伊芙琳(Evelyn)救起并送当地诊所治疗。在嬉皮士夫妇家里养伤期间,布莱德远离了城市的喧闹和物质主义,和“过着最贫苦生活的人在一起”[9]90,和“选择在人迹罕至的乡村公路边缘实现自己反资本主义理想的嬉皮士”[9]141住在一起,没有电话,没有电,只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在这摆脱了物质主义的居住空间里,布莱德捏造的虚荣浮夸的名字并未让人觉得时髦;布莱德也不需要通过精致的妆容和随身携带的奢侈品来提升自我去获得别人的认同。这对白人夫妻“像对待流浪猫或断了腿的狗一样”[9]90,把她看作一个最基本的人,用一种“生来如此”[9]85的坦率态度看待她的肤色,“毫不犹豫地为她献出自己的心血,没有要求任何回报”[9]90,让她看到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是清贫的生活吗?是没有钱、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没有冰箱、没有浴室吗?史蒂夫告诉她,钱并没有那么重要,“钱不能使你摆脱那次车祸,钱不能拯救你的生命”[9]91,世界上存在“善良本身和没有物质的爱”[9]92。在斯蒂夫夫妻的影响下,布莱德逐渐摆脱了物质对自己的异化,丢掉了虚假的优越感,与人开始进行更为真诚的交往,和雷恩建立起了“学校女生”般的亲密关系,成为她倾述的对象,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她。
伤愈后,“决心要发现她是由什么制成的——棉花还是钢”[9]143,布莱德继续踏上了追寻之路,找到了布克的姑妈奎因(Queen)所居的乡间小屋——“女巫之窝”[9]145。初见面,奎因没有恭维她的美貌,也无视她的肤色,而是像母亲一样首先注意到她的饥肠辘辘,“你看上去像个浣熊,拒绝吃东西”[9]144。对于长期以来在商界依靠外在美和肤色取得成功的布莱德来说,奎因的评价和反应让她知道“它(外在美)的浅薄和自己的懦弱——这是‘甜甜’教给她的重要的一课,用钉子钉在她的脊骨上,使它弯曲”[9]151。奎因不仅为她准备了非洲传统食物什锦汤,给她提供了身体滋养,还在她犹豫迟疑之际,用一首民歌鼓励了她,给了她勇气,让她意识到“这是关于我,不是他,是我(ME)!”[9]152。布莱德直面布克以及不堪回首的过去,向他承认了卢拉·安的罪行,澄清了两人间的误会,也修复了关系;“她感觉获得了重生,不再被迫重温,不需在母亲的鄙视和父亲的遗弃中苟且偷生了”[9]162。
奎因烧弹簧床垫消灭床虱时,不小心失火,身陷火海。闻讯赶来的布莱德和布克协同合作,奋不顾身,匍匐爬过地板,把昏迷不醒的奎因拖到前院的草坪上。奎因头发被火星点燃时,布莱德毫不犹豫地脱下T恤去把火扑灭,“他们像一对真正的夫妇一样一起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帮助别人”[9]167,“他们在琢磨该做什么的这些日子,是惬意的,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都爱的第三个人身上”[9]172-173。在无私救助和照顾奎因的过程中,布莱德身体复原了,“她完美的乳房神奇地回来了”[9]166,“布莱德摸着她的耳洞,一边笑一边泪流满面,感到这个小洞回来了”[9]169,“一切都回来了,几乎一切东西,几乎”[9]169。身体的复原,表明布莱德成功走出幽闭空间,重构了更为真实健全的自我。
在空间的流转中,布莱德认识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建立了更真诚的关系,逐渐从一个浅薄的、商业化的女孩成长为一个成熟有担当的女孩,成长为一个充满母性、期待着新生命到来的女人。在这样的过程中,布莱德超越了种族主义、肤色主义和消费主义带来的异化和疏离,避开了垂直性的地域创制,选择水平体系,形成了更为平等、更为开放的场域创制形式,也建立了更为真实的自我,完成了身份的重构,对肤色有了更为深刻合理的认知,正如布克所说,“它只是一种颜色,一种基因特征——不是瑕疵,不是诅咒,不是祝福,也不是罪孽”,“科学上没有种族这种东西,所以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是一种选择”[9]143。
4 结语
小说描写了在种族歧视操纵下,“以黑为美”观念影响下,消费主义支配的空间中,深黑肤色女性布莱德的自我迷失和身份断裂,展示了布莱德如何突破幽闭空间,解除自我防御和疏离感,恢复适应能力,与人建立起更为良性的关系。“每一个人都会带着一个或受伤或悲痛的故事——很久以前生活抛诸于纯洁无辜的自己的一些问题和痛苦……永远都在重写故事,了解情节,猜测主题,创造意义,否定起源。”[9]158莫里森强调黑人女性需要正视过去,走出个人和集体的创伤,建构水平场域创制,在合作与协调中认知自我,建构健全的人格并知晓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