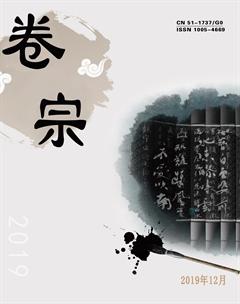略论安顿穷人
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车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昔苏子瞻治杭,以工代赈,今则以风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潘榕皐农部游虎邱冶坊浜诗云:“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真仁者之言也。
——(清)钱泳 《履园丛话·安顿穷人》
关于“穷人”的概念在中国历代社会中多有流变,实难准确定位。要将“安顿穷人”解释清楚,“穷人”又是绕不开的一环。笔者就此条史料中所提及的“穷人”略作梳理概括,以便讨论。钱泳此处提及的穷人包括车夫、舟子、肩挑之辈,也包括身处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之人。可知,就文中所言,穷人的活动或者生存的区域应集中在城镇、所从事的行业以服务业为主。谢国桢在《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 中有:“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驾长又一民也……舁人又一民也……篦头又一民也……修脚又一民也……倡家又一民也……小唱又一民也……优人又一民也……杂剧又一民也……凡此十八民者,不稼不穡……”由此可知,从事服务业是其收入的最主要来源。①除此之外,结合这些人的活动地域以及材料出现的:“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為乞丐,为盗贼”之语推测,这类人应当没有或者少有余财,大抵为无地之民。
其次,这里的“安顿”应该是安排、安置的意思。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它不能与“救济”混为一谈。“救济”多是由政府或者地方的富豪乡绅出面,直接施以钱财物资以供生存之需,“安顿”则更倾向于从政府和被安顿者两方面出发,是依据当时的客观社会条件因势利导,使得穷人可以做到自力更生、解决温饱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救济”行为是单一的,是国家或者有条件者对生存艰难者的一种救护。而“安顿”行为是多方面的,除了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以外,还应该有被安顿者的自我努力。再者,钱泳在此提及的“安顿穷人”并非政府或者社会组织的积极行为,即有意识的对穷人生存状态的改善。而是强调顺应社会发展,对穷人集中参与的行业不强加遏制。总体看来,这种“安顿”行为在内容和形式上比“救济”更加丰富,方式本身更加积极、主动。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社会人员的等级有着严格的划分,最为人所熟知就是“士、农、工、商”四民。除此之外,还存在从事“三教九流”的贱民,史料中所提及的“车夫、舟子、肩挑之辈”,以及“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之人”都在此范围。贱民的概念除了带有政治色彩,还有其道德上的意义。前者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后者更多的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但无论是姚旅②的二十四民之分法,还是钱泳的“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都表明在明清时期,贱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歧视色彩有所下降,其从事的职业逐渐被社会甚至政府所认可,故才能得到陈宏谋的弛禁。由此可知,在明清时期,虽然从事车夫、优伶等人的经济地位仍然很低,但是其带有贬低色彩的“贱民”标签开始松动,社会地位得到初步提高。③
本条史料中的安顿行为并非政府或者社会组织的积极行为是有据可寻的。第一,这些行业的开展是顺应社会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存在的即具有其合理性。材料中提到“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这说明他们从事的职业足以解决其基本的生存问题,可见当时与这些职业相关的商业活动的兴盛。且从陈宏谋的不得不弛禁以及下句中的“怨声载道”可以得知,这些活动不论是对于穷人谋生还是富人的生活都构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才会禁无可禁。《乾隆杭州府志·风俗》卷中提到这样一则故事: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坊,嘉靖间有李氏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远近傲之。旬日之间开五十余所。④这些行业的兴盛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此时期江浙地区经济的活跃发展。这也是车夫、舟子之辈摆脱“贱民”标签,提高社会地位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才会出现对这些职业需求量的增加,正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才促使社会不得不将这些“贱民”纳入社会正常运转的渠道中来,参与“常人”的社会生活。“贱民”色彩的弱化不是带有主动目的的行为,是社会发展形成的必然结果。
通常意义上的安顿或者救济穷人都是从政府或者社会上的慈善组织入手,钱泳却另辟蹊径,将目光放到商业的发展上来,究其原因,窃以为与苏杭地区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此外,雍正朝的“摊丁入亩”使得土地对于人的束缚能力减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且自清中期以后,人口倍增,苏杭一带尤甚。以乾隆十八年为例,据梁方仲先生统计,乾隆十八年,苏州省人口达12,628,987人,可耕田地70,109,995亩,平均每人所占5.46亩。至乾隆三十一年,人口增至65,981,720人,可耕田地23,779,812亩,平均每人所占降至2.77亩。⑤人地矛盾的尖锐,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不得不辗转大的城镇以谋求生存。此外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到了明清时期,江浙一代成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融之所,戏院、酒馆等作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场所自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繁盛,这也为穷人就业提供了场所和机会。故无论是从当时江浙地区的人地关系还是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商养民之法都有其具体的实施环境。就当地社会发展而言,不失为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穷人温饱问题的一剂良方。
注释
①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386页
②姚旅,明万历间莆田县涵江人,上文谢国桢所集的二十四民的划分方法即出自他所作的《枫窗小牍》
③注:这里的提高仅仅是就其道德层面而言的,政治地位并无明显的改变,且仅仅是因为经济生活的需要使得这些人能够弱化其贱民的色彩,真正的社会身份并未得到长足的改善,表现之一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即使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但是其婚姻圈依然受到限制。
④【清】刘沄,[乾隆]《杭州府志 风俗卷》
⑤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94-396页
作者简介
郝录谣(1993-),女,汉族,河北省保定市人,硕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