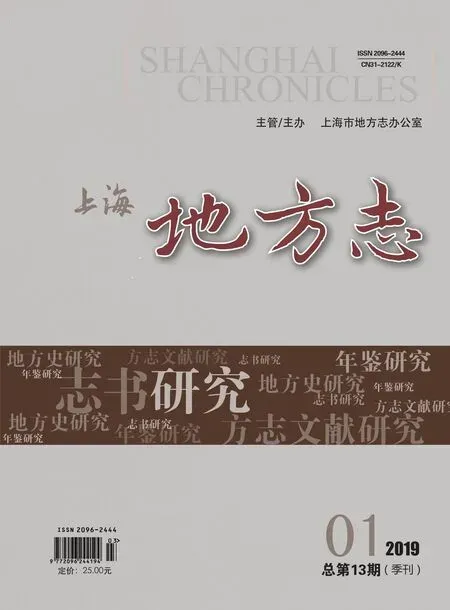《1852年上海年鉴》编译说明
周育民
《1852年上海年鉴与商务指南》(ShanghaiAlmanacfor1852,andCommercialGuide)是《北华捷报》社出版的第一本年鉴,也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
Almanac一词,根据1869年《美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起源于阿拉伯文字,意指“日记”。它不仅有日、月、年,而且标明如日出日落、日食月食等等各种天文现象的时间,但会因各地民情风俗习惯而有不同。这种编纂历书的方法传到拉丁民族,到15世纪时已有刊印。而乔治·立德菲尔得(George E. Littlefield)在《美国考古学会》(AmericanAntiquarianSociety)1914年4月号会刊上发表的《论历书与年鉴》(NotesontheCalendarandtheAlmanac)一文中认为,在中世纪的西欧,历书的编纂权在教会,而年鉴则由民间自由编纂,当时保存最早的年鉴是1646年的,缺了封面和封底,只有8页。简而言之,在英语世界中,Almanac包含Calendar,而内容要比Calendar更加丰富。西方早期的Almanac,要比中国的皇历(黄历、时宪书)的内容要少许多。15世纪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在西方开始流行后,民间刊印历书,并利用历书发行,传播宗教、文化、习俗等知识成为可能,形成了Almanac的编纂形式。至于Almanac(年鉴)最终摆脱历书,成为一种在年度结束之后,将该年度相关资料和信息进行编纂的书籍形式,是在20世纪以后。但即使如此,当代的西方年鉴(Almanac)依然未脱19世纪时刊载大量历史文化等知识的习惯。
西方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是1832年在澳门出版的《英华历书》。以《中国丛报》社(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于1845年初发行的《英华历书》(Anglo-ChineseCalendarfortheYear1845)为例,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国干支纪年表、日月食、西方的宗教节日、中国的节气、日历(配有“历史上的今天”,主要是与西方与中国关系中的事件)以及外国在中国五个通商口岸设立的机构、商号和侨民,加上每月两页的空白记事页,共50页左右。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英华历书》基本上沿袭此体例。
但1846年初由《中国邮报》社(Office of the China Mail)发行的《1846年香港年鉴和指南》(HongKongAlmanacandDirectoryfor1846),含有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的月相表,介绍了香港的地理与气候,其历表中包含有历史事件、宗教节日、日出日落时间、最高最低气温和天气提示等,并附有中英条约、警务规则、机构、商号和外国居民等。因为在历表中含有大量天文气象信息,这是它可以自称Almanac的主要原因,这多少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于“年鉴”与“历书”区别的理解。
北华捷报社编纂《上海年鉴》的最初设想,显然是参照了《香港年鉴》。但是,要在上海的历表中增加大量的天文气象信息,既需要客观条件的支持,同时也需要编纂者付出艰巨的努力。从1848年初开始,天主教会在徐家汇、伦敦布道会在英租界分别设立气象观测站,对上海的气温、风向、雨量等进行观测,逐渐积累起了有关上海气候的一些基本数据,这三年的数据为年鉴提供每月天气的提示打下了基础(到1853年的《上海年鉴》中正式编入了历表)。但是,要在历表中提示每天日出日落的时间,标明月相及近地点、远地点等,需要更多的地理和天文资料作为依据,进行复杂的计算,这是编辑人员无法完成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年鉴是采用徐家汇的耶稣会传教士提供的有关苏州的经纬度进行测算的数据,因为上海与苏州纬度仅相差一度,在时间上误差仅几分钟,编辑时并未作调整。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规律,无论在西方早期的年鉴还是在中国黄历编纂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而月相及近地点、远地点对于潮汐的影响,也是人类据以进行水上和夜间活动的重要信息。在科学数据上,《上海年鉴》的历表编制尚未达到《香港年鉴》的水准,但可以说是发挥了当时西方人在上海的科学资源的最大可能性了。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在历表编纂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上海年鉴》中的历表,充满了浓厚的天主教气息,几乎天主教中所有的节日、纪念日都分别列入了历表当中,这与《香港年鉴》的历表突出世俗性、知识性和地域相关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多少反映了天主教会编纂历书的传统。
北华捷报社限于编辑力量,第一本年鉴的编纂最初只是参照《香港年鉴》的体例,安排了历表,月相和日、月食,口岸和管理规章,有关机构、商业和侨民,进出口关税以及扬子江航行指南等内容,不愿“平庸”的只是增加了历史年代表的内容。[注]见《北华捷报》1851年11月7日刊载的有关广告。但实际出版时,其内容大大超出了原定范围,不得不另增“文献”(Misellany)一编,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三,以至其篇幅在当时外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中首屈一指。
这个编纂方案的改动,造成了本书编辑体例的混乱。《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编年史》上半部分、《徐光启记略》上半部分和《中国的黄历》三篇,已经编好制版,增设“文献”一编后,上两篇的续文再行编入,使得同一文章不合理的分列两编,《中国的黄历》不列入“文献”,也明显不合情理。增加“文献”一编后,原书的书名依旧,又出现了书名不涵盖内容的问题。这些问题,编辑应该清楚,之所以未能调整,估计是因为年鉴出版的时限和改版的成本均有问题。中文译本为读者便利,改正原版重要编辑失误,将《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编年史》和《徐光启记略》正、续篇合编在一起,连同《中国的黄历》均移到“文献”编中。“文献”编中的文章没有归类编排的问题,不作处理,以略存原貌。
耶稣会士雷孝思用拉丁文撰写的《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编年史》,在这本年鉴中,首次被译为英文发表。在这个编年史中,反映了早期耶稣会士希望根据基督宗教以耶稣诞生作为元年,建立统一的耶稣诞生前的世界编年史体系的努力,其主要目标就是将中国史纳入其中。而这需要重新架构中国历史的年代系统。耶稣会士和后来的传教士架构中国的年代系统方法,是根据“今上”年号年次,与当年西历纪年为基准,然后遂次前推,并且参用干支纪年进行校验,如果不出现阴阳历换算和年号重叠的失误或计算错误,这个方法基本上是可靠的。但在古史中,由于缺乏相应年代的干支信息,公元前的历史编年的误差也就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是中国史中尚未解决的难题,在地球上不同空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对接在同一根时间轴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份编年表在问世之后,一度成为基本参照,无论采用或是修改,也在此基础上进行。其另一个解决“中国特色”编年问题的方法是,取消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年号”编年,而以“黄帝”为第一代“皇帝”,依中国正统观念依次排列“皇帝”编号,再按朝代排列“皇帝”编号,即“中国第几代皇帝”、“某朝第几代皇帝”,这种不中不西的编年方式,在早期西方中国史的著作中普遍采用。总而言之,这份年表,其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信息,而在于建立世界历史统一的时间坐标的努力。
《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和《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是两篇有关中国科学发展史的重要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是主要根据中文资料撰写的。前者回顾了从利玛窦以来一直到晚近阮元对于这段历史的评论,基本上完整地构勒了耶稣会士推介欧洲天文学成就的概貌。同时,作者艾约瑟揭露了耶稣会士格于罗马教廷的严禁,对于哥白尼、开普勒的天文学成就刻意回避而造成的一些尴尬,对于耶稣会士认为元代郭守敬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得益于经由蒙古传入的阿拉伯文化,也提出了质疑。后者是对中国古代数学成就进行集体调研后的一篇论文。作者肯定了元代以前中国人在算学方面的重要成就,进入明代,算学处于低潮期,没有任何重要著作问世,因而认为,“17世纪耶稣会士的到来,他们新近的、完善的论理在中国科学处于历史上最不利的时期取得了优势。”作者们考察了元代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在数学上的交流情况,但认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中国人应该所获不多。作者对于西方的一些作者贬低中国人在算学方面能力的言词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们列举了中国的数字符号和因归运算方法,不定数的解法(大衍术),以及向数理分析大步迈进的天元术,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早五个世纪就会运用多项式方程运算了。开方术也是由中国人独立发明的。作者甚至与当时在杭州任官的数学家戴煦有过接触,知道他已经找到了求得对数的新方法。作者认为,如果中国人以更大自由地与西方交流,将会促进双方的取长补短,也会激发他们的科学研究精神。这两篇学术论文,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很值得进行研究和评估。
《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和《南京的旅行》是两篇游记和导游性质的文章。上海开埠初期,上海当局与英方有过外国人离开租界往返不得超过24小时的规定,严格地说,是中方规定外国人不准在上海及租界以外地方过夜。但违犯此项约定的情况不时发生。1848年“青浦教案”发生以后,中英关系高度紧张,事态平息之后,此项规定实际上无形搁置。外国侨民远足通商口岸以外的附近地区,虽然化装成中国人的样子,穿长衫马褂,戴个假辫子,但遮不住蓝眼睛、高鼻梁,不过地方官役人等大都眼开眼闭罢了。第一篇是介绍由上海到苏州的路线和景点,第二篇是介绍由苏州到南京的路线和景点,可以说是姊妹篇,留下了沿途许多村庄、城镇、河湖上的人们生活、生产、运输、交易和民情风俗的记录,有些重要的景物如南京的琉璃塔,今天已经荡然,这些文字也是它们在消逝前最后的宝贵记载之一。
《1852年上海年鉴》保留了开埠初期上海历史的许多重要信息。它所提供的《上海口岸1840-1850年气候观测均值一览表》和《气象测量记录摘要》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连续的、系统的气象统计史料。年鉴还提供了开埠以来外国侨民在上海租界的人口统计、机构行号等资料,在这些资料中,外国侨民在上海的职业、身份和地位清晰可辨。年鉴中有关上海港区的水文资料,主要是为便利外国船只进港、出口使用。其中有关上海港区的潮水表,应该是由江海关提供的,只是将时辰改为钟点而已。而《扬子江航行须知》一文,则清晰地提示了外国船只如何由嵊泗列岛进入长江口,然后进入黄浦江所须知的操作要点。它反映了嵊泗列岛作为帆船时代欧美船只前来长江流域国际航运中继站的重要地位。作为江海关理船厅的前身,上海外港区的“河泊司”是个非常奇特的机构。它是由英、法、美三国领事要求上海道台于1851年9月设立的管理外国船只停泊区的专门机构,首任“河泊司”为英国人贝利斯(Nicholas Baylies),从《五口外国居民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河泊司”有个“顺和”的行号,可见是个由外侨承办行政委托管理事务的独立民营机构,外国人在插手中国海关关税征收事务之前,早已插手港口事务了。在“文献”编中,除了有关上海地区的黄历、婚俗、灯会之外,《徐光启记略》是篇上海人物的长篇文章。有关徐光启的生平,国内已有年谱、传记等研究专著,这篇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记载了作者亲自考察过的一些遗迹,包括城内徐光启的故居与祠堂、徐光启晚年居住过的“双园”以及徐家汇徐家老宅的情况,并根据采访和地方志书叙述了徐家后代在上海地区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些铭文、碑刻、墓葬,上海地方史书缺载,这些英文史料多少可以弥补一些缺憾。
虽然19世纪50年代之前的上海地方志书中有不少地图刊载,但于上海县城之外,多为河道、分界等示意图,缺乏许多必要的地理标识。外国人绘制的上海地图,目前能看到的是1847年《中国丛报》所刊载的一份示意图,它虽涵盖了从上海县城、英法租界和虹口的一部分,但实在过于简略,很少研究价值。年鉴所刊载的上海地图,是当时西方人绘制的最详细的一份。北至吴淞江虹口到曹家渡一线,南至白莲泾到龙华一线,东至黄浦江陆家嘴,西至徐家汇、法华镇,包括了境内重要的河道、步道、桥梁、寺庙以及其他地理信息,而这一地区除县城和租界以外的地区,之前的地图都没有这样清晰的标识。这些地名均分别用中英文标注,也解决了中国读者阅读早期外人对于上海叙述的许多困惑。虽然,这份地图的文字说明存在许多问题,但地图本身无疑是上海史研究中最具价值的史料之一。
博学多才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医生玛高温向年鉴提供的两篇文章堪称佳作。《乌桕的用途及中国白蜡的笔记》根据中国的文献记载和考察,澄清了早期西方人关于中国白蜡园艺和制作的许多误区。这多少可以提示当今的我们,得留意些人类“照明史”的研究。他的《宁波的海盗、民变和家法》,则是宁波开埠初期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宁波地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前,相关中文史料十分缺乏,在19世纪50年代初,除了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之外,无论当地官员还是宁波士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献和笔记史料,即使后来的地方志有所记载,大多语焉不详,缺漏甚多。因此,玛高温对四五十年代之交宁波当地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记载,其史料价值也就尤为突出了。在他的笔下,广东海盗和葡萄牙人的“绿壳船”互相勾结,坑害海商,骚扰沿海;地方官瞒盰贪渎,疲于应付盗乱、盐变和教变的窘态;以及天主教煽动教民图占舟山寺庙的行径等等,都有十分细致的叙述和揭露,从一个局部展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的中国社会动荡。他对于天主教传教方针的尖锐批评,对于我们理解后来反洋教运动的频发,也不无启示。与传教活动有关的另一篇文章,是前往琉球传教的德伯令呼吁英美国家直接出面干涉日本禁止基督教传播政策的报告。
《土耳其的鸦片吸食》,叙述了土耳其当时拉克酒的消费量提高、鸦片吸食因年轻一代的时尚变迁而止步的现象。嗜好食品的消费与社会时尚变迁、代际更替等等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一文,展现了澳洲殖民地开发初期,悉尼作为一个国际大港市兴起的早期格局。作者对于悉尼未来格局的展望,为它后来的发展所完全印证,因此,从作者流畅的文笔之下,我们更应该注意他对城市功能、城市结构、城市建筑和城市肌理的深刻思考。
《1853年上海年鉴》的编辑体例,本无“文献”编,严格地说,只能称为《1853年上海年鉴及商务指南》,但受到上年年鉴编例的影响,编者没有根据内容及时调整名称,仍定名为《1853年上海年鉴与文编》。与1852年的比较,除了相关统计数据和规章有所变动之外,增加了各地邮费资率、美国政府方面有关贸易税收管理的文件、上海租地章程和上海口岸租地人表。被称为“上海(租界)宪法”的《上海租地章程》,中译本直接采用了英国外交部档案收藏的中文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