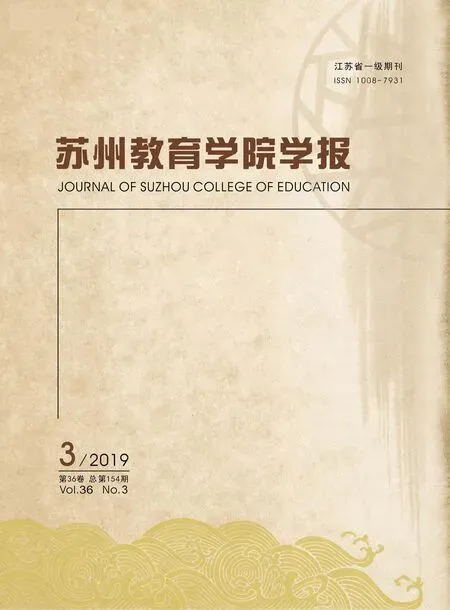还原莎士比亚戏剧的性色彩
——以傅译《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熊 辉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读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阅读和了解主要依靠曹未风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等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①曹未风从1931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从1942年到1944年间,其所译的11种戏剧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名,先后在贵阳文通书局出版;1946年,又以《曹译莎士比亚全集》为名,在上海文化合作公司出版10种戏剧。朱生豪从1935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至1944年逝世为止,共译出31 种戏剧,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又约请专家校订了原译文,并补译完善余下的几种,于1978年出版了11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从1930年开始“凭一己之力”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其所译40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于1967年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发行,中英对照版本于2001年在大陆出版。到了21世纪,由于语言表达习惯的变迁、读者对莎剧研究资料的了解以及部分人对莎剧原文的阅读,使当代读者对既有译本产生了一些质疑和批判,新的莎剧译本呼之欲出。傅光明先生重新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不仅顺应了时代诉求,而且从他已经出版的几部悲剧译作来看,又是对过往翻译之不足的极大完善,在中文语境中再现了莎剧的经典性。本文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从“性”入手,论述傅译本对莎剧经典地位和艺术品格的还原,据此说明傅光明先生的《新译莎士比亚全集》何以会成为莎士比亚翻译史上的优秀译本。
一
傅光明先生新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与已有的莎剧译本相比,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对原作中的“性”色彩作了全面的翻译和充分的说明。译者以英文注释本和大量的莎剧研究资料为参考,将莎剧中的性色彩第一次“原汁原味”地引荐给中国读者,从而打破了莎剧“洁净本”对“无性的莎士比亚”的塑造,可以说是莎士比亚翻译史上的历史性突破。
傅光明重译莎剧的初衷是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情感和语言风格,因此遇上与“性”相关的内容也毫不避讳,而是将之在译文中作了本真的呈现。作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主要的娱乐和消遣方式,戏剧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迎合普通市民的审美标准和娱乐需求,加上剧中人物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因此莎士比亚写剧时使用的语言极为丰富多彩。傅光明先生深谙莎剧的语言魅力,理解剧作受众的审美层次,对当时的英国剧场文化了如指掌,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不刻意回避莎剧中隐晦的性描写,在有些地方还会以注释的形式来提醒读者与性有关的暗示。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凯普莱特的两个仆人桑普森和格里高利说道:“我要把蒙塔古家的男人从墙边推开,把他家的女人都挤到墙边去。”因为是“下人”之间的对话,就比较容易与生理的性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傅译本的注释说明“挤到墙边去”暗指“干性事”。[1]8
罗密欧与好友茂丘西奥的对话同样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作为年轻人,他们对性欲有强烈的渴望,说话时总能很自然地转移到“性”的层面,或明或暗地指向性话题。在第一幕第四场中,茂丘西奥说:“爱原本是温柔的情物,你却把它变成拖你下沉的负担——这重压对它未免太残忍了。”罗密欧回答道:“爱是一件温柔的情物吗?它太粗鄙、太野蛮、太狂暴了,像荆棘一样刺痛人。”如果不是刻意朝着“性”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很难解读出此处暗含的性元素,但通过傅光明先生译本中的注释,我们可以自然地领会其中的象征意味。实际上,这两句台词表明茂丘西奥和罗密欧都在说话的时候“做性的比喻”,前者的意思是“你要让情人感觉到身体的重量,才能给她带来快感;如果你在性的时候失去了功能,就会让你的情人失望”,如果说茂丘西奥所说的“情物”暗指女性的性器官,那罗密欧眼中的“情物”则是指男性的性器官,“暗示男性在性行为中是粗鲁的、狂暴的”。[1]34
莎剧中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充满了性想象,为了充分显示莎翁富有“激情”的语言特征,傅光明的译文忠实再现了原作的性色彩,并通过注释使读者充分理解原文中隐含的性表达。茂丘西奥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说话最“低俗”和“色情”的角色,如在第二幕第一场中,班福里奥和茂丘西奥两个年轻人谈论罗密欧何去何从的时候,茂丘西奥的话语中总是洋溢着性色彩,他以罗密欧暗恋的罗瑟琳起誓:“我要以罗瑟琳明亮的大眼睛,以她的高额头和猩红的双唇,以她灵巧的双脚,笔直的小腿,颤动的大腿,以及毗连大腿的部位,我以她的所有这些地方起誓,叫他马上现出原形!”傅译本的注释专门解释说:“茂丘西奥在此故意暗指隐私的性部位。”[1]58接着,茂丘西奥又以“情人的魔圈”来暗指女性的性器官,以“不无神奇的小精灵”来暗指男性的性器官,这些均属于年轻人对话中常采用的“暗语”。如果傅光明不对此加以解释说明,估计很多读者会忽略茂丘西奥话语中的性意味。茂丘西奥猜测罗密欧“现在一定是坐在一棵枇杷树下,真希望他的情人就是姑娘们私下开玩笑把那果子叫骚货的枇杷。——啊,罗密欧,希望她就是,啊,希望她是那烂熟得开了口儿的枇杷,而你就是那又长又硬的大青梨”[1]59。在这段充满性幻想的话语中,朱生豪先生的译文略为含蓄,与傅译本最大的区别是喻体的不同——傅光明的译文将女性的性器官比作“枇杷”,将男性的性器官比作“大青梨”;而朱生豪则将之比作“蜜桃”和“青香蕉”。
莎士比亚原文中的“medlar”常被翻译成“欧楂”,也有人译作“枇杷”,这种长得像屁股的果子熟透后,顶部会出现又深又长的裂缝,故在英语俚语中指女性的阴部。此外,由于“medlar”与“meddler”谐音,而后者有“私通者”之意,这进一步将“枇杷”与性联系在一起,比较符合茂丘西奥的想法。而朱生豪将之翻译成“蜜桃”,不仅是对“medlar”的误译,也是对该词在英语世界中蕴含的性文化的舍弃。朱生豪先生对“Poperin pear”的翻译也值得商榷,“Poperin”是欧洲的一个地名,这里所产的梨子长得很像男性的阳物,将之翻译成“青香蕉”反而丢失了原文对性器官的暗喻,所以傅光明直接翻译成“大青梨”,并用注释加以说明,既忠实于原文,又能将莎剧语言的丰富性转化到汉语表达中来,自然也就兼顾了翻译文本的内容和风格,当然是值得信赖的译文。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戏剧可谓“性”趣盎然,茂丘西奥、班福里奥以及罗密欧之间的对话被青春期的性冲动所左右。在第二幕第四场中,茂丘西奥挖苦罗密欧时说道:“唉,可怜的罗密欧,他已经死了,他被那苍白脸、浪荡女的黑眼睛杀死;一首情歌刺穿了他的耳鼓;他被瞎眼的丘比特那小子用钝头箭射中了心脏的靶心,他还打得过提尔伯特吗?”[1]76-77朱生豪将“浪荡女的黑眼睛”译为“白女人的黑眼睛”,不管是谁的翻译,都会引起读者的疑问,为什么白人会长着“黑眼睛”呢?只有将眼睛的颜色和形状与罗瑟琳的性器官联系起来,读者方才明白为什么莎士比亚会将白人幽蓝的眼睛描述成黑色。而“钝头箭”和“靶心”则暗指罗密欧的性器官。经傅译本的引导,我们就会理解茂丘西奥的言下之意:罗密欧和罗瑟琳发生了性关系,耗费了他的精力和元气,所以他难以打败提尔伯特。当班福里奥高喊“罗密欧来了”的时候,茂丘西奥是这样描述他的:“要是把鱼子去掉,他就像一条干鲱鱼了。肉啊,肉啊,你怎么变成一条干瘪的鱼了!”[1]79前半句话的原文是“Without his roe,like a dried herring.”朱生豪先生的译文是:“瞧他孤零零的神气,倒像一条风干的咸鱼。”[2]26此译文与傅译相比,省略了原文中的关键词“roe”(鱼卵),而另一个关键词“herring”(鲱鱼)也被错误地翻译成了“咸鱼”。除字面意义上的错漏之外,朱译本给阅读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于它对原文语言风格的抹杀,弱化了年轻人偏好色情的谈话。因为在英语中,“roe”的字面义是“鱼卵、鱼子”,但其衍生义却是“精液”,此语意在表达如果罗密欧与情人发生性关系,他的精液就会被榨干,人就会变得疲软而干瘪;而他连着说两遍“肉啊”则是暗指罗密欧的性器官,表明他在性的压榨下,性器官早已失去了活力而变得“干瘪”。后面他又对罗密欧说:“当你遇到那种情况,只能弯腰驼背。”[1]80-81“那种情况”是茂丘西奥对“性事”的暗示,而“弯腰驼背”则是指性爱时的身体姿势或性事过度而疲惫不堪的样子。
作为年轻人,善良而单纯的罗密欧有时也会使用“性”的双关语,他曾讽刺茂丘西奥“除了做笨鹅,你什么事也追不上我”[1]82。在英语文化中,“goose”(鹅)暗指“妓女”,罗密欧实际上是在讽刺茂丘西奥只会找妓女取乐,没有什么比他强。罗密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苦道:“果酱配甜美的鹅,味道岂不更好?”[1]82傅光明先生认为这句话除了来自英语谚语“吃肉香,蘸酸浆”(sweet meat must have sour sauce)外,也与前面“鹅”指“妓女”有关,故此处的“果酱”应与性爱时的“精液”联系起来。茂丘西奥反击罗密欧的挖苦时,也必然是以其人之“性”还治其人之身,继续用性色彩浓厚的话说道:“啊!这时候你的脑子又变成了一块羔羊皮,本来只有一寸窄,你却能扯到四十五寸宽。”[1]82朱生豪先生的“洁净”译文为:“啊,妙语横生,越吹越多!”[2]27在傅光明先生看来,这句话是借用罗密欧的性器官来表明他们的谈话越扯越远。紧接着,茂丘西奥进一步拿罗密欧的性器官来嘲笑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情人实在像个大傻瓜,就会伸着舌头上蹿下跳地想把那根棍子藏到一个洞里。”[1]82-83这里的“棍子”和“洞”分别比喻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茂丘西奥对之加以“活用”,能很好地起到讽刺罗密欧的效果。而后,他们的谈话依然没有离开“性”。班福里奥让茂丘西奥停下来不要说话,后者说:“我的故事刚到一半,你想让我停下来?”班福里奥回答道:“否则,你又要把故事搞大。”[1]83原文中“tale”是“故事”之意,但在读音上却与“tail”(尾巴)相似,而“尾巴”在俚语中同样指男性的性器官,因此两人是在借男性的性器官展开讨论。相较于朱译本来说,傅译本通过注释使读者领会到了说话人的言外之意,莎剧语言的丰富性、通俗性乃至市民化等审美特征也会给读者带来愉悦感。
实际上,莎士比亚用这些富含性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年轻人之间充满谐趣的对话,体现出莎翁灵活多变的语言风格,对吸引观众并抬高票房收入也不无好处。
二
下层人的口头语言和日常表达中的市侩气不仅符合其真实生活,而且可以激发观众的兴致。倘若译文有意忽视莎士比亚“别有用心”的表达方式,而将之译成平淡无奇的常用语言,既是对原文内容的歪曲,也是对原文语言风格和人物个性的扼杀。
朱丽叶的奶妈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又一位“低俗”的人,她话语中的“性”意味比较符合她的社会身份。当奶妈遇到茂丘西奥、班福里奥和罗密欧几个年轻人的时候,一场“青春期”与“底层人”的对话便拉开了帷幕。在第二幕第四场中,茂丘西奥与奶妈的对话充满了诙谐与嘲讽,当奶妈告诉罗密欧有秘密要告诉他时,班福里奥说“她要请他去吃晚饭”,而茂丘西奥则说:“一只老鸨,一个老鸨,一个老鸨!啊哈!”[1]85傅译本对此有详细的解读:“晚饭”是对“性事”的委婉称谓,而“bawd”本身就有“妓院女老板”或“妓女”的意思。这两个人的对话联系在一起,推导出的意思是:班福里奥说奶妈要拉罗密欧去发生性关系,因而茂丘西奥说奶妈是老鸨。于是又引出茂丘西奥说来者“不是野兔,先生;除非是四旬斋无肉斋饼里的野兔,吃完以前就变味、发霉”[1]85。这是茂丘西奥进一步使用带有“性色彩”的语言来嘲讽奶妈。原文中“hare”有“野兔”的意思,它与“hoar”(发霉)在英语俚语中均指“妓女”,朱生豪和梁实秋均将其按照中文俚语的对应词翻译为“野鸡”,保留了原作的意义,却丢失了原文语言的文化内涵。因为“野鸡”在英语世界没有“妓女”的引申义,而“发霉”除了含有“妓女”之意外,也可理解成性泛滥染上梅毒之后引发的女性下体的溃烂。最后在与奶妈告别的时候,茂丘西奥说:“再见,老小姐,再见。‘小姐,小姐,小姐’。”[1]86朱生豪的译本为:“再见,老太太。再见,我的好姑娘。”[2]28傅译本接连唱出“小姐”,更好地对应了原文,也与当时英国流行的古老歌谣《贞洁的苏珊娜》(Chaste Susanna)相对应,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小姐,小姐,/虔敬度好日,/我们如何知?”(Lady,Lady,/ Why should we not of her learn thus / To live godly?)面对下等人,两个年轻人的话语似乎有些“过头”,并且还唱起“老野兔”的歌来取笑奶妈,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捉弄下人之上。
当然,奶妈使用“性色彩”语言的功夫并不比年轻人差,她与青年男子茂丘西奥、班福里奥一样,是莎士比亚笔下语言最生活化、“低俗化”且最生动的代表性人物,傅译本较为全面地将这个女性的丰富性呈现出来,可以说是对奶妈所代表的那个“低俗”的社会阶层、那个性欲旺盛且无所顾忌的中年妇女群像的生动刻画。她在“下流”的茂丘西奥和班福里奥离开后,对身边的罗密欧和彼得说:“他要是说了什么调戏我的话,我会让他服软的;像他这样的,甚至比他更粗壮、好色的无赖,来二十个我也能对付。”[1]86朱生豪的译本完全抛弃了奶妈带有“性冲动”的语言特色,单纯将之翻译成外在的打斗:“要是他对我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尽管他力气再大一点,我也要给他一顿教训;这种家伙二十个我都对付得了。”[2]28如此一来,原文中“take him down”暗含的使茂丘西奥勃起的性器官变软,从而暗示“打败”他的意味就消失了;同时“jacks”这个本意为“流氓、无赖”的词所指代的性器官也不见了。朱译本将一群年轻人和一个文化层次较低的奶妈的“色情”对话翻译得无比“洁净”,使剧中人物的语言在无形中变得平淡无奇,剧本毫无生动活泼的审美特点。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讲,语言失去了性色彩,不利于体现奶妈这个阶层的人物的真实生活和说话方式,也不利于奶妈与两个年轻人站在同一个“性”的层次上对话,使读者认为奶妈的理解能力和智商水平有限,面对几个年轻人轮番轰炸的语言暴力,居然浑然不觉,还仅仅停留在语言争斗的层面。
傅译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奶妈这个角色的“底层”特点,也许她并不是要刻意地用具有性色彩的语言来挑逗罗密欧或其他年轻人,但由于她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日常接触到的下层人总是有意无意地采用俚俗的语言,导致她这样的说话方式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社会阶层和身份的语言标识。奶妈与未婚女性朱丽叶的对话延续了同样的风格。在第二幕第五场中,奶妈送完信后回去见朱丽叶,故意不告诉她罗密欧的反应而惹急了朱丽叶,尔后她说道:“你就这么耐不住吗?”[1]92朱译本在此理解为奶妈批评朱丽叶性子很急,其实是对原文“Are you so hot”的误解,“有编本以为,奶妈此语或暗示朱丽叶有贪欲之意”。[1]92休息片刻后,奶妈吩咐道:“你快去教堂吧,我还得到另一个地方去取绳梯,等天一黑,你的爱人就可以靠着它爬进你的鸟巢。为了你的快活,我费心操劳,但很快,今夜你将负重辛劳。”[1]93此处“鸟巢”当然指朱丽叶的房间,但也有编本认为“bird(鸟)指青春女子,nest(巢)指女人的性器官”。奶妈话中的“你的快活”与性事相连,“负重辛劳”则是“性暗示语,指承受罗密欧身体的重量”。[1]93在罗密欧杀人后陷入痛苦绝望之时,奶奶在修道院见到他仍然不忘说话的“性”趣味:“啊!跟我家小姐的情形一模一样!……站起来,站起来,如果你是个男人,就起来;为了朱丽叶,为了她,你也要起来,立起来;你为何会这样呻吟?”[1]127原文中“rise and stand”有“立起来”和“站起来”的意思,但朱生豪的译本中却忽视了“rise”,而且最后使用的是“伤心”而不是“呻吟”,傅译本更符合原文字面意义,同时体现出奶妈话语中的性色彩。根据傅译本中的注释,奶妈说“跟我家小姐的情形一模一样”,意味着罗密欧像朱丽叶一样“在想着两人的初夜”;“立起来”或“站起来”则是“乳母无意识的性语暗示”;而“呻吟……仍是乳母的性语暗示”,指做爱时发出的声音。
第三幕第五场中,奶妈在面对朱丽叶将被迫结婚的不幸消息时,依然用具有“性”色彩的语言和朱丽叶进行交谈:“你的第一个丈夫也死了;虽说还活在世上,也跟死了差不多,你根本无法享用他。”[1]149原文中“use”意为“利用、使用”,因此朱生豪将其翻译为罗密欧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但傅译本中的“享用”与“use”本意更接近,也符合上下文语境,同时也翻译出了奶妈的“性暗示语”。[1]149在第四幕第五场中,奶妈上楼去叫醒朱丽叶,让她收拾行装准备出嫁的时候,朱丽叶已经昏迷,但不明真相的她仍说道:“等到了今天晚上,帕里斯伯爵一定会奋起神勇,你休想得到片刻的安息。……那好吧,让伯爵自己上床来弄你,我保证你就会吓得跳起来了。”[1]172这是奶妈对朱丽叶与帕里斯结婚后必然面临的婚姻生活所作出的描述,也许对她这个阶层的人来说,她所能想到的婚后生活就是这些与“性”有关的家庭生活,此外便没有其他的追求了。
三
需要注意的是,莎剧中的“性”只是停留在语言层面,并无赤裸的性爱行为和场景描写,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在剧中安排“性”的目的不是为了“性”本身,而是指向与性无关的意义表达。故而从这个角度来讲,与其说莎士比亚作品中充满了“性”,毋宁说其作品的语言披上了性色彩,直接显露出的是说话人的语言方式,显示出莎士比亚高超的语言艺术。
“性”语言与说话者的年龄、身份、说话对象以及特殊环境有关,可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内心的想法并发掘他们不为人知的面孔。在第四幕第四场中,凯普莱特夫妇在朱丽叶和帕里斯成婚的头天晚上毫无睡意,夫妇俩私下的对话也采用了充满性色彩的语言。当奶妈让凯普莱特早点回房休息时,后者答道:“哼,以前为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也曾整夜不睡,从来没病过。”夫人听了此话,立马挖苦道:“是啊,年轻时你一直是一只惯于偷腥的夜猫;但现在,我总是睁着一只眼不让你再干那体力活了。”[1]169在夫妇二人的对话中,“无关紧要的事”“偷腥的夜猫”“体力活”等均暗示男女之间的性事。在整个剧本中,凯普莱特夫妇的台词中仅有此处具有性色彩,虽然凯普莱特在骂朱丽叶的时候语言毒辣,但始终呈现出显赫家族“掌门人”的严肃形象。此处性色彩语言的使用,一方面表明旧时大家族的“家长”道貌岸然的形象,私底下他们和普通市民一样,说出来的话也具有俚俗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他们私底下的对话,揭露出旧时道德的维护者和严格要求子女遵从社会礼仪的长者,其实并不是洁身自好的君子,他们在青春年少、年轻气盛的时候,也有率性而为的“劣迹”,他们的私生活并不比现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检点”。
傅光明先生的翻译对莎剧中具有性色彩的对话从不避讳,而是将之真实地翻译给中国读者,使读者能够领略到那个时代不同年龄段或不同阶层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方式,以及更为丰富的俚语、比喻、象征或谐音词等。如在第一幕第三场中,奶妈在回忆朱丽叶小时候的情况时,转述过她丈夫的一句话,傅光明先生译为“你是向前扑倒的吗?等你更懂事的时候,就会向后躺倒了”[1]29,而朱生豪先生则将后半句意译成被丈夫压倒在床上。比较而言,朱译本表达意义的方式很直接,但在字面意义上,尤其是与原文形式和意义的对等而言,傅译本似乎更为准确,“向前扑倒”和“向后躺倒”不仅体现出语言的对称性,也能体现奶妈机智而幽默地运用日常语言来表达“性”意识的能力。如果直接将“向后躺倒”译作被丈夫压在床上,不仅与原文字面意义相差太远,而且把奶妈这样的下层人的语言方式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给“屏蔽”了。
又比如第一幕第四场,茂丘西奥在描述麦布仙后的时候说:“就是这邪恶的妖婆,在姑娘们仰面睡觉的时候,压在她们身上,教她们如何受孕,成为能生善养的妇人。”罗密欧听了不耐烦地呵斥道:“别说了,别说了,茂丘西奥,别说了!一谈到性你就来了兴致。”[1]38朱生豪的翻译很简单:“得啦,得啦,迈丘西奥,别说啦!你全然在那儿痴人说梦。”[2]14可见,朱译本没有罗密欧对茂丘西奥谈性的指责,只是让他停止说话;而傅译本将两个年轻人关于“性”的对话翻译出来,读者也明白了罗密欧阻止茂丘西奥说话的理由。
虽然茂丘西奥等年轻人的对话充满了性色彩,但他们也可以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因而读者不会认为他们是下流之辈。比如在第二幕第四场中,茂丘西奥虽然极尽所能地将谈话内容与“性”扯上关系,但同时也能对历史上的著名诗人如数家珍,他在赞美罗密欧的新情人朱丽叶时说:“他现在又开始在脑子里搜寻彼特拉克的爱情诗句了;可要是跟他的这位小姐比起来,劳拉也不过是一个厨房里烧火做饭的丫头;——但她运气好,有个更好的情人写诗歌颂她;——狄多也就是个衣衫褴褛的懒散妇人;克利奥帕特拉只是个吉普赛女郎;海伦和希罗都是卑贱的娼妓;即便那长着一双灰眼睛的提斯比,也根本算不上什么。”[1]79-80在这句话中,茂丘西奥一连列举了多位诗人和为爱而死的美女——彼特拉克是伊丽莎白时代写爱情诗的典范,他为自己的真爱劳拉写诗;狄多是传说中的迦太基女王,因所爱的英雄埃涅阿斯而自焚;克利奥帕特拉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女王,因王国沦陷和真爱安东尼的死而自杀;海伦是一位绝世美女,她诱发了特洛伊战争,但却甘愿抛弃一切,与真爱同赴战场;希罗是希腊神话中的漂亮女祭司,她因自己的真爱利安得的溺水身亡而跳塔自尽;提斯比是希腊神话中与皮拉摩斯相恋的情侣,但却因情人的意外自杀而随之身亡。这些在历史上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典型形象,“低俗”的茂丘西奥却能逐一列举出来,表明他是一个谙熟历史和文化的“有识”之士,并非满脑子性幻想的浅薄之人。
具有性色彩的语言在莎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并不停留在性的层面,或者说莎翁让剧中人物说话“低俗”的旨趣并不在性,而是为了讲好故事。傅光明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出版之后,莎剧在中国不再是任人删减的“洁净本”,而有了忠于原著的全译本,必将开启莎翁及其作品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新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