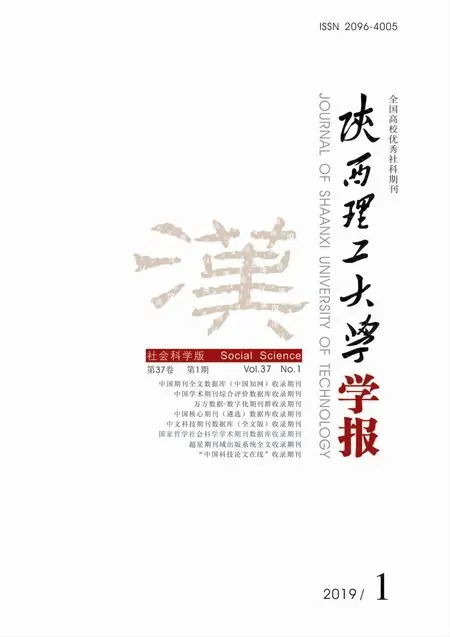文同汉中山水诗呈现的审美视界
徐向阳, 卓敏敏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文同(1018—1079),字与可,梓州永泰县(今四川盐亭永泰)人,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正月二十一日子时,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又因系西汉蜀守文翁之后,又称石室先生,以诗、文和画闻名后世。文同擅画墨竹,是北宋著名的文人画家,逝世后诗名渐为画名所淹。在画史中,文同历来被后人尊为文人墨竹宗师。文同风流倜傥,诗文书画俱佳,司马光赞美其“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1]10198,表弟苏轼对其也尤为敬重。陶渊明开创的山水田园诗派,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作风格,对仕宦汉中的文同均有较大影响,文同寄情山水,又酷爱画竹,因此将诗画结合的创作风格推向了新的高度,而少年以及青年时期儒家致仕君上的政治理想,使其诗歌作品呈现出仕宦幽隐与铁肩道义的多重声部。
一、 文同汉中山水诗所见的自然风貌
文同一生大多在州郡为官,先后任职于邛州、静难军、汉州、普州、陵州、兴元府、洋州,担任过推官、判官、知府、知州等职,在去湖州(浙江嘉兴)赴任途中卒,世称文湖州。文同晚年仕宦汉中(知兴元府与洋州),此期间是其一生重要的仕宦和诗文绘画创作阶段,文同于熙宁六年(1073)三月来汉中知兴元府,至熙宁十年(1077)卸任知洋州,共约四年半时间。此正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变法轰轰烈烈,兴元府又是北宋利州路治所之地,属汉、唐以来政治和军事重镇,又因地处秦、蜀交通咽喉,以显赫的战略地位为各代中央王朝所重视。汉中自然与人文地理条件较陵州好,加之文同知兴元府属自请自荐且得到皇帝应允,他对于此项任命喜出望外,《丹渊集》载“伏蒙圣慈,以臣陈乞,特除授臣知兴元府,仍放朝辞者……幸至是哉……亟下武都之书……顾惟多士,有愿往而不能……但竭愚衷,敢诬天鉴。臣无任感神荷圣,忭蹈欣跃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2]911。此处所引文同回复进奏院的谢表属于官府公文,但字里行间对皇帝准许知兴元府充满感恩之情。另一处回复友人的信札《回汉州郎中启》对自己东赴汉中的喜悦之情表达得更是淋漓尽致,“奏牍既行,秪虞于重谴,诏纶忽下,寻被于鸿恩。以李固解绶之乡,为阮咸出麾之地,求虽有自,得岂无缘?”[2]912这些都表明文同对京官无动于衷,自请自荐到汉中为官,其中缘由很可能与熙宁年间新法推行,政治出现剧烈变革,文同为了不被卷入政治斗争,才自请赴远离京城的梁、洋为官。而此期的仕宦经历,也促成文同将自然山水作为他诗、画和文的关注对象,寄情山水。文同少年时也曾有济世之志,希望通过读书做官实现儒家大济苍生的理想,成年之后为避免党争,只能将“兼济天下”作为终生追求的理想,而在内心留恋山水,保持精神世界的独立、自由和超脱。
文同将视角投放在自然山水之中,与他出生地梓州永泰县境内有风景秀丽的青城山和峨眉山有关,成长环境的熏陶,也使得他以自然山水为歌咏对象。等到成年后对新法的不满,做地方官时又为了回避政治话题,远离党争,于是山水自然,花鸟草木成为他关注和抒写的主要对象。这些促成了文同自然观的形成,而作家自然观的形成其实就属于哲学范畴。北宋本来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高涨期,处于这种文化环境中的文同,其诗歌中所呈现的自然观必然蕴含着北宋时期的时代精神,也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内涵,其中之一便是将自然风物作为描写的对象,试图远离政治,文同知兴元府和知洋州期间的诗作,即是北宋哲学思想发展很好的例证。
北宋熙宁年间文同先后知洋州与兴元府(今汉中)知府。任职期间,文同能体恤百姓,革除民间杂徭等积弊,解民疾苦。他在洋州重视教育等公益事业,修建园林亭榭等景观。他任内先兴办学校,“乞赐详酌,特置学官”[2]932。之后还劝勉当地百姓送子弟上学,还常在公事闲暇之时到学校亲自训导,使得此后汉中子弟求学者渐多。“自熙宁三年到任,乃权府学教授,行能为之讲说经艺,教其对答大义,诱掖后进,孜孜不倦,日授月试,皆有余绪”[2]932,使“府县子弟翕然尽愿入学,至于外郡士人闻之,间亦渐有来者”[2]932。此外,文同目睹汉中府学不振,于是亲拟奏折《奏为乞置兴元府学教授状》,上书北宋朝廷,强烈建议中央政府设置兴元府府学教授一职。文同爱民如子,诗中常念百姓疾苦,“虽名两千石,敢自辝碌碌……刻薄素所憎,忍复用刑狱”[2]117。 熙宁八年,已58岁的文同罢兴元府职守,归永泰故里度假,秋末赴知洋州任。文同在兴元府和洋州共创作诗歌60首,其中汉中府18首、洋州42首。论及的自然风物有雨、云霞、云霄、烟峦、霜林、云雾、风、山峰、波浪、山岩、横麑、云霄、日、山麓、云烟、雷、松影、雾、泉声、池塘、潭、雨、雪、烟、苔、石、湖波、风、霭、溪、酒、晚霞、晨曦、露、苔藓、星辰、断石、叶、巨木、高藤、沙、月、寒影、暑气。论及植物以竹为主,其中咏竹的诗篇达24首,兼及松、梅、菊、芙蓉、桑葚、乱絮、楠木、松子、荷花、梧桐、莼菜、苗、蟠桃、桂树、乔木、桐叶、寒柏、青松。论及的动物和禽鸟有鼠、鸡豚、燕、猿猱、鹤、鹜、雁、马、龙、蛇、虎、豹、蝉、蜂、山虫、蝙蝠、鱼、凫、鸠、鹭鸶等。
汉中丰富的自然风物,以及文同内心深沉的“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在诗歌中所表现的对自然生命的感悟及个体生命审美存在的方式对后人无疑有着恒久的魅力,充满无穷的生命哲思的启迪。竹子是汉中自然风物中极其平常的一种植物,而历代文人墨客无不钟情于它。又因竹子具有空心、有节、直挺和坚韧的特征,因而常被文人喻为“君子”,进而将竹所代表的“君子”品德作为个人修身的标准,这种现象在文同诗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同居汉中,以咏竹诗为最多,而且以“偃竹”为盛,赞美其“霜筠抱冰节,爽气常四会”[2]1266“心虚异象草,节劲踰凡木”[2]531“铁石枝梢劲,冰霜节目圆”[2]549。竹文化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东坡亦喜欢竹子,他写到:“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3]448文同在《忽忆故园修竹因作此诗》中写到:“故园修竹绕东溪,占水浸沙一万枝。”[2]484北宋时的洋州城北有篔筜谷,此地茂林修竹,文同曾在诗中赞叹“池通一谷波溶溶,竹合两岸烟濛濛。寻幽直去景渐野,宛迩不似在尘中”[2]530。文同暇日常携妻来此悠游、观竹和画竹,并先后写下《赠竹》《竹答》二诗。文同此期与竹有关的诗歌较多,一方面表明他对竹子的喜爱,另一方面也表明他闲适的心态,这些又和北宋时期的变法运动以及党争有不可割断的联系,像文同这样本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文人,试图以读书做官之路,投身政治,造福百姓,然而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却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保全自己,因而他笔下的竹子,不仅是对自然界植物的形神风貌的抒写刻画,更透露出诗人对现实政治不敢过问,有意回避的心理。其笔下的竹子“自谓偷闲太守,人呼窃绿先生”[2]513即是其回避现实心理的写照。
文同汉中山水诗对其他自然风物虽然涉及较多,但吟咏赞颂均不及竹子,且多为偶然提及,“城头看雨霁,天地若新浴。晚容变云霞,秋意著草木”[2]427是对雨后虹霓和傍晚云霞的描写。“烟峦彩翠霜林红,层楼複阁云雾中。襟怀太爽睡不得,一夜满山铃铎风”[2]428此处是对山峦、霜林、云雾和山风的抒写。再有就是禽鸟等的描绘,如“断烟横沔水,孤鹜入洋州”[2]458“雁随平楚远,雲共太虚闲”[2]458此处分别是对孤鹜和大雁的抒写。总的来说,文同汉中诗作仍以竹子为主,以描写竹子的形、态、神和韵为主。同时,文同亦将自己对政治、社会以及人生的感悟融入其颂竹赞竹的诗歌中。
二、 文同山水诗的儒家人格特质
宋代文化紧承唐代,又在政治制度、思想倾向和文学艺术等领域有较大的革新,这些革新是以文人阶层的审美趋向发生较大变化为先导的。唐代有较多文人关心政治,乐于在诗文中抒写对时局的一己之见,此期虽亦有不少山水诗人,受唐代政治风气影响,其诗歌境界多宏阔、壮丽。至北宋时期,政治制度已较为完备,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沉淀已较为丰厚,此期文人的文学作品多呈现出既关心政治,又试图自保的迹象。文同是北宋较为杰出的画家和颇有才华的诗人,因与王安石等改革派政见相左,加之受到党祸株连,其诗、文和画等作品多散佚,使得他在绘画方面的成就显然不及其在诗文界的影响。文同的诗歌以自然风物为主要吟咏对象,诗风清幽,气韵高雅,又不乏诗画交融的特点。文同这种诗风在宋诗审美取向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文同以文官出仕,又是地方官,对于北宋的政治革新和变法运动不可能无动于衷,王安石的新党同旧党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文同只能采取逃避的态度。文同曾自况“不承《春秋》学,乃好水墨画”[2]546,表现了一位儒者超凡脱俗的气象,更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想的写照。
同时,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与思想文化层面中宋学的形成和演变、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社会生活的风气转换等特定历史条件相激荡,在书法与绘画领域出现了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如以竹子作为诗歌吟咏的主要对象,或将之作为挥毫泼墨的对象。竹文化在中国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的文人墨客、士大夫对竹子情有独钟。在长期的文化活动中,竹子的生长特征被拟人化,竹子的精神进而升华至道德、人格理想层面,并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竹文化”。文同素有“周孔为逢揖……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2]3之志,儒家济世情怀与清风翠筱刚柔一体的内在肌理相一致,共同开拓出诗人襟怀坦荡、宅心仁厚的君子风度。
文同32岁中进士后所创作的诗歌,受北宋的哲学文化意蕴和社会政治因素等影响,呈现出显与隐、心怀黎元与乘槎浮海等倾向。如在汉中州郡任职期间,受到变法政治的冲击“一从入仕途,行步每踖踧”[4]144就是其饱受贬谪之苦的真实写照。也有一些诗歌直接抒写其对时政的回避心理,如“懒对俗人常答飒,厌闻时事但盧胡”[2]437“寻幽直去景渐野,宛迩不似在尘中”[2]530“放意利名外,游心天地间”[2]299“将身就清旷,名路尔何颜”[2]458“退而斋居一室,书史图画罗列左右,弹琴著文,寒暑不废”[2]1095都表明其试图置身政治之外的愿望。
三、 诗画合一、超逸远出的审美空间
从北宋时期的山水画作,以及相关的文学艺术研究理论的角度审查此期的文学创作思想和创作观念,可帮助我们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此期的诗画作品。北宋是中国哲学和审美发展的转型期,新发展起来的审美兴趣对宋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宋代文人的自然观不可避免的必然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进而呈现出多种时代特征。宋人多遵从“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5]26,于唐末五代及宋初以来的“淫靡”诗风,“作诗所患格不高”[2]206,文同继承唐诗传统,崇尚梅尧臣、苏舜钦所开创的宋诗新风。钱锺书《宋诗选注》说:“诗歌也还是苏舜钦、梅尧臣时期朴质而带生硬的风格,没有王安石、苏轼以后讲究词藻和铺排典故的习气。”[6]57
文同兼诗能文,其高超的绘画素养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创作的许多写景诗都是“诗中有画”,也就是用诗歌的语言描述绘画作品中的内容。文同以诗人的笔触,画家的视角观察和刻画自然之景,画家注重画面结构的安排,诗人注重语言的生动和传神,二者结合,在文同的山水诗作中有较为完美的体现。清人叶燮对诗、画和情间的关系有较为深入的论述,“乃知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7]265。文同的山水诗从理论到创作均表现出诗画相通的特点,风格别致,颇受时人和后人的推崇。北宋书论与画论比较研究是在接续唐代张彦远“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8]1历史结论基础上展开的。郭熙在《林泉高致·画意》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9]59,传神地阐明了诗与画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书论与画论在此期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来源。
文同生活的年代是北宋初期和中期,他的诗歌明显呈现出“写实”的风格,这与北宋初年西昆体诗歌风格极为不同,同时这也是一种不趋时俗的诗风,这种风格较为真实的表现了诗人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的社会心理和审美兴趣,他的这种诗风既是对前人创作经验的吸收和借鉴,又在吸纳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独特感悟,最终形成了他冲和而流畅的诗歌气韵,内敛而不失旷达的审美风格。唐诗重以风韵浑雅的个性表现情感思想,多向“自然形态的东西”里去发掘原料,“宋诗之妙正在它的冲淡与意境的美”[6]95而文同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这些理论。因此,文同在宋诗风格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般认为,文同诗歌的另一风格特征是用语有明显锤炼之迹,虽未趋向雕饰,所描绘大多为清幽细小的景物,用语虽质朴但失之浅近,有明白流畅之弊。亦“没有王安石、苏轼以后讲究词藻和铺排典故的习气”。在文同诗歌描摹的自然山水景中,较为真切的抒发了诗人的真实感受,其诗歌的情感基调多是冲淡而和缓,显示出旷达的人生追求和绵密的感情世界。如写汉江水“直望汉江三百里,一条如线下洋州”[2]428,画面阔大,胸次极高;写乌鸫鸟“朝朝泊我高柳上,叫破一窗残月明”[2]542,意境清新、活泼自然,没有西昆体、江西派偏形式主义的流弊,剔除了学问的展示和典故成语的堆砌,其诗歌自然英旨,质朴硬朗,气骨瘦劲。
钱锺书《宋诗选注》共选取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其中选文同诗4首。钱老认为:“文同是位大画家,他在诗里描摹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起来,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6]57也就是说钱老认为文同先是用画家的视觉观赏自然风物,然后再用绘画的技法描写所摄取的景物,进而创造了以画笔写诗情的写景手法。文同作品“辞严意清绝”,以绘画的构图方法来为诗中景物定格赋形,用绘画的设色方法来为诗中景物敷彩渲染,并常将绘画术语“画笔”“写真”“水墨画”和“形似”等运用到诗中。钱老是第一个发现并且高度赞赏文同以画写诗的技法,并进而指出这种写景手法“跟当时画家向杜甫、王维等人的诗句里去找绘画题材和布局的试探,都表示诗和画这两门艺术在北宋前期更密切的结合起来了。”[6]58钱老还引用历代写景诗句论证文同这种写景手法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以及它的特殊贡献。如“群峰南北争嵯峨,如泻大壑翻众波”[2]428,就写到山峰南北分岭,就好像巨大的波浪从山壑中倾倒而下,实际是用诗歌的文字描摹绘画的内容。再如“直望汉江三百里,一条如线下洋州”[2]428,也是用诗歌的语言描绘汉江喷薄而下的画面。
在文学创作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创作过程中主观和客观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专门讨论文学创作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他对山水诗作了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提出“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以少总多”和“江山之助”等一系列的理论。汉中明秀的自然环境,使文同创作和审美意识逐渐完善,催发文同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文同诗作所选的“幽圃”“晚霭”“暝禽”和“翠筱”等自然风物,已经超出了事物本身所代表的物理含义,具有了“万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情”在其中,更何况诗人笔下独处静观的花、鸟、草、木、虫和鱼等,如“花落留深草,泉生上浅沙”[2]482“遮根护笋今成立,好在清风十万枝”[2]137“静观只恐惊去,无语凭栏日斜”[3]162“阔外晴烟落,深中晚霭凝”[2]553。诗人独行幽篁、兀坐幽亭、沉吟诗画、林间饮酒、石上围棋,在没有人间纷扰的自然中,“偷闲太守”“窃禄先生”[2]513闲逸淡泊的情趣跃然纸上。
在诗的境界上,文同慕追古风,常有风雅兴寄之感,也有意识的创造了一些清和幽明的诗境。在写景方面,文同多采取“厚积薄发”之笔,常是积郁深厚却不喷薄而出,营造一种境界,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由自然萌生的情感又自然地化入、消融于诗的境界之中。正如胡应麟所说:“诗最可贵者清,然有格清,调清,有思清,有才清……若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10]185“清者,超凡绝俗之谓,非专于枯寂闲淡之谓;婉者,深厚隽永之谓,非一于软媚纤靡之谓也。”[10]185我们认为文同的写景诗别具一格,似是工笔画的文字呈现,他的山水诗虽不像谢灵运通过动态的游观将诸多自然之景联系起来,使山水呈现出勃勃生机,但他笔下的景物在作家静寂澄明情怀的映衬下,使诗人宁静的情感,和谐的心绪弥漫于整个诗文之中。
文同诗追求自然英旨,语言洒脱,用韵工整、质朴平易,很少使用僻典。清人沈德潜说:“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11]120文同师法自然、诗从内心的创作自由,超越仕隐的生存智慧,寄情山水的审美人生,都给后人十分有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