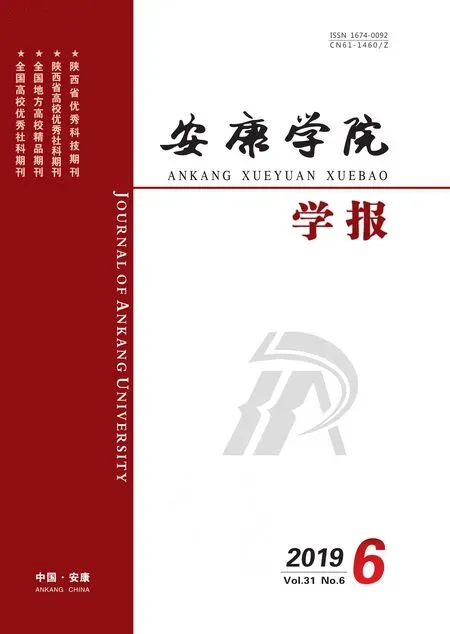《山本》:致敬之书
赵 敏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山本》是贾平凹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他在《山本·后记》中谈道:“这本书是写秦岭的,所以原定名就是《秦岭》”。2018年5月5日贾平凹先生做客央视《朗读者》,主持人董卿开场就说道:“如果说初心是一座山,贾平凹用40多年的笔墨,写满了秦岭,这座他心里最中国的山。今年四月他出版了自己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山本》,字里行间,依然能够感受到他的韧劲、力道、成色,当然也依然有苍茫秦岭的山高水长”[1]。可见,秦岭在作家心中的地位以及秦岭与作家之间血与肉的联系。《山本》可称得上是贾平凹文学创作上的又一部巅峰之作。首先,从题目来说,《山本》中的山指的就是秦岭,作家这一次没有将地点再定为像“商州系列”小说中的商州棣花镇等,而是立足于秦岭中的涡镇,将注意力放在了“最中国的一座山”——秦岭。其次,作家的视野再次放大,通过“究天人之际”去说明山之“本”,“《山本》写历史写人事,但却并不局限于历史人事的眼光,而是把历史人事放在天地自然的大背景下去描述的”[2]37。最后,《山本》的内涵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正所谓“山本”即山之根本,山本来的样子,最初的样子,山本即人本,作家旨在揭开人本来的样子,探求天地人之关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春林在《历史漩涡中的苦难与悲悯》一文的最后对《山本》做了总体的归结:“它既是一部遍布死亡场景的死亡之书,也是一部与打打杀杀的历史紧密相关的苦难之书,但同时却也更是一部充满超度意味,别具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悲悯之书。”[3]303但在笔者看来,《山本》更像是一部致敬之书——对秦岭的致敬,对秦岭生命的致敬,对秦岭精神的致敬,对作家40多年创作的致敬,对作家自己的致敬,对生活在这片热土的中国人的致敬。
一、向秦岭致敬
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说:“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只是秦岭的一个点。”[3]284商洛在作家的笔下不断地被叙述着,如《商州》 《秦腔》 《浮躁》 《带灯》等,从大的范围来讲,这其实就是在写秦岭,只是作家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呈现于大家面前,包括《高兴》 《土门》 《废都》等虽说写到了都市西安,但“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3]284。作者也表明“我就是秦岭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3]284。身为秦岭人,也“必然”写着秦岭事,之前贾平凹也许仅仅只是把乡土商州作为自己的文学根据地,但《山本》无言中表达了作家已将秦岭作为自己创作的热土。因而,《山本》的创作从小说背景的确定上无疑是对贾平凹之前创作的集大成和一大跨越。我们可以理解他对秦岭的致敬,不仅是对商州的致敬,更是对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的致敬,秦岭足以成为作家心中这片热土的代名词,因为秦岭是最中国最伟大且最有内涵的一座山,正如作家所说:“中国大部分的历史,实际上都发生在秦岭的南北”[1]。这就意味着作家在创作上有景可描、有事可叙、有意可表,总之是包罗万象。
贾平凹在《山本》题记中写道:“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在其后记中又说道:“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3]284。这与小说中麻县长的志向不谋而合,《山本》中的麻县长编写《秦岭志》不仅是他的兴趣爱好,更是将其作为工作来完成,其中包括《秦岭志草木部》和《秦岭志禽兽部》。作家借麻县长之口,或详或略地为我们呈现了前所未闻的“鸟兽草木”,并将其穿插于故事之中。呈现这么多自然景观其目的何在?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的谷鹏飞给出答案,即“自然主义描写之重”,“因为在天竞强弱逻辑所编织的历史理性世界,自然主义之重的作用不仅在于巧妙地规避历史题材所必备的价值判断,而且在于它可以诗意地拆掉历史理性的经纬,重新展现世界的复杂性,存在的可能性、人的未完成性与事物的未被决定性”[4]。贾平凹之前的作品,其中也有鸟兽草木、江山大河等自然景观的描绘。如贯穿于《浮躁》的商州唯一的大河——州河,作者称:“我的这条州河便是一条我认为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5];在《商州》中每一单元前面都有对于自然景观的浓描淡写,如写武关之险峻、山阳之灵气、达坪之深凹、照川坪之神秘等等,当然也写到了发源于商洛区西北部秦岭南麓的丹江;在《带灯》里写到“秦岭里的一个小盆地”樱镇里的各种动植物。诸此种种,仅为秦岭之九牛一毛。虽然贾平凹之前的作品也不断地在描写秦岭,但《山本》将整个秦岭作为历史、作为小说故事的背景,乃是一次大的突破,自然主义描写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厚重,与小说历史、故事叙述形成强有力的张力。贾平凹从写商州、西安,到写秦岭,都是他对自己血肉之地的深度追寻,对自己创作热土的致敬。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秦岭,才成就了今天的贾平凹,所以贾平凹对秦岭始终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和敬畏之心。
二、向民间、向传统致敬
在《山本》的写作过程中,贾平凹曾书写两条横幅。其中一条为“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作家将其作为创作的要求来警示自己。对于贾平凹来说,不仅仅在《山本》中对自己的要求是这样,在之前的创作中,他也是一直在努力践行着。就民间性与传统性而言,笔者认为二者共有的特点就是“寻根”,向土地、向民间、向传统寻根,在秦岭这片广袤的天地里寻根。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往往是把对历史的言说引向隐秘、荒诞、偶然、杂乱的层面,使历史变得波诡云谲、光怪陆离,在整体上呈现文学压倒历史之势,即历史被拆解、放逐,混沌一片,不可捉摸[6]。《山本》中所讲的故事和传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秦岭的“历史”,这段历史有其真实的部分,如井宗秀和井宗丞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包括陆菊人也是。然而,整部小说带给人的感觉是所谓“秘史”的震撼感,在叙述上虚实结合,神秘感中又有厚重感。其主要是因为秦岭这片土地上蕴含着多样的文明,秦岭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汇集了秦汉文化与巫楚文化,身为秦岭人的贾平凹,自然而然受着这些文明的影响,所以就不难理解其作品中的厚重感与神秘感。
笔者认为,《山本》中的神秘感,主要源于作家从民间传说、故事以及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的营养。《山本》开篇就提到了陆菊人的“三分胭脂地”,意指有了这片土地便可成大事,机缘巧合之下,井宗秀得到这块风水宝地后,即被赋予了传奇色彩,从而演绎着传奇历史故事。还有如陆菊人被说成是金蟾化身;德行好的人经过皂荚树会掉皂荚;麻县长知动物而算命;白起撒谎遭鬼缠身,避邪躲鬼需用钟馗画;黑色是上天赐予的大吉之兆;周一山可听懂鸟语;朱鹮、燕子、苍鹭等为吉祥鸟,扑鸽、鹌鹑等为不吉祥之鸟;猫头鹰叫意味要死人;等等。这些“历史”大都来自民间,涉及民间的风水学、占卜学、阴阳学、因果说等等。在巫楚文化浓厚的土地上,更是将其渲染神乎其神。但是其中的一些传说、故事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如陆菊人的原型为陕西历史人物周莹、井宗秀于门环上挂马鞭等,所以只能说一些传说、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加上了不同人的主观感情和想象创新,就如同作家一样,将这些传说、故事等经过“天我合一”呈现于文学作品之中。在贾平凹的其他小说中,也有大量类似的描写,如《带灯》中带灯“说事”、《秦腔》里三婶驱鬼、《浮躁》中病妇“通说”、《土门》云林爷未卜先知等等,作家追根溯源,彰显了我国多样丰富的民间文化以及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
《山本》不仅体现了民间性,还体现了传统性。邰利祥认为:“传统性则可理解为贾平凹对《红楼梦》的日常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发扬,也包括对苏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欧美现代派的吸收与融合。”[7]陈思和也认为:“《山本》是一部向传统经典致敬的书。”[8]11笔者则认为这仅仅是传统性的表现,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作家扎根于秦岭,扎根于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当中。贾平凹常翻《道德经》 《逍遥游》,通达天地哲学,《山本》中充分体现出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挖掘。同时他还经常走山访水,实地体察,感受民风民俗,在《山本》中也体现了秦地的秦腔文化,如修戏楼、唱大戏等。此外,作家还通过隐喻的方式对中国传统儒释道精神进行阐释。如宽展师父吹尺八为逝去的生命超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悯,而对《地藏菩萨本愿经》、130庙的描写则将佛教文化精神渗透于小说之中;井宗秀与陆菊人的“发乎情止乎礼”等,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仁义与礼制;小说中陈先生的言行,则是对道家文化的诠释。贾平凹一直视民间和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创作之根,在《山本》中更是把视野放在秦岭之上,把足迹留在秦岭深处,所以说《山本》是作家向民间、向传统致敬。
三、向天地致敬
贾平凹在创作《山本》时给予自己的警惕便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从小说整体来看,《山本》显然是作家在一种大境界下去创作的,他将眼光放置于整个秦岭,“因为秦岭实在太大了,大的如神”[3]284。秦岭在这里即代表天地、代表自然,作家把涡镇的历史风云放在天地自然的大背景下去描述,从而研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陈思和所说的“法自然”,即“借自然生态观察人事社会的运行演变,尊重社会现象的本然发展”[8]5-6,也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贾平凹在散文《三游华山》中说道:“天地大自然是知之无涯的,人的有限的知于大自然永远是无知,知之不知才欲知。”[9]人便是这沧海一粟,其实“人在大自然中实在难以人定胜天”[10]。在《山本》中,关于人的死亡描写尤为突出,小说每一节中几乎都有人死去,而且是冷描写,即描述得很平淡,没有大悲大痛,人的生命似一只蚂蚁般偶然或必然地死去,如叱咤涡镇的井宗秀、“大英雄”井宗丞都难逃一死,他们的死也如普通人一样,甚至更惨,井宗丞因枪走火而死,这对一个久经沙场的人来说,岂不戏剧又荒谬?但这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与秦岭广阔的天地相比,与自然相比,人更显得脆弱卑微,其实这便是人之“本”,人本来的样子,人并非万物之主,只有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才是人于天地之间所应秉持的生存原则,即“天人合一”。在小说结尾作家已经暗示了此意,陆菊人“抬起头来,而安仁堂的那几间平房却安然无恙,陈先生和剩剩,还有一个徒弟,就站在大门外的婆罗树下看着她”[3]283,“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3]283。一切兴衰荣辱都如尘土般最终落于天地之中,陆菊人、剩剩、陈先生及徒弟最终活下来,而在这广袤的天地中能够活下来,还站在婆罗树下,这些都象征着什么,作家又想表达什么?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说道:“这一切留给了我们什么,是中国人的强悍还是懦弱,是善良还是凶残,是智慧还是奸诈?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罣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3]285这不正是作家在创作中一直所坚持的现代性和想传达的现代意识吗?他希望“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11]作家一直把焦点放在人类本身上面,因为“人生就是日子的堆集,所谓大事件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写日常生活就看人是怎么活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2]30。作家揭示人本来的面目除了说明人在天地间的渺小脆弱之外,还想探求人如何在天地间生存,如作家所说的:“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3]286,说到底就是儒释道精神的传承。《山本》中不断出现的尺八,其作用是用来为生命超度,这恰是佛家所追求的大慈大悲。《山本》中被皂荚所砸意味着德行好,起初全涡镇人都以路过皂荚树被掉落的皂荚砸到为荣,陆菊人就被砸过,可后来大家对此不以为然了,最后老皂荚树也被烧为灰烬,如涡镇精神之魂的皂荚树就这样“魂飞魄散”了,这说明了儒家文化精神逐渐被人遗弃,导致人们一步步走入深渊、走向死亡。《山本》中瞎了眼的陈先生,作为医者,作家安排这样一个形象,其真正扮演的是医治涡镇人的心的角色,让人们“清心寡欲”。作家在《山本》中将历史人事置于天地自然的大背景下,探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作家向天地致敬,因为知天地之大,方能敬畏。
“如果把《山本》放在贾平凹整个文学叙事中来看,也应当说是他具有历史性总结与反思的大作品。”[12]笔者对此非常认同,可以说这是作家对过去的致敬,对其之前创作的致敬,但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是作家对秦岭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的致敬,同时也是向这片土地的文明与精神致敬,向民间、向传统致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向天地致敬,因为“大地的伟大,在于它的藏污纳垢却万物更生,秦岭里那么多的战乱,灾害,杀戮,仇恨,秦岭却依然莽莽苍苍,山高水长,人应该怎样活着,社会应该怎样秩序着,这永远让人自省和浩叹”[2]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