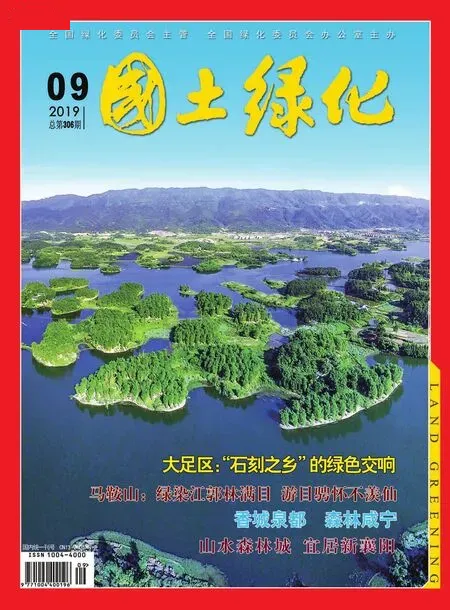母亲与草
■章中林
“咦,我的白鹭兰花呢?”出差十几天,回家,想看看白鹭兰花是不是开了,却看到花盆里空荡荡的。干涩发白的凹坑,像一只空洞的眼一样对着我。我的心头一拧。
“花?什么花?不就是一撮草吗?”母亲凑上来,问。
一看她的神情,我就知道,白鹭兰花又是被她拔了。
“你一伸手,知道多少钱吗?200多啊!”我没好气地对母亲吼着。
母亲尴尬地笑着,两手在围裙上不停地搓着。看到她进退无据的样子,我沉默了。
母亲一生都是在和野草抢生存的空间,生活在农村,庄稼就是她的命根子。种庄稼一把好手的母亲,深谙草多争肥的道理,每天一睁开眼睛,心思就到了田地里——哪一块地的草要锄了,哪一块田的草要薅了。
一块棉田,她至少要锄上四五遍,就是烈日当空也不罢手。一趟锄头过去,田地就像被剃过的光头一样——看不到一根草芽,她才放心。因此,棉田里就是棉花开了,地里也还是清清爽爽的,找不到草的踪迹。
一块水稻,她弯腰用手耘过两遍,还会用草耙耘一遍。水稻蓬起来了,草们没有了露头的机会,但母亲还是不放心。每次走过水稻田,她都会像守田阙的鹭鸶一样,昂着头,用眼睛仔细地把每一棵水稻都问候一遍。母亲是担心那漏网的稗子冷不丁地伤了她可爱的孩子啊。因此,我家的水稻成熟时,田里从来是遍地流金,看不到一点碍眼的杂色。
人们经过我家田地的时候,往往会疑心,这家的田地是不是被小鬼忘记撒草籽了。当人们和母亲打趣的时候,她总会郑重地说:“草是害人精,越宠越矫情,给个笑脸就开染坊,能给它好脸吗?”
有一年,母亲因为患病动手术,住院十多天。等到她回家的时候,地里的草蹿得比棉花还要多。她一看,急了,一边骂我们是懒死蛇,一边就往地里钻。我们哪有懒呢?还要上学,总不能学不上,去拔草……心里腹诽着,却因为畏惧母亲那要杀人的眼色,竟没有人敢吱声。一同进门的父亲一看,慌忙一把抓住了她,“医生反复叮嘱,要你休息一个月,转个背就忘了?”在得到父亲马上下地的承诺之后,母亲才收回了固执的脚步。
可是,母亲还是没在家安静几天,就趁着我们不在,一个人溜下了地。“地里那么深的草,就是拔了,也要锄一遍啊。一场雨下来,又是一青,还能锄掉吗?”她突然间的质疑,让我们恍然大悟。尽管父亲再三强调休养的重要,可是她就是听不进去,固执地每天下地。
后来,母亲一说她的刀口痛,父亲就会埋怨她:“事情是做不完的,身体才是自己的,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呢?”而母亲总是嘟囔着:“就你知道,我的身体我不晓得。我不是每天带着小马吗?”小马,对母亲有多大作用呢?那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这样的场景——母亲匍匐在地上,就像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那样膜拜在地,心无旁骛地清除着那些泛滥的杂草,不管不顾地,只有小马孤独地站立在田地旁。
在母亲眼里,庄稼是她最亲密的朋友,杂草是她最大的敌人。可以说,母亲和草就是势不两立的存在——有我没草,有草没我。所以,当母亲初次来城里的时候,她就随手把我的香雪兰拔掉了。当时,我就对她说,那是花,不是草。而她却固执地说那是菖蒲草,哪有花长得这么盛的呢?尽管她最后勉强接受了我的观点,但是没住几天就跑回去了——养什么不好,家里养草?
在母亲的眼里,草就是祸害——她是不能理解我的想法的。生活在都市里,每天看到的都是疯涨的高楼,延伸的马路,绿色被挤压得看不到多少影子。日夜被死鱼白折磨着,看不到一星绿,这是怎样的一种惊慌和恐惧呢?因此,我开始在阳台上营造我的绿色空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躲进去,给花花草草松松土、施施肥、除除虫,让身心得到片刻的释放。
今天,当母亲再次拔掉我的花的时候,我的情绪失控了。因为我想拥有自己的绿色宁静生活。而母亲又何尝不是为了我呢?因为她知道,比草更难处理的是生活,她不希望我的生活被草耽误了,因为我是她一生不离不弃的庄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