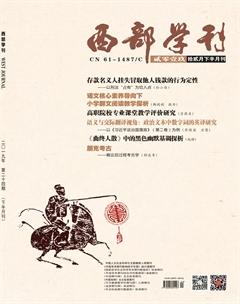存款名义人挂失冒取他人钱款的行为定性
摘要: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以成立事实控制力为核心和基础,当实际存款人利用他人名义申领银行卡并存入现金使用,卡内存款应当归银行占有,存款名义人基于合法的存款合同单独占有了对银行的存款债权。如果存款名义人以其身份证挂失该银行卡并冒领卡内存款,则应当成立侵占罪。
关键词:占有;存款债权;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4-0005-03
一、问题的提出
(一)基本案情
张某(女)与王某(男)结婚后夫妻关系长期不和,王某经常打骂张某,张某遂产生离婚念头。为防止离婚时丈夫在分割财产方面提过分要求,便借用了好友刘某身份证办理了中国银行借记卡,将家中现金存入该卡,卡和密码均由张某自己掌握。后刘某与张某关系失和,便到银行谎称借记卡丢失、密码忘记,通过挂失、重新办卡,取走卡内资金20万元用于挥霍。
(二)观点争议
对于以上案例中存款名义人(即刘某)的行为定性,目前存在多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成立侵占罪,认为在将存款存入他人银行卡内时,现行法律认可卡内存款为行为人所占有,且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保管关系。[1]第二种观点认为成立盗窃罪,主张存款名义人在明知卡内存款为实际存款人所有且没有允许其擅自动用的情况下,通过挂失秘密将钱款取出并占为己有,行为手段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2]141第三种观点主张成立诈骗罪,认为行为人所实施的挂失、补卡等行为,使银行相信其为存款合法所有人,符合三角诈骗的特征。[3]第四种观点主张无罪,认为存款名义人作为储蓄合同的相对方,拥有挂失支付的权利,故其挂失并重新办卡后取款的行为并不是刑法上转移财物占有的行为,而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只需要通过民法的不当得利之债解决即可,没有必要进行刑事规制。[4]
以是否转移财物占有为标准,刑法中的财产犯罪分为两类,一类是非转移占有型的财产犯罪即侵占罪等,这类罪名中行为人未破坏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另外一类犯罪为转移占有型犯罪,包括抢夺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等,共同特点在于行为人采取秘密取得、暴力公然取得等手段破坏了被害人事先对财物的占有并建立新的占有。因此,为了准确界定存款名义人的行为性质,有必要先判断,存款的占有方为银行、实际存款人还是存款名义人?其次,如果不存在对存款的占有,又是否存在对其他财产性利益如存款债权的占有?因此,本文将从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为视角,对存款名义人冒领存款的行为性质进行分析。
二、刑法意义上的“占有”
在占有的成立方面,目前刑法理论界主要侧重从“事实—规范”层面来加以认定。
首先,要判断是否对财物具备事实上的控制力,也即“实际支配或者控制财物”,这也是刑法上“占有”的最核心要素。一般而言,这里的“实际支配或控制财物”是指一种物理的、自然的控制、支配力,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物理的时空条件,被占有的财物需与占有人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空间、时间关系。如某人去餐馆吃饭,走前却将钱包遗忘在餐馆,但五分钟后该人便回想起钱包被遗忘并立即取回,此时该人对钱包仍成立占有。但若几天后才想起钱包丢失,便已经丧失了占有。[5]
虽然物理的时间、空间条件对于占有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财物本身的性质、大小也同样重要。比如,对钥匙等体积较小的物件,必须要随身携带或放置在自己生活的场所内才能成立占有。而对汽车等体积大、难携带的财物,即使是放置在停车场也同样成立占有。因此,占有的认定不仅要考虑时间、空间距离,同时也要综合物品的体积、种类、性质、便携程度,支配的手段、方法等一系列条件作全面分析。
其次,在事实判断基础上,也要从规范角度即社会生活的一般常识层面考虑,这种规范性指的是以法律、社会道德、习俗等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秩序”。举例而言,停在地铁口的摩托车,从物理层面来看与所有权人相隔甚远,远远超出一般人的认知,但社会一般规范仍认同这辆摩托车由其占有,假如有其他人强行拖走这辆摩托车,则构成盗窃罪。因此,在事实控制力非常微弱的场合,只有较强的规范性因素加以补足时,占有才会形成。若事实控制力已足够强大,则相应的规范性因素即使比较微弱也可成立占有。
虽然规范性的有无对于认定占有归属会产生重要影响,但事实控制力却是判定占有成立不可或缺的基础,规范因素只是一个评判基准。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占有代表的是一种财产的归属状态,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距离和市场交易的秩序。他人正是基于“某物应当由其他人占有”的想法才会约束自己不会窃取或掠走该物。但如果某人对该物已经不再拥有任何物理空间上的的事实控制力时,从一般人的角度来判断,根本无法得出其“占有”该物的结论,此時即使规范因素也存在也无济于事。失去了事实控制力,占有将无法成立。因此,在判断占有存在与否时,事实控制力便成为最为重要的标准,它是占有最为基础和核心的要素。
三、银行卡内存款的占有归属
在明确刑法“占有”的认定标准后,如何确定本文案例中银行存款的占有归属方?对此理论界有诸多观点,但笔者认为,存款应当归银行占有,存款名义人占有了对银行的存款债权。
(一)存款归银行占有
关于存款的占有归属方,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存款人随时都可以通过柜台或者ATM取款,意味着存款人对于存款具有实质的支配控制权。银行只是存款人保管金钱的手段而已。[6]第二种观点认为,将钱存入银行与放在自家保险柜没有区别,存款人与银行实际上共同占有着现金。[7]第三种观点认为,存款人与银行之间成立了债权债务关系,现金在存入银行之后,占有归属方从存款人转为了银行。[8]但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均不可取,理由如下:
首先,货币的性质是种类物、流通货币,适用“占有即所有”的规则,占有转移的同时所有权也会相应转移。一旦现金被存入银行,这笔钱的占有及所有权便转归银行。有人认为,钱存入银行后,存款人银行卡余额也相应增加,此时便相当于由银行保管储户的存款,因此存款当然由存款人本人占有。但笔者认为,银行本身的业务主要为储蓄和贷款,即吸取储户存款后放贷给其他主体。换言之,储户与银行之间并未成立保管合同,否则银行将无权动用储户的每一笔存款,这与将财物放入银行保险柜中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后一种情形中银行绝对不可以挪用、转让、使用保险柜中的财物。而储户银行卡中的余额仅仅是虚拟数额,不具有实际意义也不代表储户的确占有了同等数额的存款现金。
其次,有观点认为,存款人可以在ATM机输入密码随时支取其账户内存款便代表存款人对存款具有事实控制力。[9]但笔者认为,方便的取款方式并不能等同于存款人实际占有了存款,试想假如不存在ATM机,取款时仍需要向银行柜员出示证件证明身份,只是ATM机让审核的时间大大缩短了而已。从本质上讲,存款人仍需要插入银行卡跟输入密码证明身份才能取款。
综上,从“实际支配或者控制财物”的占有认定规则出发,存款人对银行卡内的存款本身并不存在事实上的控制力,相反银行可以对这笔存款更为任意的支配,故存款应当属银行占有。
(二)存款债权归存款名义人占有
由上可知,存款人并非基于保管合同将现金存入银行,那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呢?存款合同在民法中属于消费寄托合同。所谓消费寄托,意指以可替代的种类物为寄托对象,基于约定该寄托物所有权移转于受寄人,并由受寄人返还与寄托物种类、品质、数量相同之物的一种特殊寄托。存款是最常见的消费寄托。[10]295因此,当存款人在将现金存入银行时便失去了对存款的占有,也无权要求银行返还存入银行的该笔特定存款,相反仅能基于存款债权请求银行返还相同种类物并支付利息。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存款债权是否可成立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上文中,我们通过分析得出刑法“占有”成立的核心在于事实控制力,同时也要判断是否具备占有的规范属性。本质上说,占有也是个人权益的一种,它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占有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一种空间界限。某物归属于甲占有,就代表该物与甲之间的关系(包括事实、规范关系)最为亲密,甲实际支配控制了该物,其他人不得侵犯。而本案中刘某对存款债权,实际上完全成立刑法意义上的“占有”。原因在于:第一,该存款债权是以存款人本人的名义与银行之间通过签订存款合同而成立的,存款名义人可以随时与银行终止存款合同。第二,存款人名义人也可以通过身份证件随时基于存款债权取款。由此可见,存款名义人实际控制、支配了存款债权,构成刑法上的“占有”。
(三)存款債权可以成为侵占罪的对象
在确定存款名义人对存款债权的占有后,还需要确定的是,存款债权可否成为侵占罪的行为对象?
传统刑法一般认定财产罪的保护客体为有体财产,而随着犯罪形式的多样化,财产性利益受到侵犯的现象不断出现。侵犯财产罪的对象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引发了激烈讨论。本文的观点是,存款债权等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理由在于:一、存款债权也具备一定的价值甚至价值更高,因为它反应了“特定存款人对该存款所享有的财产权”[11],该财产性利益代表了存款人有权向银行请求返还存款、支付利息。一旦他人侵入银行的系统内获取了银行卡密码,会造成存款人失去对银行的存款债权,同样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二、《刑法》第92条规定,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属于公民私人财产。可见,股份、股票、债券等财产性利益,同样受到刑法现行规定的保护。当他人侵犯这些财产性利益,如果不加以制裁,该条规定便失去了意义。因此,存款债权和普通财物一样,在刑法财产的范畴内,应成为侵犯财产罪的保护对象。
(四)挂失冒领存款的行为成立侵占罪
在存款名义人挂失冒领存款时,存款非由存款名义人、实际存款人而是归银行占有。在将现金存入银行前,存款名义人与实际存款人之间达成了广义上的委托保管关系,由实际存款人利用了他的名义开设账户,这意味着存款名义人基于合法的存款合同关系代替实际存款人保管占有了存款债权。所以,存款名义人通过挂失重新办卡并取走存款的行为,实际上违背了委托保管约定,将受委托保管的他人存款债权占为己有,导致实际存款人产生了财产损失,应当认定成立侵占罪。
四、其他入罪观点的反驳
(一)盗窃罪之反驳
有观点认为,刑法上强调的是实质上的所有关系而非形式上的所有关系。借用他人身份证存款时,存款实质上仍然是实际存款人所有,因为其掌握着银行卡和密码。[12]故存款名义人非法占有存款属于盗窃行为。[13]
但是,虽然刑法与民法存在诸多差异,对于本案仍要回归到“占有”的认定标准层面分析。如上所述,占有的认定要考察事实控制力的有无,无论是存款名义人还是实际存款人都不具备事实控制力,二者能够从ATM中取款在于对银行的存款债权,向储户返还存款只是银行履行存款债务的表现,因此并没有占有存款。故以存款实质上归实际存款人所有为理由认定盗窃罪的观点难言合理。
(二)诈骗罪之反驳
诈骗罪观点的支持者主张,存款名义人已经明知银行卡内存款归他人所有的情形下,向银行虚构其为存款真正所有人的事实而挂失银行卡,使得银行误认为其为存款持有人,而后将存款占为已有,符合诈骗罪的成立条件。
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也存在不妥。首先,借用他人身份证办卡存款本身违反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行没有排查实际持卡人与存款名义人是否一致的法律义务,否则便对其施加了过多负担。其次,存款名义人本身并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因此并不成立诈骗罪。
参考文献:
[1]杨兴培.挂失提取账户名下他人存款的行为性质[J].法学,2014(11).
[2]强音,王彧.挂失并取走自己账下他人款项行为之定性[M]//赵秉志.刑事法判解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3]吴加明.合同作骗罪与意见代理之共存与释论——一起倒卖房屋案引发的刑民冲突及释论[J].政治与法律,2011(11).
[4]吴娉婷.从刑民交叉角度再看冒领他人存款案[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7(4).
[5]车浩.占有概念的二重性:事实与规范[J].中外法学,2014(5).
[6]黎宏.论财产犯中的占有[J].中国法学,2009(1).
[7]陈洪兵.中国语境下存款占有及错误汇款的刑法分析[J].当代法学,2013(5).杜文俊.财产犯刑民交错问题探究[J].政治与法律,2014(6).
[8]钱叶六.存款占有的归属与财产犯罪的界限[J].中国法学,2019(2).
[9]黎宏.论财产犯中的占有[J].中国法学,2009(1).
[10]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中)[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钱叶六.存款占有的归属与财产犯罪的界限[J].中国法学,2019(2).
[12]邓忠.挂失并领取自己账户下的他人钱款行为定性及分析[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13]陈兴良.挂失并取走自己账户下他人款项构成盗窃罪[J].中国审判,2010(5).
作者简介:孙小佳(1995—),女,汉族,山东省青岛人,单位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