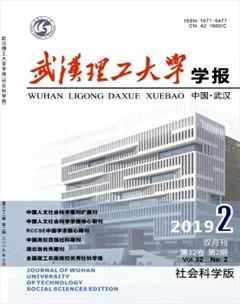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转变
李学林 毛嘉琪
摘 要: 在改革开放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点前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从毛泽东时期的自发性保护转变为邓小平时期的自觉性建设,从重视运动号召转变为着力于制度构建;从强调独立性探索转变为逐步开放性借鉴;从依靠专业人员治理转变为动员全民保护;从推广环境保护经验转变为规划大型生态工程;从优先发展农业转变为结合其他产业并举。
关键词: 毛泽东;邓小平;改革开放;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D64,X2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2.0003
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与自然生态运作系统逐步相协调的进程,通过不断改造调节人类自身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消解发展过程中的环境负效应,重新构建起更加合理且进步的生态秩序。改革开放作为新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转折点,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毛泽东时期自发性保护这一历史起点走向邓小平时期自觉性建设这一新历史起点的起承转合之逻辑结点。改革开放之前,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工业化程度还未发展到环境问题凸显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毛泽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现实,早期工业化国家几百年进程中分阶段产生的生态问题在我国集中地呈现出来,邓小平纵观全局、着眼未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和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
一、 从运动号召到建章立制的转变
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便已经意识了生态环境问题,并通过运动号召和行政命令的形式发动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强有力的领导方式,才逐步自上而下建立起了由各级政党组织领导的各级中央与地方政权,而想要进一步克服旧中国结束之初整个国家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就只有继续通过党组织对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统一组织领导。毛泽东以革命战争年代打大会战的方法,充分发挥新中国相较于旧中国的制度优势,采取运动号召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发动群众,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有效整合全国各方面的资源,在散乱的社会条件下快速地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提升效率,同时,运动号召的形式能够充分发挥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广泛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生态环境建设的社会实践活动。
水是生态环境系统中十分重要的组成要素,而中国作为一个水系丰富的大国,因为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干旱和洪澇灾害频频发生,新中国成立后,水患和河患不仅造成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大量财产损失、恶化生产生活环境,还直接威胁着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毛泽东便发动人民群众,举全国之力展开了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地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修建。1951年夏,毛泽东在淮河流域遭遇特大水灾后就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并说:“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1],治淮指挥人员和参与的工农群众都受到巨大鼓舞,“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的积极热情促使一期导淮工程很快完工。1952年10月,在视察黄河大堤时,毛泽东又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指示在黄河的上中游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以解决水灾频繁的问题。1963年12月,海河水灾之后毛主席又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1950年3月,为治理长江毛泽东号召“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同时,在毛泽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号召动员下,全国各地全面地展开了群众性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在农业水利部门的领导组织下,这些建成的农田水利设施不仅有效地取得了灌溉效益,还在防洪抗旱中发挥着特别作用。接连不断的水利建设热潮在全国掀起,逐渐建成了一系列大小规模的水利设施,成效甚佳,为抵御洪涝灾害、稳定生态环境、保障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森林资源的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林业不仅是一项改善和美化人民工作生活自然环境的公益性事业,更是关系到工农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毛泽东历来就重视森林的建设工作。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中,毛泽东便提出要号召群众植树来绿化荒山荒岭,要求各个级别的政府机关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向人民群众说明植树造林运动各方面益处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来种各种树木”[2]11。1944年5月,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看到陕北地区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太低易引起水土流失和破坏生态环境,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中提出要制定一个植树造林计划,号召陕北人民每户每年种活十棵树,并且要坚持实施十年或者八年。面对建国初期我国森林整体覆盖率仅为86%的不利境况,在1956年3月,毛泽东更是面向全国人民群众发出了“绿化祖国,植树造林”的伟大号召。即使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也在1958年1月4日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绿化工作要大搞,四季都要种树,今年还要彻底地抓一抓;在1958年8月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号召:“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2]73。在毛泽东的不断号召和倡导下,1938-1964年间,陕甘宁地区的群众植树运动就成功植树760万棵;1958年后重庆云阳人民栽植的8万亩长江流域防护林也为保护农田、美化环境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进程加速,生态环境问题也日趋凸显,邓小平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从更加宏大的视角高瞻远瞩地指出要依靠法制法规的构建来保护生态环境,让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由人治走向法治。基于对过去运动式办法的总结,邓小平看到了此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运动号召的方式虽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也往往导致人民群众一哄而上,造成资源在短期内过度集中使用的浪费,同时,在人治的情形下,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容易随最高领导人的转变而转变。加之,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组织纪律性的极大增强,采用运动号召去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已经失去了必要性。为保证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各项工作能够长期而稳定地开展,邓小平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特别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问题,进一步提出要通过科学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来有效制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落实,从法制的高度来顶层设计,使我国生态建设活动更加规范化、有序化、高效化,来有效规避仅靠领袖号召的主观随意性和变动不稳定性。
邓小平十分重视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伴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且强调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也要依靠立法建制来长远规划、全局引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应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轨道,在1978年12月13日主持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会议中,他就明确强调要集中力量制定包括环境保护法、草原法、森林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立法先行,以引导和保障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长足发展。[3]146-147同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三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地将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上升到了宪法这一基本法的高度,指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和基础。1979年4月17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会议时再次指出:“这件事要有人抓……要制定一些法律”[4]506,在他的高度关注和不断推动下,同年9月,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颁布,确立了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同步的基本方针,标志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的快车道。
此后,基于宪法中所规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和环境保护法中的主体内容,一系列针对特定环境保护对象的生态环境保护专门法律法规陆续被制定、颁布并付诸实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于1982年8月23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5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1985年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1986年1月20日)、《矿产资源法》(1986年3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1月2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1月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10月3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逐步完善的各类环境保护全国性单行法规和地方性条例,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法制框架的初步形成,对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开发自然资源提供了法律支撑。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的落实,邓小平还一直强调环境管理的行政体制建设也要转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上。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正式确立环境管理为政府职能中要贯彻执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确定了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并且上升到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生态环境保护被纳入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以统筹协调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在邓小平的不断关心和努力倡导下,环境保护部门的各级政府机构设置逐渐趋于健全和完善,从无到有,行政级别和独立性都得到相应发展而逐步提升,从1982年5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下设的环境保护局,到1988年7月成立作为国务院直接隶属机构的独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再到1998年6月再次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保行政机构的逐步扩大,为其充分发挥环境监管与执法作用、实施具体化定量性管理和保护提供了组织基础。
二、 从独立探索到开放借鉴的转变
国际社会上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这一揭示人类不合理的社会活动导致大量环境污染问题的环保著作开始,才拉开了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及采取保护环境措施运动的序幕。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初期,一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采取封锁政策,使我们不能及时掌握生态环境问题相关的新信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系统地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而此时,生态文明的建设工作尚未受到苏联应有的重视,鲜有可供我国参考的生态实践经验。我们党的领导人主要是立足于新的历史阶段和实际情况来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在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独立地探索出许多生态建设方面的规律与对应的可行措施。
在农业耕作的生产生活中,我国古代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出许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与经验,凝聚出有关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关系的生态智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初期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实践指导与经验借鉴。据古代文献记载,为了调控水资源、抵御水旱灾害和促进生产发展,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不胜枚举的治水经典案例。早在公元前246年,战国时期水工郑国便修筑了郑国渠;256年,公元前秦蜀守李冰主持兴建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以及建于公元后的通济堰、西湖、京杭运河、坎儿井等,无一不为新中国水利生态建设提供了智慧结晶,为毛泽东亲自决策指导的导淮工程、长江的荆江分洪工程、黄河治理工程和官厅水库等实践提供了参考与借鉴。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生态文明思想也滋养着新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道家文化中“顺之以天理”的遵循自然规律思想,影响毛泽东生成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与自然的关系”[5]的认识;《荀子·王制》中“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的节约自然资源的告诫,影响了毛泽东提出对“空气、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都要加以小心保护,进行合理使用”[6]的要求。
通过调査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各地的实际环境情况,毛泽东在社会实践中探索把握生态建设的规律,根据社会状况和自然条件的调查结果,准确作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策。“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7]829。早在1930年,在江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便多次亲身走访群众、深入农村调查环境状况,并在《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报告中指出,赣南地区“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8],诊断出植被林木的缺失是水旱灾害的主要成因,随后就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在当地植树造林的五项方针。1952年10月毛泽东在出京亲自视察黄河时,详细询问后得知北旱而南涝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南水北调这一创造性设想。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60年4月,第一座由我国自行独立设计建成的大型水利发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发电成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也注意到前期的砍伐森林、大炼钢铁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经过一些实际的调査研究之后,主动作出《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的批语》,以保护山林植被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