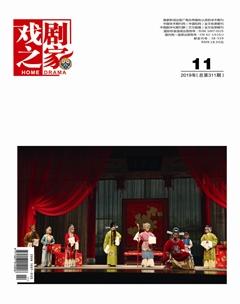仪式与治疗:一种戏剧样式的新思考
王凯
【摘 要】徽州目连戏是古徽州地区的民间戏剧,但其演剧活动并非单纯为了欣赏和娱乐,反而带有强烈的祈福纳祥、驱邪避害的意味,呈现明显的仪式性特征,并借此实现宗族内的情感抚慰和精神治疗。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徽州目连戏在抚慰人心、治愈苦痛方面的客观作用,并由此进一步结合戏剧治疗的理论,探索当代徽州目连戏,以及给我们留下的当代思考。
【关键词】徽州目连戏;戏剧样式;仪式;戏剧治疗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0-0004-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市场快速发展。丰富的文化生活使得人们对于戏剧表演活动更加熟悉。但是,当代的戏剧探索中,对于传统民间戏曲“仪式性存在”的思考跳脱出单纯的演剧活动的研究,成为理论探索中普遍性的趋势。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戏剧人对戏剧的理解大大拓展了,不再把戏剧作为供欣赏的艺术存在,还注重发掘其实效功能,探究其改造社会生活或个体心灵的作用。
在针对“仪式性存在”的探索研究中,戏剧治疗从形式来看和仪式性戏剧具有很多相似处,而仪式性戏剧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戏剧治疗可以达到的净化心灵、治愈精神的基本功效,是人类精神的独特呈现。
徽州目连戏恰恰就是具有典型戏剧治疗特点的“仪式性戏剧”个案。虽然它使用的还是戏剧表演的外壳,但整个演剧过程的内核与常规思维中的戏曲艺术有巨大差异,更可被看作宗族性聚居的村落中血亲宗亲之间的精神抚慰。这给了我们新的思考:村落中的戏剧究竟是什么样?进入现代社会我们还可以如何理解它的价值?它能够给现代社会怎样的启示?
一、徽州目连戏的仪式性存在
徽州目连戏是存在于古徽州地区的一种历史宗教戏剧,其故事源于《经律异相》《佛说盂兰盆经》等佛教经典,借助盂兰盆会的盛行,目连救母的故事也逐渐流传开来。唐朝时期,说唱文学中开始出現多种有关目连的变文,故事渐趋完整,并盛行于民间。北宋时,开始出现《目连救母》杂剧,其演出形式有“两头红”的说法,即从太阳落山开始演,一直演到第二天日出。及至明代,祁门清溪人郑之珍在传说、变文、杂剧的基础上,撰写了《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演剧者结合徽州当地风俗形成了我们所见的徽州目连戏。郑之珍人在清溪,但是剧本以祁门县环砂村为原型。在不断的演剧发展中,祁门县栗木村戏班在武戏“打目连”部分最为精彩,久而久之,祁门民间传说中便有了目连戏“出在环砂,写在清幽,打在栗木”的说法。时至今日,能够演出徽州目连戏的还剩下历溪、栗木和马山三个村的戏班,并且均有徽州目连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徽州目连戏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演剧活动积淀,而且从民间演出来看,它绝非普通的戏剧表演,反而呈现出“仪式性存在”的特点。
(一)演员构成。之所以说徽州目连戏符合仪式性存在的特点,首先因为其演员构成有明确要求。徽州目连戏的演员并不是专业的戏剧表演者,而是以村落为单位的青年男性村民,他们同族同宗,背负着共同的历史,拥有着共同的祖先,演出活动本身就是家族式活动。
其次,传统的祭祀仪式往往需要预言家或者巫师等具有神秘色彩的角色参与其中,其他人也都经过精挑细选、斋戒沐浴后才能进入仪式活动,徽州目连戏的演出与此基本相似。例如,徽州目连戏中有“跑猖”的作法和招魂行为作为开场,通过“跑猖”请来东五猖青帝、南五猖赤帝、西五猖白帝、北五猖黑帝、中五猖黄帝五位山兽之王,通过向他们祭祀祈福,求保一方平安,避免山中猛兽侵害。
最后,传统习俗中参加徽州目连戏演剧的只能是本族的男性成员,人为将演员构成和家族血亲的祭祀仪式关联在一起。因为在男尊女卑的传统中国民俗文化中,只有男性才能够成为联系家族成员的纽带。
(二)演出目的。弄清演员来历后,不难发现徽州目连戏原始的演出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某种艺术,更不是为了艺人生存生活的要求,往往是家族内部某种特定的精神诉求,故早有学者说徽州目连戏“是为了驱瘟逐疫,纳吉求丰,或为宗族修订族谱、家谱,或为香主还愿而演,如遇天灾、兵焚、人瘟、凶死等必打目连。[1]”这和祭祀在根本动因上一致,呈现为对“仪式”认识和理解。
所谓“仪式”是以特定的方式重复一种象征性活动来确保身份地位的永存,巩固某社区内成员间的共同联结,并防卫个人与团体免遭危险[2]。对照解释可以发现,徽州目连戏就是“以特定的方式重复一种象征化活动”,目的就是“成员间的共同联结,并防卫个人与团体免遭危险”。因此,徽州目连戏的仪式性存在也就无可辩驳。
(三)演出流程。目连戏表演在各地并不统一,即使在同一地因时因事不同,演出时长也不相同,有“三天三夜”“五天五夜”“七天七夜”“十天十夜”等。但徽州目连戏演出之前的组织有严格流程,绝非随时想演就能演,不但需要完整周密的筹备方案,而且必设有一套专门的人马负责。例如,环砂村在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曾演出过徽州目连戏。当时,就是先由族内的长者提出建议,再由议事组织商讨并在家族内形成统一意见后,立下文书字据才开始筹备。
徽州目连戏演出内容包括搭神台、守斋、禁赌、扫除、祭祀、进香、请神、送子、驱邪、收台等,虽然叫法上各地有差异,但形式基本相同。笔者走访历溪村时,王鑫成老人讲述,历溪村演目连戏要先“跑猖”请神,之后“放猖”清理村中的孽障,当所有的演出都结束后再“收猖”;而且按历溪风俗,必须在村中空地上搭台,以便“赶鬼驱邪”,不能在宗祠内演出,对祖先不敬。但是,清溪、环砂、栗木三地可以在祠堂内开演无需搭台。
可以说,祁门县各村在演出徽州目连戏时都会根据本地的乡俗设定具体要求,按部就班,恪守仪式规矩,否则就不能起到驱邪避害、抚慰内心、强化精神的作用。
(四)演出道具。从道具角度来看,更可见徽州目连戏仪式意味的浓烈。历溪村的王步和老人曾向笔者展示了演出目连戏时使用的通关文书,具体内容如下。
十殿阎王
丰都大帝主管阴曹地府一切冥官。
一殿阎王(秦广王)——管人生死、寿命、长短之事。
二殿阎王(楚江王)——管肢体、奸盗、杀伤之事。
三殿阎王(宋帝王)——管杵逆、尊长、教唆、起讼之事。
四殿阎王(五官王)——管粮、租、税、交易、欺诈之事。
五殿阎王(阎罗天子)——管地狱、诛心之事。
六殿阎王(卞城王)——管怨忧、强弱、哭笑之事。
七殿阎王(秦山王)——管药治、好歹、离人世之事。
八殿阎王(都市王)——管惩罚不孝之事。
九殿阎王(平等王)——管审判、杀人、发火之事。
十殿阎王(转轮王)——管善恶分明、核定分别之事。
此文书是对十殿阎王不同职责管理权限的介绍。既然是和亡灵的对话,是对其前途的指引,当然便是祭祀仪式和超度亡灵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还有招神时使用的符咒,祭祖使用的祭文等无一不向大家说明,徽州目连戏的仪式性存在。
二、戏剧背后的内心抚慰和精神治疗
仪式活动是戏剧性的,因为它要求主事者经由象征化方式创造出一个表征的世界。[3]而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剧本的完成则带来了仪式活动向戏剧形式的发展变化。当然,在普通村民那里,他们恐怕不会把徽州目连戏上升到戏剧的高度,反而更愿意将它作为一种生活中的力量,借助它,在逆境、不顺、痛苦时进行心灵按摩,悼念先人、系血亲情感;抚慰内心、保宗族延续。
(一)悼念先人、系血亲情感。徽州目连戏不是专业戏剧演员的日常性表演,而是由同一家族成员共同组成演出团队,分别饰演不同角色,只在家族遇到重大事件或者某一特殊需要才进行的活动。由于各地风俗不同,演出没有固定要求,往往“依据家族内的习惯每隔三到五年或者闰年上演一次,遇到灾年或瘟疫流行也要演出”[4],族内成员生病或去世也可演出,因此表演徽州目连戏就成为悼念先人、联系血亲的手段。
当前还能够表演徽州目连戏的历溪、栗木和马山三村中,历溪村和栗木村都是新安琅琊王氏后裔,曾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彰显王氏家族的繁盛。马山村则是叶姓家族的聚居地。他们的表演都以整个村落为演剧空间,在祠堂内或者在村落中搭台演文戏,借着村落中自然环境演武戏,即打目连。因为要进入祠堂,所以按照祖辈的要求,徽州目连戏演出不允许外姓人参加,而且本族中也只男丁才可参与,戏中如遇女性角色则由男子反串。虽然当前这种保守的传统观念已伴随着社会发展得到了纠正,村中的外姓人,尤其家族中的女性均可参与,但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很常见。即便是现在,一些农村地区在悼念祭祀先人时,对于家中男性的要求也还是比对女性的要求高。所以,徽州目连戏明显包含了对血亲关系的精神依赖。
笔者走访调查历溪村时,据老人王道照回忆:在他幼年时,村中王连生得病一直无法治愈,族中长者为了帮着亲人祈求上苍庇佑,获得康复,就曾专门为此演出过目连戏。可见,传统宗族社会,仪式戏剧可以成为守护血亲之间情感的港湾。
村中另一位老人王鑫成在带领笔者参观王氏家族宗祠“合一堂”时也说,旧时每每家族中有人离世,就会在祠堂祭祀,在村中演出,这是一种家族文化。同时,历溪村表演时使用的通关文书也揭示了亲人与亲人之间,不仅生时相互关怀,即便故去也会倾心安排,再送一程。
徽州目连戏借助宗族内的团结互助实现了对亲人的精神治疗,它可以让生者感到家族成员的关怀,提升战胜病魔的信心;还可以直接宽慰故去之人的直系亲属,缓解其哀恸的情绪。
(二)抚慰内心、保宗族平安。除了针对个体祈福生者、悼念死者之外,徽州目连戏的另一实效则是保宗族平安,它缓解了整个家族的生存压力,保障了延续和传承。
首先,徽州目连戏在本地也叫平安戏,顾名思义,保护平安,所以戏剧从命名上就承载着精神寄托,那么演戏、看戏当然就是抚慰内心的精神治疗。
另外,祁门的环砂村主要是程姓和傅姓两姓聚族而居的村落,村民说古时环砂村遇到天灾人祸,均要举行祭祀活动,上演徽州目连戏,借此宽慰族人、祈求平安。
民国二十二年,环砂村上演徽州目连戏时,留下的筹备文书中有如下记载: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二十六日善愿告示合族四股人等,在振德(即如松)家团聚公同商议,编立合文及筹款简章,告许癸酉年目连善愿以保合族平安,实为公益。
立合族告许目连筹费办事约人,族长程世英(光林公)等窃思时衰时盛,虽怨天道之流行作福作灾及由人心自召,是故欲保平安必资善愿,于事有济,筹款为先,然人必赖神以相依庶可得资保障,事必籍款而成立,自然有志事竟成也。我族自民国开基以来,于兹念载,大局变迁,散财源而村风落薄,损壮丁而户口寥稀。见此情形,不忍坐视;观斯现象,谁不寒心。于是欲挽回运地之兴隆,莫如功德,人丁繁衍,特发善良。兹经合族人等告许目连一台,公议择期开演。此宗善愿,费用当先此种良因,人力是赖。要皆藉众志以成城,持众掌而易举,公同筹款,集千狐可以成裘;四股醵资,聚多数由于少积,人人鼎力,个个倾心,将来斯愿告还。
神灵有感,户户共沐源仁;人口平安,个个同沾恩泽。是虽合族之力,要亦神圣辅佐之功也。今编立合文一样四纸,各收一纸存照。[5]
此段文书清楚表达了上演徽州目连戏的缘由,即“大局变迁,散财源而村风落薄,损壮丁而户口寥稀”,更重要的是来自族群内心无法言说的苦痛,即“不忍坐视”和“谁不寒心”,正是面对此情此景,有了族长程世英等人为整个程氏宗族“保平安”的尝试,以此抚慰整个群族内心的感伤。
三、古为今用的戏剧治疗
当代的人类学家和实验性戏剧创作者多把戏剧和仪式连接在一起,将戏剧运用到治疗上。正如我们所看到徽州目连戏一样,透过表演弥合了观众的内心痛苦,增强了他们的精神力量,个人的心理健康得到提升;对于族群,强化了宗族意识,协调了血亲联系,村落的和谐氛围得到了加强,这些内容都客观存在、无可辩驳。可以说,历史早就展现了仪式活动和戏剧表演的治疗作用具有不可言传的联系,那么,扩展开来看,徽州目连戏的戏剧治疗功能就有了以资借鉴和思考的价值。
(一)戏剧治疗的认识。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及悲剧功能时认为其可以引导心灵和精神的净化,在借助心灵深处感情的释放,进而实现灵魂的净化。1939年,英国现代戏剧教育学先驱彼特·史莱德在给英国医药协会的演讲中最早用到了“戏剧治疗”的说法。同时期,奥地利精神病理学家莫雷诺也在维也纳开展了心理剧的治疗。20世纪70年代,艺术治疗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在欧、美、日,包括中国广泛出现。
按照1979年英国戏剧治疗协会的定义,戏剧治疗是一种用来协助个人了解并缓解社会及心理问题、精神疾病与身心障碍,以及促进在个人或团体中以口语与身体沟通的创造性架构来接触自己本身,并做象征性表达的方法。[6]
因此,在笔者看来,戏剧治疗就是透过戏剧的方式来促进人精神和行为上的改变,运用戏剧的潜能反映并转化生命的体验,让个体或者一个团体表达并改善所遇到的问题,进而维系他们的健康和福祉。
(二)徽州目连戏中“戏剧治疗”的因素。徽州目连戏暗含的体验就是在人们遭受疾病、危机,或感到迷茫、有个人成长的需求时,利用戏剧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实现情感的抚慰和精神的治疗。
首先,空间的创造。不论是祠堂,还是舞台,徽州目连戏的演剧活动必然在观众和演员之间搭建起一个戏剧空间。但是演员也好,观众也罢,他们接触戏剧的缘由事先明确过,也带着具体诉求在这个空间中,通过象征的方式营造表征的世界。但是演剧活动也是仪式活动,戏剧空间也是仪式空间,演剧就成了祈求神灵庇佑的仪式,最终在仪式空间中完成倾诉,情绪逐渐放松,笃定的追求自然会在仪式空间中引导他们再一次认识自我。
其次,身份的交叉。林怡璇认为,戏剧治疗更像是一场“浓缩的生命故事”,来访者通过表演,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7]借用这样的理论,不难发现徽州目连戏让每个人进入到共同的生命故事中,既体会角色的身份,又明白自身的诉求,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观演关系被彻底打破,观演互动完全开放,界线被彻底抹平,观众与演员,或者说治疗者与被治疗者同时在场,在仪式之境中得到了情感的宣泄,感伤血亲的苦痛,表达自己的感怀,造成团体心理治疗的效应。
最后,通过戏剧故事形成精神世界的共鸣。被誉为“俄罗斯当代戏剧之魂”的导演列夫·朵金曾说戏剧通过探讨深刻的社会、人性问题,带给观众一种心灵的空间,既能够给人以共鸣,又能让人去改变自己。[8]透过故事形成精神世界的共鸣在徽州目连戏中则是一种自然而确实的状态。脱胎于祁门县环砂村环境背景的徽州目连戏,其故事内核当是本地人生活的戏剧化表达,为“族内事”而演的徽州目连戏更是源于宗族血亲的共性精神需求,象征性表达的仪式背后,族群追求维系个体和团体共存的健康和福祉,无形之中共鸣就以达到。
(三)戏剧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要素。长期以来,对于戏剧,我们总是将它孤立地看成是一种文化艺术形式,但越是经典的文化艺术反而越曲高和寡,成为一种非必要物品,也成了生活中的非必要环节。但是,戏剧对于健康的社会与个人来说,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因为它可以作为一种娱乐或者是一种文化艺术符号,更因为它与生活密切相关。
例如,每年除夕之夜,大家都习惯于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共庆佳节。大家在画面中能够看到一个个相同的故事,感受到故事背后一个个相同的情趣,而这一个个故事里也似乎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无形之中就产生了共享和交流,透过故事传递出的积极信号,再一次让我们重新标记了新定位,找到了新方向,融入到整个晚会所寄予的主题思考和精神追求中去。可以说,电视创造了一个戏剧空间,我们虽隔着荧屏,虽各自独立却又都在这个统一的空间中,潜意识和情绪就无形和这个空间产生了联系。看似观看春节晚会是与日常现实分隔开来的活动,其实它更像中华民族的精神仪式。一如徽州目连戏所提供的戏剧空间一样,在特定的时刻,全族人在同一场演出中进入同一个状态,相同背景能让他们产生相同的感触,并在空间中的形成共鸣,实现凝聚。
从个体存在来看,现代人生活在高速行进的社会中,不断遇到新困境、新问题,但是因为社会缺少心理疏导机制,就会产生各种困惑,沮丧与不安也随之而来,如同环砂村的族长程世英当年的沮丧与不安一样。不同的是,现在的我们没有以村落为单位的接触的戏剧治疗机会,所以内心的不安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便得不到缓解。
戏剧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要素,这是普遍的认识,所以彼特·布魯克在《空的空间》中说剧场就像吃与性那样必要;埃夫雷诺夫也说剧场对于人类而言,就像空气。
四、结语
戏剧是健康生活的要素,净化人的灵魂。古人用他们的智慧展示了戏剧对人的精神治疗,也展示了聚族而居的人们对戏剧实用功效应用的超时代性,给当前的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变化,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大步迈进,但同样变化的人则普遍在压力和疲惫中陷入到精神的痛苦和心理生理的亚健康状态中,很难找到疏解的渠道。其实,类似聚族而居的古人,社区里的我们同样也是聚群而居,但是我们的社区文化交流,尤其社区内的戏剧文化交流还非常欠缺,虽然大家可能同属一个阶层,同有一种追求,同过一种生活,存在明显的共同语言,但是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陌生程度很大,缺少环砂村的相互助力,扩大生命体验交流进而获得精神治疗的机会,这恐怕也是徽州目连戏提供的最直接启示。
参考文献:
[1]茹耕如.明清社会中的徽州民间仪式戏剧[D].2000年国际徽学研讨会论文,2000.
[2]Robert.J.Landy.戏剧治疗——概念、理论与实务[J].心理出版社,2010.
[3]陈长文,谷水,赵荫湘.目连戏在徽州的产生与发展[A].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祁门县人民政府编.目连戏研究文集[C].1988,252.
[4]陈琪.祁门县环砂村最后一次目连戏演出过程概述[A].徽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260.
[5]王钰.戏剧治疗:一个戏剧界古老而新兴的话题[J].艺术教育,2017,(13):18.
[6]林怡璇.艺术治疗师也是艺术创造者—谈戏剧治疗师的专业性[J].台湾戏剧学刊,2008,(4):17-29.
[7]张道正.俄罗斯戏剧大师列夫·朵金:戏剧应给人以共鸣[EB/OL].中国新闻网,2017-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