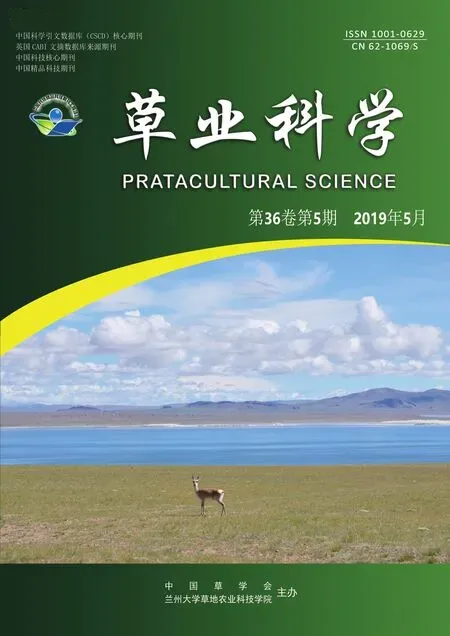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下高寒牧区退化草地生态治理途径
李祥妹,彭元柳,岳 洁
(1.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5)
草地生态系统是保障生态安全、食物安全和农牧区社会稳定的重要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我国拥有天然草地面积近4亿hm2,占全国陆地面积的41.7%[1],在我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天然草地资源利用存在着过度放牧、管理粗放、草地退化明显以及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等问题,在青藏高原地区,草地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影响了牧户生产生活,威胁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为遏制草地退化、恢复和重建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以原农业部为核心,在青藏高原及内蒙古地区实施了多样的“自上而下”的草地管理措施[3],然而,由于社区及牧户缺乏有效的经济转型模式,难以在短时期内获得有效且持续的经济来源[4],不少地区草地恢复与生态重建措施(如禁牧、休牧等)影响了牧户收入[5],导致牧户对该类政策产生了抵触,政策效果没有充分发挥[6]。
作为农村公共池塘资源的天然草地面临着“公地悲剧”挑战,其治理与生态恢复依赖于牧户的充分参与及自下而上的管理途径。牧户草地治理行为选择受政策导向、牧户个体特征及区域产业发展等的影响。资源系统特征、群体特征、制度安排以及外部产业发展环境影响着公共资源管理战略的实施及管理政策的制定[7]。群体规模、非农就业机会、群体异质性、牧户生产规模、距市场距离和领导阶层等对农村社区自发组织集体行动有显著影响[8-10];同时,牧户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个数等个体因素影响其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意愿[11-13]。区域宏观产业发展趋势影响着地方政府公共资源管理决策,如乡村旅游发展在改善环境、促进农村基层的民主管理等方面作用明显[14],同时农户是否参与乡村旅游业发展直接影响着其公共资源生态治理意愿及行为选择。
理论上看,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下,农户(牧户)旅游产业发展参与度可通过3种机制影响其草地生态治理行为:其一,参与经营旅游产业改变了农户/牧户的利益诉求方向。研究发现,参与经营旅游产业的牧户更重视成本-收益率,其牲畜出栏率及商品率远高于普通牧户,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超载过牧问题[15];其二,牧户参与旅游产业发展能有效增加其社会资本,提高其对公共事务管理及政策制定的参与度,有利于自下而上实施牧区公共资源管理措施[16-17];其三,牧户参与旅游产业发展能有效提升其对公共环境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知水平,进而提升牧户草地生态治理意愿[18]。可见,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影响牧户利益诉求、改善社会资本分享途径,有效提高牧户的环境意识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知,进而影响牧户退化草地生态治理与恢复的意愿。
西藏纳木错流域是我国典型的高寒牧区及我国草地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样本地区,同时又是我国著名的旅游景区。近年来,区域内旅游产业发展迅猛,年游客接待量平均增长速率超过35%,2017年全年接待游客80余万人次。区域内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影响着牧户生产行为决策,另一方面又增大了区域生态与环境的压力。为探讨旅游业发展背景下区域农户行为选择与生态恢复途径,本研究以藏北高寒草地典型区纳木错流域为例,以Ostrom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IAD)理论为基础[19],基于牧户参与旅游业发展及其草地管护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定量分析研究区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下牧户草地生态治理行为特征,探讨旅游产业发展对牧户践行环境友好型草地利用方式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旅游产业发展的公共草地治理途径。本研究一方面为我国草地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实践经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2017年夏季牧户调查样本为基础,基于Probit模型定量分析高寒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下退化草地生态恢复与重建路径,重点关注牧户旅游产业参与度对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知、参与退化草地生态治理意愿等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及解释变量分述如下。
1.1 被解释变量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脆弱的自然环境特征,西藏高原牧区是保留着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草地集体承包、集体利用、牲畜私有”的经营方式。在这一经营模式下,草地资源隶属于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具有较弱非排他性和一定范围内竞争性[19],每个成员都可以利用草地内的牧草饲养牲畜,但草地总量有限。本研究采用过程法从牧户利用草地、保护草地两方面反映被解释变量—退化草地生态恢复与治理行为。其中,牧户草地资源利用行为通过是否恪守载畜量表征,牧户草地保护行为用是否将获得的牧草良种等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用于草地生态建设来表征。
1.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是“牧户家庭是否参与旅游业”,研究中牧户家庭参与旅游产业发展行为包括入股纳木错景区“牵牛拉马”合作社;个体经营餐厅、宾馆、茶馆以及家庭旅馆等;从事其他相关的旅游服务业如导游、旅游车司机、牧区家庭文化体验、特色藏区文化表演等;以及制作、销售旅游相关产品如奶渣、青稞酒、特色手工制品等。如果牧户参与任何一种与旅游产业发展相关的活动则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考虑到本研究对象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研究中采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参照蔡荣等[20]、秦国庆和朱玉春[21]关于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分别从研究区资源特征、群体特征、制度环境特征和个体特征4个维度探讨公共草地治理的影响因素。
研究中选择草地规模、牲畜数量、牧户家庭距中心城镇远近3个变量表征资源特征;以成员户数、村庄非牧业就业比两个变量表征研究社区的群体特征;同时用选择牧户家庭成员是否曾接受草原生态补偿奖励的相关培训、不同质量畜产品是否有价格差异、村民小组是否安排生态岗位及村民小组内部是否有补差制度4个变量表征研究区的制度环境因素;选择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牧户家庭实际放牧劳力个数、牧户家庭少儿抚养比及牧户家庭牧业收入比5个变量表征样本牧户的个体特征。
1.3 计量模型设定
本研究将回归方程设定为基于牧户个体层面的Probit模型以探讨牧户草地生态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下标i表示第i个牧户。方程左边表示受访牧户进行草地生态治理的概率,被解释变量stocki和grasslandi是二分类的变量,表示受访牧户是否恪守载畜量/进行草地管护建设。方程右边traveli为关键解释变量,代表受访牧户是否参与旅游业经营。本研究重点关注旅游业发展对牧户草地生态治理行为的影响,即α的符号正负和统计水平是否显著。此外,方程右边的Xi是指1.2中已有说明的一系列可能同时对牧户草地生态治理行为产生作用的控制变量。α、β为待估计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衡量影响牧户草地生态治理行为的不可观测因素。
1.4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西藏纳木错流域的牧户为微观研究对象,调查范围为整个纳木错流域 (89°30′-91°25′ E,30°00′-31°10′ N),行政区划上包括当雄县的纳木湖乡,班戈县的新吉、德庆、保吉3个乡镇和青龙、尼玛乡的部分行政村。
本研究所用样本分析数据为2017年7月-8月在西藏自治区纳木错流域内牧户访谈问卷,其中村级问卷通过对村委主要干部(村长或驻村干部)的访谈获得,访谈内容包括村庄整体情况、人口和劳动力、草地和牲畜、公共事务和基层组织、村庄与外界的联系5个方面;牧户问卷包括牧户个体及家庭基本概况、旅游产业参与现状、牧业生产、草补政策认知度和满意度、公共草地管护与饲养牲畜设施5个方面。为确保调研样本具有代表性,以分层抽样为原则,按照村、村民小组、牧户3级依次在流域内的德庆镇、新吉乡、保吉乡、纳木湖乡、青龙乡、尼玛乡共6个乡(镇)随机抽取,共获得有效牧户样本354个,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列。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Table 1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 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下退化草地生态治理实证分析
2.1 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基于354个调查样本,利用Stata 11.0软件构建Probit模型,检验牧户参与旅游业对草地生态治理的影响 (表2)。模型的回归显示,R2分别为0.727 4、0.538 2,对应的P值为 0.000,方程所有系数(除常数项外)的联合显著性很高,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可信度较高。
根据上述计量模型,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参与旅游产业的牧户恪守载畜量的概率比未参与旅游产业的牧户高出7.84%,并在10%的水平上显著;同样,参与旅游产业的牧户更倾向于进行草地管护建设,其管护意愿比未参与旅游产业的牧户高出34.7%,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牧户参与旅游产业发展对草地生态治理有显著正向影响。
从资源特征看,牧户平均草地规模对其是否恪守载畜量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估计系数为负,一定程度上说明草地资源的稀缺性更容易导致牧户的超载过牧,这一研究结果与龚大鑫等[22]的认识一致;牧户平均拥有的牲畜数量对是否恪守载畜量以及是否参加草地管护建设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07 8和0.009 0,且二者都在1%水平上显著,证明牧户及社区拥有较多牲畜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容易导致超载,同时由于该社区草地资源的公共池塘性质,个体农户对草地管护参与性没有充分调动,若该因素与草地资源稀缺性叠加,如果没有农户生计转型的支撑,仅靠外部政策导向,难以实现退化草地生态恢复与治理成效;牧户与中心城镇的地理距离变量无论是对其恪守载畜量还是参与草地管护的相关系数都是正相关,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充分显示自上而下政策效应的距离递减特征,进一步验证了只有充分调动牧户的积极性及其内在认知,才能保证草地生态建设政策的持续性。
群体特征方面,调查社区牧户规模在恪守载畜量及支持草地生态建设方面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33 3和-0.056 1,通过 10%、1% 显著性水平检验。该结果表明,相对于规模较大的社区,牧户规模较小的社区更容易实现有效的公共草地自主治理,研究结论与Araral[23]、何凌霄等[24]的结论一致,这一结果显示了熟人社会及邻里网络关系在农村公共资源管护方面的重要性;非牧业就业比重在模型(1)中的估计系数为0.065 2,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当群体中非牧业就业比重较高时,牧户有较多的非牧业收入,该类牧户对牲畜饲养带来的收益依赖性较低,因此其更愿意恪守载畜量。
制度环境特征的计量结果显示,参与草地管护培训能有效提升牧户公共草地治理意愿,对协助牧户恪守载畜量有较大影响,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865 0;不同质量畜产品售价差异的估计系数为0.841 0,且在5%水平上显著,该计量结果证明了市场发育程度对牧户行为的影响,即当牧户从市场差异中获得较多收益时,其能自发地选择减少载畜量从而提高牲畜质量[25];生态岗位的设置对公共草地治理无显著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26],其主要原因是当前的生态岗位是针对贫困户的一种扶贫补贴而非惩罚“搭便车”行为的手段,政策影响面较小,无法真正对公共草地治理起到有效监督作用;补差制度在模型(1)的估计系数是0.981,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估算结果充分说明了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社区综合管理及分配制度在公共草地管护中的巨大作用,证明了社区公共力量及乡规乡约在公共资源使用及分配中的有效性。
牧户个人特征要素的计量分析结果主要有:一方面,牧户户主年龄显著负向影响草地生态治理行为,牧户户主年龄越大,其生产意愿及生产方式越保守,倾向于通过增加牲畜数量来增加家庭财富,而年轻牧户倾向于采取新途径获取经济效益,从而愿意采取新的草地管护政策,也更倾向于通过降低牲畜存栏量、提高出栏牲畜质量来获得相应的收益;另一方面,牧户户主越年轻,其获取新信息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越强[27],容易接受新型草地管护政策和技术;从牧户户主受教育程度看,由于研究区域为典型的青藏高原牧区,牧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多为文盲或半文盲,因此牧户受教育程度对草地生态治理与管护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牧户家庭中从事放牧劳力的比重在模型(2)中估计系数为0.420 0,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牧户家庭中从事放牧的劳动力越多,其对畜牧业的依赖性越强,同时对草地资源的依赖性也越强;从牧户家庭少儿抚养比的估算结果看,当牧户拥有较多子女时,其更关注草地生态恢复与
治理,更倾向于草地生产的持续性;同理,牧业收入比重越高的牧户,对草地的依赖性越强,该类牧户在草地管护方面呈现出矛盾性,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减少牲畜存栏量,另一方面他们又期望草地资源得到改善,此类牧户在确保草地承包政策持续性的前提下,愿意投入较多的初始资金来改善草地。

表2 旅游业对草原生态治理的影响估计:Probit结果Table 2 Impact of tourism on grassland management: Results of the Probit model regression
2.2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本研究用牧户所在村庄至核心景区的距离作为牧户参与旅游产业的工具变量来估计草地生态治理决策模型,以减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和遗漏变量偏误。一方面,宏观层面的村庄至核心景区距离与牧户个体层面的草地生态治理决策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即没有理由认为村庄至核心景区的距离会影响到个体牧户是否进行草地生态治理的微观决策;另一方面,至核心景区的距离与牧户参与旅游产业有较强的相关性[28],越靠近核心景区的牧户参与旅游产业的机会越多(表3)。
Wald检验的P值分别为0.05和0.01,表明本研究在5%和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变量外生性假设,即原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表3)。首先,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中,第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46.82,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研究中选择牧户所在村庄至核心景区距离作为参与旅游产业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其次,牧户参与旅游产业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3),充分说明牧户参与旅游产业能有效促进草地的生态治理;第三,本计量模型估算出牧户参与旅游产业对其是否恪守载畜量及是否参与草地生态建设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247 5和0.577 5,即其他条件不变时,参与旅游产业的牧户与未参与旅游产业的牧户相比,恪守载畜量的概率提高了24.75%,参与管护草地的概率提高了57.75%。与表2相比,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系数较Probit模型的估计系数大幅提升,这表明,如果使用一般的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由于忽略了参与旅游业的内生性,将低估参与旅游业对草地生态治理的正作用。

表3 旅游业对草原生态治理的影响估计:Ⅳ Probit结果Table 3 Impact of tourism on grassland management: Results of the Ⅳ Probit model regression
3 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下退化草地生态治理路径
根据上述针对研究区(西藏纳木错流域) 354个样本牧户的牧户草地生态治理行为计量分析,认为纳木错流域旅游产业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公共草地的自主治理意识。平均来说,参与旅游产业的无论是在恪守载畜量还是在草地生态管护方面的概率都有显著提升,分别提高了24.75%和57.75%,这一计量结果充分显示了旅游产业发展对区域退化草地生态治理与恢复的影响程度。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种基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退化草地生态治理路径:
1)以距离旅游景区核心区远近为关键变量,差异性实施牧户参与旅游产业激励机制。距离旅游景区核心区较近的牧户,如纳木错乡牧户,在当前“牵牛拉马”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励其从事旅游相关产业,加强牧户普通话及其他文化技能培训,在资金上支持牧户开办藏式茶馆、餐厅、民俗风情园、民宿等旅游相关产业;针对距离旅游景区较远的牧户,如班戈县保吉乡、新吉乡等牧户,组织并激励其从事藏文化产品(饰品、手工艺品、羊毛制品等)制造业,从而服务流域旅游产业发展。
2)以旅游产业发展为背景,促进区域市场发育,以市场经济为手段引导牧户减少牲畜存栏量,加大草地生态管护力度,提高畜产品质量。在计量研究中发现,促进牧户减少牲畜存栏量的关键是牧户能够得到有效的经济收益,即在市场机制完善前提下,如果牧户能够通过高质量畜产品获得足够的经济收益,则其愿意作为理性经济人,通过加大草地管护力度、减少牲畜存栏量、提高出栏牲畜质量来获得收益。因此,该区域应基于旅游产业的两性发展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尤其是以纳木湖乡为依托,实现不同质量畜产品的价格差异,使牧户真正获得优质优价效益,从而自觉地实施草地管护计划。
3)以旅游产业发展为背景,实现区域“自下而上”的草地管护政策。研究中发现,成熟的社会网络、牧户自发的草地管护机制等对流域草地生态治理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基于流域旅游产业发展,发挥非正式制度(如村民小组内部的监督机制、补差机制、村规民约等)的作用,提升社区社会网络建设成熟度,建立互惠互利的处事模式,从培训年轻牧户出发,实施“自下而上”的社区公共事务治理路径。
总之,本研究以西藏纳木错流域旅游产业发展为背景,基于354户调查样本,分析了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下,牧户恪守牲畜存栏量、参与公共草地生态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基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退化草地生态治理路径,研究结果有望为我国高寒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