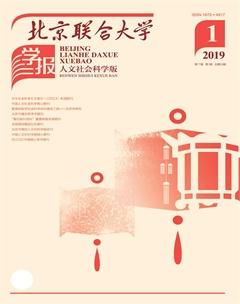基于自组织产业网络的生态城产业结构演化研究
吴杨 李学伟



[摘要]针对“生态城”这一全新的产业集群建设与发展模式,利用复杂网络研究方法建立具有自组织特点的生态城产业结构演化模型。针对生态城自身发展特点,在所建立的产业网络中引入影响扩散机制、生长机制、学习交互机制等网络演化方式,通过对生态城产业网络演化进行仿真分析,研究产业网络的聚合系数、节点度、度分布,产业网络影响力,产业网络熵值以及新兴产业的涌现机制等指标的变化趋势及作用机理,结合生态城产业网络发展的实际情况给出了企业之间联系强度、合作多样性等因素对产业网络健康成长的影响。
[关键词]生态城;复杂网络;产业网络;自组织;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1-0085-10
“生态城”(ECO)模式目前正在被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在一些地区进行探索性试验,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投资建设效果。[1-2]生态城(ECO)模式是指在中心城市与周边欠发达地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域,并应用先进的科学与技术手段协调城市经济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生态城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双向“阀门”的角色,产业结构合理的生态城有助于通过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改变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资源不均衡问题。相对于传统的产业聚集模式,生态城是一种全新的建设模式,强调各项基础服务配套产业与产业创新集群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依托完善的基础产业和多样的特色产业,催生出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新产业。
在分工日益细化的当今社会,一项社会活动往往无法由一两家组织机构单独完成,尤其是一些基础产业,更需要具有资源互补能力的企业形成共同体,共同来完成。各个组织、各种产业之间也因此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传统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即是以此为基础的。复杂网络的研究是复杂性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是研究复杂性科学的有力工具,用于研究复杂性及其产生机制,是反映复杂系统的一种网络形式,是从复杂系统中高度抽象出来的框架性表示,是对复杂系统相互作用的一种本质抽象。[3]目前已有不少学者采用复杂网络来模拟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对产业集群网络演化的特点进行分析,提出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4-6]孙梅 [7]利用复杂网络建立了企业群体竞争合作关系模型;于文龙[8]将复杂网络演化机制引入企业技术创新的网络化传播,比较了不同复杂网络创新传播策略之间的差异;谢逢洁[9]建立了快递产业竞争关系网络,分析了网络拓扑结构的复杂特性,解释了其经济意义;马永红[10]利用演化雪堆博弈模型从企业的公平偏好类型、网络结构和节点类型对欠发达地区企业创新合作的涌现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网络性质与网络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生态城与产业集群的不同之处在于,产业集群的目标是通过特定地理范围内多个产业的相互融合形成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往往具有较强的行业特点,而生态城的特点在于形成一套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更加具有人性化的特点。目前,针对生态城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居设施规划[11]、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及绿色模式创新[12-13]等方面,较少关注生态城内的微观主体,并且较少从组成生态城的产业网络结构出发提出科学问题并进行剖析;另一方面,针对产业网络的研究又大多基于静态视角进行,较少与生态城模式自身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相結合,较少关注产业网络演化、涌现的量化控制与分析,同时对产业网络多要素、多主体、多种联系的协同性刻画程度不足。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将复杂网络演化模拟方法与生态城自身的成长、发展机制进行有机结合,在既有的整体网络结构下设计演化方式更加合理并贴近实际的产业网络演化模型,采用计算机模拟仿真方法,实现生态城产业网络的发生、发展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动态变化,模拟并研究生态城产业网络这一模式的演化成长轨迹。
一、生态城产业复杂网络的现实基础与演化机制
(一)生态城产业复杂网络的现实基础
复杂系统视角下,生态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显著的“两阶段”特点。一方面,生态城自身的发展定位决定了其具有很强的产业集群经济地理特征(地理位置集中、产业领域相互联系),各类企业协调发展、协同创新,形成相对稳定的投资与发展环境,企业之间存在资本、契约、技术、合作等关系,随着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产业集群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演化网络。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不同,除了一定数量的企业与机构的聚集、企业之间的资源流动与信息交换,生态城演化与发展的参与主体还包括广泛的人类社会活动(衣食住行、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生态城在承担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功能的同时,也逐渐演化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特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以多样化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态系统。
就企业层面而言,不同产业的聚集会带来竞争、自然选择、资源互补、企业间知识交流与学习等现象,这些现象以市场作用为驱动力,会进一步促进高水平的知识溢出,最终会促进企业网络中创新的涌现。这一演化流程已被众多研究认可。
就人类社会活动层面而言,产业网络创新的产生与涌现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会进一步增加社会活力,增加就业机会、吸引人才。而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与产业间联系的不断优化又会反过来促进企业与社会其他配套行业的繁荣,形成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此时,如果相关的社会系统配套产业不能有效跟进,或是受到某些资源的制约,则又会影响企业网络的发展。
可见,产业集群网络的发展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内进行,企业网络内部存在着信息交流、互动、学习、协同创新等自组织现象;而在其所依托的社会系统层面上,又存在着广泛的他组织因素,例如政府机构对生态城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人才的流入与流出、当地社会系统发展活力的影响,环境、资源的支持等。宏观层面的结构调整与微观层面上的产业集群成长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两个层面在动态的环境中不断向着一定的方向演化,政府层面的他组织因素形成方向性产业结构布局方案,微观层面的产业网络通过网络连接的建立催生新产业的涌现,从而实现生态城模式下“乐业”与“安居”功能的协调发展(如图1所示)。
(二)生态城产业复杂网络的演化机制
1.影响扩散机制
影响扩散机制是指复杂网络中主体的行为或状态的改变会在网络中得到扩散,被其他主体模仿复制,大多企业都愿意寻找资源丰富、影响力大的企业进行合作交流。[6]而影响力大的企业通过建立大量合作关系又会进一步扩大影响力。[14]为了刻画这种影响扩散机制,本文通过构建企业间影响力参数表征不同企业间的影响关联程度,该参数是企业网络中企业间建立联系的依据和基础。
2.学习交互机制
学习交互机制的设计思想来源于传统的社会经济复杂系统演化模型,这一机制普遍存在于典型的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其根本思想在于多主体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实现自身状态的更新与发展。在产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这一机制同样普遍存在,不同的参与主体可以在网络结构下进行相互学习和信息交流,并依据外界环境的变化改变自身适应能力,提升自身信息处理能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从而在动态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15-16]在企业影响力的基础上,为了刻画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交互,本文通过新进入产业网络的节点对网络内既有企业节点进行自组织选择与识别来实现这一学习交互机制,通过新进入企业对既有产业网络内企业影响力的识别实现产业网络的建立过程。
3.生长机制
产业网络的生长机制具有现实性,刻画了一个区域内产业网络的成长过程。在产业网络发展初期,企业数量较少,配套缺失,影响力较弱。随着各类资源的完善,既有企业的影响力不断得到提升,则会不断有新的产业涌入网络,与既有企业建立联系,增强自身影响力。[14]随着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产业网络会产生新的涌现现象。为了进一步量化网络内企业数量的增加与网络产业结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自组织产生网络的新企业进入机制(节点增加机制)的基础上,通过设计产业网络熵值来量化产业网络的涌现。
4.随机突变机制
在产业网络的演化过程中,众多的参与主体并不是每时每刻都遵循着最优策略原则进行状态改变,其状态的改变在不确定、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这种具有突变色彩的随机性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并为网络的演化带来新的多样性。为了体现动态变化的市场中的随机性,本文通过在产业网络增长过程及连接建立过程中引入基于“轮盘赌”的选择方式,增加网络生长与演化的随机性。
二、生态城产业复杂网络演化模型
(一)建模思想
产业集群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网络系统。目前,复杂性理论已经逐渐成为产业集群、创新涌现领域的重要研究视角,复杂性理论在产业集群内的重要机制(促进集群规模的扩张和集群内多主体的共生作用)研究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产业集群网络中企业伙伴的择优连接机制是产业集群网络特征研究的关键问题,一些有关大规模产业网络的研究结果显示,雖然对于各种生长连接机制的具体定义不同,但由上述四种机制所反映出的产业网络内择优连接现象在网络演化过程中是显著存在并且同时作用的[17]。因此,本文将上述四种机制其贯穿于模型设计环节。
(二)自组织产业网络模型设计
令G表示生态城产业复杂网络,V表示G的点集合,n为节点总数,无向边〈i,j〉表示企业i与企业j之间的联系,wij表示企业i与企业j之间的影响关联程度。则企业节点i的影响力INi可以表示为:
INi=j∈Viwij。(1)
其中Vi表示与企业节点i相连的点的集合,在本文的复杂网络演化模型中,每个新产生的企业节点按照目前生态城产业结构的基本规划优化结果(以贵阳中铁生态城为例,详见文献[18])决定其企业类型(用TYi表示),TYi∈{1,2,…,8},分别表示旅游、生态优化、房地产、养老、教育、医疗、交通、其他传统服务业。
网络演化步骤如下:
步骤一:节点初始化。初始网络由8个节点组成(旅游、生态优化、房地产、养老、教育、医疗、交通、其他传统服务业,各一个),每个节点之间都彼此相连,初始化节点之间的权重wij。
步骤二:网络扩张。依据生态城的产业规划在网络中增加一个新的企业节点,其中,新的企业节点边数为m(m≤n),m服从正态分布m~N(m′,σ2)。m′表示企业的平均连接数量。
步骤三:建立连接。新加入的企业节点建立与既有企业节点的连接,既有的企业节点i的选择概率PSi可以表示为:
PSi=INini=1INi。(2)
选择采用(2)式所示的“轮盘赌”的方式进行,即进行m次“轮盘赌”操作建立新的m条边。可见,新进入的企业节点可以通过影响力实现对产业网络内既有企业的识别与连接,体现了产业网络增长演化过程中具有自组织特点的学习交互机制。
步骤四:更新节点影响力及网络权值。加入新的企业节点后,企业之间的连接也要进行相应的更新,因此,节点影响力与整体网络的权值会发生相应变化。令i表示既有企业节点,j表示新加入的企业节点,并与企业i建立了连接,则企业i的影响力INi可以表示为:
INi=INi+wij。(3)
可见,(3)式体现了产业网络中的影响力扩散机制。
步骤五:计算节点连接多样性。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与其建立连接的企业类型越均匀(多样性越好),对企业的发展越有利,反之,如果与其建立连接的企业类型越单一,越不利于企业发展。“熵”的概念来源于热力学,用来表征系统内的有序和不确定性程度,在复杂系统视角下,“熵”常被用来衡量系统的演化行为,“熵”值的增加意味着系统内要素多样性的增加,因此,本文采用“熵”的思想来量化这一指标。
EPi=-k∈TYiqklog(qk)。(4)
其中,qk表示与企业i连接的第k类企业数量,EPi表示企业i的“熵”值。
步骤六:新产业涌现。当企业i的“熵”值超过某一阈值时(熵的阈值用EP*表示),即与企业i建立连接的企业多样性超过某一阈值时,说明此时企业i可以聚集多种行业的资源,满足转化为新兴产业的条件,“熵”值的引入,以复杂系统中的涌现现象为理论基础,体现了产业网络的生长机制与随机突变机制。
三、模型演化分析
(一)参数设置
如后文无特别说明,生态城复杂网络模型参数按照表1取值:
其中,参数设置中的企业数量、连接边数均通过目前贵阳中铁生态城(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发展规模获得,节点“熵”的阈值通过熵值的计算公式结合生态城内企业种类、企业连接的最大多样性计算得出,生态城内行业间影响力参数通过对贵阳中铁生态城建设项目相关专家进行调研咨询获得,见表2。
(二)网络特征分析
由本文构建复杂网络的形式和结构可知,新加入的企业节点与既有企业节点的影响力密切相关,企业的影响力越大,它与新节点建立连接的概率就越大,因此,网络具有一定无标度特性。
1.聚合系数
聚合系数是网络的局部特征,反映了相邻两个企业之间“朋友”圈子的重合度,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假设某个企业节点有K条边,则这K条边连接的企业节点(K个企业节点)之间最多可能存在的连接数(该企业节点的“朋友”之间也是“朋友”)为K(K-1)/2,用这K个企业节点之间实际存在的边数除以K(K-1)/2得到的结果即为该节点的聚合系数。
在本文建立的生态城产业复杂网络演化模型中,新增的企业节点边数m是节点的生长和建立连接过程中的重要参数,在现实中决定了产业的自组织模式,对m进行调整,考察网络聚合系数的变化。
图2的仿真结果显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m的取值由大变小时(由模型建立部分可知m的取值越大,与新增企业节点建立连接的企业越多),网络的聚合系数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是由于,依据本文复杂网络模型的影响力假设,新进入生态城的企业节点会依据既有企业节点的影响力决定建立连接的概率,这意味着影响力高的企业会吸引更多新进入的企业节点,继而进一步增加自身的影响力,最终造成影响力极度不均衡的“马太效应”,(多数企业仅与影响力高的少数企业建立连接,而这些企业之间的连接数量则有限)。m取值的减小有效减缓了影响力较高企业继续积累影响力的速度,从而使新进入企业仅与影响力较高企业建立连接的概率降低,从而有效地增加了网络聚合系数。
2.节点的度与度分布
一个节点的度是指与此节点相连的边的数量。由图3不难发现,当每次增加的新节点与既有节点之间建立的连接数量(m值)较大时,网络节点的平均度迅速上升;当m值减小时,网络节点的平均度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这是由于,在网络初始状态下,8个节点彼此相连,每个节点具有较高的度,随着新节点的进入,当新节点与既有节点建立的连接较少时,便会出现网络整体平均度降低的情形,在现实中,这一现象体现了生态城产业结构并未完善时(成长初期)产业网络的演化过程,可见,对于新进入的企业,提升个体节点的通达程度可有效促进网络系统整体的通达程度。
图4给出了网络节点的度数分布,不难发现,当m值不断减小时,网络节点的度数分布差异显著增大,节点度数大于20的“超级节点”数量显著减少,同时度数很小的“孤立节点”数量显著增加;而当m值增大时,由于每个新进入网络的节点产生的连接更加广泛,因此网络节点的度数分布显得更为平均。
(三)产业网络影响力分析
调节m取值,考察网络节点平均影响力变化。
由图5可见,当m值减小时,新加入的节点与既有节点之间连接减少,依据本文对节点影响力的定义可知,网络节点平均影响力的增加幅度减少。图6给出了网络节点的影响力分布,不难发现,当m值减小时,新节点与既有节点建立的连接减少,影响力的扩散传导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连接数量的减少,又使新加入节点更加容易仅和影响力相对较大的既有节点建立连接,因此导致节点影响力集中分布于较小的区间,使影响力很大的“超级节点”数量不断减少,可见,通过减小个体企业节点的通达程度可以使网络整体影响力的分布更加平均,但会同时减弱企业群体的影响力。
(四)产业网络熵值分析
由本文的新产业涌现规则可知,当与企业i建立连接的企业多样性超过某一阈值时,说明此时企
业i可以聚集多种行业的资源,各种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为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涌现创造了条件。下面考察连接强度(m取值)对产业网络熵值的影响。
图7给出了生态城产业网络节点平均熵值的演化过程。可见,随着节点数量的不断增加,节点平均熵值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这是由于,在网络初始状态下,8个节点彼此相连,每个节点的连接具有较好的多样性(较高的熵),随着新节点的进入,当新节点与既有节点建立的连接较少时,便会出现网络整体平均熵降低的情形,在现实中,这一现象体现了生态城产業结构并未完善时(成长初期)产业网络演化过程的另一方面,即对于新进入的企业,提升个体节点的通达程度可有效提升网络连接的多样性。
图8给出了产业网络在不同m取值条件下的演化结果,表3给出了不同m取值条件下涌现出新产业的平均数量,不难发现,当m取值减小时,网络连接的数量减少,但熵值超过阈值的节点数量反而增加。这是由于,对于每一个节点而言,连接数量的增加会同时增加“超级节点”的数量(图4),导致新加入的节点被度数高、影响力大的节点吸引,虽然少数“超级节点”通过吸引连接使其连接的多样性得到增加,但这同时会降低大量新加入节点连接的多样性。而m取值的减小,则从连接数量上大大限制了“超级节点”的度数和影响力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量新加入企业节点的连接多样性,这也解释了图7中m取值较小时,网络节点平均熵值增长较快的现象。
(五)新兴产业涌现分析
对前述复杂网络演化模型中的步骤二引入一个新兴产业节点的产生机制,即由目前网络中新兴产业的比例决定网络中新增加节点类型的概率。换言之,网络中新兴产业的数量越大,网络新增节点为新兴产业的概率则越大。步骤二可以重新描述为:
步骤二:在网络中增加一个新的企业节点,计算网络中已有新兴产业的比例,这一比例即新增加企业节点为新兴产业的概率。否则依据既有的生态城产业结构规划定义该新企业的节点类型,其中,新的企业节点边数为m(m≤n),m服从正态分布m~N(m′,σ2)。m′表示企业的平均连接数量。
由表4可知,演化规则中增加新兴产业的涌现机制后,随着网络的演化,新兴产业的数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由图9可见,当m取值较大时,网络节点的平均熵值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这是由于,初始阶段新兴产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网络内企业的类型,而连接数量的增加(m取值较大)又会导致新加入的节点被度数高、影响力大的节点吸引,从而降低新加入节点的连接多样性。当m取值减小时,网络节点平均熵值则在后期呈现增长趋势,新兴产业数量也得到了提升。
四、生态城产业网络演化案例分析——以中铁生态城为例
中铁国际生态城是2010年12月贵州省政府与中国中铁正式签约的大型旅游文化产业项目。项目位于中国贵州双龙临空经济区,距离贵阳市区仅15公里,距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仅6公里,地处大贵阳空港经济区,是贵阳、龙里一体化的中心。生态城被纳入贵州省委、省政府制定的黔中经济圈贵阳城市核心区经济发展格局,各个功能模块之间已经初步实现了相互协调、相互带动的发展模式,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基础产业,实现了人力资源在贵阳、龙里、生态城之间的良性流动,为新产业的不断进驻提供了良好的配套基础,创造了产业网络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框架。依托生态城模式的实际案例,结合本文所建立的产业网络演化模型,进一步梳理和预测生态城自组织产业网络的演化过程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网络基础框架形成阶段
通过产业网络起始阶段的积累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依据当地资源状况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网络的基本形态逐步形成。随着网络内部主体之间的联系不断深入与成熟,各种资源在网络中的流动也会形成新的结构,网络内部既有的个体逐步实现了内部状态的稳定,开始寻求新的外部合作关系并以此降低初始阶段由于网络结构简单可能造成的风险。资源与合作关系的新需求催生了新产业的加入与匹配,但从整体规模而言,由于新产业引入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网络的连接模式依然较为松散和单一。因此,新进入产业所建立的连接并不广泛,和其他产业的合作模式也较为单一,互动和交流不明显,催生网络演化的整体环境还没有形成。
在这一阶段,催生网络演化的主要动力是新进入产业与既有产业的重要连接,重要连接的建立会加速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从而产生更大的产业引进需求。自2010年开始,中铁生态城依托当地的区位以及资源优势,以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与生态优化产业之间的连接作为生态城系统内部的重要连接,旅游产业与生态优化产业之间相互依存、合作互利,产生合作收益后,吸引了上下游产业的进入,加速了新产业的建立。这一时期,当地政府部门的作用同样重要,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鼓励和保证关键连接的建立,此外,当新的产业引入需求产生后,政府可以为新产业的建立创建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鼓励人才和技术流入。
(二)网络加速演化阶段
随着产业网络中既有产业与新进入产业之间的合作联系日趋稳定,网络新节点的产生模式也日趋成熟,各个企业开始展开业务,互相建立更为深入而广泛的联系,同时,各个企业的影响力不断得到扩散。新进入网络的企业不但要考虑区域的资源禀赋,同时也要考虑潜在的合作企业情况,以及其在产业网络中的生存战略。正确的发展战略会形成良性的反馈效应,使新进入网络的企业迅速获得有效的协作,得到充分发展。在此基础上,企业之间的联系逐渐深入和多样化,为企业的影响力扩散提供了强大的载体。随着演化的进行,区域产业需求的不断丰富,新进入企业的类型不断增多,企业的影响力也趋于多样化,复杂网络的成熟形态渐渐出现,产业的集群效应日趋明显,各类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流动会形成某些特定的方向,一些企业开始产生规模效益。
随着区域资源流动形成特定的模式和方向,一些学习能力强、技术领先、善于创新的企业逐渐获得较大的影响力。企业影响力的不断增大,使得产业网络内越来越多的新节点与其产生联系,对于这些影响力较大的企业而言,由于中铁生态城与一般产业集群相比具有需求结构多样化的特点(并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因此其协作关系是广泛而多样的。这些企业之间有相当高的互动频率,网络的传导效应日益凸显,在这一效应的作用下,近年来,相对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房地产、生态治理、体育文化产业逐渐成为中铁生态城内影响力增幅较大的产业,并各自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理念。而对于新进入的或影响力较小的企业而言,其协作关系则可能会越来越趋于单一,产业发展的多样性会受到影响(例如房地产项目占据较大比例),随着网络演化的进行,网络的筛选机制以及影响力的“马太效应”凸显。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这一阶段,产业网络主体数量、影响力、多样性增加,产业发展速度较快。这一时期,政府部门的作用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鼓励产业主体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使生态城的产业链更加紧凑;另一方面则是继续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维持生态城产业的多样性。
(三)网络可持续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生态城产业网络发展的涌现阶段,产业网络的规模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后,资源不断聚集,人力、资本、技术不断投入,当其达到一定阈值后,则会催生高新技术产业的涌现。经历了前两个阶段的资源积累,当生态城产业网络内的企业数量、人力资源、需求达到一定数量后,网络节点之间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互动和联系强度同时得到大幅提升,大量主体成长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网络节点,而影响力较大的节点之间也同时形成了长期、稳定、紧密的合作关系,网络的聚合系数不断增大。企业节点的新增机制、连接建立机制、演化规则逐渐稳定,知识溢出效应明显,网络的规模逐渐呈现幂律分布的态势。此外,基础产业以及配套设施已经完备,基础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源与需求对接条件已经完备。
连接多样性是涌现产生的重要条件。随着网络演化的不断深入,企业自身的资金、技术、人力投入不断增加,企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相同类别的新产业进入产业网络并获得生存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因为有的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和竞争优势。这一阶段网络规模增长的主要需求在于新兴产业的建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产业出现的条件一方面在于产业网络中主体和连接的多样性,形成多种资源的协同流动,另一方面在于网络功能的多样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投资风险,消除单一行业的区域性垄断。可见,在这一演化阶段,政府相关部门的作用依旧在于继续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维持生态城产业的多样性。
五、结论
生态城产业网络的产生、演化、发展,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由本文的演化结果可知,企业之间的连接合作强度是影响网络性能的重要因素:
第一,就网络特征而言,减小新进入节点与生态城内既有产业的联系强度可以有效减缓影响力较高企业的影响力积累速度,从而使新进入企业仅与影响力较高企业建立连接的概率降低,有效增加网络聚合系数。另一方面,减小新进入节点与生态城内既有产业的联系强度会使网络节点的度数分布差异显著增大,节点度数很大的“超级节点”数量显著减少,同时度数很小的“孤立节点”数量显著增加。因此,对于实际当中的生态城产业建设而言,应当鼓励各种企业之间开展广泛合作,尽量避免大量企业的合作集中于某些个别企业的情形。
第二,就影响力而言,一味减小新进入节点与生态城内既有产业的联系强度,会使新节点与既有节点建立的连接减少,从而使影响力的扩散传導受到影响,虽然可以使网络整体影响力的分布更加平均,但却会降低企业网络的整体影响力,不利于高端大规模产业的发展。
第三,就企业合作多样性而言,减小新进入节点与生态城内既有产业的联系强度大大限制了“超级节点”的度数和影响力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量新加入企业节点的连接多样性。
由此可知,新进入企业的合作范围、与生态城内既有产业的联系强度并不是越大越好,应该在“影响力”与“多样性”等主要指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如果生态城产业网络的建立以创新产业的孵化为导向,则可偏重于适当减小新进入节点与生态城内既有产业的联系强度;反之如果偏重高端大规模产业的规模经济,则要适当增加新进入节点与生态城内既有产业的联系强度。
[参考文献]
[1]Tjallingii S P.,Ecopolis: “strategies for ecologically sound urban development”, Backhuys publishers,1995, pp.17-30.
[2]李春发、曹莹莹、杨建超等:《基于能值及系统动力学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可持续发展模式情景分析》,《应用生态学报》2015年第8期。
[3]D.J. Watts, S.H. Strogatz.: “Collective dynamics of small world networks”, Nature, Vol.393, No. 4, 1998, pp.440-442.
[4]Zaragosi S, Bourillet J F,Eynaud F,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y Structure in China: An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anagement Review, Vol.26,No.6,2013, pp.317-329.
[5]孙锐、姚苏秦、刘闲月:《集群式创新网络中企业创新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年第23期。
[6]李晓青:《复杂网络视角下的产业集群网络演化模型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7]Sun M, Zhang P, Gao C, et al.:“Study on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enterprises: A complex network perspective of Chinas PV enterprises”, Journal of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Vol.8, No.6,2016, pp.1-16.
[8]Yu W L.:“Evolution Mode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of Software Enterprise”, Applied Mechanics & Materials, Vol. 539, 2014, pp. 355-359.
[9]谢逢洁、崔文田、 武小平:《快递产业竞争关系网络模型构建及结构特性分析》,《系统工程》2017年第7期。
[10]马永红、李欢、周文:《产业转移驱动下的欠发达地区企业创新合作涌现——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系统管理学报》2016年第5期。
[11]Kenworthy J.: “The eco-city: ten key transport and planning dimensions for 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Vol.18, No.1, 2016, pp.67-85.
[12]Huijuan Dong, Tsuyoshi Fujita, Yong Geng et al.: “A review on eco-city evaluation methods and highlights for integration”, Ecological Indicators,Vol.60, 2016, pp.1184-1191.
[13]Fei J, Wang Y, Yang Y, et al.:“Towards Eco-city: The Role of Green Innovation”, Energy Procedia,Vol.104, 2016, pp.165-170.
[14]董微微:《基于复杂网络的创新集群形成与发展机理研究》,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3年。
[15]贾晓辉:《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产业集群创新主体行为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位论文,2016年。
[16]阚双、郭伏、 杨童舒:《多组织知识学习超网络模型及其学习绩效研究——面向复杂产品产业集群》,《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7]Powell W W,White D R, Koput K W, et al.:“Network dynamics and field evolution: The growth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life sci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0, No.4,2005, pp.1132-1205.
[18]吴杨、李学伟、李雪岩:《铁路建筑企业生态城产业结构多目标优化》,《铁道工程学报》2018年第9期。
[10]馬永红、李欢、周文:《产业转移驱动下的欠发达地区企业创新合作涌现——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系统管理学报》2016年第5期。
[11]Kenworthy J.: “The eco-city: ten key transport and planning dimensions for 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Vol.18, No.1, 2016, pp.67-85.
[12]Huijuan Dong, Tsuyoshi Fujita, Yong Geng et al.: “A review on eco-city evaluation methods and highlights for integration”, Ecological Indicators,Vol.60, 2016, pp.1184-1191.
[13]Fei J, Wang Y, Yang Y, et al.:“Towards Eco-city: The Role of Green Innovation”, Energy Procedia,Vol.104, 2016, pp.165-170.
[14]董微微:《基于复杂网络的创新集群形成与发展机理研究》,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3年。
[15]贾晓辉:《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产业集群创新主体行为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位论文,2016年。
[16]阚双、郭伏、 杨童舒:《多组织知识学习超网络模型及其学习绩效研究——面向复杂产品产业集群》,《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7]Powell W W,White D R, Koput K W, et al.:“Network dynamics and field evolution: The growth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life sci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0, No.4,2005, pp.1132-1205.
[18]吴杨、李学伟、李雪岩:《铁路建筑企业生态城产业结构多目标优化》,《铁道工程学报》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