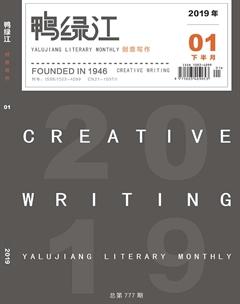数字游戏的现在与未来
何威 张圣林 张羽莎
何威:我是研究者,我在大学里教关于数字媒体相关的内容,我也研究跟游戏有关的议题。同时很幸运,认识很多年轻的游戏研究者,正在一起开展中国的游戏研究和游戏批评。目前我们国家的游戏研究落后于业界的发展情况,也落后于社会的需求。
我想讲的主要是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关于游戏到底是什么。过去我们经常会听很多不玩游戏的人乃至媒体有一种话语,把游戏比作数字毒品或者电子毒品。任何的比喻都是有力量的,它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限制了我们对现实改造的力量。我有一个更恰当的比喻,我觉得游戏是生命之糖,像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糖。糖给我们愉快的感觉,在座的年轻人喜欢珍珠奶茶或者蛋糕,这其中都有糖的存在,游戏和糖一样,带给人愉悦和快乐。第二,糖除了带给你快乐,也是我们人体能量的来源,是我们身体进行化学反应不可缺少的环节。游戏也是这样,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在我们社会化的过程中,游戏默默承载了特别多的功能,情感的、教育的、心理的功能。第三,糖会让你越吃越想吃,形成依赖。游戏也是这样,因为它太让人快乐了。第四,糖吃过量了,会带来非常多害处,包括长胖、蛀牙、营养不良、心血管等一系列疾病。游戏玩过量,同样有害身心健康。我们用这样一个比喻,既可以看清楚游戏对我们每个人、对社会的重要性,又能够提醒我们,游戏本身没有原罪,更重要的是玩什么样的游戏,怎么玩,怎么控制平衡。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游戏是糖。
第二个观点,游戏首先是一种信息的载体,是一种传播媒介。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你很难讲读书就一定是件好事或坏事,或者看电影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玩游戏当做坏事?任何一种媒介承载的内容,其品位和表达、艺术水准、思想境界上都会有高低优劣之分,游戏当然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有选择地培养自己的游戏素养,不要一棍子把所有游戏打死,或者觉得所有玩游戏的孩子都是坏孩子。同时,游戏也是文化的传承和艺术的载体,例如《尼山萨满》,又或者是今年的《中国式家长》《太吾绘卷》等游戏,或许他们都不完美,但每个都体现了创作者认真的态度,有的是想通过游戏探讨严肃的社会议题,让大家亲身体验,共同思考和交流;有些则是把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或者民族文化通过游戏带到我们面前。今天早一些时候在主论坛里面,敦煌研究院院长讲得很有道理:当新兴的互联网公司通过新兴的媒介形态,引发了年轻人对敦煌的兴趣之后,在网上能搜到哪些更深刻的、更有价值的关于敦煌的资源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些敦煌研究专家的责任了。同样,年轻人由于玩这些游戏,对于传统文化、历史、严肃而深刻的社会议题感兴趣之后,他们在我们社会中能找到更丰富、更深入的资源去进一步学习、了解、思考吗?这就不仅仅是游戏公司的责任,而是我们社会中相应的各个组织机构、也包括学界的责任。不管是讲好中国故事,还是振兴民族文化,这种责任都不是游戏公司或者网络公司能完全承担的,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工程。
第三,娱乐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各个游戏公司都在力推功能游戏,要由此提升自己企业形象,也尽到社会责任。但是我作为一个游戏玩家,觉得每一个玩家都有追逐自己快乐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放松的权利。一个游戏如果做的好玩,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至于其他更多游戏的功能的实现,以及更好地、更平衡地玩游戏,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共同负责。
张圣林:我叫张圣林,大家都叫我小黑。我参与了《尼山萨满》的开发,《尼山萨满》从开始到现在,拿了三个奖项,一个是英国Casual Connect的最佳英语,美国IndieCade Festival的最佳美术。前几天在中国南京拿了IMJA的最佳音乐。这些奖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了,相当于拿了独立游戏届的最高奖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独立游戏在制作过程中怎么把真正优秀的好的传统文化,或者现在已经不那么流行的文化怎么转换成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我希望分成两部分讲。我们真正做游戏德人看来,游戏最重要的一点,它其實不见得是故事或者是其他东西,游戏会被我们理性的拆成不同的部分。我认为把传统故事翻译成游戏过程中只有两点:一点叫标准故事,一点叫核心玩法。
先讲核心玩法,或者叫核心机制,它是游戏最重要的东西。游戏的每一类玩法通常都是被定义过的,而且游戏的玩法是从游戏开始的那一刹那就被迭代过来的。比如说《王者荣耀》目前的玩法是被定义为做MOBA,它是从六七十年代的脉络过来的。在制作游戏的过程中,核心玩法相当于这个游戏的顶层设计。每一个玩法在设计过程中都需要考虑很多的内容,因为他后面需要加设不同的模块,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很多人配合。我个人认为游戏是一种工业产品,不是一个匠人自己捣鼓捣鼓就可以做出来的。需要专业的美术、专业的策划、专业的设计和发行,需要成建制的人来把每一步都做好。一个核心玩法,如果我们故事的核心目标,或者游戏的核心目标是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故事翻译成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它的玩法和故事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游戏一定要创新,不创新的玩法不能吸引玩家。因为玩家是喜新厌旧的。一个核心玩法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说什么都不为过。
在《尼山萨满》的设计过程中我们有多次的反复,我们这个小队有六个人,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对游戏策划和设计的积累不是很深厚。我们一开始想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玩法,比如说会不会像《超级玛丽》那样的横版,或者是像推箱子,后来我们都没有选择这样的玩法,首先是很现实的考虑,你这个团队能不能支持这样的玩法。现在有无数种是横版过关,这是非常难以设计好的游戏类型,因为首先做这个游戏的高手太多了,历代的天才们都是从横版过关推箱子设计起来的,他们积累了那么多,设计了那么多游戏游走、美术风格,你很难超越他们,而且你很容易让你的核心玩法和这个故事不容易团结在一起。另外一个考虑,我们只有6个人,游戏画面每一帧都需要非常多的人和技术来堆叠。后来我们想办法,我们能不能做一个音乐游戏,这比较符合我们设计团队的设计实力,怎么能够保证把我们的故事挪到游戏里去。
一个音乐游戏到底怎样才能真正结合到这个故事的本质上去?我们这个游戏最后设计的是一个半圆形向心的音乐游戏,它的故事就是把《尼山萨满》的萨满鼓,当怪物碰到光罩的时候,玩家可以以防御型的心态把这个怪物击碎成纸片。我们设计过程中迭代了一次又一次。这个游戏为什么好玩?他可以帮助不会演奏乐器的人跳过学习乐器的阶段,直接进行演奏,所以获得快感。所以我们机制不能做太复杂,玩家都没有乐器基础,对于节奏感也不是很强。音乐游戏最常见的核心是摞圈。任何一个玩家,如果没有任何音乐和乐理技巧,他完全没有问题,我会看到一秒、两秒、三秒,他会点,我们意识到这种玩法可能会承担一种风险,所有怪物都会以曲面的方式来进攻光罩,这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而且不是非常成熟的机制。我们把直线运动变成曲面运动这样一个小游戏的变化,会导致我们会失去很多玩家。游戏的核心玩法是非常困难而且重要的,我们设计过程中迭代了很多次,最后在各方的妥协和协调之下,包括我们自己的实力,我们游戏的故事能不能转换过来,我们底层程序能不能做到,老师们觉得怎么样,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我们选择了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在我们看来已经是最优的了。最后我们得到的成绩也显示出,我们做了一些微小的创新,因为很多人还是玩得不够开心。
我相信所有人感到最惊艳的一点就是《尼山萨满》的核心玩法是非常合适的,你的游戏判定本身是萨满鼓来防御,你做的基本事情就是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我们确定了核心玩法之后,比较困难的是,如果核心玩法被确定了,游戏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也是肯定的。《尼山萨满》的真实游戏时长是5个90秒,一共就是450秒,如何把很复杂的长故事和传统的文化故事转化成我个人愿意叫它标准故事的故事。标准故事是各种口头的版本,经大家转来转去之后,转换成大家喜闻乐见的标准版本。虽然这个故事一直存在,但是长时间只存在说书人的说书里,或者是民间祭祀里,它的故事不被发现,直到几十年以前,才有了这个游戏的六个抄本,有了抄本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故事非常复杂,因为是由历代说书人传下来的。是几个小故事连在一起的。说书人说到这儿,觉得不行,我今天要加一段,下一个说书人说来说去,觉得不行,我这里要再加一段。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布达佩斯大饭店》,我看到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讲的事情是经历了什么故事,他是故事的嵌套结构,把这些说书人结构用的比较好的人是金庸,比如说《射雕英雄传》开始说的是江南七怪,江南七怪是为了引入后面的主角郭靖。大家现在愿意花时间读这些故事,并且从中获得很重要内容的精力和能力都没有那么强。如果我们把这些故事翻译成现代人喜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转化成标准故事,这其中可能会有信息的损失,但是我们不得不做。这件实行是我在做《尼山萨满》的时候感触到最深的。做出来的产品,我们能够讲出来的东西很少。《尼山萨满》的剧情是由几个不同的地方拼出来的,首先是游戏背后是一个收藏版,第二个,游戏开篇有一两句诗,引导你这里面讲的是什么。第三,开头片尾的侧记。第四,暗示你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把文字拆解,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你把一个杂糅故事变成一个标准故事的要点有很多,首先你要明确你的核心玩法能承载多大的信息量。然后你去截取游戏里能够遇到的最重要的,你认为故事最核心的内容,《尼山萨满》故事核心内容,我们六个人都读了这些故事,哪一段是你能够记下来的,大家投票,《尼山萨满》这个故事本身说一个尼山接受了一个很不可能的任务,他要上天入地把一个小孩被掳走的灵魂带回来。这个故事的最精彩的地方是尼山把小孩的灵魂救出来了,但是遇到了一个恶魔的阻拦,尼山说,我必须要把这个孩子带回去,这个恶魔说,那我给他二十年的寿命吧,我让他活到二十岁。尼山说,不行,二十岁他还没有完成生命中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娶妻生子,恶魔说,那我让他活到四十岁吧,尼山说,不行,四十岁他还没有为部族做贡献。就这样一直讨价还价,最后恶魔说,那我让他活到八十岁吧,那个时候,这个孩子会生很多小孩,会有美满的家庭,会为部族做很多的贡献。这样够不够?尼山说够,然后带人走。這一段讨价还价的过程,发生在尼山惊心动魄的上山之后,它其实是抗辩的过程,尼山这个时候代表人类的律师,恶魔不太在乎人类的寿命,但是人本身会很努力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有自己的执着。这是我们认为全剧最大的矛盾和核心,我们抽取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人如何像尼山一样勇敢面对死亡。我们会围绕他来做故事。
我们参考了很多,最后选择的是依靠情绪曲线来进行参考,你在不同时间内感受到的情绪,有高潮、低谷,我们设计了一个曲线,把核心玩法按照剧情排在这些曲线上,然后进行打磨,最后形成了这个作品。
如何把传统文化故事翻译过来,第一,核心玩法,第二,标准故事。这两类东西能做好,基本上它的雏形是存在的。
张羽莎:我们团队内部也有一些讨论。我来自研发团队,现在团队在做《王者荣耀》世界观的构建,以及《王者荣耀》IP往外延伸、授权的工作。团队内部也在探究,基于现在那么荣幸的能够得到大家喜欢的玩法之外,整个游戏往后能够争抢用户黏性、提升游戏生命力的点在哪里?很多调研和座谈,我们都发现,玩家们给了我们很多很真实的反馈。大家希望能够增强和英雄、和角色的认同感和情感共鸣。这也是今天我在第一场主论坛的时候得到了戴锦华老师很大的感动和启发,让我对我们之前思考很笃定的地方。游戏作为一个媒介的代表,不仅限于在娱乐和体验上面的呈现,还应该是在精神层面,而且还对此抱有信心。从用户诉求和我们自己的感知来讲,这一块都是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内涵可以让游戏更富有生命力的基石。我这次过来还带着探寻和请教的目的来跟各位老师交流,我们现在在游戏内角色的塑造、场景的设计、音乐的选择,都是以文化为基石的,但是也很荣幸,《王者荣耀》得到了很多人喜欢,用在游戏内的这些点得到了很多人喜欢和讨论,也成为新的文化触点。就像李白和前年《霸王别姬》出来之后,英雄在故事背景和台词上面,还是引用了很多诗词和戏曲唱段,很多玩家通过李白很热烈的讨论《将进酒》,通过《霸王别姬》沿袭京剧的精髓,让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和荣幸。
整个过程刘老师也在问我,能不能跟大家分享研发的过程,我觉得是两个路径,一个是扎扎实实的去传承我们文化的来源。另外,要赋予时代语言。两周年的时候我们出的《游园惊梦》甄姬的皮肤为例子,当时甄姬的皮肤已经选了《游园惊梦》的段子,从美术和特效都做了比较好的还原,如果最能体现的应该还是在角色的台词和唱段上面,希望能够把这个引用到游戏里面去。我们就去联系了魏春龙老师,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梅花奖金奖的得主,我们找到他,希望能给年轻人们还原一段非常精粹的内容。魏老师一开始是犹豫的,他觉得我的作品放到游戏,年轻人会接受、会喜欢吗,或者我的同行怎么看我。他会有这样的顾虑。我们也会有一些技术层面的考虑,包括昆曲的音线,配合游戏音效、打击的点能不能配合。跟魏老师以《霸王别姬》做了一个案例,魏老师很开放,愿意做尝试,我们团队跟他一起在北京找了录音棚,当时我们所有人的疑惑都在魏老师开嗓那一下全部打消了。他一开嗓,文化的纯粹和穿透力把所有录音棚里的人都震惊了。我们说,这个能成。最后到游戏内以后,我们的特效和打击点跟唱段进行了调整,最后这款活动保有量还是比较高的。这是在传承上面的一个点。
在赋予它新的时代语言上面,还是以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案例,在去传承魏老师的内容之后,我们又请了一位比较年轻的昆曲演员叫蒋柯,他跟魏老师形成老一辈艺术家和年轻演员搭档的组合,一起对这个唱段进行了作品的创作。魏老师更多在游戏内的语音,声音的节目上面有内容。蒋柯更多在平面宣传内容和线下活动,去跟二次元的用户们见面。这个作品最后在传递上也是比较成功的。在后面coser的演绎上面,也会选用蒋柯创作出来的作品内容和美术的表现。
还有北京的一个润化团队,做了定格动画,是用人偶来做的,当时动画有一分多钟,每秒24帧,每帧舞蹈动作的手腕、手指头变化都不一樣。出来之后,后台玩家们反馈,这次天美策划还是在用心做这个内容。还看到一个女孩的回复,她说每一期我们推的社区的贴子她都看,这是她第一次回复,她是学舞蹈的,她特别能够理解舞蹈的美丽在于用心和用情。她通过这样一个定格动画感受到了运维,也感受到了动画创作团队在背后的付出。这个项目里,它也结合了比较传统的昆曲的东西,定格动画,现在在动画里面用的比较少的形式,传递给现在的年轻人。这个案子从传承到赋予它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语言,这样一个路径也是我们后来在复盘和总结的时候觉得后面要比较踏实的在研发团队里面推进的一个过程。
这一块还需要何老师专业的团队和您的学生给到我们实践性的项目更多的指导。怎么样让这些文化更有体系,感受到的内容更加的圆满。这一块还是要向各位老师做探讨。
何威:社会上之前一直有一个争议,《王者荣耀》到底会不会影响玩家的历史观,尤其是让小学生的历史观扭曲。我跟我的研究生合作,做了一个《王者荣耀》是否会影响大学生认知的研究。我们的样本有一千个大学生。我们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问他们,对历史人物的好感度,问他们有没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些人物,问他们对一些相关历史常识的判断。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调查和《王者荣耀》相关。直到问卷最后,他们才被问到《王者荣耀》:你玩什么英雄,游戏时长、频率、段位是什么。通过这个方式可以把玩家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最后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大学生里面,他们知道游戏跟历史不是一回事。游戏人物是建构出来的。但是玩家对自己熟练的英雄对应的历史人物的好感度,就是会比另外两个群体要高;想了解这个历史人物的意愿也更加强烈。即使我们是一个理智的成年人,我们知道游戏和现实的差异,我们的认知也可能会被游戏影响。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你们觉得诸葛亮那么好,但其实没有一个人认识活着的诸葛亮。大家通过影视、小说、历史材料去了解诸葛亮。有几个人真正读过最严谨的历史材料?而且即便是历史材料同样也只是历史作者的叙述。区别在于,你们的父辈一听到诸葛亮,头脑里立刻浮现一个唐国强;在座各位听到诸葛亮,头脑里浮现出来的是《王者荣耀》里面那个帅哥、强大的中单法师。因为你玩这个游戏,你可能想去了解曹操、诸葛亮更多的情况,可以成为青少年更深入了解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游戏公司也可以作为一个桥梁,例如提供一些视频、链接,让大家更顺畅的找到进一步学习所需的资源。
提问:我是来自北京一名大学生,成为游戏制作人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第一,我作为一个游戏玩家,我玩的最多的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有的游戏定位是非常好的,但是有很多的功能并不受玩家的喜欢,导致了玩家的丢失。如何解决游戏制作人本身很喜欢的内容,但是玩家并不喜欢的内容?在前期能不能规避这样的问题?《尼山萨满》是您制作的一款独立游戏,像这样一款游戏是怎样从最初的构思到做成成品,大概制作流程前后顺序是什么样的?
张圣林:MMORPG这种游戏类型设计的功能不太可能是所有玩家都不喜欢的,他会先进行假设,假设完了会有一条很严谨的逻辑推理,甚至市场投放,反复测试,他要保证抓住更多的用户时长,获得更多用户付费。在这种前提下,不可能是制作人想加什么功能就能加上的。也许你遇到了一个不喜欢的功能。你可以想一想这些功能是服务哪些付费用户的,你也许可以想一想这方面的内容。在我浅短的业界经历里很少有MMRBG游戏设计人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我们通常被分工成三类,策划、美术、程序。这三类在真正独立游戏制作人那里是合并的。但是我们不能自己全部做,只能把它分成三类。我们先找到一个合适的版本,然后往里填充内部,我们会分别回头看这个东西是否合适,在游戏基本没有做完的时候,我们会执行一些比较内部圈子里的试玩和测试,保证大家的观感和我们的设计是基本一致的。需要在游戏一开始设计好,并且在小样时期都完成,后期不会砍倒重来。游戏是工业产品,和软件一样,越到后面改,你要付出的代价越大,所有事情必须在开始想清楚,并且最后逐步验证,最后逐步验证如果有不对的也需要微调。
(何威,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创意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圣林,《尼山萨满》制作人。张羽莎,腾讯互娱《王者荣耀》IP建设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