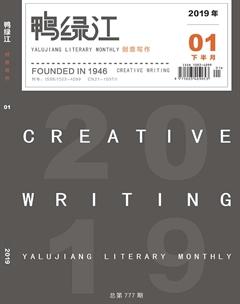怀着对鱼的向往忘掉江湖
说的是老蕭的酒事儿。
老萧,名立军。传说是契丹人的后代,自称萧太后的子孙。高大的北方汉子,他长着一副马脸,眼睛不大,鼻子不小,身材高大,肩宽臂长,腰背笔直,走起路来腿脚生风,跳墙爬树身手不凡,拈花惹草轻车熟路。江湖上无论年长还是年少,都喊他“萧哥”。就连30年代出生的翻译家叶廷芳、学者谢冕、作家玛拉沁夫见面都喊他“萧哥”。当年六七岁的小姑娘张之汇从认识他那天起,就一直叫他萧哥,如今张之汇上了大学,仍叫他萧哥。
也有人直接喊他“马脸哥”。这缘由他写的一篇散文《小眼睛的莫言和马脸的我》,这篇散文写得着实精彩,当然也与酒有关。其中这样写道:“1985年因为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我去过两次军艺看莫言,有一次在他那里吃饭,就到食堂吃。那时候大家都没钱,我一个月60元钱,而莫言的津贴费也不多。可即使这样,莫言知道我好酒,还特意给我买了两瓶啤酒,我就着白菜炒肉片、芹菜花生米喝上了。这莫言老弟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老萧也跟着火起来,各路记者都知道老萧是莫言《秀明的红萝卜》的责任编辑,都要抢先采访个“内幕故事”,于是老萧的照片也上了各大报刊,竟然有人把“小眼睛的莫言”和“马脸的我”两张照片拼在一起,有创意。莫言小眼,老萧马脸,一对说相声的好组合。
已经忘记何时何地何认识萧哥的,好像认识了一辈子。他话不多,做人很低调,只有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或者喝酒时,才会自由奔放甚至纵情。他的肩膀很宽壮,腰杆永远笔直,如一棵北方的白杨树,挺拔刚健,看着他那么直直地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朴实的脸,甚至让人有些羞愧。他为什么长那么高?总是那么直?高而且直的让人很惭愧。难道我们做错了什么才弯曲低矮吗?有时替他感觉到累,总是这么高而且直,难道不累吗?不需要弯弯腰歇歇吗?委屈一下自己不行吗?他就这么很耿直地跟现实人生打交道。他是明白的。但,他宁折不弯。腰杆就是这么直!
他抽着烟,皱着眉头时,新鲜的想法就来了。喝酒喝到畅快时,也会出来很奇特的想法,据说他有很多醉酒的事,我没有亲见,我见到的萧哥都是喝到有几分酒意,放情谈他的感觉,他的想法,他对文学的理解,那时,感觉他是一个文学的殉道者。从80年代到现在快40年了,他都在全身心地爱着文学,让人不得不因为敬重他而敬重文学了。
我喊他萧哥,我女儿也喊他萧哥,辈分有些乱,乱就乱吧,谁让他是大家的萧哥呢?萧哥做的鱼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鱼,甚至大家起哄让萧哥不当主编了,改行当厨师吧。萧哥太热爱文学了,为了文学而献身。
——摘自高秀芹《文学汉子萧哥》
上边这段精彩的文字,是北京大学高秀芹博士为老萧生日的贺辞。在中国,持续不断地在文学编辑岗位上工作40余年的人,不是很多。老萧却是之一,他被业界称为“国编酒圣”。
说酒事儿。
关于老萧的酒事儿,相信他的文友朋友都能说上一二三四。无论是道听途说还是亲临现场,我也能讲出个五六七八。老萧当编辑这几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也编辑发表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如蒋子龙、冯骥才、王安忆,这都与酒有关。他经常说:感谢酒!
喝酒要讲场,场子对了,喝着顺溜,醉得舒服,老萧是不能一日无酒。保守地算,老萧喝酒抽烟的历史至少也有50年。
前不久,写出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作家熊召政给老萧算了一笔账,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熊召政掐着指头说:话说老萧,就按一天喝六两酒,一个月喝18斤,一年喝216斤。他说从1968年16岁下乡当知青开始喝,到2018年正好喝了50年,至少喝掉10800斤酒。
我认为熊召政只是估算,这个数字实在保守。从历史事实考察看,就算当知青上大学时每天六两酒,但自从1978年26岁以后,先后到《文艺研究》《中国作家》当编辑,这40年每天平均至少喝八两以上的酒。到今天大约能喝掉15000斤白酒,约7.5吨酒。这个数字还是在保守的正常情况下计算出来,超常规的情况也非常多,毛算喝掉8吨白酒,不算是瞎吹牛。可以想象为一个若大的8吨酒池。
喝酒必抽烟。
作家熊召政又算了一笔账:老萧平均一天抽三包烟,一个月90包,一年一百多条烟,按烟龄算抽了35年,也抽了约4千条烟,正好是一辆8吨厢式卡车一整车,要是集中点着,让烟自燃,也得一整天才能烧透。我认为熊召政这个数字还是有些保守。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经熊召政这么一算,老萧却感到荣耀,感慨万千。还要感谢烟酒,让他至今身体没有一点不适,也没有“三高”。知道老萧身体好,常有人问他健康秘诀是什么,他又吹牛说:抽烟喝酒不锻炼。这不是气死医生吗!很多朋友建议:你老萧活体捐献给医学得了,做医学研究。
除了抽烟喝酒,老萧其实还嗜茶。他曾写过《端起人生这杯酒》,也写过《烟雾缭绕的岁月》,但他没写过茶。他说陆羽已把茶写得太透,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非烟酒可比,可不敢在茶上做文章。老萧爱烟爱酒,烟厂酒自然去的不少。从北到南至少去过六七十家烟厂,酒厂去的更多了,从国酒名酒的酒厂再到地方小镇的小酒厂,少说也去过一百多家。他认为酒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联系,因此他也搜集了很多有关酒的资料,他收藏不少“酒典”类的辞书。所以,他对酒尤其是白酒,还是有基础的认识。他说很多喝酒的人,真正懂酒的人少。这也许与他“喝明白酒、做明白事”的习惯有关。
老萧是出了名的工作狂。他一年除了出差,整天都在办公室。谈选题、抢稿子,编稿子,给作者打电话,骑自行车到作者家里去亲自抄稿子……他是一位优秀的职业编辑。他轰动文坛的长篇纪实小说《无冕皇帝》,就是对一位编辑的写照。
老萧的办公室极其乱,但却极其有魅力,无论多大名气的人物,到了他那里,就会特别放松,就像农民在田间地头可以盘腿大坐,海阔天空无限地神聊。一会功夫,几个烟缸就满了烟灰,只见办公室内浓烟弥漫,那个透气的窗纱早已变为实心黑布一块。因此,翻译家汤永宽说老萧的屋子可用得上:“室雅何须洁,花香不在多”。可以想象,有多少好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神侃出来的。
作家卢跃刚到他的办公室聊稿子,老萧顺手启开一瓶啤酒,卢跃刚说不会喝酒。老萧说,爱喝不喝,水,没有!卢跃刚为了听取审稿意见,只好喝酒。从此后就上了酒隐,他每每再来,自动就会提几瓶啤酒上来,跟老萧就着大蒜,吃着卤猪蹄子。
如果是众多人吃饭,老萧常常是话不多,他喜欢听别人多讲。老萧的酒风是喝慢酒,频繁举杯,如果每次都是举杯一饮而尽,他也会当场倒下。他的原则是总量控制,绝对不会少于别人。但是,也没少出洋相。有一次出差,在上飞机前喝高了酒,上了飞机就大睡,一个小时飞行时间,落地时他还在睡,飞机上所有的人都下完,就是叫不醒他。几位乘务员一起拉他,却拉不动,他嘴里还不停地说“让我再睡会儿”。耽误了好一会儿,几个大小伙子硬是把他抬下来。老萧是讲信誉的人,他对朋友十分忠诚,他善良而热心,大家喜欢与他喝酒聊天。
写出《马家军调查》《强国梦》《兵败汉城》的作家赵瑜讲,有一次他们几个哥儿喝酒,老萧为了策划赵瑜的新作《寻找巴金的黛莉》在《中国作家》发表的事,大家高兴,喝着喝着,也不计量了。不知啥时,再看老萧竟然扒在饭桌旁睡着了。大家继续聊,等了好久他也不醒,最后赵瑜想了一着,把他抬走,在附近找了一个小旅店,把老萧身上的钱和物都拿走,只给他留下零用钱,让他睡吧。第二天,老萧醒来,不知自己是在哪里,摸着兜里钱包手机都没有了,只有10元钱,他打车回单位,再问赵瑜,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作家赵瑜已是一线当红作家,他对编辑非常尊重。赵瑜跟老萧的友情也是编辑与作家的关系开始的。当年大家熟悉的《马家军调查》是极为轰动的报告文学作品,这部刊发可是一波三折,如果没有老萧的细致策划,这部作品的命运不知如何。作家和编辑的关系,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作家的名气再大,也有编辑的一份。多少年来,赵瑜一直称老萧为“萧兄”。这一声“兄”,包含着很深的情意。后来又策划了很多重大的选题,比如山西作家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也是在“不顺”的状况下几经周折发表出来。如果没有一位好编辑的精心策划,也许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也就没有后来的影响。
有人說编辑是“无冕皇帝”,手中掌控一部作品的生杀大权。其实老萧也写过很多作品,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文学评论等,但是他自己认定再怎么写,也写不过一流的作家,顶多能混上个个三流作家称号。于是他醉心要当一位中国一流的编辑。他做到了。
文坛酒事,老萧永远是话题。编辑家张守仁称老萧是条汉子。散文家韩小蕙称老萧为大男人。高秀芹博士称他是文学汉子萧哥。老萧不可一日无酒,更不能没有朋友。这一切都因老萧的仗义、豁达、善良和热情的人生观了。他把文学编辑事业视为宗教和信仰,他敬重他所爱的编辑职业。
老萧为了文学,前半辈子喝了七八吨酒,若是泡在酒池里,也是死过几次的人了。
他看清了人生和这个世界。
老萧还有一手绝活儿:做鱼。
他最大的理想是,等不当编辑时,淡出文学这个江湖。找个院子,专门做鱼。到时摆上个小桌,约上三五个老友,继续喝酒,聊江湖往事。那时,老萧的《我煮文坛这锅粥》也许就会问世了。
而眼下,他也只能怀着对鱼的向往忘掉江湖。
(朱竞,评论家,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