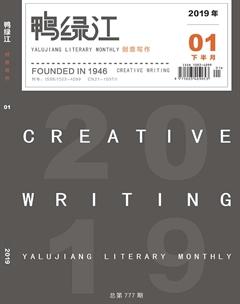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酒、色乃佛家之大忌,这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佛教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劝人戒除贪、嗔、痴,切断人生烦恼的总源头,从而脱离似无边苦海的轮回世界,进入不生不死、光明喜乐的涅槃境界。然而,酒、色二字就像是横亘在众生成佛路上的两座大山,是有情贪欲、执著和痴迷的总显现。酒、色既难戒除,则开口智悲,闭口色空,早上烧香,晚间拜佛,皆难成就任何利益。即身成佛无异痴人说梦,到头来难免再入六道中轮回。恶业既成,转生恶趣在劫难逃,来世是当饿鬼、做畜生,还是下地狱,由不得你我自己做主。
道理是如此的明白,要把它参透可让世间众生犯难。且不说那些无缘得闻正法的外道、邪魔,多少人就因为贪恋这酒、色二字,恣意作践、挥霍这千年难得的暇满人身,最后落得个早早被阎王爷收罗了去的下场,在热地狱中煎熬,在冷地狱中号叫,狱中刹那,世间千年。就是那些受佛眷顾的行者、僧众,也常有人无法摆脱酒、色的诱惑,犯下难赦的粗重堕罪,“净土变成欲海,袈裟伴着霓裳,狂言地狱很难当,不怕阎王算账。”多少世的青灯孤影、多少辈的苦行密修,统统前功尽弃、毁于一旦。本来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身边享受无边的喜乐,这下却不得不提前到阎王殿前报到,任由狱卒、小鬼们发落、蹂躏,呜呼哀哉!
世上有所谓“花和尚”“酒肉和尚”云云,事实上,和尚一花就不再是和尚了。邪淫戒就像杀生戒一样,和尚是犯不得的,一犯就决不见容于佛道僧伽,是要被开除僧籍的。可是,世上确实也有一些和尚、一些喇嘛,他们可以视酒色为无物,将酒戒、色戒一概置之脑后,相反把对酒色的贪恋表现得无以复加,却反而因酒色而留名,受万人膜拜,为万世传颂。例如,汉传佛教中那位看起来癞兮兮、脏乎乎的济公和尚,手里总拿着个酒葫芦,整日除了喝酒就是吃肉,自称“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疯疯癫癫、半真不假,“天南地北到处游,世态炎凉全看破,哪有不平哪有我,南无阿弥陀佛”。大家知道,济公和尚虽然行为荒诞,却慈悲为怀、法术无边,行止更像是一位具无量悲心的菩萨,他原本是一位对众生有大利益的活佛。
还有像藏传佛教中那位“不爱佛爷爱美人”的六世达赖喇嘛,虽然尊为天下活佛拿摩温,却半世尘缘,一生坎坷;传说他钟情于花容月貌的“未生娇娘”、流连于圣城拉萨的花陌柳巷,全不顾自己的相好庄严,也全不把佛家的百丈清规放在眼里,结果有情总被无情误,他被拉下了佛坛,夺去了菩萨果位,终于不知所终。可就是这位六世达赖喇嘛,他至今被全世界各色各目人等一起奉为“情圣”,他的“金刚道歌”被学者、爱好者和好事者们不断翻译、改编、甚至捏造成各种文字、各色情调的“情歌”,给在恋恋红尘中意乱情迷的有情众生带来传自佛国的启示和慰藉。谁敢说这位六世达赖喇嘛不是一位大慈大悲的真佛爷呢?
济公和尚也好,六世达赖喇嘛也好,他们可以如此疯癫、如此大开酒、色之戒,只因为他们决不是一般的和尚,也不是寻常的喇嘛。他们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无始以来便已修成正果,是不世出的“圣僧”(或曰“疯僧”和“疯圣”),是菩萨化身、是活佛。他们是放心不下我们这些还在六道中轮回、孤苦无依、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才重返尘世、应化人间的。他们的人生不过是一场游戏,是引导有情众生走上成熟解脱之路的宏化。只要能利益有情,能将他们普度众生的愿力发挥到极致,他们可以随机应变、为所欲为,酒、色又哪能成为他们的羁绊呢?
显乘的菩萨化身,像济公这样的汉地和尚,只不过是喝点小酒、吃碗大肉,如癫似狂,小施神通而已。而印度、西藏密乘佛教的大成道者们行为之癫狂和离谱则更让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于密乘(或曰金刚乘)佛教中,贪、嗔、痴不再被视为成佛的障碍,相反被转为道用,是众生成佛的道路。行者不应该对轮回与涅槃起分别心,作意戒除贪、嗔、痴,相反应该将它们当作修炼成佛的不二法门。从此,酒、色便不再是佛门的洪水猛兽,而是行者借以修佛成就的捷径。
印度佛教史上曾有著名的八十四(五)大成道者,他们各有超凡的神通、离奇的经历,其中一位名密哩斡巴(Virūpa),他是名副其实的“酒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密哩斡巴是一位密教行者,或称“瑜伽士”,早先修习喜金刚、胜乐和无我母等密教本尊,獲得超凡的成就。得道之后,示现种种希有神通,其中最匪夷所思的就是他为了能开怀畅饮、不付酒钱竟然让太阳足足停转了三天三夜。
传说有一次密哩斡巴携一弟子进一家酒馆要酒喝,店主是女流,有眼不识大德,竟然问他可有酒钱否?密哩斡巴让店主先供他酒喝,待他喝足后再总算酒账。可店主疑其囊中羞涩,追问他何时才能喝足?密哩斡巴便用随身携带的金刚杵在地上划了一道线,告诉店主说,只要屋子的太阳光影子到达这道线上他就付账走人。于是,密哩斡巴和他的弟子兀自开怀畅饮,很快就把这家酒店的酒窖喝干了。店主为了完成这桩交易,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从其他酒店买酒供他俩畅饮,直到把附近十八个大城市的酒窖全部掏干。据说密哩斡巴一个人就足足喝了五百头大象驮来的酒,却丝毫看不出他有快要喝足的迹象,而屋子的太阳光影也永远接近不了他在地上划下的那道线,原来密哩斡巴已经小施神通,手指太阳,让太阳停在原地不转了。
此时,整个城市已秩序大乱,接近疯狂。没有了白天和黑夜,没有了时间,城内居民纷纷抓狂,不知道何时该干啥、不该干啥,以致人困马乏,唯有望着永远不落下的日头发呆。更可怕的是,庄稼渐渐枯萎,河流也开始干凅。国王惊慌失措,急令臣下尽速弄清太阳停止转动的缘由。当国王最终弄明白原来是密哩斡巴为了赖掉酒账而让太阳停转时,便答应马上为他埋单,请求他赶紧让太阳继续转动起来。于是,密哩斡巴悄然隐身而去,太阳也终于再次旋转了起来,然此时已经是第三天的午夜时分了。
这位密哩斡巴当然不是一位贪杯的魔术师,他玩的也不是蹩脚的障眼法。密哩斡巴是印度密乘佛教之大成道者的典型,他的这个故事也只是印度大成道者种种非凡神通中的一个典型而已。他们视世间万有如梦幻往来,轮涅一如,生死无二,喝酒吃肉,无非幻化,一切都是游戏,世人千万不可当真。实际上,密哩斡巴是印度密乘佛教史上一位杰出的密教大师。他根据佛教续典《喜金刚本续》和《三菩怛本续》,再受无我母点拨而传演的一套甚深密法——“道果法”,最终成了藏传佛教萨迦派所传的根本大法,是藏传密法的重要内容。这套密法也曾在元、明间于汉地广为传播,深得蒙古、汉人信众喜欢。明代汉译的“道果法”仪轨汇集——《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共有十卷之多,其中的一部分至今依然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内。
当然大成道者们这些看似十分荒诞的行为、神通也常常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密哩斡巴上师当年就曾因在寺院里面喝酒和吃鸽子肉做的馅饼引起僧众法友们的公愤,最后被寺院方丈逐出僧伽。为了见性明志、教化有情,密哩斡巴一离开佛寺大门即显现神通,平步于莲花之上,水不沾履地渡过寺院前的湖泊,同时还将他吃剩的鸽子翅膀和骨头复活成一只比原先那只更加漂亮的鸽子。作为一名瑜伽士,又受金刚亥母怙佑和加持,密哩斡巴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显现像让太阳停转、令恒河改道一类希有的神通,无非是为了显示诸法如幻、佛法无边,以调伏外道、取信有情,激发起有情众生对佛法的无穷信仰。连菩萨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大成道者就能够做到,难道你等还敢不信金刚密乘佛法之威力和神通吗?
济公和尚和密哩斡巴上师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是佛教史家们刻意塑造出来的理想型的“圣徒”,碍难将他们视为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已经被不断地圣化和演绎,与历史事实早已有了很大的出入。对他们的行为和神通的理解事关佛教信仰,非历史学家所能随意臧否。然而,在离我们当下不太遥远的过去曾经出现过两位以酒色而闻名世界的西藏“疯僧”、活佛,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疯狂、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不幸,皆令世人为之动容、为之着迷,也深深勾起了善男信女们的恻隐之心。这两位西藏“疯僧”一位是被称为“安多托钵僧”的根敦群培先生,另一位则是人称“西藏嬉皮士”的曲江仲巴(Ch?gyam Trungpa, 1939-1987)活佛。他们同样是转世活佛、同样有盖世的才华、也同样沉溺于酒色、同样英年早逝,他们短暂的人生留下了太多让人惊叹,又令人遗憾的东西。他们的生活色彩斑斓、跌宕起伏,生前备受争议,身后捧为神明,当下他们的事迹也正在被不断圣化和演义之中。
近年来,笔者有缘多次阅读、观览过这两位“疯僧”的各种传记资料,常常被他们另类的人生经历所震撼,有时不敢相信这些都是发生在这两位西藏活佛身上的真人真事,掩卷又常难以自已,生起难抑的同情和悲悯之心。无明如我,殊愿他们端地是菩萨化现,但私心也常把他们看作如你我一样的有情,总觉得他们表面的疯狂掩盖着内心巨大的痛苦,他们那些惊世骇俗的行为与其说是游戏,不如说是出于无奈。于兹斗胆脱离前述之佛教语境,改从俗家的立场,做一番历史学家的功夫,对这两位“疯僧”何以如此癫狂、如此痴迷于酒色的缘由,权作些许纯属个人一孔之见的思量和揣度。
先说根敦群培先生。先生幼时曾被认定为一位宁玛派高僧的转世,故具活佛身份。但总其一生,活佛这个头衔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带来过尊荣富贵,他的口粮常常是用他一流的绘画手艺换来的,他的一切成就好像和他的活佛身份关系不大,他的行为可以像任何人,就是不像活佛,故笔者更愿意称他为先生。先生出生于西藏的艺术之都——安多的热贡(今青海省内),七岁削发为僧,先于支扎寺出家,后入拉卜楞寺学经;二十四岁入拉萨哲蚌寺深造;三十一岁开始周游印度、锡兰诸国,长达十二年;1945年返回西藏,不到两年即被投入监狱,遭囚禁几近三年。1950年秋获释,不久往生于拉萨,享年仅四十又八。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根敦群培显现出了盖世的才华。传说他通十二种语言,听起来像是传奇。但他至少精通藏、梵、巴利和英文等四种语言,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他曾协助俄国人George Roerich将藏文史学名著《青史》和法称的《释量论》从藏文翻译成英文,自己又将寂天《入菩萨行论》的“智慧品”从梵文翻译成英文。同时,他还将巴利文的《法句经》翻译成藏文,将《沙恭达拉》、《罗摩衍那》、《信仰瑜伽——大黑自在天之歌》、《事业瑜伽》、《度母圣言》等九部古印度文学名著从梵文译成藏文。众所周知,西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著名的大译师,但他们都只是梵藏、汉藏或者藏汉翻译的译师,译师的定义是“知两种语言者”,能将梵、巴利、藏、英四种语文互译的大译师迄今唯有根敦群培一人。
除了杰出的语文才能外,根敦群培先生还是一位学富五明的大班智达、天赋惊人的艺术(画)家,才华横溢的诗人,辩才无碍的论师、深具洞察力的哲学家、博古通今的历史学家、兴趣广泛的游记作家、术有专攻的两性学家、锐意改革的社会活动家等等。
他写作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游记——《巡礼周国记》,完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从人文角度探讨两性关系的性学启蒙书——《欲论》,他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利用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藏族古史的藏族史家,撰写了举世名作——《白史》;他写作的《中观甚深要点集萃之善说——龙树密意庄严》是藏传佛教传统中诠释中观学说著作中最富创意的作品;他还是“西藏革命党”的发起人之一,对改革西藏的政教体制充满了热忱和期待。
与此同时,根敦群培先生确确实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狂人。当他还在拉卜楞寺学经的时候,他就曾呵师谤佛,故意在辩论中站在外道立场上,为耆那教的“植物有情论”辩护,还对寺内最高佛学权威嘉木样活佛编定的教科书提出挑战,最后被逐出了寺院。进入哲蚌寺后,他师从的是当时西藏最权威的佛教学者喜饶嘉措大师,可他根本就不把后者放在眼里,常常出言不逊,狂言“喜饶嘉措懂的他根敦群培全懂,他根敦群培不懂的喜饶嘉措也一定不懂”,课上经常与老师大唱对台戏,极尽戏弄嘲讽之能事,被后者斥为“疯子”。
去印度后不久,他就把喇嘛和转世活佛的身份置之脑后,开始纵情声色、寻花问柳,成了风月场中的常客。他花了多年时间收集、研究《欲经》等三十余种印度古代性学宝典,并结合自己和印度、克什米尔女友们的房中实践经验,写成了一部專论男女性爱六十四术的《欲论》。待他从印度回到拉萨,则更加放荡不羁,诗酒华章,风月无边。不幸沦落囚牢时,据说他竟然向当局提出要允许他带个真人大小的充气娃娃和他一起入狱,以满足他在狱中的性需求。后来他在牢中居然还曾与一位目不识丁的牧羊女子同居,酒过耳热,兴致所致,照样赋诗浇愁。待终于从狱中获释,他却已经变成了一个离不了烟酒的瘾君子。
显然,早在去印度以前,根敦群培先生就已经目空一切,连当时最权威的佛学大师喜饶嘉措都入不了他的法眼,更何况其他那些面目可憎、迂腐和无知的一众喇嘛、僧官们呢?他们在他眼里大概除了可笑,就是可恨,极不屑于与他们为伍。当他终于摆脱西藏神权政治的束缚,来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他日常面临的又是现代和科学的双重洗礼,其中有现代的学术、现代的艺术、现代的宗教、现代的旅游、现代的地理、现代的考古、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爱情,这一切都给这位本来狂傲不羁、不可一世的西藏喇嘛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冲击。根敦群培先生当时在印度和南亚其他国家结交的是世界一流的画家、一流的学者、一流的诗人和一流的宗教家,为了自由地生活和写作,他甚至可以断然拒绝泰戈尔先生让他去大学教书的邀请,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有可能就是第一位受美国藏学家邀请赴美讲学的藏族学者了。
作为一名天才的学者,根敦群培先生求知若渴的天性在一个自由、现代的新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他的知识结构远远超越了佛教世界世代传承和坚守的大小五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他知道了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和佛教不一样的旧信仰和新宗教;他甚至知道欧美有一大批“神智学”的信徒醉心于获取藏传密教的神秘智慧;他对世界的地理和历史有了很多的了解,远远突破了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佛教宇宙观;他甚至对未曾涉足的欧洲也有了许多的了解,特别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有了相当深刻的领悟和批判。他夸张地说过欧洲人的“智力超过我们千倍,他们很容易就可让天真、老实的东方人和南方人脑袋打转。”“他们的心中唯利是图,他们的性欲比驴还强。”对于一位生活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藏人而言,根敦群培先生所知道的东西毫无疑问实在已经太多太多,而他对现代世界之社会、科学、宗教、文化和艺术的了解给他带来的无疑不只是求知欲望的满足,更不是勇气和力量,而更多的是激起了他对自己所处的这个远离现代世界的小社会和旧宗教的失望、愤怒,乃至绝望。
1938年,根敦群培先生曾用藏文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是平的还是圆的》的文章,想方设法要让他的同胞们脱离他们世代信奉的一个精神的须弥世界,相信他们立足的这个现实的地球确实不是平的、方的,而是圆的。
而此时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 奥托·哈恩已经成功完成了铀的第一次原子裂变试验,双引擎的飞机已经飞上了天,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彩色电视、圆珠笔、“超人”和迪斯尼动画片,等等。不用说,西藏和现代世界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可以道里计,先知先觉的根敦群培先生在写作这样的文章时,一定感受到了难以抑制的失望和丧气。据说根敦群培先生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过:“西藏没有一个人像我。”确实,他超越他的那个时代实在太远,他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现代知识人。世人皆醉我独醒,百无一用是书生。设身处地来体会根敦群培先生当时的痛苦、无奈,今天的我们当不难理解他为何如此的愤世嫉俗,乃至有点疯狂,有点走火入魔。他也许并非有意要做一个离经叛道的“疯僧”,在他的很多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佛教和西藏的精心维护。但他对宗教神权专制统治之下僵化、保守的西藏宗教和社会现状的不满,促使他只能以一种非常极端、离谱的行为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他个人的痛苦和绝望。
传说中的根敦群培是一位十分好色的喇嘛,据和他接近的朋友们回忆,当年他在印度时常常去逛窑子,而他写作的那部《欲论》似也为他好色的说法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而这一切开始于他远赴印度、脱离格鲁派僧伽之后。从一位转世活佛到一位俗家众的转变当然是他个人的选择,但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因为他好色,不如说是他对极端不自由、不平等的西藏神权社会的抗议和反抗。在今天神话化了西藏形象中,西藏听起来似乎一直是一个男女平等、两性自由的社会,事实上,根敦群培先生当年所处的那个西藏原本是一个神权统治之下极端男性沙文主义化的社会,妇女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两性关系也完全由男性主导,无平等可言。故他追求自由、平等的两性关系,正是他个人的现代性、先进性的表现。他撰写《欲论》的目的无疑不是为了诲淫诲盗,而是倡导从世俗生活的角度理解男女情爱、追求两性性爱的喜乐;他描述的六十四种情爱艺术说的主要是如何激起女性情欲和提升女性快感的技巧。这样鲜明的男女平等意識和对俗世的男女性爱喜乐的大胆追求,对饱受宗教神权统治压迫的西藏人民来说显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蒙意义,但它无疑也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根敦群培先生还是一位十分天真的革命家。在印度和南亚生活的十二年中,他接受了足够多的现代、科学和民主、自由等先进理念,也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印度的国家独立运动有切身的体验,对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企图有颇深的警觉,他幻想着能够运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用改革,甚至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改造西藏地方腐朽、落后的政教体制,所以他成了在噶伦堡成立的“西藏革命党”的发起人之一。当他于1945年后期绕道不丹沿印藏东北边境返回西藏时,据说曾受“西藏革命党”领袖邦达绕嘎的委托,绘制了印藏边境的地图,还写下了相关的文字说明。天真的他当时或许并不知道这些地图最终是为南京国民政府准备的,竟然将它们交给英国殖民者的邮传送往印度,结果被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黎吉生截获,并转交给了噶伦堡警方,埋下了根敦群培先生一年多后被西藏地方政府投进监狱的伏笔。
根敦群培先生重新回到拉萨时,曾经历了一小段荣归故里的喜悦,门前不断有达官贵人造访,身边聚集了不少学法的弟子,甚至那位洋大人黎吉生也曾来向他请教如何解读吐蕃金石碑铭的学术问题。他自己正致力于解读敦煌古藏文文献,撰写传世名著《白史》,还正帮助蒙古人格西曲扎编写《藏文字典》。
当然,根敦群培先生依然与富贵无缘,时常还得靠替别人绘画、写字维持生计,而一肚子的改革理想自然永远只能是镜花水月。不曾想到的是,一年多后,根敦群培先生竟被以传布伪钞的罪名锒铛入狱,且一关就近三年。至今没人能够说得清楚他到底为何被捕入狱,但当时谣言四起,众说纷纭,听起来都不靠谱,尽是莫须有。有人说他是苏俄的特务,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又有人说他是法西斯,有人说是因为他开罪了当时的权贵噶雪巴,还有人说正是那位洋大人黎吉生告了密才把他送进了监狱。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根敦群培先生被投进了监狱、剥夺了一位天才知识人的所有尊严和权利。这能不让他身似浮云、心如死灰吗?事已至此,才复何用,情何以堪?满肚子的学问、一脑袋的理想,顷刻间统统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何处又能排解这份旷世的委屈和怨愤呢?身陷囹圄的根敦群培先生当时一定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于是,一位天才盖世的藏族精英知识分子从此万劫不复,变成了一名酒鬼、烟鬼。这是酒之罪?抑或人之罪?该下地狱的难道应该是这位不幸破了酒、色之戒的可怜的西藏转世喇嘛吗?
再说曲江仲巴活佛。仲巴活佛在西方以Ch?gyam Trungpa著名,这个名字是藏文Chos rgyam Drung pa的英(美)式写法,而Chos rgyam又是Chos kyi rgya mtsho的缩写。准确说来,仲巴是这个转世活佛系列的名称,他的本名则是“法海”。在西藏,仲巴活佛无疑只能算是一名小活佛,他的祖寺苏莽甘露坡寺(又称小苏莽寺),位于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小苏莽乡境内,是一座噶玛噶举派的小寺院。它是与其隔子曲河相望的苏莽囊杰则寺的子寺,原属土司苏莽百户管辖。仲巴活佛原是苏莽囊杰则寺寺主之弟子仲扎娃衮噶坚赞的转世,曲江仲巴是第十一世仲巴活佛。
……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原来圣贤寂寞,菩萨也寂寞,所以都难解愁肠,难舍杯中之物,而且酒量一个更比一个大。李白的酒量大概比不上济公和尚,济公和尚的酒量则无法和大成道者密哩斡巴的酒量媲美。或许菩萨的愿力越大、事业和成就越大,酒量也就越随之无限地增大。根敦群培先生当年能喝到的酒想必就远不如后来仲巴活佛所喝的多。不过圣贤寂寞,多半是因为世人愚顽,菩萨沉醉,一定是为了让有情醒悟。我等无明众生,本来六根不净,三毒未除,切不可自比圣贤、假冒菩萨,贪恋酒色,不可自拔,那可是真要提前下地狱的。要知道仲巴活佛的“香巴拉王国”是一个觉者的天国,它的大门是不会为纯粹的酒色之徒打开的。
(沈卫荣,清华大学教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