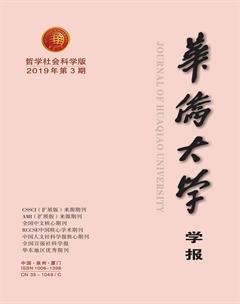元哲学语境下的全球都市化:当代出场与叙事逻辑
摘 要:全球都市化是都市从地方体向全球文明体转变的进程中,对传统意义上原始地方的摒弃和对全球尺度的自我理解、自我批判与自我奠基。全球都市化的当代出场是对传统都市尺度的颠覆,遵循着都市地理学和都市政治两条逻辑铺展开来,是对都市整体性、矛盾性和潜在性的深刻体现,与传统哲学在认识论中存在诸多矛盾和分歧。因此,构建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需要构建以对话、实践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话语,打造全新的人文主义,从都市实践中升华理论。
关键词:全球都市化;尺度转向;内在矛盾;元哲学
作者简介:赫曦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E-mail:he-xi-ying@163.com;吉林 长春 130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空间正义重塑研究”(18CZX004)
中图分类号:C0;B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3-0026-08
都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系性的空间范畴,也表征着思想、想象或者行动,是理论抽象过程的“副产品”,成为当前学术界理解全球发展状况的元叙事。都市化创造了全新的都市言说情境,差异性的事物有序存在并传达着社会关系的本质。在全球化语境中,对都市化的批判、反思与审视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理论具有代表性的主题。无论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都市社会”、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的“全球尺度城市化”,抑或是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克里斯蒂安·施密德(Christian Schmid)的“重建都市性”,他们共同的理论指向都是对全球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矛盾和危机进行反思,为研究建成环境和重构城市理论提供结构性框架。就理论脉络而言,当前的全球都市化研究多由新马克思主义者引领,倾向于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全球尺度下的都市体系,超越城乡二元观念,“进化”都市研究的范式。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市化的“尺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革,从地域尺度上升到全球尺度,都市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转型的呈现。此时,对都市理论进行反思的迫切性不仅仅反映在来自于全球都市化时代所引发的理论困境层面,更是应对来自于城市化对人类发展带来的现实冲击,迫使人们探寻超越全球危机的现实路径,探究都市元叙事的理论逻辑。
无论是对经典作品的研读,还是对都市现实的诠释,对都市问题的反思总是立基于理论上的切问近思,即所谓的切己之问与近身之思。这种切问近思隐含着对城市元问题与元叙事的探求。
所谓对当代都市问题进行元哲学的把握与叙事逻辑的清理,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当下如火如荼的都市化,实际上反映了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社会分工的细化使人类交往突破了城市、区域和国家的界限,世界的所有角落都成为统一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为全球都市化提供了根本发展动力。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结合都市实践建构符合时代特征的都市哲学,是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出场路径的重要尝试。从本文探讨的主题而言,主要是指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探讨全球都市化的当代出场,阐明都市发展的“尺度”转向,审视其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与哲学危机,进而构建都市元哲学,创新都市哲学的出场范式。
一 现实诠释与全球都市化的当代出场
众所周知,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利》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全球都市化”的概念,并论述了“完全都市化”和“都市社会”的图景。对于这一概念的深入探讨出现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爾通过建立都市化空间的全球“结构”或“网络”,预见了资本主义都市化的“泛化”[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6页。。他的论述为我们探究当前的都市化进程的走向提供了可参考的起点。本文的中心并非是探讨“全球都市化”的是非功过,也并非宣扬整个世界已经成为单一、完全集中化的都市。相反,我们要触及这样一个命题:人类社会生活的命运将会随着都市化的不断运动而发生轨迹上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将直接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命运。
1.全球都市化的现实诠释
新世纪以降,全新的都市化时代已经来临,城乡区分的预设区分已经被打破,都市已经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和地方尺度,成为了具有全球尺度的网络体系。因此,我们有必要调整研究方法和创新理论,以“全球都市化”为切入点重新认识都市的发展。全球都市化具有如下典型症候:
其一,从地理模式角度看,都市化正展现出地理规模不断扩大的新形态,横穿和渗透的不断加剧最终打破了城乡二元格局。一度局限于历史中心的城市概念已经被全新的都市生活方式所打破,过去的郊区、农村都已经变为城市副中心,人口集聚、多中心的城市聚落正在形成。
其二,从经济联系角度看,纵观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和区域经济组织,针对空间施策的经济行为正在不断增加,这促进了横跨广大区域的跨国投资和城市发展。在全球都市化时代跨国资本不会仅仅关注传统的都市中心,而是将目光转向洲际交通廊道和大规模的跨国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覆盖全球的通讯和能源网络、自由贸易区和跨国经济组织形成广泛的空间管制和积累网络。
其三,从空间管理和社会重构的角度看,随着全球都市化的推进,都市社会运动将会孕育出新的载体,固化新的利益集团。当代都市作为社会运动的发源地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都市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策源地,其空间的公共性和差异性将会给集体行动提供新的地域基础。
综合上述理解,我们所谓的全球都市化乃是指都市由一个地方体向全球文明体转变的过程中,对传统意义上原始地方的摒弃和对全球尺度的自我理解、自我批判与自我奠基。传统意义上的地方被不断更新与重塑,自然界演化与都市化进程趋于同步,具体内容体现为地方的衰落与全球话语的纷呈,在丧失了地方绝对权威的基础上,如何构建包含差异的自由与公正的全球空间是全球都市化关注的核心所在。具体来讲,都市空间已经成为理解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视角,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生态都可以在全球都市化制度的重构中获得全新的理解。
2.全球都市化研究的当代出场
全球都市化是将都市体系放置于全球的尺度下加以考量,意味着经过长期的衍化,传统上远离都市的乡村地区也被纳入都市化探讨的范畴。构建全新研究视角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超越城乡二元论,进而实现都市研究范式的“进化”与变革。全球都市化的当代出场需要对都市研究的内涵与理论进行全面“升级”,为了证明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其内容应当涵盖如下研究尺度的转换:(1)都市化的概念尺度从点状分布的城市拓展到城市群、城市带或巨型城市走廊;(2)都市的功能从中心向外蔓延,逐渐扩展到城市副中心或城市外围;(3)都市社会已经涵盖了传统的乡村和自然界,成为其组成部分;(4)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界已经走向终结,一切自然环境都已经统摄于都市化的影响之下BRENNER N. Implosions/Explosions: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Berlin:JovisVerlag,2014,p16.。所以,都市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形态,“空间修复”已经在全球尺度下展开MERRIFIELD A.The Urban Question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3,37(3):909-922.。毫无疑问,要恰当地理解当今社会,都市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尺度,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现代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本质的重要维度[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第47页。。全球都市化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已经长期存在的学术问题。但是,在都市研究的思想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对都市重要性的强调始终不足。因此,我们现在探讨“全球都市化”就是为了恢复都市在当代社会研究的中心位置。从两条逻辑线索出发,勾勒全球都市化研究的图景,厘清其当代出场的路径。
全球都市化研究的历史虽不漫长,但由于其复杂性和多样化,其研究逻辑经历了多次流变与转换,要准确地将其分类并非易事。从历史的长视角加以分析,城市研究可以从外化的地理现象和内化的政治意义两个角度进行理解,由此可以将其分为两条逻辑:其一,是强调从都市地理学的视角研究都市全球化,注重对都市化现象进行动态解析,从流变性与动态性角度把握不同尺度和边界的城市现象。都市地理学受哲学、现代技术和邻近科学的多重影响,通过消化西方的各种城市理论形成了理解城市空间形态的路径。布伦纳认为如果城鄉边界意识被打破,城市认识论的基础就将被打破,我们需要重构“表象”(nominal essence)和“本质”(constitutive essence)两种认识论。前者注重对空间现象与构造进行描述,后者则侧重探讨其机理与演化进程。全球都市化注重对后者的研究BRENNER N. Theses on Urbanization. Public Culture,2013,25(1):85-114.,认为空间形态并非是固化的,也不会被时间序列所割裂,而是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MARCUSE P,VAN KEMPEN R. Globalizing Cities:A New Spatial Order?.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128.。全球都市化研究主要关注三个层次的空间生产,即建成环境生产、知识生产和意义生产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Blackwell,1991,P89.,这是列斐伏尔对全球都市化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具体研究方法上,他们探索了“去边界”的空间可视化表达方式LEFEBVRE H. State,Space,World:Selected Essays.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45.,探索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从都市空间构型的角度看,全球都市化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1)探讨城市景观的“创造性毁灭”问题,研究新旧空间如何互动,其背后的深层次经济政治根源;(2)构建都市地理学,探讨都市化与社会演进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扩张对都市化进程的影响;(3)研究都市社会和政治运动问题,分析都市化对社会环境、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影响BRENNER N. Theses on Urbanization. Public Culture,2013,25(1):85-114.。
其二,是强调从政治意义上理解全球都市化,探讨都市化的政治影响,将全球“城市社会”的到来看做资本扩张的根本结果MERRIFIELD A.The Urban Question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3,37(3):909-922.。在全球都市化时代,地域联系明显增强,利益博弈、都市政治和空间权力的争夺进入白热化,传统的政治理念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WACHSMUTH D,BRENNER N. Introduction to Henri Lefebvres“Dissolving City,Planetary Metamorphosi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2014,32(2):199-202.。由此,在全球都市化的带动下,全新的政治格局正在酝酿。
对以上进行综合分析可见,两条逻辑的表现形态虽有差异,但皆具备一个共同点,即以全球化为问题呈现的背景,目的是实现都市化的研究转向,表现出认识论的二元分裂。一方面,对全球视野的强调使都市化的传统概念受到挑战,围绕都市化的全球变革将引起总体性的都市革命。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全球都市化”命题,天然带有激进的批判意味,强调了全球变革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一些“后现代”和“比较城市化”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验方面,希望引进多样性来推动方法革新和观念升级SCOTT A J,STORPER M. The Nature of Cities:The Scope and Limits of Urba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5,39(1):1-15.。尽管存在各种分歧,但不可否认全球都市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研究命题和新的理论增长点。
二 全球都市化的检视:思维特点与内在矛盾
全球都市化是社会的普遍变革,都市不仅仅是工业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且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从历史角度和共时性的角度看,都市化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社会,除了建筑环境与物质结构发生变革外,个体与群体安身立命之基础也被重新设定,这是来自于对都市现象普遍性、整体性和过程性的“理性”思考。都市化是时空交错的过程,必须通过辩证的总体现象才能理解那种不可归类和原始的混沌性。全球都市化标志着批判城市理论的转折点,全新的“都市”思维正在孕育,关于都市社会的探讨始终处于冲突与紧张中,以至于反对乃至颠覆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因此,我们需要对全球都市化进行全面的检视,既抓住这股思潮的思维特点,又分析其内在矛盾,从构建全球都市化元哲学的高度剖析其内在逻辑。
全球都市化理论的问题意识,是和当代社会的转制紧密联系的,其核心的问题意识是如何论证全球化都市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以及如何确立其文化法权地位。通过对这一理论的检视,可以梳理其如下思维特点:(1)将城市研究的重点从形态研究拉回到过程研究,肯定空间性并非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次生特征与景观,而是其基本存在基础。同时,都市形态的短暂性与浮动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存在,只有从整体性角度把握才能真正了解其轨迹与变化节奏;(2)都市化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集中化以及一种广泛的爆裂,都市社会中充满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形态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才能完美地理解,都市化的结果不仅仅是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也变革了市民的生活体验与日常生活;(3)全球都市化并非是一个完成形态的定义,而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潜在性存在,城市空间作为一个越界和替代性的社会想象,在“差异化”“多样性”“具体乌托邦”和“城市权利”等概念中都会投射出能量。
通过对全球都市化的检视,我们发现都市化在造成物质形态变迁的同时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认识矛盾,这种矛盾需要从元哲学的角度加以矫治。列斐伏尔在《元哲学》(Métaphilosophie)一书中,向我们分析了全球都市化理论与传统哲学在认识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与分歧,以及他对一些基本哲学概念的认识。
第一,哲学的范畴问题。在传统的认知中,哲学家处理的是抽象的思想,纯粹的概念,往往没有社会内容,而且他们往往不太與日常公众接触。日常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哲学的层面,没有被哲学所打动。因此,哲学遇到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分裂。列斐伏尔认为,全球都市化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扎根,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诗意的和活跃的冲动,实际上是三者的结合,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形成转化和创造性的突变,变成一种富有成效的对抗。列斐伏尔说:“全球都市化应该是元哲学的思想,去想象和提出新的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新的风格,它可以在实践中构建自己,通过改变日常生活来实现哲学的追求。”LEFEBVRE H. Metaphilosophy. Verso,2016,p89.
第二,实践问题。传统哲学认为,哲学不涉及具体的问题,而是研究宏观的人类问题。二元论的分野往往会造成存在与思想之间的矛盾,表现出分裂和冲突。要在统一中达到差异,统一性必须被实现或重新发现。只有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思想,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性强的能量形式,才能跨越分歧、矛盾、对立、矛盾的界限,才能克服无穷无尽的斗争中相互对立、僵化。构建理论的目的不仅仅是理解的问题,而是在生活中化解问题。
第三,普遍性问题。哲学家宣称哲学思想是普遍的,它已经吸收了非哲学世界,即整个世界都在哲学统筹之下。因此,在哲学的开端,在推论的原则和前提里,既可以找到普遍性,也可以找到真理。由此,哲学成为了封闭的系统,与现实相割裂。要摆脱这一矛盾,唯有让哲学成为世界,成为在世界上实现的存在。那么哲学世界和非哲学世界就会失去它们的片面性,都将被克服。
第四,整体性问题。哲学强调整体性,没有整体性的认识,知识就会分散,世界会出现碎片化。整体、群体、形式既是事实,又是个体现象、片段和部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人类整体是一个破碎的整体。文化本身是分离的,是一种“马赛克的文化”。它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领域、部门、观点、技术、艺术和知识的并置。除了质疑整体性的概念,如何能对整体性进行连贯的讨论呢? 哲学寻求成为人类经验或人类知识的总和。然而,它既不能达到全体,也不能达到普遍性,于是整体化的概念应运而生。如果总是有新的、强加于自身的、知识或生活经验上的、不断重复和重新开始的总和,那么哲学家就无法保证这种总和是哲学的。因此,一体化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
第五,主体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家喜欢宣称自己是主体性的辩护者和代言人,反对科学技术的客观主义和教条的非人格化。制度世界努力修剪主观性,切断一切试图取代的东西。一方面,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通过各种各样的技巧,压制主观性的发挥。大量人际关系的物化、物化到极致的对象异化。另一方面,从外部影响主体性的操作,使用的是主观手段:神话、符号、意象。因此,主体性在主张其存在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难以摆脱对其产生影响和异化的因素。因此,社会学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它超越了专业科学和技术的狭窄视野,符合一种摆脱传统哲学框架的思想要求。对于主体性和个体性的辩护,借助于一种主观的哲学绝对主义,带有主观的幻想,在这种哲学绝对主义中,人很容易迷失方向。因此,我们首先要摆脱“主体—物化”的抽象辩证法。
综上,与这些内在矛盾相联系的是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哲学家陷入了两难的状态,要么不考虑现实的政治需要,一意孤行的探讨哲学问题。另一种选择是进入政治生活,将政治和国家纳入哲学的探讨范畴。抑或是选择折衷主义,而这种折衷主义几乎没有连贯性或系统性。很显然这两条道路在哲学上都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因此,要构建一种元哲学,重新思考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与概念框架等哲学基本问题,让哲学为社会思想观念提供支撑或者思想基础,将其改造为一种关于世界观念的构造。
三、全球都市化的反思:元哲学的构建
全球都市化的智识与元哲学扎根于马克思主义,认同不同的生产方式产生不同的城市形态,主要关注一种生产方式和城市化模式如何向另一種生产方式和城市化模式的转型,提出城市化在历史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列斐伏尔认为应当把工业社会视为全球城市化的前兆。城市既是一个虚拟的研究对象,同时又是一个可能的目标——一个自由乌托邦的姿态——随着世界越来越都市化,一些中心性的转型已经发生。为了创造替代性、可能的城市世界,列斐伏尔大胆推测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将会如何变得上下颠倒。他进一步预言,当完全城市化在全球尺度上实现时,即意味着城市肌理将会不息地与整个世界交织在一起,包括陆地表面、海洋、大气和地下,这些领域将会被直接工具化和功能化(instrumentalized and operationalized),用来服务于贪婪追求工业资本主义增长的目的。
全球城市化的元哲学叙事是一种对话和实践,为社会的思想观念提供了“支撑”和观念基础,并将哲学“进化”为观念上的构造,进而统一于具有问题意识和话语逻辑的哲学共同体。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表现为如下几点叙述方式:其一,全球城市化的元哲学是一种对话。从罗蒂的观点看,哲学的根本目的并非发现实在的真理,而是挖掘我们的精神生活,实现现实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对话,元哲学正是沟通两者的桥梁;其二,全球城市化的元哲学是一种实践,即元哲学的叙述逻辑是与都市化实践逻辑相同步的,是使我们更好认识都市化的工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这一论断有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哲学的关键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美国的很多实用主义者也认为哲学的最终价值追求是为人类谋幸福,而非单纯刻画物质世界;其三,全球城市化的元哲学话语的内在发展与律动,不仅要为社会思想观念提供支撑和观念基础,而且要成为改造世界的观念构造。从历史长视角看,宗教、常识与科学常常能够成为思想观念的基础,构建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重塑认知都市的维度,尽可能地精确刻画外部世界的实在。因此,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是对传统哲学方法的创新,将以往思想资源转化为一场哲学的彻底变革。哲学需要与时俱进的发展,需要将视野扩展到现代生活的日常方面。因此,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也是日常生活的元哲学,是扎根于都市实践的方法论体系。
借用当代知识社会学的术语,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是“官学话语”“主义话语”和“个人话语”的内在统一,其中个人层次是基础。元哲学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扎根,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诗意的和活跃的冲动,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通过转化和创造性的突变,变成一种富有成效的对抗。列斐伏尔说:“全球都市化应该是元哲学的思想,去想象和提出新的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新的风格,它可以在实践中构建自己,通过改变日常生活来实现哲学升华。”LEFEBVRE H. Metaphilosophy. Verso,2016,p89.
我们认为,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叙事方式有如下逻辑特征。
第一,全球城市化的元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僭越与解放。正如元哲学是建立在传统哲学的废墟之上一样,城市社会也是建立在传统城市的废墟之上的。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一书中认为,元哲学是“把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就像城市社会从爆裂的城市中诞生一样。”[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第77页。因此,城市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的哲学范畴,是连续性中的不连续,一个重复的差异,是旧工业社会的崩溃。新城市的形式颠覆了传统城市和它的超周期性。因此,元哲学的深层反哲学问题被转移到城市社会的深层实践层面,成为一个复杂的理论和政治困境。
第二,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将自己置身于城市革命之中,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危机中打造一种“新人文主义”。城市革命是一出统治阶级起主导作用的戏剧。统治阶级开创了把生产力累加起来的意志,在世界各地实行殖民统治,使土地商品化并从中榨取价值,使人民和自然成为价值源泉,从人性中榨取价值。正如他们将一切都资本化、货币化一样,统治阶级已经将触角深入人性,从我们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攫取价值。城市进程实际上已经成为破碎的空间单元的渐进生产,成为残暴的中心、支配的中心、依附和剥削的中心,成为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一个经济、政治和生态转型的过程。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一书中表示:“城市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城市化,作为一种具有全球趋势的城市化,都是全球性的事实。”[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第194页。城市革命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第三,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汲取动力,从都市实践中升华理论。列斐伏尔对“全球城市化”和元哲学的影射在《城市革命》一书中随处可见。他认为威胁正在逼近我们,与其说是“全球城市化”的威胁,不如说是“城市的全球化”威胁。这个短语的顺序很能说明问题。城市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扩张,而是变成了一个漩涡,吞噬着地球上的一切:资本、财富、文化和人民。正是这种对人、商品和资本的吸收,使得城市生活充满活力,又充满威胁,因为这是一种集权力量,它也“驱逐”了人们,从而隐藏了城市的本质。正是这种驱逐过程使得城市空间扩大,而让更多的人被排斥于城市之外。它能产生外部推进力,实现指数级的外部膨胀。都市不仅是工业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且也变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在这个城市漩涡中,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以“革命的公民权”为基础。这种都市革命作为一种总体性战略,是遍及任何地方与时刻的微观实践活动。
四 结 论
全球都市化作为一种新的全球现象和概念,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回顾全球都市化的各种建构方式和叙事逻辑,我们认为其元哲学的构建有如下特点:
第一,全球都市化的研究框架继承了列斐伏尔对都市社会和都市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将大卫·哈维对空间的马克思主义构建纳入其中,力图超越传统的城市化研究范式,突出从地方到全球的研究尺度转换,强调空间的普遍性、去边界性,以及在都市内涵方面出现的新变化趋势。同时,全球都市化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如列斐伏尔的“都市社会”、哈维的“埃迪里亚”等。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力图弥补城市发展的历史性困境和创伤记忆,来确证全球都市化的正确性。
第二,全球都市化将人类之“栖居”摆在了核心位置。与当前都市思想的无意识简化不同,全球都市化要求我们用一种尼采式和海德格尔式的元哲学沉思来复原栖居的意义,将生活体验和日常生活纳入研究,并超越它们形成一种普遍理论,形成一种哲学与元哲学。当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时,他便为恢复此词开辟了道路。这意味着把人类与自然及其自身的本质关系,人类与存在及其自身存在的关系置于栖居之中,并在栖居中得以实现与理解。全球都市化强调都市的首要性和栖居的优先性,主张空间充满独特的意义,具有完整的意味性。这些理念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三,全球都市化的分析框架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立场和政治经济分析倾向,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对于宏大叙事与理论化的一贯追求。但是,从全球尺度研究城市问题的难度可想而知,无论是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新范式的建構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构建在叙事方式上还缺乏明确的边界意识,注重解构而轻建构,未能形成理论自觉。为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要从以下几点把握叙述的界限,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1)把握叙述主体的边界性。都市的构建主体是人,通过行为和决策主体来建构城市景观,规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够使个人通过抛却日常生活而在更高层次上发展自身。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够使决策和建设者成为“社会凝聚器”和“社会加速器”,不再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秩序而工作,而是为了移动与新建这些关系工作。因此,要把握城市建筑师、决策者和各种思想言说者的自身边界性;(2)叙事方式的边界性。虽然全球都市化研究渴求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模式,但无论是文献注疏诠释性的、都市描述的、哲学思辨的,还是个体心性的、发展见证的,每一种话语方式都仅仅反映了都市化的局部而非全貌;(3)研究问题的边界性。全球都市化理论叙事方式驳杂而多样,反映了城市矛盾的复杂性与城市发展的差异性,也展现了当代城市哲学不同话语方式之间的纠缠与张力。因此,元哲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不宜包揽一切,而应当注意其边界性。形成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并服务于人类社会,引领城市发展的潮流,将是学术界重要的使命与必须解决的命题。这要求我们既要吸收和消化最新的西方思潮成果,同时也要进一步在知识学的意义上辨析全球都市化的优劣,反省西方现代性经验的不足,并用以指导中国的城市实践。
Global urb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eta-philosophy:
contemporary appearance and narrative logic
HE Xi-ying
Abstract: Global urban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from a local city to a global civilization. The contemporary appearance of global urbanization is a subversion of the traditional urban scale, following the logic of urban geography and urban politics. It is a profound reflection of urban integrity, contradiction and potential, and has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with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n epistemology. Therefore, to construct the meta-philosophy of global urba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that integrates dialogue, practi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create a new humanism, and sublimate the theory from urban practice.
Keywords: global urbanization; scale shift;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meta-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