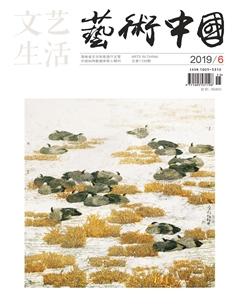论贾樟柯电影的纪实美学风格
摘要: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贾樟柯的电影呈现了与“第五代”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他将镜头对准中国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大量地运用了长镜头、跟镜头、同期录音、实景拍摄等纪实手法,以一种纪实性的风格来呈现个体的生存状态。而贾式影片的魅力之处,就在于追求真实的创作。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结合了三峡工程与奉节拆迁这一现实状况,通过非职业演员的本色表演、现实场景的客观呈现以及现场声音带来的强烈时代感,将人物境况与社会现实生动直接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本文以《三峡好人》为例,分析该影片中呈现的电影审美规律及贾樟柯影片的纪实美学风格。
关键词:贾樟柯 纪实美学 电影审美的规律 三峡好人
纪实美学与对边缘人物的关注,是贾樟柯电影的两大典型特征,共同支撑起他的电影创作。他的作品,都聚焦于当下的社会现实,记录小人物在面对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时的心理变化与生活态度,折射出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奉节县的人们面临着拆迁与搬迁的社会问题。当贾樟柯来到三峡,看到人们家徒四壁、城市在砖瓦拆卸后逐渐消失的状况后,便产生了创作的想法。与他之前所有描述小人物命运的影片不同,《三峡好人》的社会格局更大,在记录着这场大规模移民的历史事件的同时,在韩三明与沈红寻亲的故事背后,影片蕴含了奉节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人们搬迁之途的记忆流逝。
影片开始于一个缓慢移动的长镜头,三分钟的镜头里,船外是川流不息的长江,船内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镜头扫过人们,他们在嘈杂的环境里自如地打牌、抽烟、扎行李,最终定格到表情凝重的韩三明身上。和纪录片《公共场所》里人物的出现方式一样,贾樟柯对于空间结构的把握十分熟捻,主人公在长镜头的缓慢移动中不经意地出现,没有被刻意突出。韩三明是影片主要人物,同时也是淹没在众多移民中的一员,观众在悠长的镜头里随着韩三明的脚步走入船舱,感受三峡人民离乡的情绪。当韩三明缓慢地走入施工工地,观众便看到阳光下赤裸着上身的工人挥汗如雨地进行施工;当韩三明走进县城搭车,观众便感知到奉节人们较为贫穷的基本生存现状。大量的长镜头的运用,以一种冷静旁观的方式,将奉节拆迁的状况、韩三明与沈红寻亲的情绪,呈现在观众眼前。这种纪实手法,将最原始的情感毫无保留地传达给观众,就如审美的穿透律中所述:“个体因对象的形式结构而被打动,从而使个体产生一种像是被击中了的感觉”。①当韩三明接受了找不到麻幺妹的现实之后,他拿着10元的纸币对着夔门与峡江静默地凝视,在漫长的沉默中,观众能直接感受到他的孤独与陌生感。这种孤独与陌生,透过影像是能让人感同身受的。在谈及创作理念时,贾樟柯也曾提到共鸣感,他认为:“我们这些游客拿着相机看山、看水、看那些房子,好像與我们无关,但是当我们坐下来想的时候,这么巨大的变化可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有。或许我们每天忙碌地挤地铁,或者夜晚从办公室出来凌晨三点半一个人回家的时候,那种无助感和孤独感是一样的。”②贾樟柯在影片中抓住了人物与观众之间的关联性,把握住了人们之间共有的孤独感,此刻,观众仿佛走到了韩三明身边,感知到了人物淡淡的悲伤情绪。
影片关于拆迁部分的呈现,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当地居民与拆迁部门之间发生矛盾的场景,一是工人现场施工的画面。无一例外,贾樟柯选择了用长镜头镜头不动声色地凝视。他掌握着“接近与阻隔的分寸”,没有直接造成具体化的矛盾冲突,而是一直保持着固定机位的拍摄。观众可以在画面中看到,居民们围着拆迁部门的主任讨要属于自己的那份保障,在走道里熙熙攘攘,把大门围得水泄不通。工地上的工人们无止境地敲打着墙砖,没有对白,敲击声反复打响。这种不加任何效果的拍摄方法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与人物关系,更能让观众去自己体会人物之间的冲突。从影片的网络评论中可以获悉,大多数经历过拆迁的观众感受到了自身经历与情节之间的关联,这种审美认同,是能促成观众产生对影片的亲和感。
影片呈现了许多工人的生活景象。群众演员在影片的表演中,如包纱布、聚集吃饭、打牌等情节,都有出现台词卡顿、在镜头前表现得略不自然的情况出现,但他们的感情是十分到位的,因为他们在镜头里表演的,是自己反复“上演”的日常生活。比尔·尼克尔斯在《纪录片导论》中对纪录片下定义:“纪录电影谈论与真实人物(社会演员)相关的环境或事件,真实人物在故事中以他们原来的面貌向我们现身说法,并对影片中呈现的生活、事件和环境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③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在社会中充当“社会我”这一角色,本能地完成自己的活动内容与动作行为。戈夫曼也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对其做出了解释:“在日常生活中表现自身的方式,不同于有意识地接受一个角色或者虚构性的表演”④贾樟柯在影片创作时,为了增强观众的情感体验,就采用了非职业演员去本色表演。韩三明原本就是一名矿工,成年后就开始下井挖煤,在影片中他同样扮演着一名煤矿工人,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与影片的纪实风格相协调。小马哥、旅店老板、相关部门的官员,言语里都夹杂着浓重的方言,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细节使得电影更加贴近生活的原貌,让观众产生关联感。这一纪录片拍摄视角,让观众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三峡生活”, 而是直接记录的三峡的真实生活。本片中,人物的生命体验也得到了真实传达。在寻找亲人不得与生活条件艰苦的极端化情境之下,沈红与韩三明因小马哥结缘。沈红经历钱包被偷、寻夫无果、感情失意,韩三明经历了寻妻无果、不被承认、失落离开,两人正是由于特殊情境,有了情感交流的可能性。这一审美极致原则在影片中的运用,让两个失意的人走到了一起,同时唤起了观众的同情。韩三明的寻妻无果与沈红的寻夫失望,两人共同经历着寻找与失落的过程。即便沈红最终找到了郭斌,也发现了物是人非,再也找不到那份真情。在社会变动的大潮中,韩三明的漂泊感与沈红寻夫的艰辛,终究被淹没。影片中,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相关联,观众为两人是否成功寻亲而担忧,而人物的结局设置达到了直击人心的效果。
为了最大程度地体现真实性,影片采用了同期录音和置入年代流行音乐。在影片的开篇,能听到三峡游船的轰鸣声,导游现场式介绍的喇叭声,及重庆方言的出现,这些都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感与明显的地域特色。影片中出现的流行音乐,也是贾樟柯电影的特征,揭示了人物的情感與命运。如韩三明的手机铃声常常响起,是《好人一生平安》。憨厚老实的韩三明作为外来者,面对的是对现实寻妻不得的无奈与孤独,他在工地见证了一个工友的逝去,而自己的侥幸留存与歌名相呼应。小马哥过着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活得坦然洒脱,他的手机铃声就是《上海滩》,暗示他性格中的不羁。《两只蝴蝶》里爱情的破灭暗示了沈红与丈夫之间情感的淡漠与疏离,《酒干倘卖无》包含了导演对三峡人民艰辛生活的反思。贾樟柯用同期录音、方言及年代的流行音乐,将人物的生活状态呈现出来。这一创作方式,体现了纪实美学的重要特征,从全息律而言,局部把握了整体的统一性,使得影片余味无穷。
电影的审美是具有多元化与指标化的,在贾樟柯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中,出现了许多超现实主义的元素。三峡改造工地上一闪而过的飞碟、升空飞走的纪念碑、走钢丝的人、两亿四千万的桥,超现实主义元素出现在现实主义题材之中,本身具有荒诞性,也不符合影片在审美上的统一规律。但结合影片实际来看,飞碟的移动、大楼如火箭般起飞,这些非现实意象都在表明未来将要到来,三峡库区也将结束了它所存在的自然景观。荒诞的意象,将观众从剧情中抽离出来,使其更冷静地审视现实,感知影片的真实性。
将个人生命的印记讲述出来,影片便有了力量。贾式影片对真实性追求更高,取材源自现实生活,拍摄来自现场实景,他的影片将边缘群体的生存现状披露出来,他的《三峡好人》呈现了审美的多元性。《三峡好人》不断地提醒我们,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依旧缓慢地行进,而贾樟柯对边缘小人物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值得人们关注与反思。
注释
①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第115页。
②贾樟柯:《贾想I》,台海出版社,2017.2,第193页。
③[美]比尔·尼克尔斯:《纪录片导论》(第二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11,第7页。
④[美]比尔·尼克尔斯:《纪录片导论》(第二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11,第8页。
简介:梁瑾(1999—),女,汉族,籍贯:湖南长沙,单位:重庆大学电影学院,研究方向:电影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