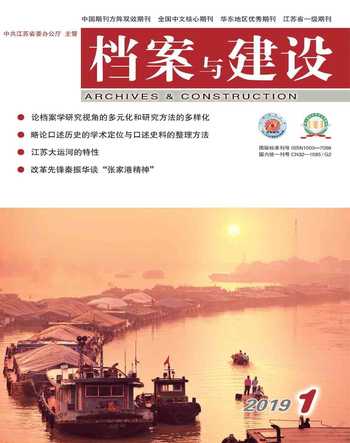论交互式档案学及档案管理的新范式
[摘要]论文基于哈贝马斯的交互理论对后现代主义部分思想的超越与反拨,揭示了档案学在当今语境下的可能形态,进而提出了交互式档案管理的新图式,并对文档的交互生成、交互控制、交互鉴定、交互利用等理念作了具体区分与阐述,旨在从交互理论的新视角对档案学既定理论与应用模式进行全新审视和再构建,以期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交互理论交互制作交互控制交互鉴定交互利用
[分类号]G270
New Mode of Interactive Archives Science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Li Peil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Harbermas, a modern philosopher’s opinion about postmodernism.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interaction and gives a further clu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action and modern archives science. What’s more, it puts forward a new mode of archives management——interaction and explains the interactive execution, control, checkup and practice of documents in detail on the basis of this new mode. This article aims at a new study, though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 of archives science from the view of postmodernism and interaction, trying to offer a new way to the research of basic theory in archives science.
Keywords: Interactive Theory; Interactive Execution; Interactive Control; Interactive Appraisal; Interactive Practice
1交互理論的提出及阐释
笔者在《后现代主义与档案学:从德里达、福柯到特里库克》[1]一文中,曾对后现代视域下的档案属性及新型文档关系做出了初步界定。而后现代理念不仅使得传统档案学在其当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获得了拓展理论空间的诸多可能,也在文档管理的实际应用环节为我们带来了挑战与启示。从档案学和信息管理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在整体上很难实现有效地反映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等新的标志性特征,在此情形下,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和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对话”“沟通”等理念就显得意义深远了。尤其是哈贝马斯具体提出了“交往理论”,一方面肯定事物的差异性或人文环境下多元对话的先在前提,另一方面他又预设了某种普遍性的单一符码作为控制项,即所谓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从而使在一种差异的境遇里实现对话成为可能。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上面的“对话”理解为信息的传递,把交往理性应用于多元语境下的档案学实际,那么档案管理的一种新范式就会建立起来。
哈贝马斯用“有效性”表示以沟通为取向的交往行为理念,把交往行为理解为一种社会化原则,将交往参与者的行为世界与生活世界形成一种交融互补的关系,把生活世界的潜在性与交往行为的公开性达成一致。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语言沟通作为协调行为的机制(这里的语言可理解为包含了差异性特征的、构成信息载体的文本及其背景结构)成了关注的焦点。这是将社会学范畴的交往理论“移植”成为档案学范畴的交互理论的可行性所在。
交互在本质上是认识、参与世界(即自身与所处系统的关系)构成及意义生发的一个方式。它首先承认人的行为具有主动性和反思性,因此重视在阐释、理解过程中人的认知能力和语言的表征能力,并且突出交互双方或多方在交互系统中的建设作用。交互作为一种方法常与档案学形成联系的主要内涵有交互认可、交互理解、交互包容、交互参与或述行(与述行主体的权力结构有着直接关系)几方面内容。所谓交互认可是指事物的个体与个体间是相互平等的,相互承认各自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认可各自的权力方式与话语方式,并互为存在的理由和依据。交互理解意即理解方式由过去的唯我的、实用的、主观的和线性的方式进化为互文的、终极的、包容的和复调的方式,并能共同构成理解本身的意义与方式——过程就是全部。交互包容指在事物存在的多个层面(包括时间的、空间的、整体的、局部的层面)允许同形共存和异质交叉,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建设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多元存在的活性结构,并承认某些“混沌点”对整个存在系统的作用(异律性)。交互参与则指具有指涉能力的述行主体间相互进行行为共建和意义生发,扩大意义的映射域,充分发挥结构对文本的生成作用,在社会理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隐性价值。
2交互理论的档案学意义
我们已经确定档案的价值指向是历史与存在而不仅是以实现某种短期实证主义的功用为目的,所以档案与历史具有同构性。但传统观念下的档案被严重地边缘化和平俗化了,造成了现实与历史的断裂。特里·库克也曾认为新语境下的档案学“在过去的这个世纪发生了一次集体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转向以更广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简而言之,将社会记忆的定义局限于有权者形成并留存的文件记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2]。而交互理论的一个任务就是使知识重新回到知识自身,回到充满活力的沟通系统和意义生发系统,在档案学领域,就是使档案得以回归,使档案重新面对历史本身(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只是体现某种短期的功用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实现由静态的实体研究向动态化的现场研究、行动研究、参与研究的转变。
另外,通过对交互理论的研究,我们发现不能仅仅以个体的档案文本及其价值实现流程为分析单元,而是应该把档案放在一个秩序化和个性化相统一的社会系统中加以研究,把档案的生成背景和运作环境(社会系统)作为一个分析单元;要转变研究方法,把过去建立在对档案的实体研究的单因素分析方法转变为对档案的生成因素、背景条件、社会变构与交互利用等等方面研究的多因素分析方法。我们要把档案认同为不同社会角色多元对话的依据和信息文化系统意义生发的依据,将档案视为社会多元对话的主控项或互文性文本。
这要求我们既要重视档案形成和运作过程的物理因素、技术因素,又要重视社会(背景)因素与人性化(心理)因素,重视各方关系与协调运作的意义,并能在此基础上建成档案运动的结构均衡模型——在考虑了档案的活性结构(包括结构与文本的差异性和交互参与功能)的情况下对档案的实体、背景、意义关系和运作过程加以分析。这样,档案的“言语者”在表述过程中就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建立起交互联系。我们说这与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完全一致的,与档案作为文明记忆的使命与价值是完全一致的。
3交互式档案管理的实际应用
3.1交互式文档生成
交互式文档生成首先要求在形成文档时实现两方面的交互认可,一方面实现文档背景与实体的交互认可,另一方面实现文件与档案的关系的交互认可(包括制作单位、制作人员权限的重新界定)。比如在文档形成之初或之前就要考虑到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和个人对信息的新型需求特点,改进文档制作系统,将办公系统和文档管理系统网络化,并建立超系统优化机制(比如电子政务系统及其数据库——数字档案馆),使之不仅满足具体事件的暂时需要,更适合服务于社会和历史的全息利用。这样,文档形成者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文、档的数据建设,且是基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大数据库的建设。当然,为此相配套的体制和机构的改革是必需的,使文档的形成者能够与其他相关主体实现联动,使文档的内容能够与其他相关社会信息进行有效关联,从而对文档内容加以综合考虑和改进。通过改进系统,文档在制作的过程中以自动和人为的方式记录文档的相关背景信息和职能信息,使文档实体具有可阐释结构(比如赋予命题以内容的背景知识),从而实现文档制作主体、执行主体、管理者、用户的权力渗透,建立起新的文档后台操作模式(行为主体多元化,责任各级分层化),为下一步文档的交互控制和利用奠定基础。
交互式生成依旧遵循文档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原则,但在文档生成时可以结合系统分析与数量分析,注重模拟方法的运用。由过去只注意单一变量的分析变为对综合变量的分析,也就是说变为对不同环境下不同概念的整合,变为与不同变量的结合,比如使档案实体与价值变量的分析与档案的社会与结构变量的分析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创建文档的标准化模型与描述性模型,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建成文档的结构均衡模型。当然,综合分析与模型结构的建立以不违背文档的有效性为前提。
交互式制作在理论上使得檔案不再像过去那样来源于同一个具体的机构,而是“从以原始文件产生部门为中心的实际来源转变为以多部门、多机构中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活动为重点的概念来源”[3],而且也必定会体现出对文档的多重支配和控制力因素,因为档案作为话语,必然反映着其背后的权力形式。文档的交互式生成则很好地体现和证明了档案的意义并不在其本身,而在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关系,因为这种权力关系正是通过复杂的来源体现出来的。
3.2文档的交互控制
文档的交互控制是指在档案控制内部仍然保留实体与智能控制的基础上,从社会有效性的角度建立文档交互控制模式,使控制主体社会化,以避免文档管理系统在交互运作中发生系统减缩和曲解文档信息意义的现象。
它首先要求放弃文件和档案仅属于个别单位和系统的观念,以使文档的控制权力得到分流和交叉使用,不仅在文件和档案部门间实现对文档的交互控制,更可以使控制主体社会化,即让过去较为集中的国家和部门的体制权力泛化和分散,使文档的多层次信息受控于一个有弹性的中间项。这就需要把文件和档案从各个相关机构和个人的手里“解放”出来,使之集中受控于公共文档管理机构,从而便于全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利用。不仅根据文档的形成过程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也要对文档的控制主体进行重新区分和界定。这样,就能使业已模糊多义的文档的来源信息以及日趋复杂的信息结构得到充分消化和重塑,做到档案结构与意义的交互包容,真正实现对文档的(社会化)活动过程的控制。当然,我们还要重视社会结构和档案自身结构(具体指档案的实体结构)对档案意义的生发作用以及文档生成的动态结构对其意义的转化作用,将文档从自身的实体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和外在环境全面发生关系。比如在文档一体化的多能模式中体现档案角色的社会化即国家行政角色向公共社会文化角色的转变,使文档在国家行政(权力)、公共社会、历史文化三个层面共同生发意义。
电子时代使得文档的交互控制成为一种可能,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旧有的文档控制理论如全宗理论等开始要求有所突破,许多档案学者更倾向于认可一种智能控制下的全宗概念,并把这种全宗概念阐述为一种概念化的整体。正如特里·库克所说,“发现并保持来源原则和尊重全宗原则的本质,必须置于以文件形成过程和形成者相互联系的框架中;档案著录的着眼点、构建和标准化也必须置于职能框架中”[4]。应该说,前些年国内学界的全宗理论,尤其是客体全宗的概念,与特里·库克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们同样取消了全宗的形成者(形成机构)的界线,而把文件的形成过程作为了主要的考察对象,这使得全宗的组织工作在虚拟技术被日益广泛应用的时代具有了便捷的可操作性。
文档交互控制的可行性也可以在文档管理一体化模式中得到佐证,包括对电子文件实行全程管理和前端控制也可看作是文档交互控制环节的体现。对于电子文件来说,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实在难以明确划分,交互式控制使文档的控制权力得到分流和交叉使用,无非是为了做到各个环节的无缝链接和系统整合。
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文档在控制主体泛化的情形下发生意义曲解,是另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它客观上要求我们建立起统一的管理体制,避免“政出多门”和标准的不统一,做好文档运动各个阶段管理业务诸环节的衔接和照应,适当归并或简化环节。我们知道文档作为社会活动的记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档在运动的各个阶段会因各种条件的改变而可能发生背景和功能的转移。这种运动包括时间上的运动和空间上的运动,在时间上表现为文档功能的转化,在空间上则表现为文档实体的转移,这种情况在交互控制的环境下会变得尤为复杂。
3.3文档的交互鉴定
文档的交互鉴定要求在文档实体鉴定与职能鉴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鉴定主体内涵,扩展鉴定范围,实现鉴定主体角色转变,即由过去第一人称鉴定模式转变为更为客观化和社会化的第三人称鉴定模式。其核心职能在于重新确定鉴定者身份的“合法性”,改变文档内容与职能信息的理解方式,由过去唯我、实用、主观、线性的方式进化为互文、终极、包容和复调的方式,并提倡在过程中寻求意义而不是在固定不变的模式中维护价值。所以,要建立灵活的鉴定机制,扩大鉴定范围(如由实体鉴定、技术鉴定到职能鉴定、宏观鉴定等),发掘文档的多形态价值,确定档案内容与职能信息的交互理解(不仅是实体价值,更多的是职能知识价值、文化价值等)。在鉴定方法上,可以综合使用逐件(卷)比照法、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但更重要的是丰富鉴定方式(比如从整个社会利用而不是从个别情形利用的角度确定鉴定方式和路径),在文档的动态存在及与社会的复杂关联中确定鉴定的新框架。与此相应扩大鉴定主体的范围,也就是说鉴定行为不仅是专家的,也可以是用户的,不仅是相关机构的,也可以是相关个人的。
以文件的实体鉴定为例。在文档交互式鉴定的模式下,文件传统意义的实体概念具有了电子环境与交互环境下的复杂性。因此,对文件实体的鉴定也就不仅仅单指判断文件的保存价值,更可具体到对文件同类性与差异性的分析(对电子文件而言就成为进行批处理的依据),还可以包含对文件形成者的权力结构及话语方式的审视。这样就拓展了文件与档案的内容含量,大大提高了文件与档案的信息辐射力和社会可用性。我们已经认识到,批处理和宏观鉴定必然为大势所趋。文档的交互鉴定目的之一即在于使得鉴定对象從文件实体转向文件的形成过程,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单纯根据当前和以后的所谓社会需要来描述文件价值的功利观念。
当今时代,“‘自然’已一去不复返地消失。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为一个完全人化了的世界,‘文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5]。在这种情况下,文档交互鉴定的标准本身也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文档的活性结构“不应该简单等同于对主体的外在制约,恰恰相反,它既有制约性又同时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6]。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档交互鉴定的标准除了档案自身状况方面的标准之外,即在基本标准(含档案内容、档案所从属的职能或项目和档案形成者)和参考标准(含形成时间、文件、稿本、有效性、相关档案保存状况、载体和外形特点等)之外,还有社会利用与社会需求的标准。由此,在把握文档鉴定标准时,如何防止在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两个极端间摇摆,也将成为当代档案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
3.4档案的交互利用
档案的交互利用是在档案价值与社会理性的交互参与中实现的。具体而言就是将档案的利用置于规范可靠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并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意义展现。交互利用环境下,原来的管理主体作为参与者与社会视角构成交互关系,从而使文档成为社会活动交互理解和阐释的资源。建立交互利用的平台就是要在“群体借助标准”和价值的整合下使该资源达到最大的有效性。在文档的可阐释性结构建成以后,加强对档案利用的具体性即各种差异现象的分析,使档案本身的特性与利用者的经验相结合,使具有关涉能力的主体产生行为共建和意义生发,在此过程中实现并延伸档案的意义。
譬如建立档案利用价值的评估体系,建设档案利用反馈系统和即时评价系统,该系统可将多种社会关系交互活动的反馈信息同时建成为档案利用的参照系,使档案文本得以进入“阐释的循环”和“利用的循环”,最大限度地整合档案资源,有效服务于社会。再如,可在确保国家机密安全的前提下,建成各级相互关联的网络化文档管理系统和集成数据库(数字档案馆就是这样一种系统),同时利用现代技术条件完善解决档案交互利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降低用户基于数据库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费用,配置多种功能模块(档案管理的登记、鉴定、检索、打印)并在多个系统之间共享数据,等等。
我们还可借用语言符号学模式来理解档案利用的交互性。在交往行为中,言语者(发送者)使用语言符号的目的,是与听众(接受者)就对象和事态达成理解,这种互动发生在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并以沟通行为作为中介,逐渐由形式向经验转化。在档案的交互利用中也是如此的一个过程,我们以规范的档案文本逐步地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前提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消除信息传递概念当中的理想化成分;这样,我们就在任何一次与人类记忆的交往行为中,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发生了关系,而且还有无限深广的背景可供互动参与者做出解释,以此使档案成为一种具有整体论结构的知识。只有这样,档案作为就事论事或是广义文化的信息载体,才能实现与用户的交互理解与沟通,才能在信息互动中实现由形式到经验的飞升。
*本文系2016年杭州师范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文化创新与传播国际中心平台建设项目”(项目编号:4155C502172041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佩仑.后现代主义与档案学:从德里达、福柯到特里库克[J].档案学通讯,2012(2):4-7.
[2]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李音译.档案学通讯,2002(2):74-78.
[3]于丽娟.全宗原则、来源原则及其有关问题[J].档案学通讯,1997(6):21-26.
[4]Terry Cook.The concept of archival holography in Postsafekeeping era: theory, problems and methods[J].Archival Science,1993(Spring):24-37.
[5]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6]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三联书店,199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