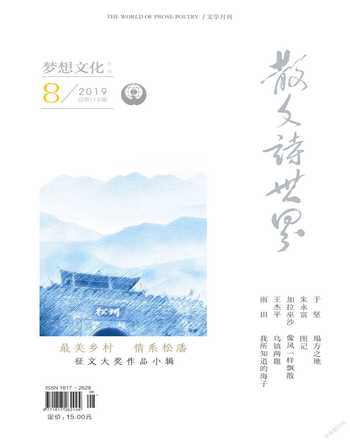我在美丽而忧伤的松潘
阿贝尔
一
在中国乃至东亚大陆,松潘都是一个罕见的有着奇美景观的地方。在漫长的喜马拉雅构造运动中,她首先以一个纯地理的面貌呈现,之后若干年(亦可以称作“最近”)才有了与“松”和“潘”的相遇。岷江和涪江两条脐带般的大河将她与东部平原相连,注定了她日后的归宿与命运,而她却身居雪域高原,直指天空,沐浴着灼热的阳光与清冽的星光,永远超凡脱俗。
“松”是她最早与植物相遇的一个指代,就像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与松潘的红花绿绒蒿和岷江百合相遇,就像我与丹云峡的杜鹃花相遇;而“潘”可以被看作是她与人相遇的一个指代,就像我在民国甲子版《松潘县志》中与小姓沟小活佛黑伦来的相遇,或者在雪山下的林坡寺1与林坡喇嘛相遇。
山水相遇就会长出美丽的植物;山水与植物相遇就会有盘羊和大熊猫现身;盘羊和大熊猫与人相遇便有了今天的松潘。
二
第一次到松潘,我便感觉到一种亘古的美。寂寥的时间像铺展在街面和瓦屋的阳光。五月,天是春色,水是春色,但城外的河谷山色却是冬天的颜色和味道。岷江对岸的草地上、石缝里只有零星的报春花。我不知道这些报春花对于松潘、对于从湔氐道甚至更早一路走来的这个奇美之地意味着什么。
午后的太阳照着松潘古城,有风吹裂阳光,释放多余的热量,给了我适度的凉意。寂寥像轻微的尘埃散布在街面、屋脊的阳光里,呈颗粒状,从街头走过的人犹如梦影。
延薰门里那家现已不在的回民飯馆是一个展开的梦,我们走进去就是梦中人。屋檐下的阳光变得热烈起来,而阳光里的风变得羞涩。我摩挲在像房檐口一样锯齿状的光带里的目光感觉到了它的热烈。有背包的旅人走过,脚在阳光里,身体却在房屋的阴影里。
这亘古的美也包括松潘厚重的历史,而今天能代表历史的就是旧时的城门城墙。置身古松州曾经所在的空间,瞭望穿城而过的岷江,或者登上古城门,我感觉松潘不仅是一个适合凭吊的地方,更是一个适合想象的地方。她曾经有黑森森的松林、松林边扎营的军帐,有从青藏高原下来的马匹,有羊角号。岷江从松林间流过,是溪水原初的模样……想象是对虚无的追述,而非对人类经历的回顾。今天我们看见的城门城墙是明代洪武时期所筑,大气磅礴的城门继承和传达的是天安门、玄武门的气质。如果说门楣上的雕石莲花和门基石上的奔马流云有什么艺术性,也都是悲剧所赋予我的,并带给了我无尽的忧伤。
我或许不爱这些城门城墙,但我爱沉寂在城门城墙里的时间,它用另一种存在印证了我的直觉。我愿意接触残破的城墙,残破是时间的擦伤,能让我欣赏到毁灭的美——延熏门外,保留下来的瓮城城门的外立面就是残破之美的极品,它以黏土的特性最大限度地截留住了时间。
三
2018年10月17日。第四次去松潘。走吉尔上尉和威尔逊走过的东路官道。
进入松潘的第一站是小河营,至今都保留着城门、城墙,老街也保留着旧时的面貌和烟火气。威尔逊对小河营的描述很准确:
在距小河营3华里处,峡谷突然敞开,出现了一个小圆形谷口,建有城墙的小河营就坐落其中。从这里看过去,那里有一个古老的城门,四周峭壁峻岭环抱,显得宁静、美丽。整个村子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威尔逊路过时小河营尚有40名驻军,80年前则有700人之多。如今的小河营只是一个承载了历史含义的地名。
自双河到黄龙是丹云峡——岷山中央部分的裂隙,有20公里长,我印象最深的是十二道拐。涪江在峡谷里孕育、诞生。这是唐代以后由蜀中通往松潘的东路官道,每次路过我都会意识到我正置身官道的咽喉。唐代,特别是明清两代,这条官道极为繁忙,想象走在丹云峡的每个人、每一天以及发生的每件事是很刺激的——人与峡谷、人与溪流、人与岷山,人与自己想象和预感到的危险与死亡,构成了历代人为生活奔波的图像。
在丹云峡,除了呈现于岷山裂隙的“一线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涪江源头的溪水和树。落差大的地方响声轰鸣,透过稀疏的灌木看得见粉状的白沫;平缓处水声潺潺,宽敞的河道已经有了一条河的样貌。在深涧奔腾又是另一种声音,另一个模样。行径在这样的河源,可以听见河流的呼吸。
三路口三面皆是直入云天的峭壁,涪江奔流其间。公路与江隔着灌木、杂木林,看不见江流,听得见水声,偶尔在灌木稀疏的地方可以看见河面。秋天,超过乔木的高度,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都能看见红叶,在崖壁和崖壁坍塌的堆积带上,在对岸的河滩和平缓的半山。路上没车没人,林子和山一片静谧。《水经注》说“涪”是水流声,这条河流淌时发出“涪涪涪”的声音,所以叫涪江。不经意抬头,望见峭壁上的孤松或杂树,感觉是远古的遗落与印证。
我独自走在林间,感觉一下脱离了俗世,做回了一个纯粹的人。回归自然,就这么简单,多余的负担自动卸下,欲望杂念自动卸下。
秋日的丹云峡,云雾缠绕中的绚烂很是暖人,无望中给人希望。想起自己的先祖在明代甚至更早便走这条路过松潘下叠溪,我油然生出关乎历史与时间的感触。
在红叶季,丹云峡——岷山最高冷、最丰饶的裂隙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地貌,而是一个星际的局部。斑斓,带一点衰微的星际,一条银白的溪流从灌木林流过,那是星河;斑斓里藏着深邃,不是指向地下,而是指向由众多高洁的植物织成的另一星空。
丹云峡的美在威尔逊的眼里,也在他的笔下,但不是一种抒情的渲染和哲思的随想,而是精确的记录:
撂荒的开垦地上长满了粗生草本植物,其中齿叶橐吾高4-5英尺,开金黄色花,很显眼。落新妇和醉鱼草都很多。有一种亚灌木状的接骨木3-5英尺,橙红色的果实聚集成簇,是较开阔的湿润地区的一道美丽风景(此后被认为是一种新发现,命名为血满草)。
……
我无法用文字来恰当地表达这荒野深谷的蛮荒和令人敬畏的景色……云杉、铁杉、落叶松、白松、刺柏、紫衫皆有,华山松是最常见的树种,其分布可上到海拔3000米以上,以非凡的方式抱住陡峭的山崖。树干矮小,发育不良,叶短,几乎认不出来,看起来更像是绿色的五月柱而不是松。很多云杉和冷杉果实累累,冷杉蓝紫色匀称的球果直立,异常漂亮。
丹云峡的松、杉、柏等乔木固然很美,但我最欣赏的是那些杂树。它们是椴、槭、白杨和桦,还有少量栎和珙桐。秋天叶子不是很红,但虬枝极美,折射出岁月的历练。杂树的美除了作为一棵树的真实的美学,还有一种隐喻之美:“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丹云峡的杂树不是树于广漠之野,而是立于云上峭壁。
四
牟尼溝是风景区,有扎嘎瀑布和二道海。白林说牟尼沟就是牦牛沟,牟尼是牦牛的变音,我倒是觉得“牟尼”是牦牛的叫声。2016年走西岷顶南侧过隧道去牟尼沟,给我的感觉是与松潘古城隔得很近。特别是中寨子一带,牟尼沟炒辣子松潘古城咳嗽。在松潘古城也闻得到牟尼沟煮酥油的味道。
就我所见,牟尼沟是距离松潘古城最近的游牧区,“庚申事变2”过去了150余年,呈现的仍是异质的高原文化。不管是中寨、上寨还是土官寨,相较于岷江河谷的村寨要更像藏寨,虽说也有耕地,但草场、草地、沼泽和山林要广大得多。五月,透过车窗吹在脸上的风还有刀子的刁蛮。面对沿途风光、风情,我滋生的爱比牟尼沟的溪水还要多。
扎嘎瀑布是隐藏在雪峰下原始丛林的一匹哈达,因为丛林的映染带一点雪蓝。扎嘎瀑布的扎嘎,也是扎尕那的“扎尕”,都是藏语石山、石匣子的意思。尽管扎嘎瀑布已开发为景观,却依然有着纯粹的自然性和神性。其神性是原著民的拜山情结赋予的,与我返璞归真的心相吻合。
扎嘎瀑布的神性潜伏在众神身上,而众神则是由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朵野花和每一块岩石构成的,包括鸟兽虫鱼……打动我的不是瀑布,而是瀑布脚下的每一寸湿地——这个岷山植物的博物园,保留了植物原生的状态,不需要任何过渡就能与神通灵。
即使在交通发达的今天,牟尼沟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由大自然和藏文化构成的,静谧的时候如同史前,苍穹在上,海子湛蓝,溪河蜿蜒,呈现出生命共存的原生与恬静。
五
车进不了松潘古城的北门,我们沿213国道绕道东门入城。
北门叫镇羌门,如今“镇羌”二字被除去,政府文书简称北门。东门叫觐阳门,名称还保留着。“觐阳”就是“观日”。我还记得第一次站在城门下仰望“觐阳”二字的感觉——与古城还有很远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前两次到松潘,我登上城墙,从东门顶走过,尚不清楚这里发生的悲剧——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围城一方由此门攻入。从某种意义说,觐阳门是“咸丰事变”的转折。城门开,看见的不是朝阳,而是洪水般的原住民。
从东门进城是广场,古时的衙署所在地,新城建成前的行政中心。我2007年来,还能感觉到行政中心的气氛。2016年进城,恰逢广场搭台唱戏,省里的艺术家送文化下乡,热闹的场面像是过大年。读民国甲子版《松潘县志》后,我来此就会想到清咸丰十年、十一年的情形——守城的情形和城破的情形,同知张中寅殉难、总兵联昌被林波喇嘛救走的情形。
松潘古城唐已有之,我们今天看见的、谈论的松潘古城是平羌将军丁玉在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设置松潘卫时修筑的。
第一次到松潘古城,我便记住了南门外的瓮城。城墙城门的墙面剥蚀得厉害,墙砖裸呈,有一种真实的年代感,十四世纪的时间直接与二十一世纪对接。在瓮城,我会去想与每一处剥蚀相对应的年代、年份,要么是一场狂风、一场暴雨暴雪,要么是一场战争。特别是靠近金蓬山一方保存下来的瓮城城门,拱门最外层的明砖裸露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砖身,有的砖已经断裂脱落,留下黑洞或深陷的凹槽。
每次在瓮城转悠,我都会生出忧伤。不是一种旷古抒情,而是对具体事件的感怀,对众多个体生命的毁灭的不解。1941年6月23日,日本战机的空袭3是最近的毁灭事件,更让人忧伤的是延时更长、死人更多的“咸丰事变”。穿过不曾整理的草地,看着眼眸一般的蒲公英,内心迟迟不能平复。我把我内心悄然发生的震撼归于一种审美——与看似古代物件所携带的时间的碰撞,归于生命的自我寻找——在时间的保留物中找到生命原本就蕴藏的痛苦与悲伤。
而今,南门外的瓮城城门没变,但瓮城内的野地规整出了花圃,西南一侧靠近村庄的地方修了广场,造出一道山墙,墙上拼贴着威尔逊拍摄的松潘古城的老照片,墙边塑着威尔逊的铜像。两年前,我在此欣赏到了小姓乡多声部羌族民歌展演。
松潘古城的南门叫延薰门——众多古城都有一个这样的城门,以示感恩,亦是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出延薰门,一路向南,如同岷江之水汇入长江,松潘也归属于中华版图。帝国的权力、皇恩、文化也自遥远的内地经此门进入松潘。
读过松潘旧志再到松潘古城,我格外留意穿城而过的岷江。旧志对“庚申事变”破城有两处记载: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八日番兵由西门顶破大西门入城,“掠镇边存储银数万两,毁七层楼,居民哭声震天,男女投河死者数百”;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七日破城后,“四门纵火,三昼夜弗熄,房屋无一存者,官绅兵民死者无数,暴骨原野,江中积尸累累,水为不流”。
我停留在岷江的两处河段,一处是觐阳门外的通远桥,一处是城中的古松桥。这两处江水带给了我更多的想象和忧伤。
岷江源自弓杠岭,沿途纳羊峒河等多条溪河,即便是五月水流也很丰沛、湍急。我看着笼罩在河面的阴影,忽而红如鲜血,忽而黑如药膏,恍惚中似乎看见了官军投入江中的传递求救信号的木牌以及堆山塞海的尸体。
倘若遮蔽上述事变,遮蔽日军的空袭,松潘古城便是纯美如画的。这是一个纯粹地理的角度,也是一个有所取舍的历史的角度。“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国西部生活,我别无所求,只愿生活在松潘。”一百多年前,威尔逊就是站在这个角度写下这句话的。
2016年5月的好几个清晨,我都是站在威尔逊的角度打量、欣赏松潘古城的。我爬上西岷顶和金蓬山,在更高的位置看岷江、看古城。在金蓬山,我找到了一百多年前威尔逊拍摄松潘古城的视角。
太阳初升,古城还在山影中,瓦屋顶加重了山影的黛色。岷江在阴影中像一条凝重的血管,只有对面的西岷顶照到了朝阳,日线以上的部分像金字塔一样耀眼。
回到松潘古城,我尽力避开历史的阴影,不再去想古城几次失守被焚、被践踏的事,回到现实和它的风情。在古松桥,我欣赏到了堪称风情的一幕——一位藏族小伙儿牵着一匹长鬃白马滴哒走着,马背上坐着一位金发碧眼的洋女郎。不过,我更多欣赏到的还是藏羌风情。羌族服飾偏于精悍绚美,藏族服饰偏于隆重庄严,惟有头巾和腰带像一把火。还有回族风情,我印象最深的是面纱和琵琶弹唱。自然,在松潘古城,闻到最多的还是酥油茶和糌粑的味道。
遮蔽的只是视角,忧伤却无所不在,因为记忆——文字——不灭。
松潘古城从筑城第一天起便是一座汉人城。筑这样一座城在雪山脚下,政治作用大于军事功能,对番民不仅是一种震慑,更是一种教化——平常由土司代为管理,出现动荡才动用国家机器。如此,在逾千年的时间长河中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景:中央政权强盛,松潘古城便强硬、强大,所辖村寨便宁静,酥油味、糌粑味和牛羊的膻味便隔绝在古城之外。在有的朝代和年代,松潘古城强硬得就像一艘炮舰,不只是岷山四野的番民归顺,就连千里之外草原上的牧民都主动请降、请治。然而,当中央政权风雨飘摇鞭长莫及时,边城军力虚空,松潘古城自然变得空虚、弱小。军力弱,人心也弱,那些看上去森严厚重的城墙城门一下成了宣纸糊的。
忧伤源自美的毁灭,而这毁灭与消失看似源自异质的文化碰撞,其实是人性恶的总爆发——常常假以道德的面目。
在松潘古城的夜晚,因为“高反”无法入睡时我便会想,我所置身的古城和当年的古城已不是同一座城,除去城墙、城门,地面建筑已没有一件可以作为证物。这样想,我的忧伤便淡去了,不再看见血浸浸的历史和犬齿交错的滴淌着矿物机油的人性齿轮。
六
松潘的美丽有一个适中的海拔高度。低于这个高度,天空便不够蓝,水便不够圣洁,植物也不够清丽。在这个高度,不只是绿绒蒿、岷江百合、雪莲和杜鹃花才有灵魂,牡丹、杓兰、紫堇、风毛菊、龙胆等每一种野花都住着一个灵魂。
在西沟,在丹云峡,我已经察觉到了那个神。它住在五月鸽子一般洁白的珙桐花里,住在每一颗成熟或有待成熟的野草莓里……弓杠岭尚有植被,星星点点的报春、毛茛、点地梅、刚毛忍冬和蓝钟花里也住着神。高山绣线菊和全缘叶绿绒蒿里住着最为华贵的神,不起眼的草甸和石楠状灌木丛住着平凡的神。雪山梁子一览无余,已经抵达草甸与砾石滩的边界,盘山公路像一支神曲蜿蜒折回、攀升,接近、抵达并超过雪线。如果说这样去会见神,怕找不到神的居所。在接近垭口的一个积雪覆盖的草坡,我看见了一处废弃的碉房,我想那就是神的栖身之所。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威尔逊在此过夜,是否与神有过交谈?
岷山主峰雪宝鼎屹立在云海之上,虽然无法抵达,但视线尚可企及。雪宝鼎本身便是一尊神——“夏尔冬日”,东方海螺山,上面如果还住着个神,那一定是某个夜晚穿越星际而来的外星人。雪宝鼎是松潘的高度,也是桥梁,松潘的很大一部分美丽都是她分派的。
天气晴好的时候,站在雪山垭口极目眺望,碧空淼淼如海,数十座雪峰屹立天边,构成一道雄奇圣洁的景链,凌驾在诸峰之上的金字塔状的银峰便是雪宝鼎。
黄龙寺是她裁剪下的蓝天或打碎的翡翠,每一处钙化池、钙化滩在照见天空的时候都可以照见她。她分派出众多的神,一簇杓兰或一树杜鹃,一只盘羊或雪豹,甚至是一滴包裹着钙的凝重的水。
在旧时文人墨客眼里,雪宝鼎和黄龙寺只是对仗的骈文和抒情的托物,我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黄龙寺与迂腐的骈文并无关联,也绝不是为游人的抒情而存在的,不管是高拔雄伟的轮廓还是细致婉转的细节都是上天造物,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真实的美。
尕尼台是岷山山脉与青藏高原的一个分界。从松潘古城上到尕尼台,才真正有种身临异境的感觉——从政治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感觉是准确的。尕尼台往西进入草地,虽然看见的草木花卉大多还是在弓杠岭和雪垭口看见的,但里面住着的神却有了不同的面孔——如果开口也会讲不同的语言。
七
在松潘,万物有灵,但也建有寺庙,供有名有姓的神居住,同时让人在此与神交流。松潘人信佛拜佛,也转山朝山,他们与山有着一种天然的根本的联系。
在松潘众多的寺庙中,我觉得最美的是林坡寺。
2016年5月第一次去林坡寺。之前在松潘旧志上读到,叫林波寺。林坡寺是小西天尕米寺的分寺,比尕米寺建寺稍晚,但相较尕米寺能让我感觉到忧伤。我去林坡寺,便是因了这种忧伤——从悲剧里渗透出的对人性的反思。
那日天气诡异,路上还是晴好,紫外线如野蜂蛰人,一进林坡寺便下起大雨。大雨来临的瞬间,我的镜头捕捉到了黑压压的云层,黑云里透出白光,像舞台上的大幕拉开。第一眼看见林坡寺,就觉得它极美,远离屯镇,坐落在雪山脚下的岩岬上,像一片森林自自然然。
记得那天是农历四月初七,恰逢佛诞日,大殿里七八十位僧人正在诵经,两位僧人吹着羊角号,场面令人震撼。殿外是雨声,殿内是诵经声,两种合唱,我听后灵魂快从毛孔逸出。灵魂不是闪电或蝴蝶的模样,而是一些细微的湿润的颤栗。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到:
下午,和白林找到了林坡寺,即历史上的林波寺。见到了林波喇嘛。在雨中,诵经和羊角号的声音很打动我。主持巴桑是白林的老熟人,带我们去了他的住处,接待了我们,领我们拜望了历代活佛的灵塔——第二尊就是在1860年的番乱中救过多人性命的林波喇嘛的灵塔。林坡寺是我见过的最僻静的寺院,超过了记忆中的郎木寺。
诵经还在继续。雨住了。白林跟巴桑站在院里说话,我走到院前看雨后的岷山。雨后的太阳照着对面的松林和青稞地,有些发白,不是想象中的金子一般。我是很希望进到大殿,在低沉的羊角号声里去感受诵经的场面,这种直接把身心交付于一种自己从未涉足的宗教氛围的体验等于是一次洗心革面,也等于是由肉体深入灵魂。然而,我没好向巴桑请求。
随后,巴桑带我们去了他的住处——寺外东侧山崖的一栋砖混吊脚楼。置身巴桑的卧室,我的感觉奇特而复杂,现代性已占据了雪山脚下这位喇嘛的卧室,自然也占据了他部分思维与审美。我想象他的那些前任,一百多年前的前任和三百年前的前任,占据他们思维和审美的除了佛主和经意还有什么?我想可能就是救世。“庚申事变”时的林波喇嘛就是这样,没有回避激越和血腥,而是站在佛主普度众生的立场,不分敌我,尽力拯救冲突双方的生命。
林坡寺是一种记忆,一种审美,它关照灵魂,也关照历史。在我审慎又不乏理想主义的虚构中,它更多是一个舞台。近在咫尺的松潘古城在被围攻、被破城、被焚烧和践踏,而林坡喇嘛奔波其间,在普度——挽救众生。
慈悲是一种胸襟,也是一种审美,它超越了政治和文化,以雪山的高度观照每个生灵。
八
历史如岩层,揭开能看见化石,气味消失,色泽依旧鲜艳;距离近的历史也如苔藓,尚且保留着气息和血迹。
所有生命都是创伤的修复者,在大地震撕开的裸土裸岩上新生的植被就是一个例证。现实——我们经历的每一天、每个时代都无一例外地修复着历史。
遮蔽不是修复,是视而不见。
第一次去小姓沟是为探寻“庚申事变”的起源。车到镇江关右拐,经过镇江关一村。砾石、灰土、崩塌的山体,植被稀疏几近裸山。过碑子寺植被渐好。乡政府驻地北山荒疏,南山植被繁茂,河流极美,河畔高大的白杨极美。北山有爬城、爬城小寨子和平安寨。最远是热溪和纳姑寨。每一个寨名都是一块化石。
我们上到平安寨。从寨名可以窥见其早年的动荡,而这动荡必定与“咸丰事变”有关。
平安老寨已经搬迁,仅留下一栋木屋。耕地为台地,多已撂荒,长满野草和蒲公英,只有不多的台地还种着莲花白和叫不出名字的药材。平安寨原本是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因为缺水和交通不便才搬下山的。如今,撂荒的台地和搬迁后的老屋基还残留着生活的气息,由这些气息尚能想到曾经的劳作与喧腾,想到“庚申事变”期间那些喧腾而不安的夜晚。平安寨的远景是葱郁的森林和雪峰,就地势和植被,跟我熟悉的白马寨相似。
龙头寺在平安老寨脚下一个小山嘴。相比两年前所见的龙头寺,多了几分金碧辉煌。寺庙刚刚完成风貌改造,几位村民正在庙下的山坡铺设水管。我感觉小庙日渐多了凡间的气味,如同我对村委会的感觉。人还在大殿前的院里,眼睛已搜寻到上次拍过的那尊石碑——石碑依旧立在大殿右侧的菜地里,只是野草长深了,把石碑显矮了。第二次来,我依旧视它为“庚申事变”的唯一证物。我环顾四下,再无法将小庙与小活佛黑伦来联系在一起。眼前的寺庙呈现的整洁、平和与敞亮,完全无法让人联想起当年的事变。
从龙头寺下来,我们由新建的平安村过铁桥,前往两年前没能去到的大耳边。
154乡道植被很好,整条溪谷都很幽静,有种纯正的农牧味道。路上遇见一棵几百年的白杨,我感觉如同见到了这个地方的神。这条叫不出名字的美丽溪谷颇像去扎尕那的益哇河谷。
大耳边已经废弃,但还没有坍塌、没有被打造,还弥散着民国甚至咸丰庚申的气味——这是我此行想要的。这气味是一种忧伤,叠加在古老的废寨之上。
这里是“咸丰事变”的策源地,黑伦来的出生地,美丽松潘的忧伤便是从这里弥散開来的。
同行的人进了寨子,我愣在寨口,心里一遍遍念叨:“大耳边,大耳边,大耳边……”
寨子背后的台地很陡,一台台上去,视线所及都是秋色浓重的荒草,荒草之上耸立着几栋独立的木楼。
驻足大耳边的内部,我开始什么感觉也没有,包括恐惧和茫然。大耳边很美,即使被废弃也很美,时间在各个方位、各个细部雕琢,粗放的门槛、槛石以及裂口的夯土墙都堪称杰作。
大耳边遗址保留完好,老屋、新房、圈道……没有新近生活的痕迹,但可以见出村人搬走并不久,旧时生活的痕迹保留完好,看见的器皿空置着,但绝无丢弃,木凳、木梯、水桶以及农具的摆放都在应该的位置上,像是还有期待。
院落中央的一两户人家的房子特有意思,下面土基,上面木楼,木楼的板壁上画着图案,像阴阳八卦又不是阴阳八卦。我感觉到了一点气氛,但不浓。踩着秋来的衰草拍照,倏然想到脚下的草根从来都不曾死过,一茬茬地生,想必也有咸丰年间甚至更早的……星移斗转,人事更迭,唯有野草不死。
走木梯上到木楼,从夯土墙上部的小窗往里看,里面是烟熏火燎的黑暗。木梯、夯土墙、小泥窗……看上去都有百年了。百年里,多少人从这架木梯上上下下,多少代人,而今被弃置,再无实用的功能,只是作为像我一样的旅者眺望历史的阶梯。
继续前行,眼前全都是土基屋,且更古老、破败,屋间通道也更荒芜,野草丛生,夯土墙或开裂或垮塌。伫立其间,思绪渐渐被荒芜淹没……那一夜,最终决定起事的那一夜,小活佛的母亲额能作住在哪间土屋,说了什么,已没有人能从158年前站出来指认。
我的忧伤犹如大耳边往日的炊烟是青蓝色的,它们脱离我,弥散在基石敦厚、夯土古旧、几近坍塌的老屋里,萦绕着那些已经变成时间本身的房屋构件。我听见了一声响动——说话声或脚步声,或雕刻、堆叠木片的声音;接着是犬吠,由一只犬到一群犬;随后我看见了人影,在被夯土压住的木门背后,在路下一人深的狗尾草丛,他们或蹲或立,手托烟杆儿,嘴角沾着白沫。
我这样想象,并没脱离现实,那些响动和影子不过是些线头,松手即可消失。158年的距离,至少需要五六代人来丈量。但眼前的老寨、老寨内部的通道、通道地下的草根是没有距离的,随手摸一把夯土墙便可触及历史。
此行我见到了两个大耳边人。一个是热切,在大耳边的老寨,红脸膛,个子不高,但长得壮硕;一个是龙布塔——一个老者,他是现今小姓乡唯一的释比。问及黑伦来与额能作母子,他们都闻所未闻,他们的记忆仿佛只局限于移民搬迁和近两年扶贫的事。
面对热切和龙布塔的记忆缺失,我生出一种错觉——历史是人为切断的,就像我们读到历史的某些段落,不敢面对便哧溜一声将整页撕掉。
这么想,我的耳畔回响起小姓乡人的多声部羌族民歌合唱。2016年我听过两场,一场在古城剧场,一场在瓮城。合唱萦绕在耳畔,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感觉,很像是白马人唱自己的民歌……此刻我想到了,谁说大耳边人记忆缺失?多声部便是他们的记忆——永远的记忆。
九
松潘还有一种美丽、一种忧伤,那就是松潘独有的星空星象,与雪宝鼎和松潘古城相照应,也与我的内心相照应。
我先是在杨友利的摄影作品里看见,之后方得身临其境。
那是一个晴好的夏夜,我从平武驱车前往雪山垭口,大地是点缀着野花矮灌的草甸和砾石滩,头顶是繁星建构的苍穹。置身这样的夜晚即是置身松潘的美丽,也是置身星际苍穹。短暂的喜悦之后是长久的寂静与孤独,伴随着突袭而来的忧伤——犹如凝固的颤栗,透着凛冽的紫蓝色的弱光。
注释:
1.林坡寺:小西天尕米寺之分寺,旧志记作林波寺,位于雪山梁子西坡林坡村。因时任林坡喇嘛参与抢救“庚申事变”中的重要人物并说服官军平叛后和平解决事变而载入史册。
2.庚申事变:史称“庚申番变”。清咸丰十年时属松潘辖区的藏羌原著民反抗松潘官府营兵的暴动。详见民国甲子版《松潘县志》《书庚申番变事旧案》一文。
3.日机轰炸松潘古城:民国30年,1941年6月23日,27架日机由武汉起飞,上午十一时许开始轰炸松潘古城。投弹105枚,死亡198人,受伤49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