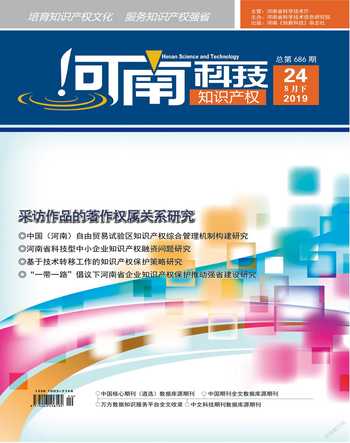采访作品的著作权属关系研究
采访作品俗称采访稿、访谈稿等。流行的观点认为,报刊社记者采访作品的著作权属于采访者。本文基于权利人对采访作品维权三个案例的研究,揭示了采访作品是在合作作品基础上形成的整理作品,具有双重著作权属性和复杂的著作权关系。
学术研究、司法实践与问题的提出
学术研究概况
对采访作品,学术界从著作权视域出发进行研究者较少。目前,学者研究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采访作品属于合作作品。冯建华在我国可能是最早研究采访作品著作权问题的学者。他认为访谈作品是访者和被访者的合作作品。二是采访作品是合作作品和演绎作品。如杨玉凤在对采访作品分为问答式、散文式和实录式三种类型基础上,提出了问答式在具有合作意向和合作创作事实基础上构成合作作品;散文式和实录式构成在被访者享有口述作品著作权基础上的整理作品,著作权由访者享有。詹启智研究认为,采访作品的初始形式是属于合作作品,采访稿是对双方合作作品进行再创作形成的新作品,著作權属于双方共同享有。此外,郑松辉也持相同观点。三是采访作品应区分作品类型,具有不同权属。陈咏梅在将访谈作品分为直接对被访者的口述或录音资料进行文字化而形成的访谈作品、被访者仅提供一些原始素材,由访者独立创作完成的访谈作品、由访者和被访者共同完成创作的访谈作品三类基础上,认为第一类访谈作品著作权属于被访者,第二类访谈作品著作权属于访者,第三类访谈作品属于合作作品,著作权属于访者和被访者。袁志赟、张佳欣在对访谈作品分为问答式、自述式、散文式三种不同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问答式、自述式访谈作品属于合作作品,著作权由访谈双方共同享有,散文式访谈作品是采访者独立创作行为,著作权由采访者享有。但从学术界的研究看,无论所持观点是否有所差异,基本都认为问答式采访作品属于合作作品,著作权属于双方共同享有。
司法实践
在司法实践中,笔者检索到了三个相关判例。这些案例对采访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则存在不同的裁判结果。
案例1:余秋雨诉中国文联出版社纠纷案。案中余秋雨共主张包括《从真实到有序》(简称《从》)、《余秋雨一声不吭也不好》(简称《余》)共11篇作品的著作权。但法院认为,《从》等8篇因署有余秋雨名字予以支持;《余》等3篇文章的署名均非余秋雨,基于本案提起的侵权诉讼,使之著作权的权利归属产生异议处于不确定状态不予处理。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和《余》文均为访谈作品,《从》的署名方式为:作品名称下署杨澜、余秋雨;文中署名使用符号署名方式:问用“□”标示(杨澜)、答用“○”标示(余秋雨)。《余》文的署名方式为:作品名称下署谭璐;文中署名方式为:问用“记”标示(谭璐),答用“余”标示(余秋雨)。
案例2:三面向公司诉网易著作权纠纷案。初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作品《三问“石化双雄”:油价上涨何时休》系访谈式文章,文章正文以被访者的回答为主,文章署名记者对该文所涉问题进行了首段介绍、引出,以三个小标题对全文内容整理、提炼,并对具体的问题进行了排序的设计,以及对被访人口头陈述内容进行文字整理,文章作者的以上创作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涉案文章构成独立作品,署名记者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被访者虽然对其口述内容部分享有权利,但涉案文章系独立作品,在署名记者与被访者就涉案文章著作权未做出明确约定情况下,被访者无权就涉案文章对其他主体作出授权许可,遂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例3:冯娴与贠思瑶等著作权纠纷案。法院查明斌认定:《杭间访谈录》是冯娴对杭间进行的访谈,文章采取了一问一答的方式,体现了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互动与相互配合的过程。该类访谈作品的形成不是采访者一人完成的,而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共同合作的结果。该作品系合作作品,且属于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对于采访作品,特别是问答式访谈作品属于合作作品,著作权属于访者和被访者共同享有没有争议;但在司法裁判者中既有认为问答式访谈作品权属不稳定,还有认定为系合作作品,也有认定为系独立作品,与此相应著作权归属就有不同的结论,相应就有不同的司法裁判结果。由此引起了笔者对记者采访作品的著作权属关系中涉及的署名问题、新作品内部蕴含的权属关系及其被访者是否有权独立授权许可他人行使、如何主张侵权责任等问题进行思考。
采访作品的署名与首要著作权属意义
署名与署名权
作品乃作者之子。署名就是表明作者与作品具有亲子关系的特定行为。为此著作权法赋予了作者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这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核心人身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非常重视对作者署名权的保护。著作权法对署名权的保护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以积极方式进行保护。《著作权法》采取积极方式保护署名权,主要表现在授予作者享有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这一积极权利,此外还表现在第十五条在影视作品著作权属规定中强调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第十六条在职务作品著作权属规定中强调作者的署名权、第二十条在著作权保护期规定中强调署名权保护期不受限制等积极权利视域进行保护。二是在著作权限制规定中,将尊重作者署名权作为著作权限制成立的前置条件予以规定。在第二十二条的合理使用中规定须指明作者姓名;在第二十三条教科书法定许可中规定,须指明作者姓名。三是将署名权保护作为作品使用者依法使用作品的强制性义务和并课以侵权责任进行强制保护。如第二十九条规定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作品使用者不得侵害作者依法享有的署名权;第四十七条在法律责任中规定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和剽窃他人作品的均要承担侵权责任。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也对孤儿作品、作者死亡后署名权的保护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也从三个方面对署名权的保护进行司法界定。一是在何处署名进行规范。其第七条规定,作者可“在作品或制品上”署名。二是对署名顺序进行规范。即有约定的按约定确定署名顺序;没有约定的,可以按照创作作品付出的劳动、作品排列、作者姓氏笔画等确定署名顺序。三是将署名作为出版者合理注意义务进行规范。如第二十条第二款。这些规定从不同方面相结合,形成了我国严密的署名权保护体系。
关于署名权,学术界最权威的解释认为,署名(权)是作者依法享有的包括在作品上是否署名以及署实名、假名(笔名)或不署名(匿名)的行为(权利)。基于《著作权法》《条例》《解释》对著作权人如何行使署名权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在学术界仅见到冯晓青、尹西明、修扬、商志超、张玲等少数学者进行专门且有一定深度的研究。笔者认为通说和相关研究对署名行为的认识并不完整。要准确理解把握署名行为,还需要注意下列两点。
1.在作品何处署名。对此,《著作权法》《解释》均有明确规定,即“在作品或制品上”署名。总结我国作品署名情况,可以发现作品的署名位置通常有:(1)题前或题上(文前或文上)署,如《詹启智:自主创新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载《金融博览》2011(11)]。(2)题中署,如《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3)题下署,如《学术数字出版面对市场必须把握好的关系》/武宝瑞[载《出版发行研究》2016(8)]。(4)文末署,如《新时代跨越大洋的牵手》……(作者为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载人民日报2018年1月20日第3版]。(5)文中署,如《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记者问:……李克强:……[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16日第1版],也会采用文中夹注时使用文中署等。(6)页末署或文章首页页末署,前者署名主要出现在文章引文采用页末注时出现;后者主要在出版个人文集时收录合作作品时对其他合作者进行署名时使用等。因此,从现实看“在作品或制品上”署名之“上”,应有多种理解,不应仅从上、下方位视域进行狭义理解,此“上”泛指在作品的任何地方进行署名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本文总结的六种情形。案例1中,法院认为《余》等3篇文章的署名均非余秋雨,就是将“上”仅视为题下署排除了文中署的结果,是对“上”的片面理解所致;案例2存在案例1同样的情况,均将文中署不视为署名方式和署名顺序的常规安排。
署名位置或是根据作品形式、或是出版者或作者根据惯例或习惯决定。在作品何处署名,尽管没有具体而明确规定也不必要规定,但与作品的署名顺序有一定的关系。确定在何处署名,可参照《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合理确定。涉案作品的署名位置即是按照作品排列顺序确定的署名位置或署名顺序。被访者是否在题下署,都是被访者行使署名权的方式;无论作者在作品上何处(题下或文中)署名,均不会违背著作权法的规定。
2.与著作方式相结合的署名行为。这是诚信著作的署名规则。著作方式即创作方式,主要有著、编著、编(包括主编)、改编、译、注释、整理、绘画、摄影等。除报刊文章原创直接署名不加著外,其他著作方式都要和创作者名与著作方式相结合进行署名,以表明作者的何种创作方式,如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沈仁干、钟颖科著《著作权法概论》等。因此,报刊上的不加著作方式的署名,直接表明的是原创或独创著作方式。
署名的首要著作权属意义
根據《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署名权的规定和第十一条关于著作权归属的规定,署名权作为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其首要意义在于确认署名者是作者,依法享有署名作品的著作权(如有相反证明者除外)。个人独立创作完成的作品,应当属独立完成者的姓名(名称);合作完成的作品,对作品创作做出了实质性贡献者,均有权在作品上署名。演绎作品、汇编作品除了署名演绎者、汇编者姓名(名称)外,还应当指明原作品的作者姓名(名称),以直接标示署名者的著作权属关系。因此,凡在作品上依法署名者,均与被署名作品之间具有这样或那样的著作权属关系。
基于三案作品的署名为记者题下署和记者、被访者文中署。记者题下署表达的是记者对文章享有著作权,这种著作权性质需要根据作品创作性质进行界定。被访者文中署表达的是被访者对其文中内容享有著作权,其著作权性质需要根据作品创作方式进行界定。三案中根据涉案作品创作方式,记者题下署表达了作品系记者演绎之子,被访者文中署表达了可分割的部分作品是被访者原创之子。这就是三案不同署名的首要的著作权属意义。这是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得出的必然结论。被访者依法享有涉案作品回答部分即口述作品的著作权。在三案中只有案例3的处理结果是正确的。
共同所有、单独行使与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问答式访谈作品,通常记者提问,被访者答复,答复内容通常占据作品的主要部分。三案作品情况均是如此。根据作品概貌,从著作权意义上看,涉案作品存在下列作品形态和复杂的著作权关系。
整体作品形态及其著作权关系
1.涉案作品作为采访者与被访者合意创作的作品,是一部合作作品,且是一部可以分割或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
三案中涉案作品文中的共同署名、署名位置或顺序证明:采访作品首先是合作作品。作为合作作品著作权归合作双方共同所有。因其合作作品具有明显的可分割性,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被访者对其创作部分单独享有并行使著作权。在案例3中,法院直接认定了涉案作品系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是完全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这是第一次在司法上明确了问答式采访稿系合作作品,这一认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案例1、案例2并未将文中共同署名视为合作作品的署名方式,有违著作权法的规定。
2.涉案作品总体是一部整理作品或演绎作品。问答式采访作品除了问答之外,通常还会有一个记者创作的按语构成。读者看到的采访作品,并不仅仅是一个合作作品。记者以其职务行为,在合作作品基础上添附了新的创作劳动。这种创作劳动基于初始的合作作品而产生了一个新作品,即整理作品。根据案例2、案例3法院查明的事实,署名记者对被访者的口述作品进行了整理,其整理创作行为具有独创性,涉案作品总体上具有整理作品的性质,属于整理作品。这一观点被案例3判决至少间接确认——对案例3的另一涉案作品,即《理念与运作》法院认定:《关乎理念》(原载《设计》杂志2011年3月期)是冯娴与罗思娜的采访稿,《理念与运作》将《关乎理念》中的一问一答形式进行了修改,形成了一篇文章;在法院对争议问题的评述中认为:《理念与运作》系冯娴根据其与罗思娜之间的访谈稿整理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后的改编作品;笔者注意到法院在认定与评述中对于《关于理念》的称呼是不同的:前者称为采访稿,后者称为访谈稿——前后不同称谓可以证明这样一个问题:采访稿是发表的稿件,访谈稿是未发表的原始稿或作品的初始形式,采访稿是对访谈稿整理的结果——由此证明了采访稿是基于访谈稿(合作作品)的整理作品。事实上,记者采访后无论以问答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发表的采访稿都是记者以其职务行为对访谈稿进行整理(条理化、系统化)的结晶,记者的采访稿的主要创作方式就在于整理创作。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二条之规定,署名记者或报刊社享有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演绎作品的著作权。访谈作品通过记者的加工、整理,是记者和被访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因此,记者在问答式等采访作品中通常在题下署名,表明的是记者对整理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权(或署名权,这是著作权属于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记者保留的著作权),记者的整理著作权延及整理创作的独创性部分,不延及合作作品的著作权。这就是问答式等采访稿记者通常在题下署名并采用记者、被访者文中署名的著作权法意义所在。因此,案例2中法院认定系争作品为独立作品,值得商榷。
综上所述,涉案作品均是署名记者基于与被访者合作(创作,原创)作品(原作品)基础上经演绎(整理)而产生的作品。原作品作为合作作品具有可分割性或不可分割性。作为演绎作品,行使著作权须“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双重著作权属性及其内部关系
《著作权法》第十二条中的“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的含义,从该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二款等具体使用演绎作品的规定看,是指应当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这就是著作权法构筑的使用演绎作品需要取得双重许可并支付双重报酬的著作权法律关系。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与原作品的著作权是不同的著作权。演绎作品具有双重著作权属性,是双重著作权作品。这是著作权法构建使用演绎作品需要取得双重许可支付双重报酬法律关系的基础。因此,访者依法独立享有演绎作品著作权,但不延及原作品的著作权;他人使用演绎作品应当取得被访者的许可并支付报酬。被访者在涉案作品中享有的著作权与演绎者享有的著作权并行不悖。被访者依法行使原作品的著作权,并不需要演绎作者许可或同意。相反,演绎作品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则需要受到“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原则限制。
1.作品的内在关系决定作品创作者间的著作权关系。
涉案作品均是在已有作品(原作品)基础上经署名记者演绎产生的新作品(演绎作品)。因此,署名记者新作品著作权内涵了访者与被访者合作完成的合作作品(原作品)著作权,新作品著作权基于原作品著作权而产生。三案被诉行为或侵害了被访者在新作品中内涵的原作品著作权,或同时侵害了署名记者在原作品基础上产生的新作品的著作权。
2.署名记者新作品是对可以分割的合作作品的演绎。
涉案作品均是在合作作品基础上产生的演绎作品(经对初始访谈稿整理产生的作品)。记者采访被访者最初通常都是问答式,记着将对其问与被访者答通过一定方式(书写或录音录像)记录下来。初始问答式口述作品经过书写或录音录像,形成文字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此时采访作品的初始形式属于可分割的合作作品。但记者使用初始作品,需要根据报刊社用稿目标、原则进行整理使之成为整理作品。可分割的合作作品经整理后产生的整理作品,具有两种结果:一是主要问答部分具有可分割性;或将原问答式合作作品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理作品。基于可单独行使可分割部分的著作权和双重著作权中的采访者与被访者的单一著作权关系,双方均可依法独立行使其著作权。基于不可分割的共同著作权关系,则按照“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原则和双重著作权中的原作品、演绎作品关系行使著作权。
3.署名记者的合作作品和整理作品是职务作品。
记者采访形成的合作作品和对初始采访作品的整理产生的整理作品,都属于职务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署名记者单位至少享有两年的优先使用权,署名记者是否享有著作权还取决于署名记者与单位的合同约定。但该约定不影响被访者对其独立创作部分的著作权。因此,案例1、案例2中法院简单认定署名记者享有著作权法律依据不足。
总之,在采访作品复杂的著作权关系中,基于初始合作作品的可分割性和使用演绎作品双重许可并支付双重报酬的著作权关系中的基于应当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的法律关系,采访者、被访者均有权单独行使著作权。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双方均无正当理由阻止对方依法向侵权者主张权利的著作權行使方式。
采访作品被访者如何主张侵权责任
基于采访者通常在题下署名和不成文的观念,记者或报刊社享有采访作品即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如有侵权,其维权依法必然得到支持,案例3就是对这种现实状况的有力佐证。因此,现实中记者或报社依法维权并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案例1、案例2被访者的依法维权,则出现了不应有的维权障碍。因此,本文重点关注被访者依法维权问题。根据采访作品侵权的作品性质,笔者认为,被访者维权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被访者应以原作品著作权人身份依法主张著作权
采访作品的最终形式是对采访稿(原作品)经过整理后的演绎作品。被访者并不享有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侵害著作权者通常表现为对演绎作品著作权的侵害。但演绎作品之基系原作品,侵害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必然包含了侵害原作品的著作权,因此,被访者主张著作权的身份应为原作品的著作权人。
被访者通常不宜基于合作作品进行维权
采访作品的初始形式作为合作作品,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能够与读者见面的作品则是具有可分割性或不具有可分割性的合作作品的整理作品。如果具有可分割性,则可独立主张其创作部分的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行使著作权包括积极授权他人使用或消极禁止他人使用。根据《条例》第九条规定,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协商一致是行使的前提,这个前提并不一定能够具备。虽然被访者依法制止侵权主张权利,合作者阻止被访者行使权利的理由不正当,但并不等于可以协商一致。特别是合作作品往往并不是采访作品的最终形式。因此,除了部分可分割的作品外,通常不宜以合作作品主张权利。
被访者应基于演绎作品以“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为由主张权利
“演绎作者对侵犯其演绎作品著作权的行为,有权独立提起诉讼,同时,原作品的作者也可以对侵犯演绎作品的行为提起诉讼,因为侵犯演绎作品的行为,也可能同时侵犯了原作品。”被访者可以主张原作品的著作权,但原作品是未发表的作品。已经发表的作品是演绎作品,其中包含了原作品。因此,他人侵害演绎作品著作权是被访者维权之外壳,其中包含了原作品著作权是维权之内核。实现维权目的须借助于演绎作品之壳。被访者单独主张著作权的法律依据在于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以被告未经许可并未支付报酬侵害原作品著作权为由主张权利。案例1、案例2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原因就在于:被告和法院均未认定采访作品初始形式是合作作品,均认为被访者无权行使著作权,这是判决权利人败诉的根本;在后判决案例3正确认定采访稿系合作作品,为被访者依法主张著作权奠定了司法基础。
结论:谁动了被访者原作品的著作权
三案被告未经演绎作品中的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未支付报酬动了被访者的奶酪,侵害了原作品的著作权,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案例1、案例2人民法院以在署名记者与被访者就涉案文章著作权未做出明确约定情况下,被访者无权就涉案文章对其他主体作出授权许可、对侵权人主张权利,遂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违背了使用演绎作品“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的规定,违背了使用演绎作品应取得双重许可并支付報酬规则,与法律的明确定相冲突,系适用法律错误 。
案例1、案例2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源于对作品署名方式的片面理解上和对涉案作品形态为独立作品的错误认定上。应当说,独立作品并不是严格的一个著作权法概念,但它是一个法学研究的学理概念。从法院对这一概念的使用看,其独立作品相当于学术界一般作品的概念。一般作品是指根据创作产生著作权原理因作品的直接创作行为而独立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如个人作品、合作作品;与一般作品对应的是特殊作品,是指著作权属于非原作者情况下创作的作品,如演绎作品、汇编作品、职务作品、视听作品、委托作品等。在著作权法上,与独立作品相联系的法律概念是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使用的“原作品”概念或第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使用的“已有作品”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均出现在演绎作品(第十二条)、汇编作品(第十四条)的授权或使用的相关规定中,因此,“原作品”“已有作品”是与演绎作品、汇编作品相对应的,产生演绎作品、汇编作品的基础性作品。涉案作品的初始形态均是合作作品,终稿即发表的采访作品从本质上看属于在合作作品基础上的演绎(整理)作品。因此,案例2法院将独立作品作为一般作品且将其限定为个人作品,是适用法律错误的根本原因。
三案纠纷对传媒界使用采访作品敲响了警钟。包括出版、表演、录音录像、网络传播等采访作品使用者,应按照《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等规定,尊重原作品、新作品著作权,严格遵循双重许可并支付报酬的著作权使用规则,全面尊重采访者、被访者的双重著作权,防范侵权现象发生,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做出应有贡献。司法者应充分理解和把握双重许可并双重支付报酬法律关系的意义,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和法律环境。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