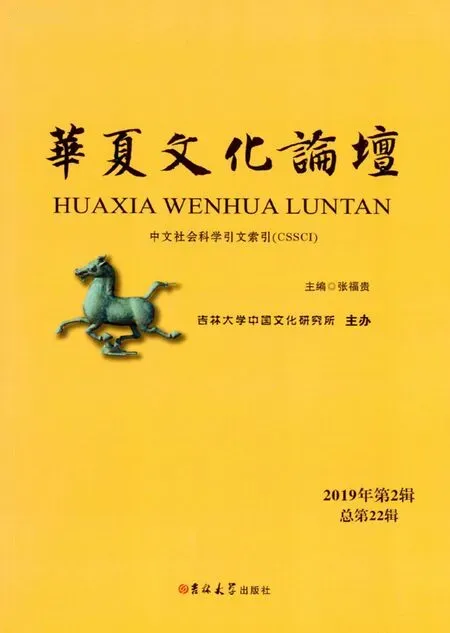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融通探论
——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
魏 涛 王 宁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具有双重超越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主流的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融通和契合之处。从以仁为本体的仁爱思想衍生出以仁政为根基的民本思想,到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友善、民主观念;从传统尚诚守信精神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弘扬的诚信精神;从传统明道正义精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坚守的公正观念;从传统和合大同精神到新时代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处处展现了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现代观念背景下对儒学进行阐释,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既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传统文化进行“双创”的发展战略,同时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立足于未来世界民族之林和多元文化之中的信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任何民族的价值观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积淀而成。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同其他民族的价值观一样,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根据时代的需要跨越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最终凝结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习近平同志在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针对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习近平同志提出了重要的发展战略,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之主流,儒学无疑带有时代的烙印,但若以其固有的伦理道德思想特质、以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久远价值的基本精神来表现自身功能时,儒学仍是珍贵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因此,要摒弃那些不合时宜的糟粕,透过理论的疏导发掘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成素,充分实现“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追源溯流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返本开新中突出当代价值观重塑之中国特色。
一、讲仁爱:友善观念的中国传统性善论根基
在中国哲学的思维中,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以“仁”建立人间及天地万物亲合关系的文化。孔子以宗法亲情为出发点,创造性地把“仁”建立在了孝悌的心理情感之上。这一思想确有其合理一面,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以宗法血缘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特征。继孔子之后,孟子改变了以孝悌为仁之本的看法,提出了“四心”说,此后把仁的基点从血亲孝悌转换成“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并发展出“仁政”思想。西汉董仲舒对于先秦儒家的“仁”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他说道:“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董氏从外部入手,以阴阳学说找寻到了“仁”的宇宙论根据。唐代大儒韩愈以“博爱”一词释“仁”,并对其做出了明确规定,他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仁义)而之(往)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北宋以降,儒释道融为一体的理学思潮盛行,不论是程朱理学派,亦或是陆王心学派,均根据自己的哲学思想将“仁”纳入了理学范畴体系中,并把“仁”由伦理道德范畴提升为本体论和境界论范畴,使“仁”成为“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境界。周敦颐发挥了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以爱释仁,指出“爱曰仁”。(《通书·诚几德》)张载也主张以爱释仁,认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此外,他在《西铭》一书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这恰恰是对天地万物为一体境界的具体说明。程颐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思想,以“与物同体”释仁,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把他的致良知学说与宋代的“万物一体”之说相结合,并在其《大学问》一书中,集中阐述了“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贵于万物,完全是人能超越自己的形体而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清代儒者戴震提出“生生之谓仁”(《原善》卷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戴震的仁论,是从理学道德境界说向近代人本主义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自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图强救国的时代课题。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谭嗣同在广泛吸取“西学”的基础上,把传统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相融合,为“仁”注入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因素。
盖依上述所言,“仁”这一概念虽具有抽象的、空想的性质,但它凝聚了中国传统人道主义的思想,并基于此铸就了一批仁人志士,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毋庸置疑,这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最具耀眼的民族之魂。在西方成熟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感到人生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工具理性、个人主体性的生活方式在极度张扬,一种人生意义的心理感受、理性自觉在不断被现实生活所剥蚀。世俗的力量和政治的推动不断地削弱人们内心的道德堡垒,但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无疑是人的现代化,人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创造者。然而在今天到处都是以自我的利益、群体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为驱动力的社会中,还有谁能穷仁之理,仁爱天下万物呢?有谁还能极仁之性,以同然之心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呢?诚如陈来所言,“仁体论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一个包含无数关联的、变化的世界,一个内在地含有价值的世界。”换言之,我们所生活的宇宙并不是一个机械的存在,它是一个动态的、有机的、相互联结且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德国思想家舍勒以为爱是宇宙动因,是创造生命的方式,是宇宙的爱之力,简言之,他要把基督思想的爱感优先引入哲学以重建本体论,以此来修复现代社会破损了的人心秩序。这也与我们的思路接近。在仁学的立场上,“仁”字代表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即双方互相关爱,和谐共生。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随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价值观念方面,西方的“普世价值”无孔不入地侵蚀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主流意识形态这个“一”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多”并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竞争态势,使得人们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现代人的“优越感”日渐凸显。同时人们的人生无意义、无价值感受的孳生蔓延,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仇视,加深了人自身的荒芜感、孤独感。大体上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处在制度和价值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仍葆有广阔的社会进步空间,在此背景下审视儒家传统,用自己的思想资源对发生在现代化已成熟的西方社会失落的精神危机做出可能的回应。“仁爱”作为儒家哲学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核心理念,其推己及人且关爱他人的内在精神,无疑对于处理当下社会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在现代观念背景下从儒家思想和生活方式中诠释出其内涵价值,找到中国传统人性论根基,重新唤醒人们心中的“爱”的观念,要求做人要讲仁义,重信用,讲礼貌,行孝悌,懂宽恕,并汲取仁爱思想的营养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友善。
二、重民本:民主观念的中国传统民本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从西周时期开始倡扬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再到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最后发展到明代大儒黄梨洲的“民主君客”说。儒家民本思想一以贯之,皆代表了传统价值观中“以民为本”的民本精神。台湾学者李明辉将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容归纳为六点:“一、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二、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之同意;三、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务;四、‘义利之辨’旨在抑制统治者的特殊利益,以保障人民的一般权利;五、‘王霸之辨’意涵:王者的一切作为均是为人民,而非以人民为手段,以遂行一己之目的;六、君臣之际并非片面的绝对的服从关系,而是双边的相对的约定关系。”概言之,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防范权力的作用,并且成为清末知识分子接受近代西方民主观念的桥梁,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现代民主观念相接榫的枢纽,从这个方面不能说传统的民本思想业已失去意义。
此处需要强调的是,民本观念并未在传统社会得到广泛落实,依陶希圣所言,民本思想是地主士大夫的思想,这并不代表民众普遍政治个体的自觉,所以中国历史上虽有民本思想的巨流,但并无民权运动的兴起。士大夫们提倡贵民、爱民,究竟由谁来贵来爱?是君。可见“士人阶级的民本制,要有绝对主义君主与之提携。”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百姓仍然受到统治者的支配。刘泽华指出:“许多学者由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出中国早就有了民主思想、民主主义。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还有一个词:君本。君本、民本两者是互相定义的。中国最早的民主,是‘君为民主’,也就是君王是民众的主人,这与现代的民主观念是不一样的。君为民主,民为邦本。这是一个典型的组合结构。你只抓其中一点是不行的。”可以说,百姓除了为其效劳,还要充当统治者表现“父爱”的对象。在具有等级性的社会阶层结构、以伦理义务为本位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真正改变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式。诚如狄百瑞所言,在儒家思想中君子没有有效地得到百姓的托付,不论其内心的良知多么强烈,却无力调和“君本”与“民本”的矛盾二重性,更多的时候只是政治空想家,君子和帝王之间的张力也正是历史上儒家最大的困境。
近现代以来,虽然儒学的发展几经波折,但研究儒学的队伍无疑在不断壮大。除了鸵鸟心态的保守知识分子之外,开放明敏的知识分子无不面对儒学与现代民主此一问题而苦心思索。与激烈的传统批判思潮几乎同时,出现了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且以重振儒学为己任。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并不是把儒学当成一个僵硬的传统教条来研究,而是坚持站在儒学之内,从学说本身出发探求其现代发展。譬如熊十力立基于“体用不二”之哲学,透过仁者与物同体的道德证成来建构儒家新外王理论,阐发了儒学之体,同民主、科学与社会主义之用相互融通;牟宗三站在儒家德性优位的角度,通过儒学内在的辨证展开构建以融通现代民主的理论,提出了“良知砍陷说”;徐复观透过对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诠释,发掘出一些民主的萌芽,提出“民本跳开民主论”。诚然,上述新儒家基于西方唯心主义开展儒家哲学,尽管在道德哲学上发挥地淋漓尽致,但能否使其通向现代民主之路,关键在于能否将道德上的积极自由观念,与政治上的消极自由观念二者,以一贯的理论衔接起来。
直到今天,学术界仍不假思索地认为,以“民惟邦本”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其中与今天的人权、权利意识、主权在民的思想绝不可同日而语。但需要明晰的是,民本思想中展现的对传统单一政治权威的打破、凸显对民众价值的尊重以及以均平为理想目标的价值观念仍值得我们重新检视和研判。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一文中谈到:“孟子和荀子都主张人类是平等的,这就是民主思想中的重要核心。”当今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这一宗旨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而不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以维护资本家的“自我利益”为目的社会理性化进程。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是极为根本的。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历史之覆辙,读懂中国历史,才能开创未来。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存世界和利益诉求,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要之,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深入地分析中国传统式的“民主思想”因子,科学审视其新时代价值,合理地扬弃,从中废弃死的糟粕,救出活的精华,在“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范式中创造性地转化“重民本”的价值内涵,使之为新时代培育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营养。
三、守诚信:当代诚信观念的中国传统理论基础
“诚信”是中华民族五千年道德文明的精华,儒家倡导“信”德,讲究诚实不欺、恪守信用、言行一致。孔子在《论语》中曾38次提到“信”字,其中,有24处体现出“诚信不欺”之意。他说道,“主忠信,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在传统儒家看来,“信”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范畴。《论语》开篇就告诫人们应当“每日三省吾身”,而其中的“二省”便是反省自己的信用如何:“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简言之,“信”是立身处世、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儒家还主张“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礼记·中庸》)从文字上讲,“诚”与“信”共同构成了“诚信”一词。《说文·言部》语:“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宋儒周敦颐把“诚”视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诚下》)《礼记》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礼记·大学》)朱熹有言,“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朱子语类》卷一一九)“妄诞欺诈为不诚”,(《朱子语类》卷六)“诚意,只是表里如一”。(同上)张载说:“至诚,天性也”,(《正蒙·乾称》)“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正蒙·诚明》)“诚”作为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其原意是真实无妄、笃实无伪。自先秦《中庸》、《孟子》以来,它是指本体、规律、万物的实存性;就价值和应然之义言,它是指道义、品德的笃实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道德原则,修身、做事、治国都要基于信用、信任、信誉的基础上,诚信不仅是一种美德,一种善德,更是从商从政的基本准则。中国历朝历代的经商之人都格外注重“以诚立业”,恪守商业信用,讲究生财有道,追求利以义取,做到“称平斗满不亏人”。“诚信”的具体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但其一般意义无疑是永恒的。
尚诚守信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今天,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人们的生活速度急遽加快,各种自媒体极度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消费的多样化,娱乐的大众化,个人主义与物质的享乐主义被一些青年人奉为主导原则和生活方式。现代社会中存在大量问题,使作为主体性的人陷入道德的困境,这一向来被奉为圭臬的传统道德正经历着空前的考验。譬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只要能赚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行为原则,以至于出现“大头娃娃”、“三聚氰胺”等毒奶粉事件,还有医生收红包、学校卖文凭、学者剽窃论文等,以及不久前网络上曝光“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诚然,这些不诚信现象强烈的昭示着我们已处于诚信濒危的社会危机中,如若任其滋长蔓延,则必然会损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在伴随着经济起飞,而体制、法制建设显得滞后的情况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内影响、破坏社会秩序的形形色色的失范现象,也滋生蔓延起来。人对事物的道德感受、道德立场、道德意识渐渐失去,导致一段时期内失范现象的难以遏止,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空白或混乱中,滋生了驾驭不住的欲望,带来了行为失范的后果。
从现代思想的视野和理解来看,导致社会诚信道德的缺失既有客观因素,也存在主观原因;既有历史根源,更源于现实土壤。儒家的道德传统具有抵御、消解失范行为的功能,应该说是很明显的。诚信问题遍布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直接映射出个体或群体对于社会规范的认同。因此,需要立足于“诚”,有力地唤醒、激励人们的道德心灵和道德情感,重新让至善的价值原则挺立于人的内心之中,避免成为现代社会中空心化的主体人。当然,儒家传统的尚诚守信精神是在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伦理本位的道德观念,在工业社会的、契约性的公共生活发达的环境下会有不能适应或缺弱之处。中国现代社会是经济制度、政治结构、意识形态道德价值至今复杂互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成员失范行为,需要用完善制度、体制、法律,增强社会控制能力来阻止、救治。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要素,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成长,城市无信不繁荣,社会无信不稳定。离开了诚信,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在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国,大力建设信用文化,努力弘扬诚信精神,是构建当代民族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下,发掘儒家尚诚守信的德性观念,弘扬“诚中形外”,人己、物我、内外一体贯通的道德,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良能,逐步提升国民素质。
四、崇正义:公正观念的中国传统正义基础
从早期中国文化的演进来看,孔子首倡“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主张;秦汉时期,《礼记》记载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宋儒张载有“尊年高,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正蒙·乾称》)的情怀,以上皆展现了传统儒家对社会公平的憧憬与向往。儒家倡导的公平思想亦即是主张民众能够合乎“礼”的行为,同时也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关照,可以看出,追求平等是对中国古代等级社会制度导致不平等的一种价值抗争和价值诉求。美国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谈到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并把其基本意涵界定为:“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就此所引观之,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公平观念主要体现在人人平等(人无贵贱之分)、财富均等(均无贫)、教育平等(有教无类)等方面,其基本内涵,与现代的正义理念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在儒家看来,“均平”思想同样是传统社会建立公平正义的重要一环。何晏对“均”释为“政理均平”,朱熹则解读为“各得其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所讲的“均”并不是平均,而是指正义。在中国文化的理解中,“义”常常与“利”相联系,诚如蒙培元所讲,“儒家正义观建立在人的内在德性之上,因而是德性伦理。义和利不能分开,它是处理利益关系的根本原则,包括公平,公正的原则。它是在仁即普遍的生命关怀之下的广义的正义观,包括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公正原则。它以善为自身的最高价值,视人为目的,避免了工具意义。”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价值范畴,义利之辩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个过程。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义利双行”(陈亮语)的文化。“义”的原意是“礼仪”的“仪”,后来假借为“适宜”、“合宜”,意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事情或行为。在进入理论领域后,即表示人们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义”最早出现在《周易》中,“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孔子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主张“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在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生产力的农业文明社会,生长出了崇尚正义的均平思想,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作为东方价值观的中国正义论传统。
盖依上所述,古代的公平正义在某种程度上直指“公道”精神。正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均平”、“平均主义”观念,对于当代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根基。做到公平正义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践行大道的根本。但令人忧虑的是,在以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基础的未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是难以践行的。一位对后人类主义存有质疑的学者批评说:“后人类主义话语的一个特征,是它通常使用不确定的‘我们’来表示一种普遍的人性,从文字上看,似乎是为全体人类说话,但实际上是为极少数富裕阶层、科技授权的美国人或其他可能的‘第一世界’的国家说话。”这无疑是悲哀的,那些最发达国家以及少数有钱财权势之人最先、最多的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最新成果,而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弱势群体往往最后、最少甚至品尝不到高新科技的果实。恰恰相反,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关照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要坚守伦理底线,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道德和利益等辩证思想的指导下,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明道正义精神与现代公平正义理念相结合,从而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各种主义给现代性的道德建构带来的困境。
五、尚和合:和谐观念的中国传统思想目标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学界有人将传统文化称为“和合文化”,并有学者据传统“和合”一词创立了“和合学”。“和合”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即商契把五种不同的人伦之教进行融合,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姐妹之间团结有爱,和平共处,则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尚书·尧典》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内政外交发表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了“和合”思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他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看,《易传》云:“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与四时合其序”,“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卦》)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宋儒张载云:“乾称父,坤称母”,“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程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儒道都强调自然与宇宙的共生,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体现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主流的儒学把“和”视为人文精神的核心。从以和为贵的人际观来看,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有若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先秦儒者基于现实需求提出这些主张,皆以人际关系的和谐为旨归,讲求做人要宽厚处世、与人为善,追求人际和谐的价值立场。从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来看,传统和谐观念认为在处理不同国家、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做到“和万邦,与邻为善”,孔子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孟子云“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武力霸道,并倡导用仁义道德维护邦国之间的关系。在儒家看来,所谓“和”并不是否认矛盾之间的对立,而是倡导求同存异;同时也不是绝对地排斥斗争,而是倡扬争之以礼,在和谐有序的关系中开展竞争。在现代文明阶段,由于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相互联系更为紧密,如果不注重“以和为贵”,那么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就难以存在和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和合”一词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由此观之,和合思想在当今时代不仅体现为个人身心的和谐,更要求人与社会的和谐,“从文化渊源看,崇尚和谐,企盼稳定,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平安社会、和谐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内正处于改革攻坚的转型期,各种利益需求呈现多样化,价值观念展现多元化,人们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复杂。反观西方社会,自近代工业文明以来,西方社会以追求物质利益价值为至高取向,使人类在过度的物质追求和物质享受中沦为物欲的奴隶从而造成了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以及发展的异化,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提出“单向度的人”的概念,意即处于这种文明之中的人们缺乏批判性、超越性,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奴役自然为满足物质欲望的基本途径,以拥有支配自然和其他物种生命的权力为确认和提升人的主题价值的根本方式,这即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人的身心和谐的恶果。另一方面,就世界局势来看,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逐渐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也在不断加剧。宋儒张载有言,“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和合”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观念,经过创造性转换以后,必将成为宝贵的智慧资源,为当今倡导和谐精神提供丰厚的土壤和营养。
六、求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理论归宿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在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略之一,并写入了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之中。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最终目标即是实现美好夙愿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据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平、民主、自由的“大同社会”也就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同”一词始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在传统社会,“大同”是儒家所倡扬的“人人为公”的理想社会形态,也是历朝历代仁人志士所孜孜追求的目标。近人康有为作《大同书》,其中在如何构建“大同”社会时他说道,“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就蕴含了大同理想,“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就此所引观之,中国自古就以“大同”为最高社会理想。从儒家提出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最后达到“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的境界,即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和谐,也就是传统儒家的终究理论归宿——大同社会。
若站在全球化的社会远景的角度,儒家先哲在中国哲学语境下追求的大同社会并不是一种乌托邦或浪漫主义式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符合理性的、开明的和人道的策略。“从本有理论内质来看,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儒家大同理想有近似之处,都以追求人的解放和幸福为目标;哲学上两者都是人学而非神学,都讲对立统一、与时俱进、变化日新;社会治理上都重视民众力量;在群己观和义利观上,皆提倡先人后己、以义导利等等。”在马恩经典著作中可提取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表述,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的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透过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二者均代表着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向往和追求。作为在传统社会的一种美好理想寄托,大同理想与西方社会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关于未来社会的“和谐制度”、以及人本主义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平等”和“爱”,其中的精神显然是相互融通的。
在中华文明长期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历代仁人志士都未能找寻到通往“大同社会”的正确道路,这一美好夙愿仅存在于人们的祈盼之中。伴随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28年浴血奋战,最终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将国人带进了“天下为公”的新社会。然而,在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中,尤其是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神速发展涌出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可能使更多的现代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风险并陷入现代人性的困惑之中。面对着驰鹜不息、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致使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会被全球化浪潮中冲“散”或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化”掉。近年来,理论界普遍意识到,在当下新时代面对这些挑战时,要发挥儒学伦理的现代意义,唤醒其中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人性论根基,完善德性,提高境界,用儒家的终极关怀和伦理共识支撑健康的现代化社会。在面临世情、党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习近平同志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仁爱民本、尚诚守信、明道正义、和合大同的价值观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可以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儒学依然保有取之不竭的理论资源,展现出现代人类思想理念和社会生活一定方面、一定程度相吻合的持久生命力。
七、结语
从现代思想的视野和理解来看,传统文化中既包含着丰富的精华内容,也掺杂着落后的糟粕成分。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到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对传统儒学价值观不是简单的直接照搬,而是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时代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是其自身的价值体系的自我组织系统的吸收和重组,是文化本身的自造或是价值上的适应、融合和涵化,如果从根上去推翻它、粉碎它、毁灭它而创造另一种文化,或是用其他文化替代它,势必会造成民族文化价值上的颠覆和断裂。在“双创”的时代背景和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要求下,要激活传统儒学的价值,让老树发出新芽新枝,让旧瓶装入新酒,让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更加稳固,更好的发挥传统对现代化补阙拾遗的功效。总之,身处新时代境遇中的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需要经由现代文明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批判扬弃,才能在危机和质疑之中迸发活力,从而有机融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为新时代的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