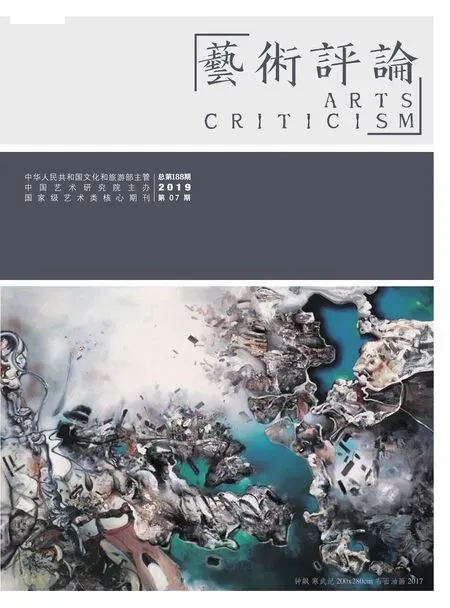电影工业美学的三重建构路径
[内容提要]电影工业美学可以说是时代转型下的一次理论重建,它既体现出询唤工业意识的先见,又强调了坚守美学品格的价值。其建构路径可以通过三个方向展开:于理论层面而言,电影工业美学实际上与技术美学、劳动美学休戚相关,它在本质上承袭了工业美学的研究基础,既是一次在艺术学科领域的美学外延,又是一次针对电影现象的美学建构;于现象层面而言,部分电影展现出“轻工业化”的特征,部分电影走高度技术化的倾向,呈现出“重工业化”的特征;于创作层面而言,电影工业美学不仅强调电影创作上的形式美,更重视内容的美学品格,这也为今后的电影创作提出了形式与内容上的双重要求。
随着中国电影产品化之路的日趋完善,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之货架成为现阶段电影人共同努力的方向。放眼世界,以欧洲为代表的传统作坊式制作流程所产出的电影少有能获得优渥商品效益的作品,很难实现电影的工业价值;以好莱坞为龙头的电影工业体系已成规模,其标准化、统一化的生产模式缔造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票房神话。不过,好莱坞所生产的大量带有快节奏、快消费意味的电影总是于获利后便烟消云散。因此,看似折中的电影工业美学实际上是“以质量为本,促产业升级”语境后的真挚感召。它一面呼吁中国电影走向工业化之路,以图实现商品效益的最大化;一面发掘工业背后的精神内核,以期创作出具有艺术价值的电影产品。
在陈旭光的表述中,电影工业美学尽管是折中的、大众的,但它“最大程度地平衡了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的关系,追求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更在一定程度上触底了“电影是什么”的本质问题。然而,理论建构终究面临着质疑与争鸣:徐洲赤在《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及其建构》中尽管肯定了电影工业美学的意义,但也强调工业美学体系“应纳入诗性内核”;李立在《电影工业美学:批评与超越——与陈旭光先生商榷》中指出“它是一种国家电影理论,是中国电影进入新时代的电影生态的认识论”,但却缺乏现实根据。然而,电影工业美学实际上既不否定诗性,亦不缺乏现实,它意味着理论的延伸、现象的总结以及创作的探索。
一、理论层面:从工业美学到电影工业美学
于理论层面而言,电影工业美学可以作为工业美学在艺术领域的一次外延。所谓工业美学,即是“关于工业生产方面的美的科学,它的范畴是劳动的场所和环境、生产资料和产品”。起初,工业美学仅是特殊背景下工业艺术设计活动的归纳与总结,呈现出应用性特征。最具典型性的“包豪斯”艺术设计院始终坚持产品功能与设计形式相统一的创作理念,强调经济实用的设计观念与美观的作者品味相结合的创作形式。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以及审美的不断更迭,当下对于工业美学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它不再只关涉技术产品的审美形式问题,而把社会审美文化作为研究内容之一。在此之后,工业美学研究亦不断扩展,演变成“以带有自由劳动促进劳动的效率、创造和人的发展”的劳动美学以及“以丰富多彩的产品审美文化给社会以美学影响,从而对劳动主体本身进行审美塑造”的技术美学。因此,工业美学这一理论不断扩容,它不仅面对工业生产的部分,同时还对准工业产品的销售环节。无论如何,工业美学这一理念始终对准工业产品,是现代工业体制下对于产品功能与形式的考量。
电影工业美学袭承了工业美学的美学理念,将电影作为现代工业体制下的产物进行美学阐述。从一个层面上讲,电影符合技术美学的基本特征。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电影与技术的联系更为密切,可以说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卷到数码、从宽银幕到IMAX,无不与技术的演变相关联。放眼电影的当下与未来,无论是CG技术的应用、3D技术的普及还是VR技术的拓延,都更与技术进步骨肉相连。不仅如此,电影创作者倚仗不同的技术优势产生出迥异的美学效果,使得“工业技巧发挥出了美的作用”,《爵士歌王》《化身博士》《阿凡达》等处于影史转折部分的影片都是依靠技术实现了自身的美学价值。可以说,电影美学是建立在工业技术的应用基础之上的,新技术驱动了电影美学的发展。但随着电影美学的确立,技术的方向与使命也愈加清晰明确,早期依靠“土法炼钢”而实现的电影“特效”不断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而趋于完善,譬如停机再拍的弃用与数字特效的普及。因此,电影技术与电影美学之间互相指涉、互相关联。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电影的创作方式契合了劳动美学。实际上,电影的制作流程倾向于工业化体系。它有别于纯粹依靠艺术家单人力量完成的艺术门类,呈现出群策群力、分工明确的工业创作模式。这一点在好莱坞电影的制作体系上最为典型。好莱坞制作公司一方面展现出垂直一体化的创作特征,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司内部的资源整合,另一方面则充分吸纳了其他公司的制作资源,实现了垂直分离。正如马克思所言,“‘单个人’已不如以前那样全面”,而协调完成的创造活动才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一个共识是,“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职业分工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它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全面提高”。也就是说,工业体制下的电影创作方式是诸多创作者在和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最佳方案。在这种方案下,大到前期、中期、后期互相配合、各自完成,小到策划、编剧、摄影、灯光、特效等细微部门各尽所能。因此,电影的工业化创作之路完成了个人独创与集体需求的统一。
除此之外,作为工业化的产物,电影被作为商品出售。这也意味着电影的成功标准不单取决于其自身的艺术价值,更取决于其产生的商业价值。也因此,很多电影创作者将电影看成是待销的商品,期望制作出有人买账的作品。从一方面而言,作品自身的大众属性更易于被审美主体接受,而工业体系下完成的作品相较于个人化产物而言,更具备大众性特征。因此,我们既不可急于否定电影的商品属性,亦不可将其商业属性与工业性质进行切割。从另一方面而言,票房作为观众接受程度的一面镜子,实际上折射出社会审美文化的影子。作为审美主体,观众对于影片的喜好实际上与整个社会、文化、政治休戚相关。因此,作为审美对象的电影观众,同样是电影工业美学的研究对象。不可忽视的是,电影的宣传工作与电影的“销量”直接挂钩,它实际上等同于工业领域中的信息部分。从美学角度而言,电影的宣传工作直接涉及艺术设计、艺术作品、艺术宣传等环节,是传递影片信息与审美的结合。
总而言之,电影工业美学在本质上承袭了工业美学的研究基础,是一次艺术学科的美学外延。在此,必须要强调的是,“工业”与“美学”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不相及的两端,技术是实现美的途径,劳动是实现美的前提,而美本身同样反作用于工业,成为产品创作的指南和方向。尽管电影工业美学绝不缺乏理论基础,但它绝非仅是理论上的延展品,它还是针对当下电影现象的一种归纳、总结和梳理。
二、现象层面:电影的轻工业美学与重工业美学
电影工业美学并非是一个大而空的概念,它同样与转型阶段的中国电影关联紧密。可以说,当下大量的电影作品呈现出类型化创作的方式,落脚于轻工业美学的研究路径;部分作品则体现出了高度技术化的倾向,落脚于重工业美学的研究方向。在诸多表述中,轻工业电影是指作品的创作方式是在工业化的流程下完成的,这一类电影往往“投资少、见效快”,呈现出规范化、标准化、程式化的类型特征。重工业电影则注重高投资、高效率,“是诸如《阿凡达》《地心引力》《变形金刚》等风靡世界的高概念大片”。这一类电影往往注重特效、特技,呈现出大制作、大视效的重工业特征。近年来,轻工业电影与重工业电影都成为观众茶余饭后的主要观影选择。
近年来,轻工业电影的票房成绩不容小觑,单是位于国内总票房前茅的便有6部之多。其中,《唐人街探案2》以33.9亿元的票房成绩名列前茅,《我不是药神》30.9亿元的票房成绩也雄踞榜单,而《西虹市首富》25.4亿元的票房成绩与《羞羞的铁拳》22亿元的票房成绩同样值得言说。其中,《唐人街探案2》延续了《唐人街探案》的整体风格,集探案、喜剧、动作于一体,呈现出轻工业电影的典型特征。《西虹市首富》与《羞羞的铁拳》作为同一制作公司打造的影片,两者具有十分明显的相似性——喜剧电影搭桥爱情元素。为了表现爱情,《西虹市首富》更进一步,表现了情感生活高于物质生活的核心主题。这三部影片在制作上契合了工业化的制作流程,既遵循程式化之路,又进行类型化融合,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受益的最大化。作为审美主体的受众,从这些影片身上获得娱乐快感、疏解生活压力的同时,弥合了自身与梦想之间的沟壑,在电影中完成了自己的侦探梦、爱情梦、富贵梦。
《我不是药神》不仅结合了类型元素的通俗性,更实现了主题内涵的社会性,因此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这也与早年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影片相似。一方面,作为一部典型的轻工业电影,《我不是药神》具有鲜明的类型意识。首先,《我不是药神》在内容创作上借鉴了经典好莱坞的叙事经验,使情节点有序、严格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开始、发展、结尾环环相扣的三幕剧结构。其次,《我不是药神》中四男一女的卖药团队搭配实际上同大量好莱坞犯罪类型片的人物配比相像,这组卖药团伙不仅呈现出了迥异的个性,更覆盖了各个阶层。再次,《我不是药神》中摄入了大量的类型元素,如喜剧元素、警匪元素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该片的喜剧式表达。另一方面,《我不是药神》的存在也在无形中击破了工业与美学之间存在沟壑的言论。作为一部典型的轻工业影片,《我不是药神》并没有放弃追逐艺术的脚步以及观照社会的功能。在程勇与吕受益寻找思慧的那场戏中,一个漂亮的长镜头将社会两端进行连接,使得底层、边缘的景观慢慢地随着人物走位渐渐浮现出来。不仅如此,影片关注高价药、关心底层人的社会寓意也是在工业化的制作体系下展现出来的。
重工业电影的票房成绩更是无可匹敌,其中,获得56.8亿元票房的《战狼2》与获得46.6亿元票房的《流浪地球》、36.5亿元票房的《红海行动》稳占国产电影的内地总票房三甲。可以说,《战狼2》与《战狼》不啻为英雄片的变种,而《红海行动》则与惊险刺激的前作《湄公河行动》一脉相承,堪称质精效优的动作大片。《流浪地球》作为中国首部硬核科幻电影,更是一手接下了中国电影类型化制造的大旗。三部影片类型化明显,但更为典型的是三者具备的大场面、大制作、大特效的特征。其中,《战狼2》的开头部分,导演吴京使用一镜到底的方式捕捉了一场水下杀敌的动作戏,为了突破技术性难关,特别请来了《加勒比海盗》的水下摄影团队。结尾处两个人物的激战更是惊心动魄,爆破、燃烧、轰炸,无不凝聚着技术的力量。《红海行动》表现战争的场面可谓煞费苦心,为了展现真实的画面效果,导演林超贤摈弃了特效的处理方式,而是选择以“实景实拍”的方法诠释战争的激烈,电影到北非摩洛哥取景,且拍摄中的战火、炮弹全部采用了真实的炸药爆破,可谓设置了一个十分逼真的战场。
《流浪地球》则完全展现出了电影技术性的一面。《流浪地球》中的2003个特效镜头意味着中国电影的重工业之路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该片的特效制作由MORE VFX等公司完成,其中,MORE VFX是国内体量最大的特效制作公司,曾完成过《悟空传》《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等重工业电影,尤其擅长写实环境的重塑与再建以及极端环境中的坍塌、破碎等场面。影片中共设计了宇宙场景、木星场景、地球场景等三个主要场景,其中,无论是地球上被冰封的地表,还是重要的大爆炸场景,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而运载车、地下城、空间站则是在实景搭建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加工,实现了小说中对于宇宙空间的遐想。可以说,《流浪地球》初步实现了重工业电影在本土化移植中所呈现出的共存样态,摆脱了“中国式大片”的尴尬境地。可以说,重工业电影迎合了“电影强国”的战略诉求,承载着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的重任。
总而言之,轻工业电影与重工业电影表现出类型化创作、分工化作业、技术性支持的特征,但重工业电影更加重视场面效果的演绎以及特效、特技的运用,呈现出“高概念大片”的样貌。无论如何,两者都共同支撑了中国的电影票房,成为审美主体的主要选择。也就是说,在电影创作中,个人的审美需求必须让位于大众的审美诉求,才能实现电影作为商品的价值。但电影通往成功的大门不仅于此,无论是轻工业电影还是重工业电影,它们都应该在工业体系下实现其自身的追求,显现出形式美与内容美兼具的美学理念。
三、创作层面:工业化的形式美与工业性的内容美
作为一种实用性较强的美学,电影工业美学对电影创作具有指导意义,这尤其体现在电影的内容与形式两个部分。一般而言,电影的内容是指电影的人物、故事、主题等回答电影“实现了什么”的相关内容,而电影的形式则是指电影的拍摄方法、剪辑、蒙太奇、特效等回答电影“如何实现”的相关内容。实际上,电影应该倾向于“内容”还是“形式”,一直以来都是专家、学者们讨论的重点,它关涉着电影本体、电影创作、电影发展的走向。期间,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电影的大讨论最为典型,以李陀为代表的电影理论家认为,必须通过以标榜“形式”的极端方式才能扭转中国电影当时的窘境。而80年代中后期,当“第五代导演”实现了中国电影艺术化探索之时,电影理论家则在“以经济为核心”的时代背景下集中转向到“内容”问题上,考量“娱乐片”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两个方向的争论是时代性与先锋性拉扯、权衡的必经过程,而无论是激进地侧重于哪一面,都显得矫枉过正。我们既不能忽视电影的形式,亦不能无视电影的内容。毕竟,失去前者的电影将倒向庸俗,失去后者的电影将沉沦于虚无。
作为重要的哲学概念,形式早已被历代思想家、理论家一遍遍地复盘、强调、演绎。在电影美学的范畴中,我们不能忽视由形式造就的美的规律与法则,即形式美。实际上,由工业化的制作形式所赋予的电影形式美更具典型性。针对较大面向而言,无论是轻工业电影还是重工业电影,它们都是在分工明确的状态下完成的,任何制作环节都成为产业链条中的一部分。针对较小的面向而言,产业链条上的一些环节极容易被制作者总结经验、提取成分,从而形成程式化、固定化的创作套路。比如三幕剧戏剧模式作为工业化制作的产物,实际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观看需求。通过悉德·菲尔德的剧本积累、影片观摩、创作经验,“他总结出优秀的剧情片背后,隐藏着一种相对稳定、一以贯之的戏剧性结构”,即占片长四分之一的开端、占片长二分之一的发展以及占片长四分之一的结尾。这样的剧本创作范式等同于工厂的流程,意味着好的剧作不仅能通过天才式的想象完成,还可以是一种技巧性、工业性的产物。通过票房结果可知,审美主体并不会对由三幕剧构成的故事产生审美疲劳,而会在此起彼伏的情节中忘我沉浸。因此,这些带有工业性质的形式创作契合了大众审美所认可的标准化、规范化特征,是一种走向大众的美。尽管工业化本身就存在着形式美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作者气质的创作就可以被排除在工业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虽然大量导演需要在工业化的制作体系中权衡、妥协,但部分“新力量”导演却深谙电影创作的规律,在自我复制、自我指涉中建立艺术性与商业性、体制性与作者性兼具的电影形式。早在“新力量”导演之前,香港导演吴宇森便继承了张彻的阳刚美学,他或是通过升格镜头的方式诠释暴力,或是以移动摄影加入转切、定格的方式连贯性地表现暴力场面,形成了极具个人风格的暴力表现形式。我们可以说,吴宇森导演也是通过艺术性的探索,实现了商业化的道路。“新力量”导演更加明显,其中徐峥、宁浩、陆川等便以自身独有的处理方式,游走在艺术性与商业性、体制性与作者性的复杂关系之中。
艺术创作者通过不断地发现、发掘和表现,以实现创作者主观能动的理解、认识与创造,完成具备主观美感品格的艺术内容,从而实现了内容美。电影工业美学不仅强调电影创作上的形式,更重视内容本身,即影片“实现了什么”。实际上,类型片制作在内容上呈现出了工业化的一面,正如理论家所言:“在一部又一部的拍摄过程中,同一条西部街道或同一个中欧居民村广场可以被反复地使用。‘独特的’布景不必为每一部影片专门制作。”不仅如此,定型化的角色、公式化的剧情以及图解式的视觉影像都使得类型片自身工业化,展现出规范、通俗的大众美学特征。那种极受观众喜爱的、约定俗成的类型模式,是对大众日常审美规律的归纳,也是作为艺术的电影对日常大众审美的询唤和接纳。
在此,必须强调三点:其一,尽管纯粹的内容复制是工业的,但绝不是工业美学一味追求的,它更多是作为工业美学下社会性审美的认识来加以论述、实现的。工业美学所强调的内容制作,更多的是在分工合作、各尽所能的条件下完成的艺术共谋,而非是对同一内容反复的、无条件咀嚼的认可。以剧本创作为例,擅长台词、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的不同编剧各司其职,共同完成艺术作品,实现艺术价值。其二,电影的内容是通过电影的形式加以实现的,工业美学一方面希冀于电影创作时的技术力量辅佐,另一方面则期待作者性与集体性的协调。这就意味着电影内容不能仅通过技术实现,亦应该接受艺术水准的考量。其三,尽管工业美学依靠技术条件的支撑,但在内容层面应侧重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要求,实现类型性、技术性与民族性的融通。因此,如何巧借工业体制的外壳,将文化中国的精神诉求包裹其中,也是电影工业美学的探索方向。
总而言之,尽管电影工业美学强调类型意识、工业化的创作模式以及特技特效等相关技术的支持呈现出大众艺术的特征,但大众艺术绝不是受大众裹挟的产物,而是强调作者性与集体性相互协调、风格化与集中性相辅相成。由于现阶段的工业电影仍处于摸索阶段,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尚不全面、普及,因此,现阶段的中国电影并未从集体工业制作的漩涡中走出,继续走向由作者引导电影工业制作的局面之中。实际上,这也造就了电影工业与电影美学相互背离的整体错觉。总而言之,电影工业美学为电影创作指明了方向,工业化是实现电影工业的手段,艺术性是达到电影美学的要求,两者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端。
电影工业美学的建构在实质上与电影强国的梦想、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期盼相一致。电影发展到今天,我们见证了电影经历了数次革命性的发展、变化,更应该理解对于电影的认识不应只守望着电影艺术的一种法门,固步于一处。电影工业美学尽管看似中庸、平和,但它体现出询唤工业意识的先见,又强调了坚守美学品格的意义,表现出了对照电影历史、对标电影创作、对准电影现实、对向电影未来的建构意识和经验洞察。
注释:
[1]张卫、陈旭光、赵卫防等.以质量为本 促产业升级[J].当代电影,2017 (12):4.
[2]陈旭光.论“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33.
[3]徐洲赤.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及其建构[J].当代电影,2018(6):112.
[4]李立.电影工业美学的批评与超越——与陈旭光先生商榷[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4):93.
[5][6][7][10]章斌.劳动美学与技术美学[J].社会科学杂志,1991(7):66,69,69,78.
[8]〔美〕邓肯·皮特里.电影技术美学的历史[J].梁国伟、鲍玉珩译,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1).
[9]〔匈〕富卡斯.论建立劳动美学[J].星云摘译,哲学译丛,1981(6):30.
[11]饶曙光、李国聪.“重工业电影”及其美学:理论与实践[J].当代电影,2018(4):104.
[12]康尔.悉德·菲尔德剧情片叙事理论评析[J].艺术百家,2014(5):436.
[13]陈旭光.新时代 新力量 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J].当代电影,2018(1):31.
[14]〔美〕T.贝沃特、T.索布夏克.类型批评法:程式电影分析[J].肖模译,世界电影,1997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