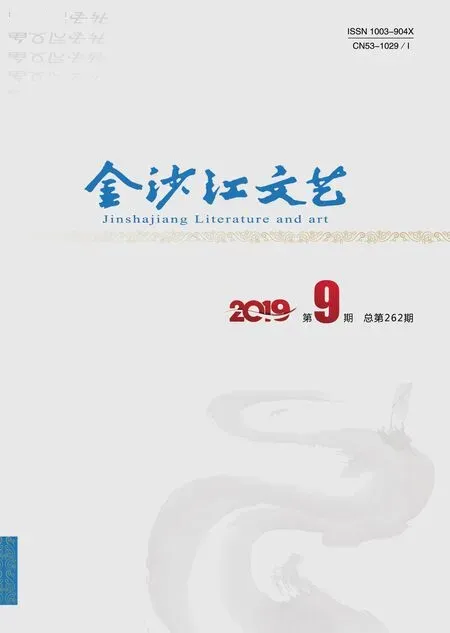危情元永井
◎李绍全
一
崔建彬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找到丁上淮时,丁上淮正坐在一棵老锥栗树的裸根上凝神远望,默默地用心灵勾画着元永井的美好未来,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有人来找他。而崔建彬一路上迫不及待,在老远的地方一见到丁上淮的身影,就高声喊了起来:丁代表,丁代表!
丁上淮听见深沉而浑厚的男中音在叫自己的名字,不由自主地把思绪从远远近近的青山里收拢回来,循声望去,见是滇中盐场公署场长崔建彬,心头不禁一热,微微笑起来,立马站起身,向他不停地招手,示意他赶快过去坐坐。
青石板铺成的石台阶路边正好有个缺口,被走进古树下休闲的人们踩踏成了小路。崔建彬就会意地顺着毛毛路急走了过去,要把紧急情况向他作及时汇报。
然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两人在焦急而莫名的紧张中折腾了好一阵,崔建彬才把话说出来。他说,刚才有两个背柴卖的彝族背夫找到我,说他们是托李惠仙来找你的,但是他们不认识你,怕把事情败露出来,就让我把情况转告给你。他们说,李惠仙说了,最近有土匪要来抢劫元永井,要杀害军事接管小组的全部人员。元永井内部也有暴徒要响应。她让你们接管小组成员赶快跑去躲一躲,以防不测。两个背夫还说,土匪攻打的时间可能是4月25日天黑以后。
丁上淮听着崔建彬的讲述,身上的鸡皮疙瘩一会儿凸起来,一会儿凹进去,把体内的汗水都挤出来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土匪和国民党军统特务相互勾结,伺机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由于元永井聚居着上万人,东南西北的人都有,谣言盛行,真假难辨。他刚来时,就听到了一些危言耸听的消息,曾主动向云南省政府请求军事支援。但是,昆明市防务紧张,他的请求未能得到上级批复。
崔建彬报告的这个消息仿佛是一枚子弹,无情地射向他的胸膛,让他在疼痛中更加清醒了。国民党特务及残余势力必然要反攻,元永井将面临一场殊死搏斗。
这时正是1950年4月23日的傍晚,暖暖的春意浸泡着绵绵的紫云峰山脉的群山,浇开了漫山的野花。红的,粉红的,紫的,黄的,浅黄的,白的,绚丽多彩。一群自由的小鸟在他们头顶的树枝间窜来窜去,兴奋地欢唱着。鸡鸣山脚下的小平街上渐渐闹腾起来。这个景象用春意盎然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了。然而,丁上淮不敢贪图这样的美景,自从踏上元永井的那时起,他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焦虑不安。他刚刚从昆明来到这山青水秀的繁华小镇时,万万没有想到元永井这口老井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复杂得多,危险得多。尤其是近十几天来,他每天刚吃完晚饭,就独自到这片古木参天的锥栗树林中来走一走,坐一坐。一来是让凉爽的晚风吹散心里的焦热,二来是寻找一个较好的办法来接管滇中盐场和国民党税警队,然而,在这陌生的深山里,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困的老虎,威武总是被一个无形的笼子笼罩着,头脑里总是空荡荡的,仿佛被谁给掏空了。
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时,国民党在元永井的旧机构依然十分完整,顽固势力还相当强大。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盐务接管小组经过缜密遴选,派他率领十几名南下学员进驻元永井,对其实行军事接管。丁上淮他们来到元永井时,滇中盐场和税警队都举行了欢迎仪式,整条街上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晚上还在李家大院的戏台上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免费让观众进场观看,铺张程度让他想也想不到,阻也阻止不住,全然一个新日子,新天地,那些渴盼新生活的人们甚至做梦都是美好的梦了。丁上淮也确实感受到了元永井各方面对新中国的普遍支持,得到了一些进步的上层人士的积极帮扶。比如,滇中盐场公署场长崔建彬就密切配合他的工作,主动带领他走街串户,下井进灶,让他尽快熟悉元永井方方面面的情况,大事小事都找他商量,征得他同意后再行事。但是,随着他对元永井的深入了解,旧势力旧生活旧思想旧方式也扑面而来,他越来越看不懂元永井的真实内容了,新旧两种思维在他的头脑里相遇相融,搅混了他清澈的胸怀,每当深夜,他就觉得元永井内部暗涌激流,让人防不胜防,仿佛即将面对一场艰巨的激烈的战斗。
丁上淮现在站的位置是鸡鸣山的山顶,山顶上矗立着一棵棵苍老的古树,这些古树是灶户们的山神树或者风景树,树干粗大得两个成年人也围抱不拢,树枝连着树枝,叶子牵着叶子,密密麻麻,把天都遮住了。但从树干间的缝隙中看去,一眼就望见了西边的老高山、东南边的灵鹫山,和流淌在两山山脉之间的一条涓涓的溪流。在这里虽不能说一览众山小,但元永井的全貌却尽收眼底,通往税警队的路就从前面的斜坡上穿过。丁上淮平时就是从那条路上沿阶而上,来到这里消减内心的压力和憧憬未来的。
丁上淮被指派到元永井快有两个月了,他是三月初来的,现在是四月下旬。但是他对元永井的情况确实不是了如指掌。元永井是一个老井,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是明洪武年间开的盐井,经历了明、清和中华民国三个朝代,现在正昂首走进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怀抱。由于其纵向历史十分深邃,横向贸易流通广泛,正处于改朝换代的交汇时刻,社会情况无比复杂。国民党税警队那帮人还保留着 “国军” 的刁滑本性,滇中盐场场署的那帮人也似乎面和心不和,多少有些枯枝烂叶的腐朽味道。街上的野风社、松柏公社、青年先锋社、红帮启文公社等民间组织成员的思想比较动荡,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特征比较明显,长工队中的个别人更是与惯匪神来意往。这张陈旧而牢固得像蜘蛛网一样的社情使他夜不能寐,他虽然身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内心却焦急万分,身子也日渐消瘦了下来。他原是一名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1949年12月9日,卢汉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后,他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接管委员会盐务接管小组的指派,于三月初带领朱靖宇、邓有庆等战友和 “二野” 军政大学的十几名南下学员,来接管元永井的税警队和滇中盐场。
元永井是古滇九井之一,在滇中楚雄境内还有白井、黑井、琅井、阿陋井。1936年盐运使张冲移卤就煤,建成一平浪盐矿后,元永井的卤水成为云南盐业的重要源泉,产量突飞猛进,成本大幅下降,不但保护了当地的植被,而且改变了当时斤盐斗米的高价状况,税收猛增,占据云南经济的半壁江山。1936年解放军在元永井进行了扩红,为西进部队增添了新的活力。接管好滇中盐场,惠及民生,巩固新中国的政权,这是丁上淮及同志们和十几位南下学员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啊。丁上淮不敢丝毫懈怠,除了夜以继日地思考工作方针之外,还得不断地向崔建彬等老领导及井下工人了解实际情况,密切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带领他们走向新生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因此,崔建彬主动来找他,是他求之不得的,他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崔建彬走近他,两人在如伞一样的大树下并肩而坐,促膝相谈,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接管好滇中盐场,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一块重要的基石。
但是,当崔建彬走近他时,他从崔建彬惊惶失措的表情上察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崔建彬脸色都变紫了,喊了好几声丁代表,也没有把正事说出来。
丁上淮像兄弟一样轻轻拍打拍打他的肩膀,说:老崔,你慢慢说,慢慢说,不要着急!
但是,崔建彬能不着急吗? 他急死了。匆匆忙忙地从元永井小平街上赶了上来。从小平街到鸡鸣山是一条狭窄而陡峭的小路,平时慢慢走也要淌一两回小汗,急着赶路就更不用说流多少汗了。他用长长的衣袖揩了揩脸,气喘不定,这让丁上淮忍不住怜惜起来。他希望他彻底冷静下来再说,免得说不清情况。
他微微笑着,一直拍着崔建彬的肩膀和后背,让崔建彬感到十分温暖,过不多一会儿,就冷静下来了。他说,丁代表,有个新情况,我必须立即报告给你,不管情况是真是假。万一是真的,敌人趁机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起进攻,破坏盐场,那罪责我可担当不起。
丁上淮听着他的讲述,心里像关着一只活蹦乱跳的野兔,惴惴不安,但是他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说,什么情况,你慢慢讲吧。又花了好大一阵耐心,崔建彬才把那关乎元永井安危的核心情报从心中倾吐了出来。
4月25日天黑后,丁上淮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烁着这个可怕的夜晚。时间紧迫,只有一天多的准备时间了,而元永井现在能用的兵力十分薄弱,这可怎么办呢? 他觉得一股鲜红的血液正在街上流淌开来,继而漂浮起来,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红布,红布上隐约闪着镰刀和斧头,继而闪起耀眼的星星,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交替在眼前浮现起来。在万分紧张的关键时刻,他想起了元永井区政府的畅达书记。他刻不容缓地说,老崔,快走,我们把这个消息立即传达给区委,和他们研究一个万全之策,以防万一。
二
消息传到元永井区委书记畅达的耳朵里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天上的星星与地上的街灯相互辉映,赌博声、唱卖声、说书声、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副食店里的磨盘声此起彼伏,回旋在两山对峙的山箐箐里,让人们感觉沉闷、烦躁和不安,显得这元永井的社情更加复杂,仿佛它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河流。
畅达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觉得一头雾水,又仿佛这消息就在深不可测的水里,而自己是一个不谙水性的老公鸡,双脚一踩进水里,心就慌乱了,无法分辨这个消息的真假。但是军事接管小组进驻以来,元永井的情况发生了让人难以捉摸的变化,每个人的脸上都显露着新的表情,有的微笑,有的哭丧,有的安祥,有的恐慌,反正你是看不透的。因此,听了这个消息后,他的想法与丁上淮的想法一拍即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他神情凝重地说,他们胆子也太大了吧!
丁上淮看准时机说,狗急了都会跳墙,何况是这些为非作歹惯了的土匪呢。畅书记,请立即召集保寇文、张光裕、陈顺仁,我们六个人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研究一下如何对付土匪的进攻。
畅达不加思索地说,是,丁代表。
丁上淮似有所思地抬起了右手,作了个等一等的动作,然后对崔建彬说,老崔你没有意见吧?
崔建彬谨慎地望一眼畅达,笑了一下,说,我完全同意丁代表的意见。
丁上淮得到崔建彬和畅达的支持,心头好象扯开了一片乌云,阳光照射了进来,情不自禁地微微笑了一下。他说,这样吧,为了保密起见,就到我的住处去开吧。畅书记你通知保寇文,并和他一起来,老崔你通知张光裕和陈顺仁,和他们一起来。走路的时候,要放松情绪,像往常到我那儿玩的样子,尽量不要表现出紧急的样子。万一遇到其他人,向你们打听动静,你们就说是到我那里喝茶去。不能耽搁时间了,你们抓紧去,赶快来,人到齐我们就开始开会。
畅达和崔建彬按照分工,开始分头行动,丁上淮先回自己的住处等他们。
会议安排在丁上淮的宿舍里,是怕打草惊蛇,引起敌人的警觉。在这特殊的时期,信息混乱,丁上淮不敢有半点马虎,他这样小心谨慎也是迫不得已,畅达和崔建彬从心里理解他,相信另外几个人也会理解他。
那是一间两层楼的土木结构房,房子的地基用一米来长的石头砌成,一直砌到窗户那么高,看起来非常牢固,让人由此感觉到这个小镇历史的悠久。房顶上的灰瓦呈倒 “U” 字型,井然有序的瓦沟一条一条排列着,披在两边,晴天流着阳光,雨天流着雨水。雪天是少有的,一年也没有几天,有些年份则一场雪也没下。楼上楼下的窗棂都是木质材料,雕花刻龙,精工细琢,既有古色古香的浓郁气息,又有浓重的旧房子的陈香味道。如果军统特务和土匪不在暗中破坏,弄得人心惶惶。那么,这样的环境绝对是修身养性的人间仙境,是云南省少有的富庶之地。张冲移卤就煤工程实施后,岩盐在这里溶解成涓涓的卤水,顺沟流淌到一平浪,在一平浪盐矿用煤煮成雪白的盐,雪白的盐换来了白花花的银子,是名符其实的滇中小金库。
丁上淮来到这里以后,常约滇中盐场及区政府的一些人来聚会,喝茶的喝茶,说闲话的说闲话,谈正事的谈正事,颇有几分热闹气氛,很快就交了一些知心的朋友。不久,他平易近人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在这里开会,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也不容易引起敌人的警觉。
不多一会儿,大家都来了。屋还是这间屋,人还是这些人,但是,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沉重,氛围显然郁闷,丁上淮看见大家消耗时间不是办法,就开门见山地说,刚才老崔场长找到我,说,有人带来了消息,土匪要与元永井内部特务相勾结,内外呼应,将于4月25日攻打元永井,要杀害我们军事接管小组的人,炸毁盐井,抢夺财物。杀我们是小事,炸毁盐井,抢夺财物,那是对人民的犯罪,是对新中国的挑衅,是天大的事。所以,我请大家来开个会,请大家出出主意,看该怎么对付敌人?
保寇文听了,大吃一惊,不禁 “哦”了一声,并情不自禁地打了一拳桌面,使会场立即严肃起来,显得寂静无声,仿佛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丁上淮的心血就在这个时候沸腾起来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希望大家都冷静下来,严肃对待这件事情。他强忍着内心的冲动,用鹰一样的眼神扫视着每个人的眼睛,努力看透他们的心思,但是,他看不透。
看不透就等,耐心地等。这样的消息灌输到人们的耳朵里,相信谁也做不到心静如止水,必然会掀起心灵的波澜,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果然,最先沉不住气的还是保寇文,他是盐兴县副县长,驻在元永井区政府,负责指导这边的工作。云南和平解放以后,他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一些花花绿绿的闲言碎语。谣言多半来自矿工、商人和普通群众,很多谣言听起来都是危言耸听的,这是改朝换代给人们带来的恐慌,心里不安,生活迷茫,使每一个新现象被赋予新的想象,谣言也就诞生了。保寇文最近听的谣言多了,谣言过后,街上依旧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异常事,人们依然早睡早起,似乎非常平静。因此,当大家都不知所措时,他却有了新的思路,他问,这是谁带来的消息。
李惠仙托人带来的。崔建彬慢吞吞地小声告诉大家。
丁上淮早已预料到大家会怀疑这个消息,他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说,老崔,你把情况再向大家陈述一遍。
崔建彬又把李惠仙带来的消息向大家详细地陈述了一遍。
保寇文是个直爽的人,他一听消息来自山里的彝族女人,就爽朗地笑起来,说,谣言,谣言,又是个谣言。
崔建彬、张光裕、陈顺仁等也都相视而笑,连连点头,仿佛恍然大悟。随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曾经流传过的种种谣言。崔建彬说,丁代表,如此说来,是我多虑了。你不用担心,该吃饭就吃饭,该喝酒就喝酒,该睡觉就安安心心地睡觉吧!
会议室里就丁上淮来元永井的时间最短,对元永井的情况还不是太了解,他当然希望这是一个谣言,被晚风轻轻吹来,又随着晚风悄悄地离去。但是,他怎么也忘不了李惠仙来找他的那些情景。他刚来元永井没几天,李惠仙就来找过他,那时,她的眼神里全都是对敌人的仇恨,眼泪里充满着痛苦,哭声中流淌着中国共产党必胜的信念。他感觉李惠仙是真正把他当作亲人了,把共产党当作救星了。而最关键的是李惠仙是盐兴县龙骨甸的一个彝族妇女,三十出头,头上缠绕一块黑纱帕,耳朵上坠着一对闪悠悠的银耳环,身穿一套绣花的彝族妇女的对襟长衣,脚穿一双绣花尖顶鞋,看起来既不华丽,又不寒酸,这是彝族家里经济相对宽裕的妇女的装束。头上的纱帕证明她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了。龙骨地区彝族妇女的装束是非常讲究的,未婚少女头戴艳丽的公鸡帽,已婚生育孩子之后,配戴艳丽的公鸡帽就改成了绕黑纱帕。正是她的这个装扮使他充分相信了她的话,相信了她丈夫就是元永井的井下工人。如果丈夫不在井下干活,没有一点收入,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彝族妇女们是断然没有条件穿得这样好的。
他向大家摆了摆手,坚定地说,我也希望这是个谣言,但是万一不是谣言呢? 他停顿了一下,望望大家,见大家都表情严肃地看着他,他就语重心长地说,那我们将遭受惨重的损失啊。
这时,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了,都说,那是! 那是!
丁上淮听见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信念更加坚定了,就加重语气放缓语速说:因此,我决定,大家就针对这个消息作出妥善的处理办法。关于消息的真实性,由我丁上淮负全部责任,以后万一消息是假的,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后果由我负全部责任,跟大家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大家推举一个会议主持人,我们专门商量如何对付土匪的偷袭问题。
对于在座的几位来说,丁上淮的这番话,好比就是一付安神药,仿佛是一粒定心丸,大家都松了口气,开始认真起来。
畅达扫视了一圈大家,说,那我提议会议就由丁上淮同志主持。
其他人员也一致同意。会议正式开始。
丁上淮说:同志们,谢谢你们的信任与支持,我来元永井快有两个月了,组织派我们来,目的就是进一步管理好滇中盐场和税警队的工作,保一方平安,让大家朝着光明的道路前进。但是,我才疏学浅,今后的各项工作还得仰仗各位的大力支持。不瞒大家,刚才,崔建彬场长找到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真的是吓出了一身冷汗了。我想,如果只是针对我们军代表,那我们死也就死了,军人嘛,死是必然的,两脚一蹬,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那盐井是滇省的心脏,如果守不住盐井,我们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啊。
大家听了,都把目光投向崔建彬,想证实一下事情的虚实。崔建彬感觉大家的疑虑,也抬头看了看大家,说,我也是从接管人员的安全和场署的安全着想。因此,不敢隐瞒事实,也不敢拖延时间啊。
大家点点头,表示对他的赞许,也表示恍然大悟。
丁上淮接着说,我个人的安危不足一谈,我们其他几位军代表的安危也可以不谈,十几位 “二野” 南下学员的安危也可以忽略,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人民牺牲的。但是,人民解放军更重要的职责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不是作无谓的牺牲。元永井的安危我不敢忽视,我是接管了税警队。但是,说实在话,要依靠税警队来保一方平安,我没有这个信心。工人们的觉悟倒是很高,但是工人们的职责是安全生产,确保一平浪盐矿的正常运行。再说,面对残暴的土匪,他们还真的没有经验。区政府这边呢? 这边也没有几个兵,根本无法抵制土匪的进攻。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元永井要是真的来了土匪,内部还有特务接应,后果就是生灵涂炭,盐井将遭到灭顶之灾。
说到这里,大家也都紧张了起来,交头接耳地纷纷议论起来,纷纷提出建议。有的说从昆明要部队,有的说向楚雄专署求援,有的说到盐兴县搬兵。丁上淮正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是紧急情况,必须拿出最稳妥的办法才行。他否定了向昆明要部队的建议,因为,他刚刚来的时候,看到元永井情况十分复杂,曾经主动到昆明,请求云南省委调部队来维护元永井的安全。但是,省委书记宋任穷说实在调不出兵力了,昆明的防务十分紧张,他说要首先确保昆明的稳定,元永井的事情让丁上淮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现在消息是否属实,是否准确还无法确认,上级肯定不会派部队的。他们只好兵分两路向楚雄和盐兴县求援。一路由畅达连夜奔赴楚雄求援,一路由区干部李玉生到黑井向盐兴县委求援。
兵分两路的方案通过后,大家对留下来的同志也作了详细分工:滇中盐场税警队的动态由丁上淮和张光裕共同负责; 元永井地方上的动态由盐兴县副县长保寇文负责; 元永井北硐方向的情况由陈顺仁负责。并由丁上淮同志负总责,发现的任何情况都应及时向丁上淮同志报告,以便作出积极应对,统一指挥。
这时,时间已经是4月24日凌晨一点多,畅达他们必须连夜出发才能确保4月25日夜将援兵带到,确保元永井的安危。
三
丁上淮送走畅达和李玉生后,陷入了心急如焚的等待和焦虑之中。他想,参会的人员中会不会有叛徒,会议的内容会不会泄密出去,敌人会不会预料到他们的决策,土匪会不会在路上设下埋伏,阻断他们求援的道路?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有提问而没有答案,就会使人去无边无际地想象,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一边默默地祈祷着他们一路平安,顺利完成任务,一边仔细地聆听着窗外沙沙沙的风声,风声中夹杂着昆虫的淫笑声、夜鸟的咕咕声、魔鬼的窃笑声和春芽的破土声。这时,夜已经很深很深,破晓的雄鸡已经叫过两遍了。元永井已经进入梦乡,空气的温度降了下来。要是在前些日子里,这个时候他盖着被子睡觉都还觉得凉。但是,今晚他的心里好象堆满了干枯的野草和掉落的松毛,被他的焦炽烧着了,身上一阵一阵地烘热,一点睡意也没有。一些声音远去,一些声音又临近。一些情景刚刚消失,一些情景又涌上心头。李惠仙这个彝族少妇,好象是个幽灵,一个大胆而美丽的幽灵,借着月亮和星星的光亮,乘着她美丽的梦幻,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脑海。再一次向他讲起了不幸的遭遇。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刚好是春天,他小心翼翼而又津津有味地吻着一朵鲜红的玫瑰花,遐想着曾经深爱过的战友郝梦。郝梦已经牺牲了,只留一朵美好的野玫瑰在他的心里。现在那朵玫瑰花复活了,就在他的眼前。它在早晨才刚刚开放,好象是为他而绽放的。淡淡的清香流进他的心灵,缠绵着他钢铁一样的军人的身躯。他都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会迷恋上满园的春色,为什么要去吻那朵象征爱情的玫瑰花,难道自己真的想女人了?
就在这春意迷蒙的时刻,有人在院门外叫了起来:“报告首长。”
他抬头一看,是 “二野” 南下学员徐平。徐平后面站着一个满身花朵的妇女。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感到一阵害羞,忽然间看花不是花,看人不是人。镇静了一会儿,才看清了一对蝴蝶从院外蹁跹飞舞而来,优美地飞舞到他刚刚吻过的那棵玫瑰花前。
他说:什么情况?
徐平说:这位大嫂有急事找你!
他声音洪亮地说:请进来!
徐平就侧过身,伸手作了个请的动作,说,大嫂请!
在徐平的带领下,那妇女进了他的办公室,并向他讲述了不幸的遭遇。她说,她丈夫的老家在黑井,原来是元永井盐矿的井下工人,1936年红军过元永井时,他曾想去参加红军,但是他的父母都在生病,她不让他去。后来,他几次深更半夜带人回家,神神秘秘,有时又在家里宰鸡喝酒,跟那些人的关系比亲兄弟还亲。她怕他出事,就多次逼问,后来丈夫才告诉她那些人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是为老百姓做大好事的人。一开始她还有些反感这些操着汉语的外地人,不知为什么,她也慢慢地觉得他们是好人了。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支持起丈夫来,开始给他们做些煮饭备水之类的小事,在耳濡目染中,她竟然也爱上丈夫所做的事了。她的父亲,一个赶马人,在五年前被土匪杀死在老高山的大石板上,财物被抢劫一空。如今她还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她恨那些不分清红皂白的土匪,她也想报仇。没想到,她对丈夫事业的热爱,却变成了与丈夫的阴阳两隔,国民党特务分子在井硐内把她丈夫杀害了。她说,她丈夫接触过的地下党人都是好人,她相信共产党是老百姓的救星。她要求他们一定要消灭国民党特务,为她丈夫报仇。她一边讲,一边哭,伤心的泪水淌满整个脸庞,跪着就不起来,还是徐平等几位南下学员用湿毛巾给她揩干泪水的。丁上淮答应她,一定要为她丈夫报仇雪恨之后,她才从跪着的冷地上爬起来。
本来,丁上淮担心她有危险,决定派人护送她的,但是,她说她娘家就在山那边的锣锅甸,离井不远,她常来元永井赶街,特务不知道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她不会有危险。她还说,即使有危险她也不怕。丁上淮就依了她,告诉她这个情况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李惠仙离开后,丁上淮还是不放心,就派人暗中保护,一直在暗中把她送到老高山山顶,看着她翻下山,看见了村庄才回来。
李惠仙后来又找过他三次,都是要求他们一定要把国民党特务消灭掉,一定要为她死去的丈夫报仇。
李惠仙为死去的丈夫报仇雪恨的决心溢于言表,对敌人的仇恨闪烁在炯炯有神的双目里。丁上淮看着她又心疼又害怕。心疼的是那可恶的特务狠心杀害了她的丈夫,使她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整日怀着恨在生活。害怕的是她已经恨到了极点,如引导不当,很可能就会走上为丈夫报仇的险路,做出蛮干的事情来。丁上淮来元永井不久,就了解过关于土匪的事,最让他记忆犹新的就是普太太了,据说普太太曾经是土匪普学红的太太,由于丈夫被害,她举着为丈夫报仇的旗号,招了三千人马,盘踞在离元永井并不算太远的五台山,三千土匪的吃穿用等财物都靠抢夺获得,给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对她而言,则是报了仇,顺了心了。这事虽然过去了,但普太太的英勇举止却给这些地方的人民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李惠仙也表露出要像普太太一样为丈夫报仇的愿望。谁知道这个可怜的彝族妇女会做出什么事来。最好就是答应她帮她为丈夫报仇,这样,她也许就会重新过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丁上淮回忆着往事,回忆着这个彝家少妇,眼睛就湿了。不知是伤心过度,还是劳累异常,他坐在木椅上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那是一个恶梦,梦中的李惠仙手持一把长刀,赤身裸体地和几个税警队员拼杀,杀得他们鲜血直喷,喷得她满身鲜红,吓得满街的人惊声尖叫,叫声把他也吓醒了过来。这时,窗外射进了微微的亮光,黎明悄悄来临。
四
天一亮,丁上淮就安排几个南下学员,悄悄地到四处搜集情报,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
昨晚在会议上虽然已经作了明确分工,但是,这一夜里,丁上淮不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天亮了也不见有人来汇报情况。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不得不防备,不得不多心,毕竟参加开会的几个领导他还不完全了解他们的底细,他只能凭直觉判断哪个可靠,哪个得提防。虽然,他一再想起领导说的 “疑人勿用,用人勿疑” 这句话,但是,他也不得不使用 “兵不厌诈” 这个成语。在这关键时候,他得充分利用南下学员,相比起来这些人的思想要清纯一些,政治立场也鲜明,靠的是共产党这边。
约半小时左右,李兵回来了,报告说:报告首长,元永井地方上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和往常一样,卖菜的卖菜,买菜的买菜。接着杨楠也小跑着进来,立正汇报道:报告首长,元永井税警队情况正常,他们都在那儿训练着,和往常一样; 接着,张福安返回,报告说滇中盐场没有动静; 最后,马超跑来了,他汇报说:报告首长,北硐方面平静如水,无异常情况!
这小子还有点文学修养! 丁上淮心里不由一亮,对他们比着 “好了” 的手势,稍微放下心了。他多么希望崔建彬给他带来的消息是一个谣言,是一个弥天大谎。这样元永井就平安无事了!
然而,谣言归谣言,阴谋背后必将是刀光剑影,危机四伏,生灵涂炭,他不敢把李惠仙的话当作谣言。
这时,太阳已经冉冉升到东边的山头,暖洋洋的阳光洒满鸡鸣山东部和老高山的东部,炊烟缭绕在阴影中的房舍,有女子的歌声响彻在带着露珠的深箐里。连夜摸黑三十多公里的李玉生,也不负众望,已经安全赶到了黑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