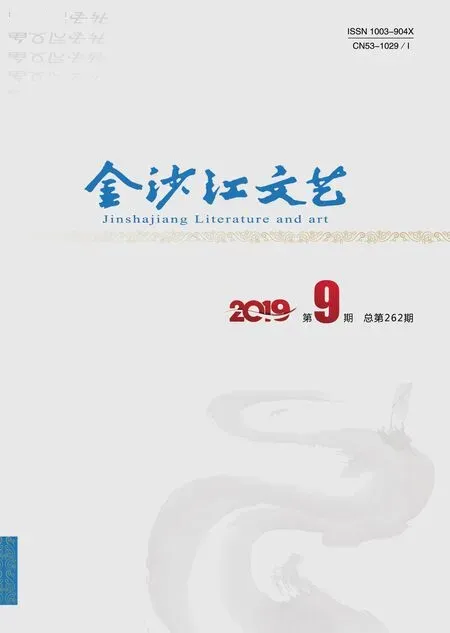母亲
◎许从芬
母亲出生于50年代初期,在外婆的五个儿女中排行老大。外公去世得早,从懂事开始,母亲就已知道帮助外婆操持家务,照顾弟妹,由于从未进过一天学堂,直到今天,母亲只知道自己的名字,但却从不知道如何书写。
随着岁月的增长,母亲逐渐到了该出嫁的年龄,然而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并没有在母亲身上发生。母亲嫁给了和外婆家同样穷困的父亲,由此开启了另一段更为艰辛的人生旅程。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住在一个大杂院子里,和我族人里的大娘大爷、婶婶叔叔住在一起,一大排的长房子,每家有一至二间不等的住房,而我家的住房,就在这一整排老旧房屋的最顶端。
外婆家穷困,母亲嫁给同样穷困的父亲后,随着我们兄妹四人的相继出生,加之父亲有严重哮喘,无法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日子过得更是穷上加穷。看着我们兄妹四个瘦岑岑的身体、眼里不时露出的饥饿眼神,母亲一边拼命地劳作,一边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爱占别人小便宜的习惯。那时候农村在插秧或者收割水稻、小麦时,邻里之间会相互帮忙一起劳作,被帮忙的一家会煮两顿饭,伙食也比平时好得多。母亲往往会在吃饭时抢先把自己的碗里盛满,趁别人不注意时快速地把自己碗里的两片肥肉悄悄塞在衣袋里带回家给我们解馋; 有时会在天黑回家时悄悄地把别家地里即将成熟的玉米掰三四个回来,放在清水里煮熟让我们充饥。在那个困难的家庭里,在那个饥饿的童年里,母亲带回的这些东西无疑成为了我们兄妹儿时最期盼母亲回家的理由。然而母亲的这些行为终究还是被眼尖的人发现了,并且被一传十十传百的夸大,很快母亲就被村邻快速的孤立了。
每年农历的冬月,农村人几乎都要上山砍柴,那时的农村,所有需要火的东西,依靠的几乎都是木柴。深秋的冬夜,没有钟表,当鸡叫三遍后,同一个大杂院里的婶婶大娘们就陆续开始起床,邀约着到六七公里外的山林里砍回杂木或者松枝,作为一整年的生活用柴。起得相对早的女人会挨家挨户地一路大着嗓门叫过来:走啦走啦,顺英嫂子,走啦五叔,起床了……然后是一串的应答声和开门声。然而邀约的声音到我家旁边时戛然而止,没有人叫我母亲一声,哪怕是叫错了的时候也没有。我母亲知道、我们全家人都知道,那些大娘大婶们是在有意地孤立我母亲,孤立我家。然而我母亲会假装不知道,她会在别人叫到我家隔壁的时候,赶紧把头伸出破旧的窗子,急急地说:三大娘,等着我,我也起来了。被我母亲称为三大娘的人会假装没听见,低着头转身到院子里另外一户已经起床的大娘大婶家里,继续等院子里其他的人,然后一起出发。母亲为了能和院子里的其他人一起出发,往往会更早起床,家里的公鸡才叫三遍,无论冬季的早晨有多么冷,母亲都会一咕噜就爬起来,三下两下收拾好砍柴的刀子和绳索,站在大杂院她们必经过的路口等着她们,期盼着能加入她们的队伍,融入到她们的圈子。可即使这样,母亲仍然还是被孤立了,我那些所谓的大婶大娘,即便从我母亲旁边走过,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动和我母亲搭腔,纵使我母亲主动和她们说话,她们也会默契地装作没听见,更有甚者还会挤眉弄眼,相互会意地斜看我母亲一眼后把头扭向远方,继而一大群女人爆发出忍不住的嘲笑声……母亲讨好的笑容慢慢地僵硬在脸上。
之后的日子,母亲没有再刻意地去融入,无论天气多冷,母亲都会在鸡叫三遍之后准时起床,利索地收拾好砍刀和绳索,摸着黑走向那熟悉的山林。
从古至今,无论是生活在哪个地方,也无论是贫穷或者富有,在人的内心里,都有被人接纳的期望,谁也不希望在群体之外孤立地生活。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一些劳动力多的家庭已经不去上山砍柴了,他们储备够了一整年所需的木柴,已经开始准备杀猪过年了。我家没有猪可以杀,家里精心饲养的两头肥猪是我们兄妹四人来年学费的全部希望。慢慢地,继续走在山路上砍柴的只剩下我母亲了。
一次,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听到母亲在说话:“奇怪,咋今天鸡还没有叫啊,不知是几点钟了?” 母亲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推开破旧的窗子准备观察月亮的位置,多年的生活经验,练就了让母亲几乎能准确地通过观察月亮位置来推算时间的本领。可那天夜里下了一场毛毛雨,外面一片漆黑,看不到月亮。母亲站在窗前犹豫了一小会,最终还是决定起床了。家里的公鸡听到动静,以为天亮了,开始一声接一声地鸣叫,听到公鸡的叫声,母亲没有再犹豫,裹了裹身上的破衣服,推开门出去了,随着吱嘎的开门声和关门声,四周又恢复了寂静,迷迷糊糊中我又睡着了。
待我起床时,天色已经大亮了,想起母亲为全家奔波操劳,我拿起镰刀和篮子准备到地里割青草回来喂猪,却看见母亲已经背着一大捆木柴回家了,我正诧异母亲今日为何回来得那么早时,发现母亲比以往任何一天都更疲惫,她瘫软坐在地上,身体无力地靠在她刚刚背回来的那一大捆木柴上,嘴唇灰白,眼窝深深地陷进去,两眼闭着,仿佛再也无力睁开,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蜡黄的脸滴落下来,印在破旧的衣服上,胸前的衣服已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紧紧地贴着瘦削的身体,黝黑的、长满老茧的双手满是鼓起的青筋。看见我,母亲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努力挣扎着坐起来,我丢下镰刀和篮子,把母亲扶进家,拿出母亲平时从来舍不得吃的白砂糖,浓浓的泡了一杯水递给母亲,母亲大大地喝了一口,脸上有了少许的红润,再喝第二口时,母亲却只舍得小小地喝了一口就怎么也不肯喝了,她把泡糖水的杯子硬塞在我手里让我喝完。
我后来才知道,母亲那天出门的时候应该还是半夜,凭着熟悉的记忆,母亲在熟悉的山路上一开始走得很快,可越走四周似乎越来越黑,旷野里愈发的沉寂,听不到一丁点人的声音。母亲不知道到底是几点,一路上走走停停,往前看一团漆黑,往后看看也没有来人,在无尽的黑夜里,母亲不知道要继续走还是停下来,就这样在犹犹豫豫中越走越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凭着记忆摸黑前行。一直走到了要到达的山林,天色都还没有亮,母亲更加恐惧了,她找了一棵粗壮的松树畏缩着蹲在树根下,一边忍着寒冷一边期盼着天色赶紧亮起来。四周的山林静悄悄的,连鸟鸣的声音都没有,只听得见一阵阵山风吹过树林的声音。
天边终于开始泛白了,四周的树木也隐隐约约地开始清晰起来,待天色完全亮起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背着一大捆木柴走在了回家的路上……上天对人是公平的,太阳每天都东升西落,并不会因为某些人的贫穷或者富有而推迟升起或者落下的时间,黑夜,终究是会过去的……
在兄妹四人中我年龄最小,我继承了父亲多病的体质,和刚强的个性。面对大杂院里受那些大娘大婶们耳染目睹也想孤立我的同龄人,纵使我内心是多么地期盼和她们一起玩耍,但我从不主动去讨好他们。闲暇时,两个哥哥和大姐会教我认识汉字,上了小学,我的识字量更是突飞猛进。六年的小学,班级里的第一名永远是我,我越来越不惧怕同龄人的孤立,在她们玩耍嬉闹时,我选择了看哥哥姐姐的课本和她们带回来的小人书,我的视野越来越开阔,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甚至开始在内心嘲笑那些试图孤立我的同龄人。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可我还觉得,书中还有一种力量,那就是哪怕你被周围的所有人隔绝,你的内心也依然不害怕。
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的开始越走越远,我不断看到新的世界,那些曾经孤立我的同龄人,那些曾经不止一次孤立母亲的大娘大婶们,早已被我的内心远远抛弃。然而我始终无法忘怀她们曾经对我母亲作出过的伤害,始终无法忘记母亲那挂在脸上讨好的、最终变得僵硬的笑容……
多年后,我已经能客观地评价母亲当年的行为,也理解了她们孤立我母亲的举动,然而我始终无法原谅她们。纵使我母亲当年的行为有多么地惹人生厌,她们也不应该那么过火地对待我的母亲,因为那些让人不愉快行为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母亲对自己子女深深的爱。
我大学毕业后一举考起国家公务员,成为了一个端 “铁饭碗” 的人,这个消息震惊了我曾经生活过的小山村,那些曾经看不起母亲的、当年曾经带头鼓动边缘我母亲的大娘大婶们,再次遇到我母亲时,完全没有了当年的盛气凌人。然而母亲似乎淡忘了她曾经受到的伤害,她变得更加随和了,遇到当年带头嘲笑她的人,她也仿佛忘记了曾经有那么一回事,她主动和她们打招呼,主动约她们到家里唠家常,还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用的东西拿出来分给她们一些。面对我对她们冷漠的态度,母亲还会絮絮叨叨地批评我,说我没礼貌,要求我下次遇到她们时要主动和她们说话,还说她自己当年的行为也确实不对,现在日子过得好了,人与人之间更要和睦相处。
我对母亲的批评特别的不服气,总是会想起母亲当年受过的苦,可看到那些大娘大婶们日子过得依然不富裕,我内心也会莫名其妙的有深深的疼痛感和失落感,想起现在党中央从上到下都在号召脱贫攻坚,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而我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我的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可我居然还没有母亲的胸怀肚量……在以后的人生旅程里,也许我应该把自己的内心适当的清一清零,学一学我亲爱的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