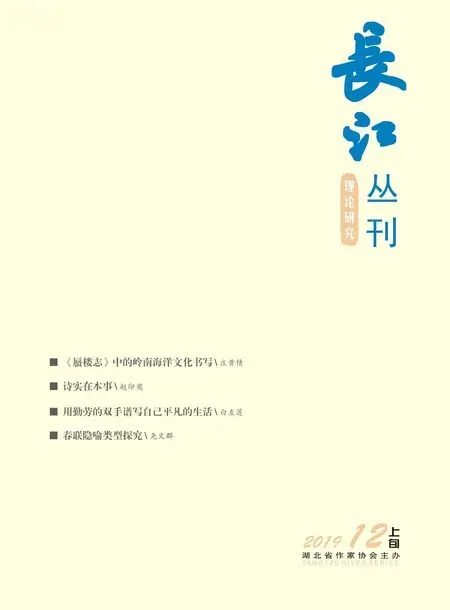美术馆策展,一种艺术史的记忆方法
■王艳华/广西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一、策展人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美术馆策展人制度”的兴起
据考证,“策展人”一词出自于西方博物馆、美术馆体系建立之初期。在西方艺术体制中,“curator”原本是指博物馆馆长,后来被专指博物馆中“常设策展人”一席位,专门负责馆藏艺术品的整理、分类、研究以及专题陈设和展出。“美术馆策展人制度”的建立,旨在通过将策展重新纳入美术馆的机构体系,重溯其作为美术馆的一个主要功能,来调和策展与美术馆机制之间的关系,并试图解决策展、美术馆与美术史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被史泽曼称为“一段纠结的友情”。
在西方国家,比如MOMA以及伦敦多家公立美术馆,他们自身都设有严格的策展人机制,而且,他们的策展人多是以艺术史学者或者有着深厚艺术史学术训练背景的人员担任。“美术馆策展人制度”的基本立足点是艺术史,它的倡导者认为艺术史是策展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是后来于 2001 年前后在美国先后成立“美术馆策展人协会”以及“策展人讨论会”的根本出发点。美术馆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中,美术馆体制内部对策展以及策展人机制也是不断进行反思的,只是由于“独立策展人”连年来呼声强大,“美术馆策展人”消匿了其声息而已。
其实,不管是就策展对前卫艺术的表征功能来说,还是针对其学术性及艺术史定位而言,策展的发展都受制于美术馆这一母体与艺术史的关系演变。可以说,独立策展人,正是当美术馆与艺术史关系紧张之时,出于对美术馆这一职能机构的不信任,才脱离美术馆这个策展机制的母体而独立出去的。然而,独立更加剧了上述二者之间的矛盾。对于“独立策展人制度”和“美术馆策展人制度”的学术性,中国一位策展人认为,“我们今天在国内所理解的策展人,其实是体制外的独立策展人概念。这个独立策展人是跟着国际艺术节或双年展出来的,通常是一个临时的项目。所以,这些策展人要有十八般武艺,既要有学术,又要会推销,还要找赞助,其实看起来更像一个生意人。”而美术馆策展人,应该是“一个做学问的读书人,是一个研究员的身份。策展人原本就是属于美术馆的一个职位,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策划、举办、研究展览,以及教育推广。”可见,在美术馆内部提升策展人的学术环境是十分重要的。策展是“艺术史创新研究之部件”,我们可以通过关于策展的学术性论文的跟进,“助推研究机构与博物馆之关系的递进”。此外,美术馆要加强与艺术史家的对话,增进与独立策展人或作为客座策展人的来自大学的艺术史学者之间的通力合作,强调美术馆体制内策展人的学术性并提升他们的科研能力,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美术馆策展人制度”,同时,抓住“历史物质性”回归的历史潮流,在艺术史家努力解决与美术馆之间矛盾的同时加强彼此的互动和协商,这样,才能在多方合力之下使得美术史、美术馆、策展三者得到和谐、统一的发展。
二、美术馆策展是一部“正在发生的艺术史”
“美术馆策展人制度”,将策展重新纳入美术馆体制,这既符合策展自身对当代前卫艺术的表征身份,又符合美术馆作为当代艺术的展策机构的体制特征。追溯美术馆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方面美术馆被称作“当代美术馆”,以与博物馆相区别,“是公立或私立的非营利机构,宗旨是推动国际或本地的现、当代艺术”;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艺术史学家或者艺术理论家而言,美术馆又是“艺术博物馆”,在与艺术史关系方面,有着与博物馆共同的职能和物性基础。美术馆的这个双重身份,一般在学术研究中不被同时提及,美术馆或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对于美术馆问题进行研究时将其预设为前者,而艺术史论家通常将其认定为后者。然而,这一身份的双重性十分重要,它使得美术馆既在当代艺术活动中扮演重要的场域角色和收藏之地,与策展建立天然的母体联系,又与博物馆拥有共同的艺术史根脉,是有关各个阶段艺术史研究的重镇。
在艺术史上,策展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它通常与某种艺术运动的兴起有关。它和前卫艺术家对话甚多,甚至能起到直接影响当代理论家的作用。1787年巴黎美术展上,人们一睹大卫的名作《苏格拉底之死》,正值此时,新古典主义的风潮来到艺术界,它“有意识地选择对象,既排斥罗可可的浅薄,也否定巴罗克的以假乱真的错觉构图”。1904年,巴黎举办塞尚作品的大型画展,与此同时,文森特·威廉·梵高以及保罗·高更的作品也陆续展出,这是二十世纪艺术骚动的伟大开端。此外,策展的影响有时也通过它对理论大师的作用而得以显露出来。1964年11月,安迪·沃霍尔在纽约举办了首次个展。丹托据此受到极大的启发,于当年岁末的哲学年会上提交了《艺术界》一文,并进一步写作,于1981年又有了《寻常物的嬗变》一书面众。这本书在国内外理论界引起了热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沃霍尔的纽约个展对于丹托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丹托的理论不仅成为艺术史研究史上无法逾越的一笔,更为策展日后的发展起到了理论导向作用。
可见,无论从美术馆的前述的哪一种身份出发,美术馆与策展都是站在同一队列里,它们共同构成了与美术史的悖论关系。就二者的当代性而言,美术馆对于策展具有母体的身份。策展的时空观是在这个母体中得以实现和完善的。策展与当代的艺术运动以及前卫艺术分不开,它书写的是一部“发生的艺术史”,是当代艺术的一种艺术史记忆方法。在这层意义上来说,策展的时空性与时代同步。同时,作为艺术史“载体”的策展,它自身另有一套时空方法,或缔造时空,或回归历史现场。上述两种情况,都与美术馆这个母体的物理空间以及“物件”材料的支持无法分割。美术馆是“可视的艺术史”,展览是“可视的史料”,展览的时空性是“策”展的第一预设,当策展人制度与这两个属性尽可能贴合时,才会有效促进策展的发展。“美术馆策展人制度”在策展的时空性上实现了美术馆与策展之间的一种契合关系。
从时间概念来看,策展不仅是“正在发生的艺术史”的书写者,更是时间的缔造者。美术馆展厅可以容纳的不仅是展览作品、物件,它更是一个时间场域,人们的时间感被创造,人们的历史感被创造,甚至,人类的历史记忆,经由一次次策展而或可全然被改变。这也可以看作策展作为艺术史记忆一种方法的第一层解读。
策展这一新事物,出现在艺术史的某个时间段里,具体说来,是启蒙之后的事情,或者,是美国第一个独立策展人史泽曼大展身手的时候。从那时开始,陆续的,我们发现,主体与艺术品客体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人们开始大力着手研究艺术品价值界定问题。迪基的艺术制度理论着力分析艺术品价值的定义法则;丹托则将“艺术史链条”派生出的关联性“艺术界”视为界定艺术品价值的参照。总之,艺术被置于时间段里,从永恒中抽离了出来。当艺术抽离出了永恒,艺术的界定就得被重新考察。我们可以设定,策展是作为一种与“艺术界”类似的话语权利枢纽登上艺术史的,经“策展”的“策”之内核被展览界所接受时起,艺术价值的时空性就被重新体认,或者说,意念或观念开始挑战艺术世界的历史传统,企图切断时空感而对艺术价值重新界定。
此时,当策展成了观念判断的演说者时,策展就成为了第一个考察艺术品价值的活动,策展人也即成为了第一个考察艺术品价值的主体。艺术品一经面世,则无法以其面貌单枪匹马出现于受众面前,而是带着策展人的理念桂冠面向众人,使人分不清策展所展示的,是实物,还是观念。
人们最终承认,是观念招致众人远道而来,汇众一处。在这种主体自由的放纵中,丹托的“艺术界”可谓之是回归艺术史判断的一大努力,也就是说,是对艺术史古老时空性的一种坚守。同样,“美术馆策展人制度”,也是以对传统时空观坚守的姿态而对抗“独立策展人制度”的。它对策展人之“独立”行使一种体制职能,或制度的羁回,它以“艺术史”(不管是回溯还是当代创造)的场域感,来参与策展的时空缔造,它以“艺术史”的统一感来审视新起的艺术潮流,诚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言,人类的文化历史是人类不断追求自我解放的历程。如果说“独立策展人制度”是为着“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而宣布与美术馆体制的决裂的话,那么,我们无法忽视的,正是人在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的“张力与摩擦,强烈的对立和深刻的冲突”,而回归美术馆与艺术史的据点,是策展发展史上的必然,其典型体制呈现,则是“策展”与“美术馆”重新结构起来的统一。
促使“美术馆策展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物质性的实质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则对于我们时代而言,“正在发生的艺术史”的书写则绝无可能。这个问题是,对于策展而言,策展观念的呈现方式变得越来越昂贵。比如,贝尔廷曾描述过一次价格昂贵的策展:
在像一座被遗忘的集装箱矗立于卡尔广场的维也纳新艺术大厅里,美国的媒体艺术家加里·希尔运用极为昂贵的、耗费了数名专家数周工作开发的技术呈现过一次展览。展览开幕时,电子设备像戏剧舞台的后台机关一样隐藏在后,由之产生的图像看起来似乎与技术毫无关联一般。只有当接通电源时,展览才能运转,因为组成展览的元素只有播放的监视器,它们发出的光亮为黑暗的展示空间提供光源和运动的影像。……真实的展览空间中产生了以时间为基点的、非物质形态的观看空间,无法拍摄,也无法用文字描述。
参加这个展览的观众,他们享受着昂贵技术缔造的的时间出现的那一刻,他们同时也无奈地被填充记忆,因为,之前根据时间长短呈现的作品的在场被观众的在场取代,观众走进这里,呆上一会,根据自己的印象自动生成对于展览的记忆。短暂的原初印象在这里被长时的原初印象代替,而且,电脑可以控制胶带播放的时间。
可见,当今前卫艺术的呈现需要昂贵的技术支持,策展的背后也就需要巨大的财助后盾,而这对于“独立策展人”来说,时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正常的。我们呼吁体制的援助,而美术馆是首当承担这一历史革新的机构,它转变机制适应新的艺术策展需求,是当务之急。这向我们提示了几个问题:一、“美术馆策展人制度”,必将取代“独立策展人制度”,因为后者财力技术上越来越无法单枪匹马完成一次成功的策展;二、策展将以强大的技术支持,呈现给人们一种前卫艺术所需要的展览场域,在那里,艺术史可以被改写,精神史可以被重新审视,人们的记忆,或人类的记忆将被重新注入,被重新填充,被随意割断,被时间序列内的符号任意编排或恣意编排而彻底改写。博物馆以及它的展示之物将退为作为存在背景或辅助之物的“硬件”,如天空大地对于人们的生活环境来说一样,必不可少,却无法抗衡于千变万化的世道。于是,“在博物馆中,人们一方面获得的是场所的经验,有形的产品存在其中;另一方面,人们还会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展品寓于时间之中,通过时间传达自身。”当作为背景材料的有形产品无力抗衡时间的任意编排以及记忆的随意创造时,美术馆策展对于前卫艺术的展示则不可替代,它书写当下“正在发生的艺术史”的强大记忆功能也就不可抗拒的呈现于我们的面前了。
总之,策展一旦脱离“美术馆”这个母体,比如“独立策展人”这一现象,只能是策展制度的过渡阶段,不能成为策展制度的最终形态。最终,“美术馆策展人制度”的确立,将策展回归于美术馆机制,并以建立美术馆与大学、艺术史学者、以及独立策展人之间的联系为途径,才能将“正在发生的艺术史”写入历史总体,将策展这种艺术史方法,纳入艺术史的范畴中来,也只有这样,才是有望实现彭锋先生所谓的艺术之三大回归的必然途径。
三、“美术馆策展人制度”的艺术史意义
卡西尔说,科学在思想中给予我们以秩序,道德在行动中给予我们以秩序,艺术则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之把握中给予我们以秩序。而恰恰是策展,将单个物件的艺术史价值,转成为序列的艺术史价值,为“风格矩阵”提供这样或那样的可能的组合。“美术馆策展人制度”是对“独立策展人制度”的一种反拨,后者在艺术史序列的组合中太过强调人类主体观念的干预。将策展归复于它的母体美术馆或博物馆,是对物本体的一次重新体认。只要物本体存在不被完全消灭,只要尽可能保留完好,那么,这部精神主体干预的序列的转变史就是一部新的艺术史,序列的转变就意味着艺术史的重构。在这层意义上来说,美术馆不仅是一部“可视的艺术史”,更是一部“观念的艺术史”的物理呈现;美术馆策展,则或可代替艺术作品,成为艺术史记忆的一种方法。
——《艺术史导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