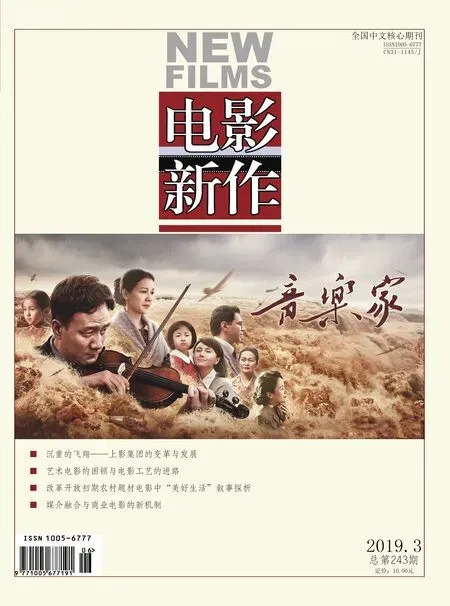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题材电影中“美好生活”叙事探析
林进桃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起,改革初期各种题材的电影佳作迭出。如包括《当代人》(1981,黄蜀芹导演)、《钟声》(1981,马尔路、文彦导演)、《血,总是热的》(1983,文彦导演)、《赤橙黄绿青蓝紫》(1982,姜树森导演)、《代理市长》(1985,杨在葆导演)等在内的改革题材电影;包括《邻居》(1981,郑洞天、徐谷明导演)、《人到中年》(1982,王启民、孙羽导演)、《逆光》(1982,丁荫楠导演)、《大桥下面》(1984,白沉导演)、《雅马哈鱼档》(1984,张良导演)、《二子开店》(1987,王秉林导演)、《夕照街》(1983,王好为导演)、《街上流行红裙子》(1984,齐兴家导演)、《烦恼的喜事》(1982,天然导演)等在内的都市题材影片。本文将要探讨的是这一时期包括《喜盈门》(1981,赵焕章导演)、《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张其、李亚林导演)、《咱们的牛百岁》(1983,赵焕章导演)、《乡音》(1983,胡柄榴导演)、《人生》(1984,吴天明导演)、《野山》(1986,颜学恕导演)、《老井》(1986,吴天明导演)、《咱们的退伍兵》(1986,赵焕章导演)、《月亮湾的笑声》(1981,徐苏灵导演)、《村路带我回家》(1988,王好为导演)、《哦,香雪》(1989,王好为导演)、《陈奂生上城》(1982,王心语导演)等一批农村题材电影中的“美好生活”叙事想象。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电影中的“美好生活”叙事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①。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部分电影创作者敏锐感知到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对古老中国的强烈冲击,不少电影转而开始关注农村、农民、农民进城等话题,塑造了一批极富生活质感、颇具艺术个性的农民形象②。通过这些影片,我们得以管窥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美好生活”图景的想象。其中,《人生》(1984)、《黄山来的姑娘》(1984)等影片,呈现了现代都市对传统村落的巨大诱惑力,这些影片由于能够迅速、准确地切中时代脉搏,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语境深切契合,从而获得较高荣誉③。《野山》(1986)、《老井》(1986)等影片,则秉持更具现代性的立场,对落后愚昧的传统进行反思,“农村”在这些电影中成为亟待变革的传统的象征。《野山》结尾电磨与石磨的对比,《老井》结尾机械打井对人力打井的取代,无疑都在宣告现代性的胜利。《乡音》中独轮车的吱吱作响与火车的呼啸轰鸣等的对比设置,亦构成了别富意味的隐喻。
一、“美好生活”影像符号建构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需求层次理论中指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⑤。对于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尤其是对于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农村来说,“改革开放”所昭示的美好生活,其想象更多时候是建立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初始阶段。
其中,“吃”与“穿”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影“美好生活”想象最常见的影像符号。《乡音》中只有小家,没有自我的陶春,跟丈夫余木生的相处之道及口头禅便是“我随你”。穿上新衣服去看火车曾是她最大的心愿,但是就是这一卑微的心愿,也只能在她确诊肝癌并将不久于人世后才得以实现。懊悔于之前的种种,余木生赶赴县城为陶春买猪肚、购新衣,用独轮车推着陶春去看火车—对于一直身处闭塞贫困小山村的陶春、余木生们来说,吃上一口猪肚,穿上一件新衣,看上一眼火车,就是“美好生活”的全部,满足这些美好想象,也便可以不枉此生。在这里,“新衣”不再是单纯的、外在的、实体的所在,而更多是一种象征和隐喻⑤。影片意欲通过陶春、木生对待“新衣”的微妙态度,洞悉这对清贫而善良的夫妻静默而不失激烈的观念撞击和精神洗礼。革命话语主导下所推崇的集体价值,在影片中主要表现为陶春对“家”的无私付出,开始被启蒙所宣扬的个人价值所替代。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新衣,既是改革开放初期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发现和期许,更是对自我对他人的允诺和认同,是人物打破自我行为约束,重新发现自我的标志。正如同时期的都市题材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中那袭飘逸鲜艳的红裙子,不仅仅是时尚的标志,更是青春自信的自然流露,是对美的大胆展现与向往追求,影片中劳模陶星儿公园中“斩裙”一幕,借助特写慢镜头,把红裙子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未出现,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火车”也是影片《乡音》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建构起改革开放初期闭塞山村百姓对外界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而在影片《哦,香雪》中,火车所承载着的同样是几个乡村少女对山外世界的美好憧憬⑥。
纵观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叙事更多是建立在吃、穿、住、用等方面。《喜盈门》中,大嫂强英的几次“闹”都是因为“穿”“吃”,想要涤纶绸裤子,偷吃饺子等;《乡音》中陶春一家为了改善住房而欠款;即便是都市题材电影如《邻居》等,也聚焦于住房问题;《烦恼的喜事》中,普通人的婚恋之喜,同样受制于物。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题材电影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对“物”的生产与占有的基础上。而作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相对高的要求者,《人生》中高家林与黄亚萍的“心灵沟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批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题材电影强调“物”的重要性,但这一时期的农民,其“美好生活”更多的是建构在“物”的生产而非是“物”的消费之上。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消费主义是作为‘四化’的对立面而被否定”⑦。作为“物”的重要生产者,《乡音》中,陶春从来没有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面对女儿询问,“你给自己买了什么”,陶春答道买了猪娃。在改革开放初期,“猪”成了众多农村题材电影中另一个常见的“美好生活”叙事符号,陶春夫妇一直心心念念的是改良猪娃,即便是陶春读小学的女儿,也为了喂养猪娃而欲放弃上学;《人生》中,巧珍在给恋人高加林写情书时仍不忘提及家中的老母猪,“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而《喜盈门》中,泼辣嫂子强英后来与大家庭的和解则主要缘于她所牵挂着的猪娃在她离家时仍然被照顾得很好。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题材电影,“生产”作为主要的话语机制,对“物”的享用在一定程度上仍表现为一种期许或者承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基于马斯洛的低层次需求理论的“美好生活”影像建构更多时候仍然是停留在未来的图景想象之中,真正的“美好生活”与人们的实际需求之间仍相差甚远。
除了“吃”“穿”“住”,以及作为美好生活期盼所在的“猪娃”等常见元素和符号,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题材电影中,对作为遥远他乡的城市和城市人的想象,也频频出现在大量影片,尤其是农民“进城”影片中。《黄山来的姑娘》中,小保姆龚玲玲对城市生活的想象更多是一头“鸡窝”似的卷发和尖细的高跟鞋;《陈奂生上城》中,乡下女人们口中,城里女人个个“雪白粉嫩”,城里尽是“花花世界”;《特区打工妹》中,作为从穷山沟挺进大都市的“淘金者”,打工妹们渴望能够像公司江董事长所许诺的那样,“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便可衣锦还乡”;《野山》中,初到县城的桂兰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无论是穿着时髦的漂亮女人,快速行驶的摩托车,还是商店里的大彩电都让她兴奋无比;影片《哦,香雪》中,尽管从未走出隐藏在大山邹褶里的台儿沟,但透过那趟一天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山村少女香雪、朵儿、凤娇等却建构起她们对于城市美好生活,尤其是对北京的美好想象。与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影“美好生活”叙事对“物”的强调与凸显不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借助一件在母女三人中传递的红毛衣,通过母女两代人三段不同的情感经历,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题材电影“美好生活”想象提供了独特的“情爱”视角。
二、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与分野
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农村来说,乡土社会的思维方式、劳作方式、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随着社会文化语境日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不少电影在“现代化”视域中展开叙事。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影中的“美好生活”想象,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与分野愈发明显。这尤其体现在根据贾平凹小说改编的系列电影,如《野山》《乡民》等中。
《野山》根据贾平凹的中篇小说《鸡窝洼的人家》改编。影片中的禾禾身上有着对农业文明的强烈反思,属于改革开放早期有着强烈变革欲望,试图创造“美好生活”的“折腾者”。影片开始,安静的山村深夜,在灰灰香甜的鼾声中,一盏油灯,一条老狗,禾禾一人推着石磨做豆腐,天未亮就挑着豆腐担子走乡串巷,吆喝叫卖,一副孤寂、落寞的失败者形象。禾禾早年当过兵,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具有强烈的变革要求和朦胧的商业意识,然而,正如前妻秋绒所说,“烧窑,窑塌了;养鱼,鱼也死了。一点家当,全都贴了进去了”。禾禾不满足于从土地里讨生活,凭着一股倔强劲,他继续尝试各种营生,卖豆腐,养蚱蚕,养飞鼠,跑运输。正是由于他不愿意“老老实实地蹲在洼子里,务庄稼,过日子”,秋绒执意与他离婚。尽管“政府提倡个人折腾,发家致富”,但在秦岭深处山村鸡窝洼的村民看来,禾禾属于典型的“瞎折腾”“浪荡哥”“败家子”。
如果说禾禾与嫂子桂兰代表的是改革初期开风气之先、有想法、敢折腾的早批农村变革者,那么灰灰与弟媳秋绒代表的是传统的、保守的、喜欢过安稳日子的农耕一代。作为庄稼好手的灰灰更是在秋绒面前扬言:“不管那禾禾怎么折腾,到头来也得来我的面前认输。我可把话说死了。”灰灰是典型的安于过小日子、恪守本分的农民,他一再劝诫禾禾,“当农民就要像个农民的样子,只要你答应往后不再折腾,我包你一家还是滋滋润润地过日子”,并感慨,“如今这道理呀摸不清,过去呢,穷是穷点,啥事都队长操心,这日子过得倒也安稳。可是这地一分,人心各有各的想法,日子反而过乱了,不知是咋了”。正是在长期的相处与劳作中,禾禾与嫂子桂兰,灰灰与弟媳秋绒由于趣味相投、惺惺相惜而相互产生了感情,从而出现了“兄弟换妻”、“家庭重组”的悲喜情感故事。影片重点讲述了禾禾与桂兰的情感发展与情感认同,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禾禾不止是把一点生活表象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把一种新生活的实体带到了‘野山’,带给了桂兰。他抛开以土地为本的传统意识,左一个主意右一个想法的‘瞎折腾’中充满了生命力的色彩,打破了‘野山’生活的沉闷空气,迎合着桂兰对生活朦胧的期待,使桂兰身上那股被压抑已久的生命的活力找到了自己认同的对象。”⑧
影片中饶有意味的一个细节是,桂兰在禾禾的影响下用盐水漱口,而遭到丈夫灰灰的嘲讽,“那嘴是吃五谷的,莫非有个屎不成?”⑨桂兰到县城找禾禾,两人同逛县城一场戏是推动影片叙事的重要环节。走进县城的桂兰对禾禾的“瞎折腾”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和理解,正因为这次外出,村里盛传“桂兰跟禾禾私奔了”,并直接导致灰灰与桂兰的离婚,也成为两个家庭“重组”的关键。影片尾声,灰灰与秋绒仍使用着传统的旧式人力石磨,而禾禾与桂兰在村人一片“发了”的赞叹声和艳羡中买来电动磨面机。影片在夜色下鸡窝洼阵阵欢快的鞭炮声中结束,意味着商业战胜了农业,现代战胜了传统。而这,也正是从肯定“劳动”向肯定“经商”的转变。通过讲述大山深处两户人家分化与重组的故事,《野山》塑造了改革开放初期两类农民形象,恪守传统农耕生活的灰灰与秋绒,敢闯敢冒险向往现代生活方式的禾禾与桂兰,并通过禾禾这一“折腾者”形象表达了对农业文明的反思。正如有学者指出,“《野山》从表面看,讲的确是一个‘换老婆’的故事, 然而导演颜学恕不仅出色地描写了这个事件的过程, 而且着力于揭示出这一过程中普通农民复杂的文化心理因素的演变,以及由此透视出文化转折的意义。在变革的文化背景下, 禾禾在经历了多次折腾之后, 不仅终于在经济上告别了自己那贫穷的过去,而且在文化观念上也挣脱了‘鸡窝洼意识’的牢笼。新的经济活动和新的经济意识赋予他一种新的文化意识,使自身作为人的素质得到了提高。也正是由于他具有一种新的文化观念, 才又反过来保证了他的经济活动最终得以成功。”⑩与《人生》中对舍弃巧珍、背负道德枷锁从而饱受批评的高加林相比,《野山》中对禾禾更多持正面肯定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这种肯定被指认为是影片叙事上的巨大进步。“其中的换老婆尤其换得好,它冲击了农村中的封建婚姻,不像《喜盈门》分了又合,转一圈又回去了,还搞那四世同堂。那是一种陈腐的道德观念,而《野山》是一种新的伦理观念。”⑪“现在三中全会后,越来越有个人选择,越能表现个人不同于别人的特色。社会需要这样将个人的聪明才智表现出来。……这也是对改革的颂歌。”⑫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与分野同样体现在影片《乡民》中。该片根据贾平凹的小说《腊月·正月》改编,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秦岭山区以韩玄子为代表的富有权威与名望的旧式知识分子与以王才为代表的善于抓住社会变革时机创业的新式村民之间的一场博弈,“它不像有些电影只着眼于农村经济的改革即农民生活的变化,而是着眼于当代农村的文化意识的危机:当前农民在改革中不只是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而更需要树立一种新的文化心态”⑬。这种所谓的“新的文化心态”,其实正是对现代性的呼唤。而这种借助“新”与“旧”对比,注重“现代”与“传统”对峙的讲述方式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常见的叙事模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美好生活”的精神内核和叙事策略简单等同于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与分野,这一典型的现代性叙事,其中隐含着现代性常见的以单线性时间置换复杂性空间的逻辑,这种简单的“现代—传统”对峙观念,难免容易片面否认传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中“美好生活”的现代性叙事中,并没有为几千年的乡土传统留下合适的位置。
三、叙事伦理审视及其当下启示
纵观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中的“美好生活”叙事,固然与“中国梦”“大国梦”相关联,但对于普通小人物来说,“美好生活”想象仍与“吃”“穿”“住”“用”“行”等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紧密相关。从《喜盈门》(1981)、《二嫫》(1994)、《没事偷着乐》(1998)到《美丽的家》(2000)、《高兴》(2008)、《水煮金蟾》(2014)、《西虹市首富》(2018)、《李茶的姑妈》(2018)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无论是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还是电影中“美好生活”的叙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题材电影中的“美好生活”叙事更多是对辛勤劳作、对劳动致富的肯定,如《咱们的牛百岁》等;是对个人自身不懈努力的礼赞,如《野山》等;是对技能对知识的虔诚和敬重,如《人生》中,刘巧珍一直爱慕着高加林,尽管大字不识,“可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她在高加林最落魄的时候大胆向他表白,“你要是不嫌我,咱俩一块过,你在家里待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让你受苦的”;《黄山来的姑娘》中,龚玲玲在学得一手烹调技艺、练就一笔好字、讲得一口流利普通话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农村老家建设农村,而“回归农村”、期盼“消灭城乡差别”、“城里农村都一样”也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影片解决城乡冲突和矛盾的基本方式。除却农村题材电影,《快乐的单身汉》(1983)、《阿混新传》(1984)、《飞来的女婿》(1982)等对知识的推崇更为明显,反映了知识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和变革中的重要地位。
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生产”的主人公,新世纪以来电影小人物的“美好生活”叙事已经转变为“消费”的主人公。较为典型的是《西虹市首富》,穷困潦倒的王多鱼意外获得横财,必须在一个月内花光10个亿以获取巨额遗产,为此王多鱼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消费”奇观和想象。如果说,“有关现代化的想象是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个超级能指,其不言自明的合法性毋庸置疑。在这‘四个现代化’的想象中,并没有涉及消费,而主要与生产有关,这就决定了80年代大凡涉及现代化题旨的城市影像中,是生产而非消费,构成了城市的背景或前景。”⑭则当下电影的“美好生活”想象,更多是依靠消费来推动,通过消费来营造美好,《西虹市首富》借助一个月花光10个亿的想象,赤裸裸地呈现与强化了由肆意“消费”所带来的种种“美好生活”的想象。
迥异于改革开放初期小人物的致富故事,新世纪以来小人物的“美好生活”叙事中,小人物的逆袭更多是依赖“外力”,或获得意外之宝物,如《水煮金蟾》中,蛤蟆村村民田胜家分得一块没人愿意要的宅基地,却不想烂地里挖出宝物温泉;或如《西虹市首富》中王多鱼意外得到二爷的巨额遗产;或如《一出好戏》中,马进靠一张中头奖的六千万彩票赢得翻身的机会,改革开放初期所崇尚的知识改变命运、劳动改变人生等在当下电影的“美好生活”叙事中已不多见。《西虹市首富》通过塑造女主人公夏竹前男友、知识分子柳建南这一海归知识分子阿谀奉承的形象,对知识的作用、对知识分子的虚伪性做了无情调侃。《夏洛特烦恼》中,沉沦在底层的夏洛穿越回过去时空,通过贩卖/抄袭/翻唱经典歌曲大获成功,过上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羞羞的铁拳》中,艾迪生奔向成功与美好的捷径,是通过男女互换身体,颇有点无厘头的味道;《西虹市首富》更是直接借助天降财富,飞来横财来改变命运;《李茶的姑妈》中各路人马脑汁绞尽丑态百出,就是想凭借李茶那传说中贵为首富的寡妇姑妈莫妮卡摆脱窘况奔向美好。过多“意外”与“巧合”的设置,使得小人物的逆袭之路显得格外轻松,但却失去了生活的根基。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现实生活中,小人物单纯凭借一己之力,无论是劳动、技术还是知识,其通往“美好生活”之路仍障碍重重。此外,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题材电影倡导启蒙话语推崇现代性,对传统加以片面否定不同,新时期的小人物“美好生活”叙事,现代性的追求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消解,而回归传统伦理,回归家庭世俗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和颂扬,包括《人在囧途》、《泰囧》、《港囧》在内的影片,其“美好生活”叙事无不显示了回归传统伦理的诉求⑮。
【注释】
①党的十八大以来,“美好生活”一词在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中被多次提及,已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际上,“美好生活”作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想象和向往,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努力追求和实现的,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体现得尤为迫切。
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五四”后的第二次启蒙大潮中,中国电影中农民形象的建构,明显有别于左翼电影及“十七年”电影中鲜明的政治诉求,农民形象已经不再是作为昔日革命话语中的主体力量而出现。也就是说,随着社会文化语境日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时期电影中的农民形象塑造呈现出对革命意识形态的有意疏离,更多是在“现代化”的视域中展开“美好生活”想象与建构。
③影片《人生》获1985年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吴玉芳因饰演女主人公刘巧珍获1985年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影片《黄山来的姑娘》获1985年第5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剪辑、最佳女配角、最佳录音等多项提名,李羚因饰演女主人公龚玲玲获1985年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④第一层次为生理上的需要,包括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等,如果这些需要(除性以外)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人类个人的生理机能就无法正常运转;第二层次为安全上的需要,包括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等;第三层次为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包括友情、爱情、性亲密等;第四层次为尊重的需要,包括自我尊重、信心、成就、对他人尊重、被他人尊重,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等;第五层次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包括道德、创造力、自觉性、问题解决能力、公正度、接受现实能力、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其中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限度。
⑤通常认为,“服饰”分实物的、意象的和象征的三个层次。相关观点可参看冯鸣阳.从意象服饰到象征服饰[J].艺术设计研究,2015(2):44.
⑥关于火车的意象分析,可参看笔者的顾长卫电影诗性叙事的坚守与变奏[J].电影新作,2018(2).
⑦徐勇.20世纪80年代城市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和文化政治[J].当代电影,2014(4):73.
⑧李一鸣.在深层与表象之间徘徊:《野山》的一点遗憾[J].电影艺术,1986(5):41.
⑨对于“漱口”“刷牙”等细节的呈现是20世纪80年代文艺作品呈现农民向往现代性文明的一个重要叙事手段。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人生》中,同样设置了刘巧珍在高加林的影响下“刷牙”,而遭到村民起哄这一情节。
⑩仲呈祥、饶曙光.文化反思中的新时期电影创作[J].当代电影,1987(1):42-43.
⑪欧晨整理.《野山》探讨录——1985年故事片创作回顾座谈之一[J].电影艺术,1986(1):10.
⑫欧晨整理.《野山》探讨录——1985年故事片创作回顾座谈之一[J].电影艺术,1986(1):13.
⑬晓瑶.影片《乡民》座谈纪要[J].当代电影,1986(6):98.
⑭徐勇.20世纪80年代城市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和文化政治[J].当代电影,2014(4):73.
⑮相关观点可参考笔者的中国低成本喜剧电影的文化建设——以《泰囧》为例[J].中州学刊,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