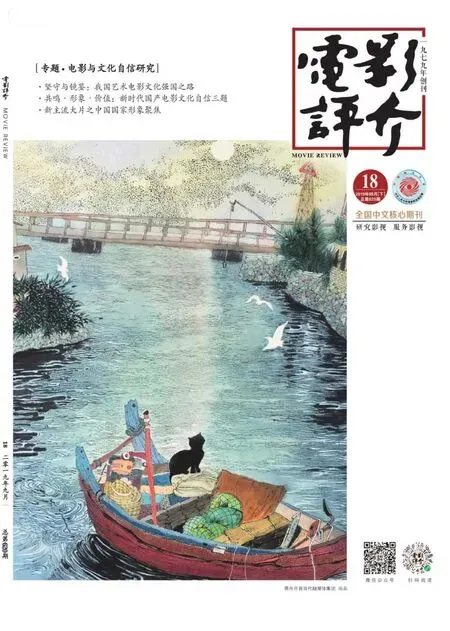由《何以为家》透视影像与现实之互文指涉
王 鹭 陈晓军
《何以为家》是由黎巴嫩导演娜丁·拉巴基执导,赞恩·阿尔·拉菲亚、约丹诺斯·希费罗联合主演的剧情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已于2019年4月在中国上映。影片以黎巴嫩男孩赞恩将父母告上法庭、对簿公堂为开头,以回忆和插叙的手法,讲述了他这一行为的前因后果,描绘出在难民潮的现状下个体的不幸际遇。故事中,赞恩的父母在无力抚养他们为数众多的孩子,无法给予他们教育和食物的情况下不断生育。将赞恩的妹妹萨哈以几只鸡的价格卖给小卖部的店主阿萨德,萨哈因难产而死,赞恩因为砍伤阿萨德被捕入狱。
影片以孩子为主角,旨在讨论难民潮中贫困家庭的父母缺乏养育的能力而对孩童造成的痛苦和创伤;剧情也是以男孩赞恩的视角来推进,但极少有童真的时刻流露。在整个家庭以及社会环境的强迫下,12岁的赞恩不得不成熟起来。影片所关注的是在成长过程中异化的孩童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一、关注视角:孩童的何去何从
对于孩童的关注向来是文艺作品的一大母题。在以儿童为描写对象的电影中,通常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向的叙事:其一是专注于表现孩童的天真、幼稚等等的特质,并以此表达出某种对于童年时代、童真的怀旧之感;其二便是聚焦于孩童的变化,多以旅程、经历的形式出现,在一系列的发展历程后,孩童通常会产生某种觉醒。当然,这两种叙事方向时常是相互纠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譬如在《佛罗里达乐园》中,孩子们的各种表现无不显露着一种童稚之趣,而影片结尾两个女孩的一同奔跑,又渗透出孩童对于世界的反抗。但在《何以为家》中,前一种叙事的倾向被压缩到接近于无。整部影片都在描述、表现一个孩童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以及他的认知与应对。
在《何以为家》中,赞恩从出场伊始就显得不像一个12岁的男孩。他成熟、清醒,对于他要面临的环境有一定的认知。这种认知在影片的后续发展中不断加深。影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可是说是赞恩的成长之路。而赞恩对于社会环境的认知加深的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察觉缺失亲人关爱、寻求关爱并尝试自己充当给予者、妥协并发出对根源的控诉。
首先,他知道商贩和房东托他带给妹妹萨哈零食是出于某种邪恶的目的。他直言,那里面有催化剂一样的东西,并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当萨哈的月事到来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不能让父母知晓这件事。因为他知道,如果父母知道萨哈的生理已成熟,可能会将她卖掉。他替萨哈清洗内衣,掩饰这一切,让妹妹对于这件事情守口如瓶。商贩来到赞恩的家里时,他拉走了萨哈,擦去她的口红,并谋划着带她逃离。但赞恩的所作所为并未能阻止妹妹萨哈的离去。赞恩的母亲并没有保护他的妹妹,反而充当了帮凶。于是赞恩离家出走了。他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中,父母无法充当他的依靠。在游乐场,赞恩掀开女人雕塑的衣物,露出它的乳房,象征着他对于母亲的渴望。他并没有真正得到过母亲的关怀。而后,赞恩遇见了拉希尔与约纳斯。在短暂的时日里,赞恩得到了他之前从未经受过的温情关怀。他们一起吃拉希尔偷拿回来的蛋糕,吹熄蜡烛,睡在拥挤的小窝。赞恩将一块玻璃摆在高处的窗子上。玻璃反射出隔壁放映的动画片。赞恩惟妙惟肖地配音,约纳斯高兴地笑了出来。但这一切转瞬即逝。赞恩被迫扮演起拉希尔的角色,提前成为了“父母”。此前,赞恩对抗着的是他的不作为的父母,此时,他直接面对着的是整个社会不公正的结构。为了存活下来,他思考如何领取救济物资的措辞。这是影片中赞恩不多的童真的流露。他想,我要说,约纳斯是我的弟弟。要是有人问起约纳斯的肤色为什么那么黑,他就回答,那是因为母亲怀他时,喝了太多的咖啡。赞恩尚没有关于种族、肤色的知识,他的想法幼稚天真,却更令旁观者心碎。赞恩拖着约纳斯游荡在大街小巷,卖所有能卖的东西,只为了换回一点食物,供他们二人生活。从此刻起,在冷酷的现实中,赞恩不需要母亲。他自己就是母亲,他决定要成为一个和自己的母亲迥然不同的抚养者。他不会抛弃约纳斯。
但现实的处境不允许他这样做。赞恩屈从于离开这里、过上体面的生活、能睡在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上的诱惑,将约纳斯交给了一个男人。经历过妹妹萨哈的离去的赞恩,不可能不明白交出约纳斯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如此做了。此时的赞恩已经隐约意识到,如他在影片结尾的那一番陈词,他知道母亲再次怀孕意味着又一个悲剧要降生,于是他打电话给电视台说出自己的故事,甚至把自己的父母告上了法庭。赞恩未能拯救自己的妹妹萨哈,因为他没有决定的权力;而当赞恩拥有抉择的机会时,他放弃了约纳斯,因为他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于是,赞恩不再渴求那些来自父母的关怀。因为他明白,自己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那还不如不曾降生。他发出了一个孩子最深刻的控诉。
依据此种方式,影片勾勒出一个孩子遭受异化的经历。异化最早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发扬光大,它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和社会分工固化导致人的个性无法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地得到发展。回到赞恩的身上,可以看见,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上的责任意识得到觉醒,从而清晰地认识到,对于孩子而言,悲剧的源头究竟在于何处。同时,影片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孩子注定遭受苦难,那他到底该不该降生,他该何去何从。
二、内在关注:个体的生存困境
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在于它足以引起读者、观众的共情,与之感同身受。共情是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所阐释的一个概念。它旨在描绘一个人是如何浸入他人内心,并以他人视角来看待事物和世界的过程。体现在受众观看阅读文艺作品的这个过程中,共情是受众理解作品的基础。
在《何以为家》中,最引起观众共情的时刻,便是赞恩在影片结尾对于父母的控诉。赞恩的母亲又一次怀孕了,而赞恩知道,这一个孩子不过是对于他和妹妹萨哈命运的重复:男孩是劳动力,他通过工作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女孩是商品,在到达一定年纪便卖给男人换取钱财。这种认知是赞恩将父母告上法庭的直接动因。
从古代开始,不停生育就是贫困家庭对于生活重负的唯一解法。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中这样描写那些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上,湄公河的炎热丛林中的女人们:每年的旱季开始怀孕,等十个月生下来,活着的背在篓子里,带到果园里去干活,死去的就埋在森林的土地里。孩子的尸体在雨季的潮湿中腐烂。不停地生,年复一年。劳动和生育伴随着太平洋的海潮在夜间冲击盐地的声响,贯穿她们的一生。
对于贫困的个体来说,生孩子并非只是出于生殖的本能问题。在不断的生育背后,潜藏着的是残酷的存亡问题。当个体的生存遭遇困境,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新生命的诞生。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在这个“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一个痛苦的人。影片中同样表达出了这种哲思,对于赞恩而言,个体的生存困境似乎无法可解。赞恩是父母行为的切实的承受者。作为一个孩子,他要遭受的是不符合体格的重负、过于提前的经验、教育的缺乏以及温饱的忧虑。童真还未降临就已流逝。假使赞恩一直生活在那个家庭中,那么在长大成人后,他大概也会重复父母的足迹,陷入父辈们的窘境——结婚、生育、不断生育。在成为约纳斯的抚养者之后,赞恩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无能为力。阶层的固化堵死了赞恩改变自身与他人的道路。阶级本身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地位相联系的,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富人自然会把持好自身的资源,为后代谋利,而穷人的孩子却根本不可能拥有富人孩子享受的种种教育和体验。就像在影片中,赞恩用尽方法维持他和约纳斯的生活,但他的身份还是从受害的“孩子”转变为施害的“父母”。赞恩在挣扎过后,无奈地将约纳斯交给了阿普斯,就像他的父母送走萨哈一般。而赞恩的心灵尚无法负担这些。因此,一种对于本源的控诉诞生了:如果不被生下来,这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
此外,在影片中,曾经数次出现过关于超级英雄的画面:游乐园的老人“蜘蛛侠”的扮像,赞恩身上带有美国队长盾牌图片的短袖衫。在这里,超级英雄并非仅仅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出现,它更代表着人们对于生活的反抗。这种表现手法,使得影片的现实意味更加浓厚。现实中没有超级英雄,当足以毁灭个人生活的厄运降临,人只能依靠自己的肉体凡胎来拯救自己和他人。但是赞恩不得不放弃了,因为他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阻力,那是远超他的能力范围的事情。于是,影片所想要描绘的,关于父母与孩子的困境便跃然而出:每个人都在奋斗,都在试图继续生存下去,但这些尝试却像螳臂挡车一般。在这种困境当中,赞恩父母的心灵已然麻木,赞恩似乎也在走上他们的老路。在每个人的面前,仿佛都有一堵看不见的墙阻拦了他们的去路。
三、情感诉求:赞恩流浪之因
作为一部难民题材的电影,《何以为家》并非仅聚焦于一个孩子的不幸遭遇。它的视野可以延伸到大环境中的种种。在电影艺术对于社会的各种议题的讨论中,通常存在着两种倾向,即环境中个人的困扰和结构性的公众议题。以本片为例,当一座城市只有赞恩一家出现了此种情况,那么人们可以说,这是由于赞恩父母自身能力、性格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政府部门需要对赞恩的家庭进行干涉,判断他的父母究竟有没有继续抚养孩童的能力;但当一座城市有数千个类似于赞恩这样的儿童时,那么对于个人的种种特质的考量则要退却一步了。批判者和意图解决问题的人们不能简单地说,你们应该抓住机遇,努力工作,送赞恩去上学,给孩子们体面的生活。因为能够产生机遇的空间已经解体覆灭了。人们的目光需要落在各种宏观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上,而不是专注于个体行为的种种考察。[2]《何以为家》最终的情感诉求便是探求赞恩的流浪之因,以求能够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不公的社会结构,关注难民,引起人们对于难民真实现状的关注和讨论。饰演赞恩的小演员本名是赞恩·阿尔·拉菲亚,他本来的身份便是叙利亚的一名难民。赞恩在难民营中被本片的选角导演发现,他在影片中“表演”的,也是他每日都要经历的真实世界。因而,影片与现实便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互文性。在观看《何以为家》的过程中,影片给人的感觉仿佛就是一种现实的重现,这大大加深了观众理解影片的深刻程度。观众往往倾向于将影片视作现实中发生的某一具体事物,而非虚构情节来看待,因为《何以为家》的主题与主演皆是真正的难民。这种现实与影片的互文对照彰显着创作者的表达意图,即在对某一个群体进行关注的同时,用艺术反馈现实,并试图寻求改变。
这一表达手法的好处,便是使更多的观众将自身代入进赞恩的角色。假如你是影片中的赞恩,你会怎么选择。命运如同高墙摆在面前,假如他没有离家出走,而是留下来上学读书,给家里减轻压力,或者等待其他时机去救出妹妹,也许能够改变些什么,过上相对更好的生活。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想要的并不是凑合着活在那堆烂泥地里,父母送走妹妹夺去了他的爱和尊严,他选择赌上自己的人生。即使入狱,赔上了自己的一切,他还是要控诉。他赢了吗?他的抗争战胜命运了吗?也许并没有,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现实过于残酷,并且没有遇到好的机会。但至少在命运面前,他做了自己,做出了跟随自己的选择。也许他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控诉,为了告诉更多的人这个世界的不公,他尝试了,他面对了命运,他留下了自己最想留下的痕迹。
而造成此种局面的直接原因便是“赞恩的父母们”。作为一部极度接近于真实的电影,《何以为家》对于父母刻画的笔墨可谓是可圈可点。在影片中,赞恩的母亲在法庭上流着眼泪,质问由本片导演所饰演的赞恩的律师:假如她来过这种生活,不到一天就会崩溃。她从没有得到去过一种体面生活的机会。等待她的只有无尽的劳动。她要为喂饱孩子不断工作。此时,影片对于赞恩父母的塑造立体起来,他们不再是扁平化的、只知道生而不懂得养的作恶者。而是同样生存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他们的行为模式是社会的畸形投射在个体身上的作用。正如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所描绘的,主角的母亲在殖民地上得到了一片无法耕种的土地。她起初以一种精力饱满的姿态来面对那块海水会漫上的“耕地”,但不断的跌落和摔倒,使她也有了将女儿出卖给有钱的若先生的想法。殖民地上来自宗主国的白人尚且如此,那些原住民们又如何呢?她们的儿子在学会走路与说话前,就学会了用手去摘下树上的果实。她们连拥有一片“除了香蕉,什么也没有”的土地的机会都没有。她们只能不断生育,来维系已经十分臃肿的家庭。这便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所致。
影片中所呈现的另一个母亲——拉希尔,只生下了一个孩子。她说自己是出于爱情,而她确实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但她的孩子照样沦落到喝劣质奶粉、居无定所的地步。这正是影片所想要表达的——底层阶级无法对自己的孩子负责,归根结底并非是他们个人的原因。当一个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难民、贫困人口,源头必然在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
因此,在《何以为家》中,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穷人们不断地生孩子,而是整个社会体制的问题——是战争产生了难民,而和平才是人们所需要的。影片以一种全人类共同体的高度与视角渴求着真正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的降临。在《何以为家》的结尾,男孩赞恩得到了一张去往欧洲的护照,现实中,男孩的扮演者一家引起了难民署的关注,被转移到瑞士。相比起他们的过往,这当然是一种较好的收尾方式。新的生活的转机出现了,能够产生机遇的结构再次浮现。影片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生活的向往,而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结语
《何以为家》真实地反映了黎巴嫩等地区的难民现象及底层阶级孩童的生活问题。社会环境就如同一把牢固的枷锁,困住了赞恩,也困住了赞恩的父母。影片在对赞恩父母、童婚者、人贩子的行为进行揭露的同时,直指这些都是不公正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恶果。就像赞恩的母亲在法庭上对律师所说的他们从未得到过机遇,从没有给孩子过上体面生活的机会。而对于父母个人行为的控诉,则由赞恩发出:如果无法抚养孩子,那为什么还要不停生育。在影片向我们展示的世界中,人并非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体。在时代的大潮下,个体的挣扎看起来往往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千千万万个人的共同努力,说不定就能使新世界真正的降临。就像影片导演拉巴基所说的那样:“我不想天真地说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如果它可以改变你看待这些孩子的态度、或是你看待你自己生活的态度,那么它至少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你。当千千万万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时,真正的改变才会开始发生。”这也正是影片《何以为家》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