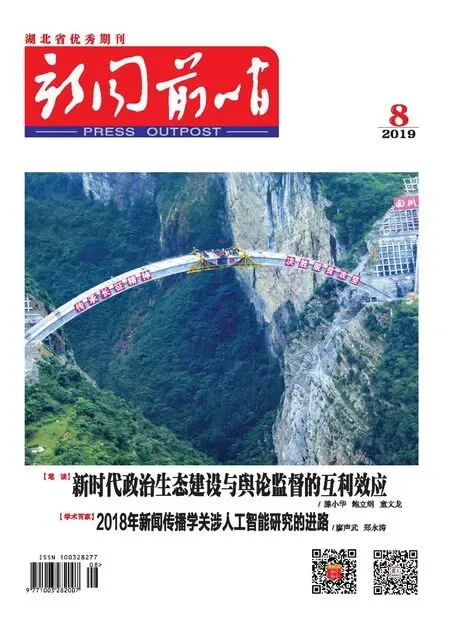侦探小说影像化的叙事技巧
◎陈昶洁
侦探片是电影史上较早出现的影片样式,它的起源与19世纪末欧美各国盛行的侦探小说有着密切关系,从而导致其后诞生了许多翻拍自侦探小说的经典电影。而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著名的英国推理小说家,和日本的松本清张、英国的柯南道尔一同被誉为推理文学的三大宗师。由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具有通俗性与大众化特点,使后来众多优秀推理小说家如江户川乱步、森村诚一、赤川次郎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小说风格的熏陶,影响了一代人的阅读兴趣。这种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使国际文坛称她为“罪案小说女王”。[1]而《东方快车谋杀案》作为其代表作,首创了侦探小说中的合作谋杀模式,至今仍然被各国导演多次翻拍,也引来后续许多文学家、导演、编剧的效仿。本文将以1974年经典版和2017年新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推理片段为例,对比其小说文本,按照时间、空间与视角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探究其影像化过程中叙事技巧的使用与变化。
一、时间的畸变:闪回与概述
电影的叙事时间不像文学中对时间的描写那样简洁,它的呈现需要更多的艺术技巧,其中时间的畸变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如热奈特所说:“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2]这种违背时间流逝顺序的叙述顺序被其称为逆时序,分为闪回、闪前与交错三种表现手法。
在小说文本中,由于《东方快车谋杀案》是集体谋杀,凶手不止一人,每个人的证词都难辨真假。因此在波洛侦探的推理过程中,就会频繁地涉及闪回的叙事手法,以拆穿凶手们的谎言并推翻之前的假设。小说中高频率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对时间次序的直观描写往往暗含在人物语言中。例如“昨晚12点37分...”“那是列车离开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天”“今天早晨发现雷切特先生被刺死时……”等。这也为导演翻拍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电影的翻拍过程中,1974年版本和2017年的版本正好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推理时间的方式,具体差异体现在闪回的次数、画面的布光以及闪回的手法上。前者完全遵照原版小说,将小说中涉及的局部闪回逐一且多次的呈现,甚至包括推理过程中涉及到的错误假设。而后者相对而言更为精简,只对真实发生过的犯罪过程予以画面形式的单次闪回,其他则以波洛的台词形式回溯,并否决了发生过的可能。阐述的时长,相较于前者也大大减少,将闪回着重于波洛对集体谋杀的推理猜想。在具体画面的表现手法上,老版本在闪回的过程中使用具有朦胧感、梦境感的柔光,并以蓝光为主色调,使画面内的色调发生明显的差异,体现时间的闪回。新版则直接换用黑白色调的画面,表现时间的过去式。而在闪回的手法上,老版本显然并不太注重叙事时间的连贯性,使用硬切的手法,将两段毫不相关的时间拼接在一起,由观众自行体会和理解闪回的时间点。新版则是以波洛的声音作为旁白,画面上虽然闪回的是犯罪过程,却能够被旁白连贯起来。简而言之,新版本对于叙事的重点和整体性有着更多的考量。
当然,以上两种设计叙事时间的手法,不能简单地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优劣之分,但无疑表现了导演在侦探小说影像化过程中对于时间安排的不同手法——突出事件重点或是描述事件全貌。这也依赖于编剧对整个故事内容的梳理及把握。在翻拍过程中,导演甚至可以通过针对某一段剧情的详述或省略,从而突出作品的个人风格。
二、空间的使用:叙事和写意
能够表现导演个人风格的除了叙事时间外,电影叙事空间作为艺术再造过程同样有着独特的个性与风貌。电影的叙事空间包括构成性空间与观念性空间。构成性空间,也叫再现性空间,可归属于电影画面构成的技术性范畴,也是电影叙事的语言;观念性空间则属于电影构成的艺术性范畴,它并不能在视觉上直观地看到,而是通过蒙太奇之类的艺术手法来呈现,存在于观众的想象中。[3]在侦探电影中,空间的表现主要用作对叙事内容的补充说明或是人物所处场景的交代。因此,导演对构成性空间的设计往往决定着影片叙事的范围与基调,而观念性空间往往辅助于人物塑造与情感的表达。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小说文本中,作者对于空间的描写涉及较少,一般以人物的行动在故事中简略带过。例如“列车员在门口徘徊”“所有的旅客都拥入餐车”“整个餐车异常安静甚至可以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等。作者对空间缺乏大篇幅或是具体描写,一方面为小说的影像化带来了困难,导演需要通过自己的构想,去还原作者心目中发生凶案的豪华列车。但另一方面,也为导演表现自己独创性和个人风格增加了表现机会。
在电影中,两个版本对于推理场景的构建有着截然不同的手法。在构成性空间的设计上,1974年版的电影更遵循小说原貌,尽可能还原列车上的餐车场景。例如华丽的装潢、高雅的餐具和精致的桌椅等;车窗外的场景,导演用水汽铺满整个车窗的遮挡方式,尽可能避免穿帮镜头,同时让叙述聚焦于狭窄的车内,营造压抑的氛围。在推理过程中,导演大篇幅地使用长镜头,镜头随着波洛的徘徊,扫荡整节封闭的车厢,利用推拉镜头改变景别的方式来完成画面中的主体转变。对于现在时的场景,导演则利用人物及其对话,完成长镜头的空间描写。
而在2017年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导演进行了大胆改编,将小说中餐车这个密闭空间转换到了火车外的一个隧道口,将推理这个环节替换为审讯。人物的分布不像原先簇拥在餐车中,而是安排所有嫌犯坐在火车隧道口临时搭建的简易木桌前,12个人的坐姿模仿意大利艺术家达芬奇的画作《最后的晚餐》。不难看出,导演试图用这种空间布局的方式,暗示12人的罪行,营造紧张的推理氛围。而对于镜头的使用,摄像师舍弃了原先长镜头的惯用手法,在人物的对话中频频使用正反打的镜头剪接,同时增加了细节的刻画,例如雪花、手枪、火焰等。由于嫌犯身处阴暗的隧道,光线昏暗,而波洛侦探站在敞亮的隧道外,背后还有打着车灯的火车头。对话镜头的剪接下,可以明显看出空间不同造成的布光差异,喻示正邪两方的对立冲突。特写镜头的加入,则是本片对观念性空间的重要描述手法之一。一方面以细节描写空间,如落在衣服上的雪花预示大雪封路;另一方面以细节表现人物情绪,如摇曳在隧道口的火焰,表现人物内心的波动。
在两个版本的电影中,观众看到了不同的推理场景:老版电影通过狭窄的空间完成了人物之间高频率对话,营造了紧张的氛围;新版电影则是利用明暗对比的空间构建对峙的场面,营造强烈的冲突氛围。
三、视角的转化:旁观到带入
导演对于空间的布置和机位的设置,其实潜在决定了整个故事的叙述视角。学者热奈特在托多罗夫提出的3种叙事学视角基础上,又更详细将其分为4种内视角和5种外视角。[4]而在侦探小说与电影中,创作者常常会利用叙述者、故事中的人物以及观众的信息不对称等情况来制造悬念。这种手法与视角的选择密切相关。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小说文本中,叙述视角一直是戏剧式视角。叙述视角像是剧院里的一位观众,客观地观察和记录人物的言行,例如“波洛站了起来”“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哈伯德太太点点头”等。对于推理的叙述呈现亦是如此,以第三者的旁观视角看待波洛侦探的推论。这一视角的叙述方式被延用至1974版电影中。在狭窄的餐车内,导演没有使用主观镜头,而是依靠长镜头使主角波洛和乘客们同框出现。包括对犯罪过程的闪回片段,都是以第三方观察的视角,回溯了整个谋杀计划的实施。
而在2017版的电影中,叙述视角却不再是单一的戏剧式视角。导演将小说中餐车上的推理改成了火车隧道前的审判,人物的位置关系由簇拥在一起变成了对立和对峙。因而在人物频繁的对话过程中,长镜头不得不换为正反打。这也就使故事由刚开始的戏剧式视角,随着推理进程逐渐转为了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镜头分别以波洛的视角和嫌犯们的视角来回切换。例如波洛观察嫌犯的微表情及其变化,被审讯的嫌犯仰望高高在上的波洛。这种由外而内的视角转换,在无形之间将观众进一步带入到故事中。
众所周知,电影不仅仅是视觉艺术,也是听觉的盛宴,声音在电影中常常也承担着叙事功能。为了能够使观众更为清晰地知晓犯罪的过程,在嫌犯忏悔,闪回谋杀过程的时候,新版电影以戏剧式的视角,客观回溯案情发生的原委。但又因为这一片段是来自嫌犯的自述,因而在整个嫌犯认罪的叙事阶段,既有旁观者视角又有人物视角,在视听上表现出视角混合的状态。这种手法也是当代侦探电影推理片段的惯用手法。
四、影像叙事变化的原因
对比两个版本《东方快车谋杀案》叙事的差异,老版相对而言更加尊重小说原著,新版则更具有导演自身的风格。究其原因,不单是技术的革新或叙事技巧的新探索,更是由于受到来自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共同影响。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小说创作于1934年,当时的英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低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电影业更是无法正常生产,多年得不到足够资金支持,陷入一蹶不振局面。[5]另一方面,受上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运动的影响,导演主张采用低成本制作,广泛使用能够表达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的长镜头、移动摄影、画外音、自然音响等。[6]受此影响,1974年该小说首次被翻拍为电影时,大段地使用长镜头,严格遵循原著的剧情和台词,也没有足够资金去进行棚摄,基本就是小说文本的视觉影像化,而不像新版电影那样在剧情上做出大胆改编,使用多元的视角和壮阔的场景空间。
用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该小说,作者表达了法律与人性的对抗。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将故事文本中的人物分为白、黑、非黑、非白四种类型。[7]在该作品中,白方即代表法律的波洛侦探,黑方是凶手,非黑方是协助调查的警察,非白方是背负许多人命的被害者。作者通过黑白两方的对抗,讨论了逃过法律制裁的恶人,应不应该被处以私刑,以及这种“替天行道”的行为要不要受到法律惩处。
为了使英国电影尽快复兴,从1956年开始,英国电影学会发起了一场“自由电影”运动。其思想观点大致可概括为:强调电影制作者的自由以及电影人应该成为当代社会的评论家。[8]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批判了当时法律的疏漏给人民带来的伤害。因而留下了开放式的结局:波洛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推理交给警方,让他们自己判断,而不是直接指出真凶,表达了作者对那些无法放下仇恨,但是心存善念的人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在新版的电影中,导演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凶手因内心愧疚选择自首,而没有让波洛说出那个开放式的两种推论。电影将叙述重点放在波洛的推理上,而不是现实主义潮流下对社会、法律的反思。
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翻拍的劣势在于不容易跳出既有框架,但这不代表翻拍就没有创新。只要翻拍者能在对经典的不断推敲和解读中读出时代的新意,不仅不用反感,甚至可以鼓励。”[9]在对比《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小说和电影叙事差异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既有时代的印记也有导演个人的风格。而排除这种审美的差异,其实更多的表现在叙事手法多元化的使用,以及传统类型电影的互相借鉴和相互融合。在2017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最后,导演布拉纳宣布对《尼罗河上的惨案》等阿加莎小说继续翻拍,意味着经典侦探小说的影像化潮流还将持续下去。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影视改编的潮流让故事尊重时代背景,做出了迎合新时代审美的改编,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也使文学作品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注释:
[1]曹正文:《米舒文存》(卷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
[2][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
[4]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刘立滨:《当代世界电影文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
[6]杨远婴:《多维视野:当代欧美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
[7]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8]王永收:《中外电影艺术史纲要》,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
[9]毛亚兰:《经典电影翻拍的时代性思考——对比分析1974和2017版〈东方快车谋杀案〉》,《文教资料》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