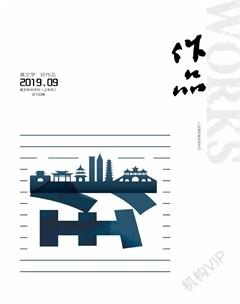苍天在上(散文)
贺颖
1
常常想,季节其实是有性别的,比方说除了冬天,其他三季应该都是女性,不同岁年不同韵味的女性。而冬天则是雄性的,而且必定是父亲,是盛年的父亲,是苍天大地间目光深邃,心魂深远,灵智深沉,银发闪亮高贵雍容的四季之王,神话中气度雄浑的英雄,是季节中阔远唯一的时间史诗。
一直庆幸自己偶然的生命,出生于灵魂无计贪恋复迷醉的冬季。
北方以北零下三十几度的隆冬,曾经的大雪封门,半米高的雪覆埋了的辽阔的北方大地,丰盈饱满又空无一物,唯有烈焰般的深寒。滴水成冰,冰河铁马,冷得雍容、彻底。
双亲的骨血诞育了我的性命,深寒锻造了我的魂魄,莽撞冥顽的童年一如冰原上的雪兽,爱着冷,冷中的寒风,风中的暴雪,暴雪中的万千世界。
成年后的自己,感知世界的视域似乎渐渐变得多维,一些变化在生命前行的历程中不可规避地发生着,而唯有对冬天的贪恋与迷醉如一,以至愈发挚炽深重。日久天长已然深知,自己灵魂的故乡,便就是冬天。于是四季轮转于自己而言,就成了每一个年份一场无奈与故乡话别的必经之长旅,年复一年。因为爱着冷,就爱着一切与此相关的人间。隆冬的大年,因此是生命经年最刻骨的记忆,已然成为自己精神基因中最为盛大的一部分,不独源于节日本身,而是因为这个节日所身处的隆冬最深处。雪打红灯,锣鼓喧天之后,每当大年的灯笼渐次撤下,仿佛渐渐后撤的冬天,正在与我挥别。哀伤与失落一日日铺天盖地,这每个年份必将历经一次的挥别,没有因不断重复而麻木,相反永远令我伤感惶然。每个冬春交替的时节,自己都有如被迫被季节带去远方的旅人,无奈、怅惘、不舍中目睹故乡渐远的背影,从而在即将到来的三个季节中,开始了对来年冬天漫长的遥望、期冀。
历经了春的微燥,夏的暴烈,秋的酷闷,当某个沉热的夜晚,秋风裹着一缕不易察觉的微凉忽然吹进窗口,巨大的欢喜每每令自己怦然惊悸,我知道,一年一度我的性命与灵魂,即将如约再次返乡。
当某个拂晓,眼前的天空忽然舒朗广大,熟悉的清冷有如某种异香蓦然撞进脑际,我会报以惊呼,报以奔跑,直到每根发丝每个毛孔都感受到,被熟悉的寒冷围裹的异美和战栗。就像孩子与父亲的久别重逢,委屈而喜悦,悲欣交集,禁不住低叹:这一年,如此漫长。
如许之岁年在流逝,岁岁如斯。
庆幸亦如斯,庆幸自己生于隆冬的深处,于自己而言神话般的节令。而这样的庆幸也一度令自己心生疑问,一直不曾想清楚,到底是源于生于此季,使得自己对冬天必定的刻骨之情,抑或是相反的么,皆因自己对冬天的迷醉太过强大,以至使得命运悲慈,令得自己得以生于斯时?一切无从得知。更无法得知的还有,一个人出生的季节,与这个人自此之后的精神轨迹与审美维度,究竟有着怎样神秘的内在渊源与必然的联系?答案如一难以为定。
无疑,这已然是个波及生命科学、哲学、宗教以至于神秘主义的巨大命题。
那一年,读加缪在《夏天集》中写道:在冬天我终于发现,我身体中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不由心下一惊遂脱口而出:在四季,我终于发现,我身体中有一个不可战胜的隆冬。
而隆冬至此,成为身魂恒久之故乡。
毕生最奢华之所愿,也因此便是对世界上所有冬天之奔赴。
二月末尾,京城已然繁花春早,绿意横陈,街巷一日一变。抬头花就开了,转身草就绿了,大太阳倾情直下,气温一度升至二十六七度。人们观花望景的欢呼中,我像冬天最后一个雪人儿,在早春恣意的阳光下,一日日变矮,变小。怕热的自己,在这个城市的早春中已开始汗意涔涔,不堪狼狈。早春的炽热引我惊遽,对刚刚远去的冬天愈加刻骨怀恋,梦境只剩下了一夜连着一夜的皑皑冷雪,以此告慰自己雪人儿般日渐消失的灵魂,那只即将消失的雪兽。是的我的灵魂,原是隆冬深处那只雪做的兽。
而这个早春慈悲,一次神异的契机引着天意而来,有如神话,以至我的隆冬去而复返,我的冰雪失而复得,我的雪兽起死回生。
2
雪原,雪野,雪山,雪峰,莽莽苍苍一路相伴而行。我面向车窗,用力呼吸久违的寒意,肺腑渐渐苏醒,随后一点点唤醒周身。身体中的雪兽在丰盈,欢腾,凛冽,低鸣,竟似乎如同历年的返乡一般无二。
冬天原是慢慢离开的,原来只要速度足够快,方向足够准确,居然可以如此重逢。
这里是青海。
有着青海蓝的苍天穹庐,神话遍布的大山河、古冰川,雪峰连绵,瑰丽洪荒。
西寧以西的高速路,并行的是青藏线的铁路。去往青海湖的路上。
满目之雪,无尽之雪,雪线上的三月,是隆重素朴而盛大的寒冬,仿佛世界所有的冬天,所有的雪花,在历经游历之后最终都悉数回返了这里。平原内陆出生成长,似这般雪山连绵从未有见过。惊异。更惊异的是惊异中怎会也有莫名之熟悉?是莫名,那么这熟悉便是雪兽与雪的几世渊源?与这山峦雪峰的几世渊源,与这神话遍地的青海山河大地之几世渊源吗?
雪峰连绵的起伏中映着大太阳刺目的金光,有如高原岿然磅礴的史诗,宏阔苍远;云层时而覆住雪峰后渐渐涌荡进山谷,整个山谷就被云朵充满,那么低,就如同刚刚自大地深处生长而出;刹那就又高悬升空而遮住阳光,雪峰大地就明明暗暗,如巨大舞台上恣意更迭的灯盏。这是不可想象的一种光的跌宕,苍天之下,大地之上,非是亲眼所目睹,无法将其传神表述。总之就像是神话。
据说浩浩雪原下覆埋着的,有些是昨年有意留存的青稞麦秸,这些麦秸,是春天羊群们的好草料,而麦秸中尚存的稞麦籽粒,则是刚刚产羔后的母亲的美食。
天生雨水阳光,地长万物,上苍已然如此慷慨悲慈,那人呢,必当更有心有情有义才是,于是有了这雪野下的美物美味,待高原早春的群羊来享用。
抬眼看,果然就有羊群在雪中觅食呵,是不少的一群羊,有母亲,应该还有小小蹒跚的羔羊。眼见小羊偶尔倾斜的小小身姿,却最终稳稳跟定的脚步,不由醒悟羊终究是高级于人类的,你看那么小的生命,便就可以在雪中自行觅食,相比而言,人类漫长的身体哺乳期与更为漫长的精神哺乳期,真真须得向雪野中的羊子默默致敬。
雪中稞麦的籽粒,一定是清冽而味美的,雪成了天然贮藏的最好保证,而且雪中觅食,原是连口渴也一并解决了的。
有些偶然,竟似比之刻意的必然更加妥帖。
时隐时现一条冰河,远远望过去,时宽时窄,时明时暗,蜿蜒曲折向前。这就是自东向西的倒淌河了。此刻这条发源于日月山西麓查汗草原的河流,正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于冬天绵长的怀抱中沉睡。那么它的梦呢,可曾会遇见一个远行而来的异乡人,正久久凝望于此?可曾感知有羊群正在它的岸边踽踽流连?好吧,如此匆匆而擦肩,这样对一条河梦境的揣测倒仿佛奢望了。
这些沉默的水,当它醒来,它将以区别于大多数河流自西向东的姿态,自东向西流入青海湖。显然这是倒淌河的流水之姿,更是她的名字之由来。
忽然忆起,我出生的辽河一段,竟也是罕见的自东向西而流,儿时冥顽,并不曾懂得河流的走向等这些专业的认知,只是因为好多外乡人纷纷来此河中放生祈愿,据说只有向西流的河,放生才灵验,于是使得大人们不断说起这条河的流向之特异,也让自己记住了这条人们口中不寻常的河。想来这许多年过去了,若非这条同样自东向西而流的倒淌河,已然忘却了这自东向西的意义。
在此地,据说这条倒淌河是文成公主思念家乡泪流而成。高原苍茫,回首不见长安,泪倾城却也不能再流往长安城,竟唯有倒淌而汇入青海湖。这便是宿命吗?如果是,那这不息的泪水便是命定如此的对众生的救赎吗?就如同我儿时家乡那条河,不也同样救赎着无数满怀期许的人心?难怪有人说:“……河流如同神秘的命运,主宰人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这神秘而神启的话,来自达·芬奇,这个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称为“世界上懂得东西最多的人。”这样来看,达·芬奇果然懂得多,他话语中的河流,想来也必定包括这眼前泪水聚成的倒淌河吧,因为这倒淌河的传说中,不正是深藏着他说的“主宰人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吗?对了,还有那不远处的日月山。
日月山上的雪,据说是刚刚下过的,大而厚而美。可以下车了,我以雪兽之姿跃然其上,清冽深冷,璀璨夺目,雪足以没过脚踝,我奔跑,惊呼而忘乎所以。不仅仅是因为眼见到了久违之雪的狂喜,而是忆起这样厚的大雪,竟也是多年不曾见到了。是要奔跑的,就如同雪兽于远年神话中返回阔别之雪原故乡。
日月山口的风很大,据说这里是青海东西部的分水岭,东部农区与西部牧区自此泾渭分明。那这些风呢,是为了令猎猎经幡不息之铭记?想起木心说,“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吹来的”,那么皑皑白雪覆盖的日月山山口的风呢?风从何方来,吹往何方去呢?可是来自翘首的长安城?或来自谁的前生?
好吧好吧,我这匆匆途经的路人,怎样问都像是随性胡想,也许只有当年泪倾城的文成公主,方能听懂风中的百般音律以及其间的万千肝肠。
3
青海湖,离天最近的水,我此行的心心念念之水。
这片真正广大的水域,据说它最初的名字,是叫作青海。只因后来成立省份,名字为青海省,故而将其称谓中加了一个湖字,易名为青海湖。
我未去考证,只面对这片无边无际之冰雪之时,我情愿是如此,情愿她的名字就是青海。青海,就是青色的海洋,对青蓝色的无边之水,与头顶的苍天之色一般无二。
这片青蓝色的海洋,据说每年十一月开始结冰,及至十二月中旬封冻,次年三月下旬开湖,四月而重现万顷水波。这众多时日之间,我独对结冰的日子深感悠长隽永,因为那是我出生的时日。
那么这无数无端莫名之熟悉,便是与此相关吗?出生于北方平原的隆冬大雪之中,对水自来便无端畏惧,而对冰雪则满怀宿命般的迷醉与贪恋。
这片青蓝色的海洋,每年纳入湖水中的河流有四十条之多。四十条?闭目冥想,数十条大小不一的河流,在四条大河布哈河、沙柳河、乌哈阿兰河和哈尔盖河的号角声中,以各自生命最嘹亮的身姿,义无反顾投身于这片高原之上深深的海洋。
何等壮阔瑰丽,何等撼人心魄?而这裹挟着义无反顾的精神力量,又是如何征服并洗礼着途经的一路长旅,并气贯长虹地与最终的归途浑然合一?只一想,便已荡气回肠如斯。
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这最终的归途,那么有没有可能也是它们曾经出发的地方?比方说这片广大的水域,每时每刻被大太阳炙烤而蒸腾的水汽,是否也汇入了这些河流诞生的源头,继而水汽化为水流,一路奔行再回返而来?若果然如此,真真天道循环之伏笔命定,无增无减之锦瑟流年。哦,对了,还有我,这冥冥之此行,已然仿佛在印证这神话之域的雪兽传说,不是吗?若万千年前的史前上古,当真有雪兽自在出没,那必定只有于此了,万山之宗众水之祖的大青海,华夏传说昆仑神话的母腹之地,雪兽必定于昆仑山中腾跃奔跑嘶鸣低叫,必定于青海湖岸饮雪弄冰好不恣肆欢腾。
好啊,必定就是如此,以至连同遥远地球彼岸的诗人,不也发现了这世间雷霆万钧的秘密了吗?听听T.S.艾略特说的:我们所有探寻的终结,将是来到我们的出发之地。
出发之地,远方的探寻,于此就多像是在说曾经的丝绸之路,驼铃阵阵,马蹄嗒嗒,及远及近而复又及远……
据说青海湖的南北两岸,曾是当年丝绸之路青海道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那么这于丝路文明中的要居重所,真真的是必定有过多样文明的交汇与激荡,有过精神之惊鸿与擦肩,即便匆匆,却必定终究是有过了的,必定这头顶的星空,曾经一同沐浴过这些遥远的异乡人,驼铃与马蹄,必定在同一片月光里沐临过夜露,继而才各奔东西……否则何以会有今天共同的秘密?
是的還有神话,在这华夏神话的腹地,必定有看不见的神灵,将这一切收录于神话的某一处,于是有了神话的前世今生,有了雪兽的神话故乡也未可知。
青蓝色的海洋,这片离天最近的水此刻仍在沉睡。
站在湖岸,已然尽是冰湖、雪湖,湖面目之所及皆为白雪皑皑无际,覆住广大的冰面,璀璨沉静,及至与苍天弥合浑然无分。极目远处,绵绵雪山,闪亮的雪线围绕着这一侧的视野。因为冷而人迹稀少,愈加使得这一刻平添庄严神秘,以至愈加空灵奇幻到失真。我在巨大的惊艳与惊悸中茫然四顾,果然,就是这里了,雪兽的故乡。这样的雪、冰,这样熟稔的冷,恍然而在的白。
终于知晓,这已然是我性命魂魄中,第一次身临的最奢华之冬天。
小心翼翼下到岸边的湖面,贴近岸边而不敢走远,非是担心冰面封冻不够彻底,而是不知自己这样走在冰面之上,睡梦中的湖水会不会被踩疼?身后这串串如雪兽般的足迹,会不会惊扰一个最广大的青蓝色的梦?
庆幸自己的忧虑是多余的。冬季漫长的青海湖,这片青色的海,依然在沉睡。
神异的是,若用心体会,会感受到脚下冰面在呼吸,是的,大雪覆埋着的冰面,在漫长的冬梦中正无声地呼吸。据说这场雪是前一天下的,愈加惊悸庆幸。我深知,雪是对隆冬最终极之加冕,那这场雪呢,是对一只浪迹归来的雪兽的欢迎礼吗?哦,若果然,却真真不敢当啊,未免太过盛大,太过隆重了。
这个刹那,我是决计要在雪湖上奔跑,跳跃,翻滚,鸣叫的,一而再再而三。我的雪兽早已如笼中困兽,远归故乡,无可阻挡。而事实上,我只默默坐在雪湖上,双手深入雪中,彻骨熟悉的冰寒令我狂喜几近巅峰,但我是克制的。
冰湖上刚刚下过的雪铺张而奢侈,没有任何人迹,漫漫远远直至与苍天浑然而合一。这样稀有的完整,本身便是一种不可触碰的惊心至美。这样的美显然超越了美的一般意义,已经蕴含着罕见的力量,无声中给予人隐秘的惊异、敬畏。安静,因为这场大雪,安静也有了颜色,原来有时候安静是白色的,就像有时是纯粹的蓝,有时是彻底的黑。
双手依旧在雪中,极致地感知着关于隆冬的神秘讯息,靠近掌心的雪开始隐隐融化,凉凉的沁入心神,指尖已然触摸到了冰面。是更销魂的一种冰凉,光滑,岩石般的坚定,此刻正透过十指,传递着这片青蓝色的沉睡之海深处,关于冬天的永恒的力量。
这样静静触摸便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仿佛一种神异的魔力,如此也许只有瓦格纳笔下的巨人安泰脚下的大地能与之媲美:欢乐是这样一种事物,它就像巨人安泰脚下的大地,只要他的脚步轻轻触碰,便给予他无穷的力量。善用音符的瓦格纳将这样的力量与欢乐紧密相连,但事实上,这样的力量何止是欢乐,而更接近庄严之洗礼。在一年中最后的冬天,在最长的冬天的长梦之间,在神话般的冰湖雪面之上,犹如浪迹的顽童回归父亲之怀,雪兽的隆冬去而复返,冰雪失而复得,性命起死回生。
记起有人说过冬天的青海湖之荒凉清冷,却不知是否有人知晓,这里深藏着最神秘深邃的冬天神话。冰雪盛大,醇酽杂糅,富足异美,又空灵奇幻。冬雪无声,以沉默覆埋起这片青蓝色的海之涛涛波涌,连深藏的神话也显得格外素朴而克制。
时至正午,起初远处仅有的几个人不知何时已悄然离开,此刻再无一人,靠近另一侧的湖岸,一艘轮渡仿佛静止的时间,正以一种肉眼可见的光阴样态,在冰湖之上默然矗立,与周围的雪峰遥相呼应。除了连天的冰雪还是冰雪,苍天之下,冰湖之间,空无一人。
巨大的安静,异美奢华得令人惊悸肃然,继而泫然泪奔。这仿佛是我诞于隆冬的生命,几十年来第一次目睹真正意义的冬天。
我的感恩与慌乱远远胜于惊悸与狂喜。
自然造物之神秘雄浑,彻底完成了对一个生命的洗礼。是的洗礼,我将手心里花掉的雪水,涂在额头,冰冰凉沁入脑际心神。想象着,如果冬天这位父亲,可以神话般幻化人身,必也會慈悲于我如斯,只缘于这遥远的数千里山河之奔赴。真的会吗?也许。
缓缓起身离开湖面向岸边走,身上脚上手上的雪舍不得碰掉,一丝丝兀自默默融化着,透进衣物正与自己身心交融。
我要记下这细微的分秒,细碎的光阴,以及自然对生命磅礴的洗礼,以及众多不偏不倚之侥幸,以及苍天之垂怜,以及神话对雪兽的慷慨回应。
欲离开之际,忽见几位年轻的阿卡,正从湖面的另一角走向湖心,藏红色的僧袍,在冰雪炽白的湖面之上,犹如朵朵盛开的绛色莲花缓缓游移,向着湖心处越走越远。
这情境忽而是引人恍惚的,海拔三千多米的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和咸水湖的冰面之上,几位年轻的阿卡,向湖心游移着的身影,于苍天之下传递着的,是无尽的安谧与巨大的静寂,仿佛他们此刻,是在完成着与神的邂逅。是的,不只是邂逅,应该更有如护佑,正如威尔士诗人牧师乔·赫伯特所说“在平静的水中,神会保佑我”,那么无独有偶,在这更为平静的冰湖的湖面,神必定亦会眷佑每个生灵,不是吗?我抬起头,头顶的苍天不同于周遭与湖面的相连的亮白,它是永恒的青蓝色,就像海,我确定这颜色必定就是这片青蓝色的海洋,醒来后的颜色。且它是温润的,不同于亮白的夺目刺眼,它是温润的,就像一种玉,一种源自昆仑山深处的玉。
是的,昆仑山,神灵遍地的万山之宗,那么此刻呢,在我目之所及的苍天之上,有多少神灵在俯瞰苍生,护佑天下生灵,与凡俗之你我同在?
4
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这里,更让人想起神灵,想起神话的远年,上古的万物与天上人间。大青海,昆仑神话的发源地,不,也许说诞生地更为恰切,昆仑神话,是中国传统神话永恒的母题。想起自幼听来的神话传说,数不清的神灵,各司其职,建构着一个苍天之上的神灵世界。
而在这里,直到今天,据说天一直就是至高无上的神,的确在中国传统神话中,天就是最高的神。就因此有了天神之说?仿佛有些道理。那么人呢,在遥远的远年,在人类的童年,在生命的史前与灵魂的上古,苍天之上是天神,那人呢,一定就是半神。
而这一切,《山海经》中已然早有铭证。
上古的《山海经》时代,人与天地万物交互而在,苍天之上是天神,而之下,则是无数神兽、灵兽、异兽,人自是其中之一。自在相合,诞育出那些灵兽,有人的部分、有神的部分、有兽的部分,相生相合而在,彼此难分,难以界定。想着倒是对极,可不就是吗,所谓今天对人的定义,及对内涵的界定,原本就是充满歧义与误读的落魄之举。因为那时的人,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那时的人,绝非今天人类认知意义上“人”的概念之内涵与外延,是今天的人类哪怕想象力也难以轻易抵达的——神及兽的一类。当然,也是生活在今天的人类想象力难以抵达的神秘之地。
这神秘之地,应该就是《山海经》中的山海之间。近年来,学界关于《山海经》的探索愈来愈成熟,众多研究结论皆有出处,令人耳目应接不暇。关于《山海经》中的山海,作为《山海经》的终极热爱者,更倾向于青海之论。如此这华夏秘籍之一的《山海经》之于青海,当真是渊源了得。曾在一文中读过,仅就《西次三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这三句而言便可认定,我们可以看出,“昆仑之丘”就是“昆仑之虚”,因为它们都是“帝之下都”。那若果然如此,巍巍昆仑无疑已然是《山海经》中的重要山之所指。而却不然,文中经过严谨之学术推理研究,得出更为惊人之结论:在《山海经》中的“昆仑”的东北、东南和西面分别存在着三片沙漠,而这些限定条件显然是今天的昆仑山所不具备的,因为今天的昆仑山只是在它的北面有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东北面有内蒙古的巴丹吉林、腾格里和毛乌素沙漠,而在它的西面和东南面却决无一片沙漠。那么因此,《山海经》中的“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决非今天的昆仑山而是另有所指。如此,《山海经》中的“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究竟是哪一座大山呢?翻开中国地形图不难发现,符合上述条件的大山只有一座,那就是位于我国甘肃和青海交界处的祁连山,因为在它的西面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它的东北有巴丹吉林沙漠,而在它的东南有腾格里沙漠。
《山海经》中的“昆仑”原来竟是今天的祁连山。作者随即以同样的严谨学理,推导出了这一结论:“祁连山”又是匈奴语“天山”的意思,《史记·匈奴列传》索隐曰:“祁连一名天山。”而“祁连”与“昆仑”古音正可通转(祁,脂部群纽;昆,文部见纽;见群同属牙音,脂文韵亦近。连,元部来纽;仑,文部来纽;元文韵近又同为来纽。“昆仑”亦应为“天”义)。
略显古奥晦涩之解,却清晰而惊人地表述着一个石破天惊之论。与其说事实如此,毋宁说是读到的人愿意相信更为精准。不是吗?就如我便是如此。再或者,与其说是我闻之极愿意相信这样的结论,毋宁说是这学术的论断,恰与我冥冥间的无端感应相契合一更为恰切。是的,我知道就是如此,未曾到来时便已认定,而今前来,所见所思所感,更毫无二致,关于山,海,上古与史前,神话与灵兽,人与半神。
《山海经》中记述了无数有翅膀可以自在于苍天飞翔之人,有鳍可以无拘潜游海洋之人,等等。而地球另一端已然神秘消失了的遥远的亚特兰蒂斯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海洋深处的国度?与希腊神话齐名的昆仑神话中,更加不乏如此仙异奇幻之人,而这样的人,是否就是最初的神之由来?
自古昆仑山就是华夏原先民天堂般的天上乐园,承载着古人最瑰丽奇谲的想象。上古西王母、黄帝、伏羲等中华始祖,以及后代流传而来的无数未解之谜,以及从天而来的黄河水,这一切无不始于昆仑神话对华夏大地的滋养。昆仑神话中最主要的主角之一就是西王母。相传西王母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掌管不死药、罚恶、预警灾厉的长生女神,居住在西方的昆仑山,是众女仙之首,主宰天地间之阴气,因而亦是育养万物的创世女神。
西王母的形象随着朝代的变迁,在不同文献中有着不同的模样:在《山海经》中,豹尾虎齿、披发戴盔、怒吼长啸;在《竹书纪年》中,西王母变成了一位雍容的女帝王。还有更多对西王母的描述,而事实上这一切正是殊途同归,因为作为创世之女神,自然无所不能之极,一切空间时间并不存在。天地万物尽在掌心足下,如此人与神竟已难分难辨。或者说,在上古并没有今天的“人类”,上古只有无数神灵,这些神灵在漫长的所谓进化史中,一些不幸渐渐失去神性与灵性,沦为今天之物化的“人类”,被所谓的时间驱撵,被所谓的空间囚桎,被所谓的疾病吞噬,被所谓的命运消耗,如一截廊下朽木、一片水中浮萍、一只笼中家雀、一牲待宰牛羊。不不,比作牛羊其实尚还不如呵,失去神性与灵性的人类,真真只如“物”而已,早已不记得曾经的“人类”便是上古的半神,是全然可以与天地万物诸神交流的半神。而今呢,每次地震之前,总有动物发出各种异兆,而所谓万物灵长的“人”呢,卻浑然不觉,直至千百年来灾难反复降临。
那么也或者人应该是犯了错的神仙,被贬谪至人间,并渐渐丧失神性,以至被物化从而沦为物,并如物一般“活着”或“消亡”,也未可知。
神性的退位与缺席,必然源于灵魂的悲情寂灭,以至由半神而沦为物化的生物体。今天之“人类”,不能不为之哀鸣。而幸好,并未全军覆没,幸好仍有不曾被收割的灵魂还在。庆幸呵。庆幸自己还有愿望回到史前的上古,寻找遗失的灵魂。世上只有一种东西,在我们对其倾注一切后会倾尽全力反哺于我们,那就是我们的灵魂,除此别无。
有时就想,这历经千万年进化浩劫而仍未曾灰飞烟灭的灵魂,是否就是远年的上古人类进化中渐渐隐去的翅膀?也就是说,那曾经上天入地下海的翅膀,并未所有人都悲情地退化消亡,而是劫后余生地有那么一小部分,更改了样貌隐身于人类的肉身?否则你看,灵魂引着人的肉身所行之事,不正是与曾经的翅膀一般无二吗?
原来这关乎灵魂的返魅与复古,在《山海经》的史前早有预设之答案,曾经作为半神的“人类”,曾经如何与天地神明交互而在,彼此息息相关。
5
我头顶的苍天,依旧是青蓝色的,像海。我确信,我是那万千年来劫后余生的一小部分中的微小一个,我确信这是罕见的一刻。遗憾的是,我凡俗的肉眼,仍不见有哪位神明于冰湖之上翩然而临。
可是,仅凭肉眼又如何能因此而断定,神灵并未降临?
记得电影《海上钢琴师》中一句经典之语:“我们肉眼看见的,远远不及灵魂所能看见的更为确凿与庞大。”是了是了,此刻我眼前的世界,这片青蓝色的广大水域,头顶这片天空之海,远处不绝绵延的雪峰,我数千里之迢迢奔赴,难道仅仅是源于一处地理意义上的所在?不不,当然不是,分明是循着灵魂之所感而来,循着灵魂之所见而思呢。否则何来这一番返魅复古的史前之旅,何来这苍天之上的神话之游?
今天,神话无疑堪称是文化的发祥地,更是文学永恒之母题,更仿佛整个人类共同的梦境,尤其当人类已然离神明愈来愈远的时候。而好在神明从没放弃人类,哪怕人类已然自己放弃了自己。否则人间何以会仍有神话,育养蕴藉人的灵魂心魄。那么此刻,皑皑无垠的冰湖之上,是否真的早有神明降临,在我迢迢奔赴的初始,并一直伴我这絮絮叨叨的隆冬一日?
这样想着,便似乎果然瞧得见冰湖之上仙影绰绰而动,身体中再次异动的雪兽让我知道,这自神话中降临的必是隆冬之神,那位司掌冬天的慷慨父神。
是这位父神,让自己想起美洲神话中庇护众生的“看不见的神”,想起欧洲神话中托尔与奥丁,以及古老的苏美尔神话中的吉尔伽美什,想起他面对乌鲁克城的城池之时所默默刻进灵魂的一句话:“一眼万年。”
一眼万年,一个人与神话的邂逅,雪兽与隆冬的重逢,眼前的隆冬哪一眼都配如此。
润朗明目的太阳光,青蓝色的海一样的苍天,淡淡隐隐的月影,这便是罕见的日月同辉吗?那近处的一个小小的月白亮点呢?竟是一颗小星子?那不就是日月星辰同现了?记得曾读过这样的句子,“日月金星同现苍穹,龙凤麒麟齐来世间”,那么这便是更为殊异的天象奇观了,如此神话之地,幸运之行,如此祥瑞之异兆,更幻炫如神话,令人惊异瞠目,静气屏息。
或者这本身就是神话也说不定吧?苍天在上,自己有幸因神话之感召而来,在神灵遍布的大地山河中历经心魂游历,遂以此行文,这一切不正是由始至终与神话之同频与全息?对了,必定便是这样了,正如博尔赫斯在一篇小说的结尾中提到:“文学的开端是神话,结局亦如此。”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