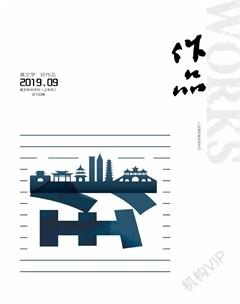在这个世界留下举足轻重的位置(随笔)
兰川
你最看重男人什么特性?
荣誉、可靠。
你最看重朋友什么?
我没朋友。
你最喜欢的女人是?
爱过我的女人。
最喜欢的作家是?
巴尔扎克。
你最大的缺点?
温柔。
你是生活中的英雄吗?
我不相信英雄这个概念。
你最欣赏什么政治改革?
废奴。
1983年,51岁的作家奈保尔在一份杂志的调查问卷中这样“揭露”自己。他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以《米格尔街》《大河湾》《印度三部曲》等作品闻名于世的大作家,同时还是与石黑一雄、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那个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会在同一年的私人笔记中写下这样的话:
51岁时我的真实情形如何?做了一辈子作家,因为职业所需而劳作,我依然像开始一样不满,一样(字迹不明),一样空虚,就像在伦敦那些日子,后来在牛津,牛津之后,后来又在伦敦。这么多开始,这么多热情,这么多随之而有的失望。几乎一样孤单。我现住在威尔特郡一所小房子里。我有足够的钱让自己过上几年……我有个妻子。过去11年,我有个情人,一个情妇。我们过着一种扭曲和支离破碎的三角生活。
这则笔记字里行间的情绪并不难捕捉,空虚、失望、孤单。显然,这位51岁的作家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而且他说了,“依然像开始一样不满”。开始如何呢?为何又落得如此境地?要揭开这个谜题,就非得沿着奈保尔的人生足迹走上一遍不可。
一、无根的漂泊者
特立尼达,奈保尔的出生地,一个他一生都要与之斩断关系的地方。对它不熟悉的人需要打开世界地图,找到墨西哥,绕过古巴和牙买加,找到大西洋上散布的一个名叫小安的列斯的群岛。还没有结束,继续向前,你会发现群岛末端有个较大的岛,这个岛就是特立尼达,它位于西南方向的那个触角伸向了委内瑞拉。
这是个鱼龙混杂的岛屿,岛上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委内瑞拉人,中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美洲印第安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凡是你能想到的,都不难在这里找到。
1834年,日不落帝国废除奴隶制之后,以前在英国控制下的印度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也丧失了来自宗主国的扶持。一部分印度人选择漂洋过海来到这个色彩缤纷的岛屿上做契约劳工。
1894年的圣诞节,一艘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船抵达特立尼达。船上有一个来自学者世家的印度人,属于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但他必须隐瞒这一身份,因为募工者需要的是靠出卖体力赚钱的劳工,而不是什么学者,更不是上层社会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
很快,这个隐瞒身份的印度人受雇于一位工头,开始了在特立尼达的生活。不久,他能读懂梵文的事情被人知道了,这让工头刮目相看,竟愿意把自己15岁的女儿许配给这个21岁的单身汉。再后来,这个印度人成了知名学者,为别人讲解宗教经文,主持礼拜,还带着信众到海边朝圣——大西洋成了恒河的替身。
这个印度人的故事出自奈保尔的父亲之口,据说是奈保尔家族一位祖先的故事。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是真的,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是个好故事——不仅解释了祖籍印度的奈保尔为何出生在了特立尼达,它的传奇色彩还让奈保尔铭记了一生。
距离那位印度祖先踏上特立尼达的土地一个多世纪以后,维迪亚达·苏拉吉帕拉萨德·奈保尔出生了。具体时间是1932年8月17日。
“维迪亚达”,这个名字不简单,意思是“智慧的施予者”,印度历史上的昌德拉国王就叫这个名字。多年以后,维·苏·奈保尔(即V.S.奈保尔)谈到自己的名字时,不无骄傲地说:“这个名字气度超凡,非常特别——我为了这个原因而珍视它。我觉得我要做大事。”
特立尼达不会知道,印度也不会知道,奈保尔致力一生的大事就是和它们划清界限,从世界的边缘地带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他的出发点是20世纪30年代的特立尼达,那时那地的印度人在别人眼中贫穷、吝啬、异端、好斗、排外、没教养。这,就是奈保尔落地的那个人世间。他不要在这里生根,而要迈开腿艰难跋涉。
12岁的时候,他就决定离开。他的底气来自令人称羡的学习成绩。按照当时的政策,只要学习成绩好,就有机会获得来自英国的奖学金和在英国求学的机会。为了得到这样的机会,奈保尔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不可大意,因为对手太多,而名额只有四个。他必须击败女王皇家学院其他成绩优异的同学,还要击败来自圣玛丽学院等各大名校的学生。
1949年3月,录取名单公布了,上面没有奈保尔的名字。就在奈保尔一家沮丧痛苦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奈保尔不是成绩不够好,而是他的试卷被误判了。教育局随即请求政府给奈保尔颁发一份特别奖学金,政府同意了。
在六年级的毕业派对上,奈保尔活泼极了,他在女孩子面前展现各种“才艺”,翻跟斗,讲笑话。他想立刻就踏上前往英国的旅程,但教育局认为他年纪太小,要等到1950年才能出发。
1950年转眼到了。他选择了牛津大学。这是他“成大事”的第一步,也是从“洞穴”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我离开他们所有人,轻快走向飞机,头也不回,只看着前面我的影子,在跑道上跳动的侏儒。
他在飞机上请一位空姐帮他削铅笔,“因为我要去当一个作家,我得开始。”
雀跃的节奏在飞机落地后没有持续多久,奈保尔发现黑色皮肤让他在英国成了一个太过明显的异类。数据显示,当时英国的外来移民只有2.5万人,奈保尔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与众不同不是什么好事,这让奈保尔自卑且自负。为了防御来自外部的攻击,他总要做那个先下手为强的人,他语言刻薄,不讨好任何人。大学的门房主管回忆说,“大学有很多印度人,都是很好的人,都是绅士,但奈保尔不是。他经常取笑人。”
也许就是在牛津求学期间,奈保尔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足轻重。逃离,成了他一生的主题;无根,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后来他和朋友聊天时讲道,“在英国我不是英国人,在印度我不是印度人。我被拴在1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那就是特立尼达,但我要逃避这一命运。”
做大事的人继续上路,艰难依旧伴随着他。
本科毕业后,奈保尔没有找到工作,因此决定继续在牛津读研。为了维持生计,他在一家农场做假期工,一周4英镑,工作时间相当长。他把那些和他一起打工的人叫作“笨蛋”,因为这些人宁可自己摇摇晃晃把一袋袋小麦从一个地方背到另一个地方,也不愿意接受奈保尔的建议——做一个滑槽,好让工作变得轻松。
智力上的优越并没有让奈保尔的日子更好过一些,反而在他最拿手的学业上也遭受了挫折。他本来打算读研,但却在一场口试中被拒绝了。这对他来说是个意外,他把这次失败归因于那位拒绝让他通过的老师对他怀有的种族情绪。丧失了牛津大学的保护,他的路更难走了。留下还是回去?这是个问题。
奈保尔给妈妈写信说:
要是必须在特立尼达度过余生,我想我会死。这个地方太小,价值观都是错的,人很狭隘。此外,对我来说在那儿真没什么可做……不要以为待在这个国家我很开心。这个国家的种族偏见很强烈,而我当然不想待在这里……既然即将离开牛津,我把所有英国朋友和熟人都抛开了。我要以努力忘掉我去过牛津来度过余生……这个世界颇为糟糕,但是我们将福星高照。
事实证明,信中奈保尔对特立尼达、英国和世界的看法没有问题,但“福星高照”的想法却过于乐观。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不仅接二连三地被拒绝,而且一共被拒绝了26次,这是生活给他的迎面暴击。贫困、痛苦,还有不时发作的哮喘病,几乎要了他的命。
最大的伤害还不是来自这里,最大的伤害发生在一次面试后,他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结果是被告知“走吧,别为自己难过了,回家去。你会找到事儿做的”。但奈保尔坚决不回特立尼达,因为那里没有他想要的生活:“40英里长40英里宽,没有前景,没有高山,远在天边。却苟延残喘,没有抱负,既不为人看到也不为人听到?”
终于,1954年12月,转机来了。奈保尔得到一份在BBC《加勒比之声》做广播节目的工作。这份工作再好不过,足以成为他当上作家的一个立足点。广播大厦对面就是古老的朗翰酒店,马克·吐温在这里住过,奥斯卡·王尔德在这里喝过酒,还有,夏洛克·福尔摩斯在这里探过案。除了阅读,这无疑是奈保尔离作家最近的一次。
有了较为稳定的工作后,奈保尔希望改变在朋友家寄居的局面。他四处找房,但很多房东因为他的肤色而拒绝将房屋出租给他。
艰难是一贯的,顺利只不过是人生的短暂插曲。这就是奈保尔的处境。不过,那颗“做大事”的心在某种程度上让他获得了拯救。他需要作品,需要享誉世界的作品。是的,他必须是一位作家,一位震驚全球的作家。作为作家,他不再无足轻重,而是稳稳地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一切,还要从他遥远的童年说起。
二、高贵的生活
“当作家的抱负是父亲给我的。”在父亲眼中,“用一双敏锐、幽默、仁慈的眼睛记录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带有自己的独创性,这就是高贵的生活。”
奈保尔的父亲一生中大部分时候是个记者,先后两次被他们所在的地方报刊——《特立尼达卫报》雇佣。但靠这点收入,不能确保一家人过上好的生活。
好在奈保尔的母亲有着强大的家族背景,能在奈保尔一家——父亲、母亲、五个孩子困难时伸以援手。甚至,他们举家搬入奈保尔外祖母名下的一座房子里。这栋房子在当地颇负盛名,具有印度北部的建筑风格。奈保尔这样描述它:
屋顶的阳台围有栏杆,主阳台的两端各装饰着一头凶猛的狮子雕像。我不喜欢,但也不痛恨住在那儿;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但我喜欢搬到西班牙港,搬到人少一点的房子里,我喜欢城市的快乐和风景:广场、花园、儿童游乐场、路灯港口的轮船。
这些幼年印象,为奈保尔日后创作《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积累了素材。
父亲在《特立尼达卫报》的文字工作让奈保尔有了与印刷文字相关的抱负。他觉得他被赋予了书写的感觉,甚至有某种特权。他看到父亲以各种笔名在报刊上写下精彩的故事——家族仇杀、乡村故事、选举激战……还有,还有一个奇怪的黑人隐士曾经富甲天下、寻欢作乐,而今只有一条狗陪他住在小屋。
这些惊险、奇幻的故事,无一不在奈保尔心中积淀下巨大的创作冲动。
他读父亲写的故事,他听父亲为他读大作家们写的故事——《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麦琪的礼物》《项链》《寻欢作乐》……
他喜欢上了一件家具,不是外祖母大房子里任意一件名贵家具,而是父亲从乡村带去的一张书柜式书桌。它笨重,沾有暗红色颜料,涂了清漆。三个书架上有玻璃门。“得知这是父亲的,因此也是我的,并开始喜欢上它。”
一个人小时候喜欢什么,往往对他日后的兴趣爱好、职业走向有所影响。因此,从小对父亲的书写、书桌十分喜爱的奈保尔,在十一岁时就萌生了当作家的想法,这并不稀奇。
我听说,书画收藏家们非常年轻就开始他们的收藏事业了。有一次在印度,著名电影导演山亚姆·班尼戈尔告诉我,他六岁就决定要当电影导演。
可惜他的整个家族不看好他在文学上的野心。
“他们会问我,”他回忆道,“‘你以后干吗?‘噢,我想我要试着写作。这就成了个笑话,对,笑话。”
他的父亲创作过小说,一部长篇和四五部短篇。让奈保尔记忆尤深的是,童年的他完全性地参与了父亲那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部小说缓慢的创作过程。每一篇新写出来的章节,每一处细小的改动,父亲都念给我听。随着故事的进展,我读了父亲创作的每一份新的打印稿。那是我童年时期最富有想象力的一次。我背下了整个故事,但仍然喜欢读它或者听父亲读它。在每一个熟悉的转折处,我都会有一种兴奋感,准备好了面对接下来多变的情绪。
这部长篇小说出版了。并未引起轰动。但这对奈保尔父子来说,足以兴奋。父子二人当作家的想法,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活。奈保尔在牛津读书期间,他与父亲的书信往来十之八九所谈的都关于写作。父亲鼓励他说:
不要害怕成为一名艺术家。
除了你自己,不要去讨好任何人。只须考虑你是否准确地表达出了你想表达的东西——不要卖弄;带着无条件的、勇敢的真诚——你会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因为你就是你自己……要发自内心地写作,而不是为了脸面。
奈保尔的父亲深受小说家欧·亨利、毛姆等人的影响。他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一系列写作技巧,并把这些技巧传授给儿子奈保尔。很自然,毛姆也成了奈保尔的偶像。
颇有戏剧性的是,在1959年,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获得了毛姆文学奖,毛姆很高兴把这一奖项授予一位非英国出身的作家,并亲自为自己的崇拜者颁了奖。这次获奖,最高兴的人恐怕是奈保尔的父亲。可惜他在1953年就病故了,年仅47岁。
这个奖项的获得,起源于模仿毛姆,得益于跳出毛姆。就在他留学英国疯狂模仿毛姆的时候,他的专业课教授,也就是著名的《霍比特人》和《魔戒》的作者托尔金,告诉他,“没有原创性的作家毫无前途,你这么搞有什么用呢?”
无论如何,他成名了。
五年之后,奈保尔完成了献给父亲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在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他发现他的派克钢笔的镀金笔尖有一侧被严重磨损。他把稿子放在碗柜里,踏上了前往意大利的旅途。但旅行并没有让他得到放松,因为他上路后才意识到,小说手稿没有任何副本,一旦碗柜里的这份遭遇不测,他将功亏一篑。
意大利之旅结束后,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碗柜,确认手稿完好无损。啊,如释重负。接下来是修改。改到手指生疼,纏上胶布,继续改。“最后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觉得我成了一名作家。”是的,直到这个时候,奈保尔才觉得自己成了作家,此前,用他的话说是,“我在假装自己是个作家”。
他坦言《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为他父亲作的传记。书中塑造了一个被强势丈母娘束缚的男人形象。他当过学者,做过小店主、监工、社会福利职员,还在《特立尼达卫报》当过记者。他一生都被自己身处的环境左右,寄人篱下,饱受殖民地社会诸多不利因素的限制。“他是个深沉的人。他一生创痛巨深, 决非外人所能道出。”
奈保尔相信这本书能够大卖,结果只卖了3200册。它的价值,直到多年后钦努阿·阿契贝出版了《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萨尔曼·拉什迪出版了《午夜之子》,才被真正意识到:原来奈保尔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一部开创性的后殖民文本。
完成这部小说时,奈保尔29岁。较之以前,此时他的名气更大了,成了一个名叫《书摊》的电视节目的常客。也是在这个时间前后,他有了召妓的习惯。一次,他在床上被一个妓女认了出来。
“你上过电视。”
“你怎么认得我的脸?”
“你的脸令人难忘。”
接下来的十年之间,奈保尔又有多部作品问世,有小说,有游记,《重访加勒比》《斯通和骑士伙伴》《幽暗国度》《守夜人记事簿》《模仿者》《失落的黄金国》《自由国度》《过分拥挤的奴隶市场》《游击队员》等。
就这样,奈保尔在自己40岁的时候,走上了属于自己的独家文学道路,找到了自己擅长驾驭的题材,那就是对黑暗殖民地面貌与人心的描述。紧接着,在世界范围内无以为家的奈保尔把世界当成了他细致观察的对象,什么也不遗漏。“我对我发现的世界没有责任。我记录我发现的东西。我没有观点。我想我只是列出素材、证据,让大家自己拿主意。”他发挥得游刃有余,但随着年纪增长,困境也随之而来。
在接下来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重复写这些东西。他非常担心自己会死于自我复制,他不得不面对黔驴技穷的危险。作家,是的,这就是奈保尔想要成为的人,必须成为的人,已经成为的人。可是,人不是想要做什么就能成什么,那个“必须”应由自己定义,“已经成为”也并不意味着一直是其所是。与奈保尔的抱负共存的,是维持抱负的焦虑。
即便周游世界,他还是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创作素材,每到一定时期,就灵感殆尽,对一个作家来讲,没什么比这更要命。另外一个致命问题是,他缺乏集中的主题。这还要归因于他在不同地方辗转,却无法获得一致的身份认同,他不能在一个主题下历经命运。他有的,是巨变和搬迁:
尽管作家的一半工作就是发现主题。对我来说,问题是我的生活改变了,充满巨变和搬迁:从乡下外祖母的印度教房子(依旧与乡村印度的宗教仪式和社会方式关系密切),到西班牙港及其街道上的黑人和美国大兵的生活,殖民地英语学校(皇家女王学院)秩序井然的生活,然后到牛津、伦敦和英国广播公司那间自由作家房间。我试着像个作家一样起步,但不知该聚焦哪里。
素材缺乏、主题涣散,足以使一个作家焦虑,足以让他结束创作生涯。他深知哪怕是一位伟大作家,其创造性也很难持续20年以上。缓解焦虑,接续创作生涯,其间发生了什么,具体策略如何,都不是外人所能知晓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从《米格尔街》《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大河湾》,到《抵达之谜》《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等,奈保尔的作品一步步展现出惊人的技巧。在内容上,所讲述的,都是有关人类文明和历史的重大问题。他没有死于自我复制,那些重复性的主题恰巧说明了一件事,奈保尔作为作家,完全成型了。他名正言顺地跨进当代文学大师之列,并成为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当之无愧的得主,实至名归。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是:
奈保尔的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人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虽然时刻焦虑,但奈保尔对自己越已成型的作品却始终怀有极大自信。1988年5月,他给一位编辑发去传真,目的仅有一个,要求编辑保留稿件中某个至关重要的分号:
我34年写了20本书,我知道怎样写作,并不希望标点符号让文字编辑帮忙……我不希望任何人删掉我的分号,连带它们不同程度的停顿;或者干涉我的“而且”,连带它们不同方式的联系……英语的荣光在于没有这些宫廷规则:它是书写它的人创造的一门语言。我的名字印在我的书上。我对词语怎样组合负责。这就是我为什么成为一名作家的一个原因。
三、世界如其所是
“感谢妓女!”
据说这是奈保尔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面对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
感谢妓女,奈保尔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她们能给他安慰,又不妨碍他追求文学。
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我完全没有兴趣,根本就无所谓,因为我是为这个叫文学的东西服务的。
不难看出,奈保尔对妓女的感谢只停留在她们对自己有用上。即便是那些和他一样跻身文坛的女性也不能得到他的认可。理由是,女性天生“多愁善感,世界观狭隘……就像女性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家之主一样,她们也不可能主导写作这门艺术”。
在奈保尔的传记《世事如斯》中,他自私、嫖妓、折磨妻子、奴役情妇,甚至,无所顾忌地透露自己迷恋性虐游戏的怪癖,还曾把情妇打得鼻青眼肿,导致她无法出门。他亲口承认是自己的婚外情和嫖妓毁掉了妻子的生活——“可以说,是我害死了她。”
奈保尔这些“非同寻常”的举动,也绝非天性使然。早年的一些经历对他日后的行为造成了很大影响。他曾经和第一任妻子倾诉过影响了他一生的两件事。
1941年左右,9岁的奈保尔和家人住在乡下的小屋。热带地区,入夜之后天黑得很快。奈保尔望着窗外,瞬间觉得全家都迷失而绝望,哭了起来。接着,他看到母亲少女时代的一些东西,感觉她一生徒劳而荒废,更加深了他的无助感。
还有一次,他和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去海边,哥哥妹妹落水,淹死了。当地渔民本可以救他们,但渔民更关心能从中得到多少报酬。人死后,渔民才用渔网把尸体捞上来,还捉了很多鲶鱼。这一年,奈保尔12岁。
可以想象这两件事在奈保尔心里留下的深刻印记,也可以想象这对他后来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多大影响。面对黑暗时的无所适从感,伴随了他一生。也许只有在女性那里,他才能得到片刻安宁。他需要她们,但他又不那么尊重她们。
在牛津求学期间,具体时间是1952年,他在学院的戏剧演出中认识了一个叫帕特的女孩。帕特跟他一样,家境贫寒,但智力超群,靠奖学金在牛津读书。他们相遇时,奈保尔正处在人生低谷期,甚至极度抑郁,不时有自杀的想法闪过脑际。帕特的出现对他是个安慰。他们在文学上趣味相投,关系很快变得亲密。在奈保尔无法继续学业又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帕特给了他最切实的经济援助。但帕特的父母对自己的女儿与一个异族交往并可能与之结婚的事情表示不满。为了让父母放弃管教,帕特从家里搬出来,获得了和奈保尔交往的更大自由。
1955年1月10日,新郎维·苏·奈保尔,新娘帕西特娅·安·赫尔,在双方父母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结婚了。这一年,两人都22岁。意味深长的是,奈保尔竟然没有为新娘准备结婚戒指,后来帕特自己给自己买了一枚样式简单的金戒指,虽然很少戴。
帕特在奈保尔生命中的角色可以这样形容:生活上的照顾者、事业上的助手、精神上的伴侣,但在肉体上所能提供的愉悦却有限。奈保尔对帕特更多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依恋,他几乎在结婚前后就在脑中有了和另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想法。阻挡他如此行事的,除了贫穷以外,就是害羞腼腆没经验。
1958年,想法变成了实际行动,他开始嫖妓,而且是经常。但到了30岁之后,他开始觉得跟妓女做爱没什么劲,他觉得自己被骗了,并且不满足。嫖妓的事情,帕特是后来才知道的,透过《纽约客》对奈保尔的采访报道。当时的帕特已经年老,且身患癌症。读完报道后,帕特的眼泪流了下来。她没想到奈保尔那么早就有了别的女人,更没想到他在有一个情妇之外还有过那么多女人。
奈保尔确实有一个情妇,名叫玛格丽特。他们相遇在1972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奈保尔说自己一看到玛格丽特的时候就想拥有她。虽然那时她已经30岁,而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玛格丽特活泼、迷人,他们在性方面的怪癖一拍即合,奈保尔甚至去珠宝店给玛格丽特买了一枚戒指。
帕特是智力的陪伴,玛格丽特是肉欲的满足。奈保尔知道玛格丽特很愚蠢,但他无法拒绝她给他带来的身体上的享受。这一关系持续了十几年,其间,玛格丽特为他怀孕三次,都选择了堕胎。她完全被奈保尔操控,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奈保尔从她身上得到的除了肉欲的满足,还有一些是突然迸发的创作灵感。他开始对性描写有了新的创见,在《游击队员》这本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玛格丽特的存在很快被帕特得知了,两个女人没有过正面交涉,她们唯一的联系就是这个叫奈保尔的男人。玛格丽特因为不时怀疑自己只是奈保尔“床上的女人”而多次有过离开的打算,但最终还是无法抗拒奈保尔对她构成的吸引力。直到帕特死去,直到奈保尔第二任夫人的出现。
没错,第二任奈保尔夫人不是玛格丽特,而是另有其人。
1995年,63岁的奈保尔认识了一位42岁的新闻记者,笔名“纳迪娜”。她给人的印象是强势、活跃、大方、感性,还有一点放肆。在她42年的人生履历中,有不少困难,作为女人,她坚强地生活,像个男人一样。听完纳迪娜自述身世,奈保尔被她的脆弱和勇敢吸引住了。
“你要不要考虑有一天成为奈保尔夫人?”
求婚来得很快,回应也很快。
第一任奈保尔夫人帕特火葬后的第二天,奈保尔就和他的下一任走到了一起。他说自己坠入了情网,并为情网中的另一半买了一枚戒指,上面镶有两粒钻石和一块青金石。
我们很难用一句论断来说明奈保尔对女性的态度,但有一个故事或许能提供帮助——当别人让他解释印度女人前额上那个圆点的象征意义时,他脱口而出:“这个圆点表示:我的脑袋是空的。”
2018年8月11日,维·苏·奈保尔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证实,维·苏·奈保尔已于伦敦家中去世,享年85岁。
不敢想象一个没有奈保尔的世界将会损失多少精神财富。他的作品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是那样独一无二,无可取代,即便这同时意味着,读懂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书,是超越读者头脑的书,读罢,让人为之一新。当然,还是那句话,这同时意味着,读懂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深知自己的作品不容易读懂,但他从不对读者迁就。在他的书中,地名尤其多。并非他有意设障,他首先是这些障碍的受害者。读者遭受的仅仅是阅读障碍,他所遭受的,却是活生生的生活障碍。每一个地名,都对他的身份认同造成困扰。
他出生在印度移民家庭,但他的印度不是那个因为民主独立运动而声名远播的印度,而是有着多层苦难、巨大人口压力的印度。他留学的地方是英国牛津大学,但不是开放包容、思想自由的牛津,而是那个让他对自己身份认同感到茫然无措的牛津。
作为一个印度人,他无法平衡英国和印度之间殖民与被殖民、统治与臣服的复杂关系。无论印度还是英国,都让他无所适从。可悲的是,他必须面对地名与地名之间的巨大落差,也自觉不自觉地将各种地名的切换放置在自己的作品中。
他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他为写作而生,他才华横溢,他繁荣了世界文学,成了当代作家中人们不得不提的一个人。与此同时,他饱受争议,生活充满悖论,语言犀利,总能毫不留情地一语道破天机,不惜当一个令人生厌的话题终结者。
他就是真实地活。《卫报》曾对他如是评价:
作为一名叙述者,V.S.奈保尔不随和,不完美,也不怎么在乎有没有人喜欢他。但他也是最诚实的,从不伪装。
他对世界眉头紧皱,冷眼旁观。冷酷犀利的言语是对人世间种种荒唐与罪恶的仇视,更是对黑暗世界的控诉。看似无情的他,对世界其实有着温柔与宽仁的心。
他说:
我想,我们内心有一种渐渐累积的良心,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我们的确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偷盜、通奸、不忠、杀死你的一个同胞或族人、撒谎和不诚实。陈腐的美德对所有种族都一样,对违反良俗的监视所有种族也一样。不要觉得我想改革人类,我是个旁观者,超级游民。我不受解放之火的影响。我想创造自己,产生我自己的哲学,它会带给我安慰。我想看好的与坏的。
或许在这个无情而不讲宽恕的世界,他只能做个孤军奋战的孤胆英雄,因为他坚信他在《大河湾》首行写下的人生信条——
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