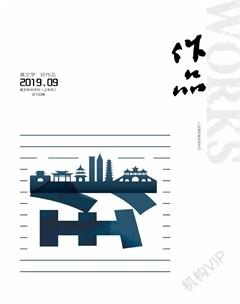我的一生在我之外
姚钰婷 杨虹晖 熊育群
姚钰婷 杨虹晖(以下简称姚): 我了解到您曾担任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工程师、羊城晚报高级编辑等职位,现在担任广东文学院院长,从事文学创作。我觉得您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经历很丰富,想知道您从建筑设计到编辑再到文学之间的转变契机是什么?
熊育群(以下简称熊): 我觉得更多的是本性。我7岁时第一次花钱,就拿它买了小人书。初中的时候,我旷课十来天,躲在家里写侦探小说,自己画封面和插图,装订成手抄本。小说在同学间传阅,很受欢迎。少年时,我喜欢讲故事,听故事的人围着我,讲累了,我就要他们抬着我走。我画画,学过素描、水彩,做过画家梦,声乐还学过美声。就是没想过做建筑师。那时候高考理工科吃香,不太重视文科。我在屈原农场高考,以第一名的成绩填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并没有报同济。没想到录的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
上海离我的家乡湖南岳阳很遥远,环境大不相同。那时我刚满17岁,特别想家。春天来了,上海的春天跟我家乡的春天是一模一样的。那种乍暖还寒,盎然的春意,勾起我的记忆和乡愁,冲动之下我写起了诗。学校团委正在组织“五四”征文比赛,我投稿得了个三等奖,奖了一个小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我还留着,它对我的鼓舞很大。从此我就疯狂地迷上了写诗,一写就是10年。
搞建筑设计的去写诗有点离经叛道,有人说我不务正业。那时建筑设计论资排辈,个人的构想无法实现,我不愿把生命耗费在画设计图上,那是机械劳动,虽然收入很高,但我这个人对钱没有多强的欲望,于是,调去一家报纸编副刊。羊城晚报引进人才又将我从湖南调到了广东。新闻也非我所愿,一干却是20年,直到我想写长篇小说,报社没有创作的时间,广东作协引进人才又将我调到了文学院。
姚: 您在文章中曾说过现代社会人被科技裹挟着往前走、市场经济调动人性的贪婪。这种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
熊: 这个问题很大。我对人类的前景感到悲观。譬如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被人掌握甚至控制。我们的生活也被科技改写、规定,个人正在失去生活的主动性,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小。人类正失去私密空间、失去隐私。隐私与自由几乎等同于生命,是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不只是温饱,人的尊严、主体性、自主性、个人的意愿,都是不容侵犯的。失去这一切,人的价值就失去了,形同囚徒和行尸走肉。
在高科技面前人太渺小了,甚至显得多余,有着深深的挫败感。一个生物体的能力是有限的,而科技没有极限。人的主体性在丧失之中,绝大多数人会活得毫无价值,甚至可能被圈养。人类的未来不一定会由人类自己控制,或者被一些偶然事件,一批又一批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极端少数人所左右,他們凭借自己的本能与所能行动,不知道责任也无法负责。人类坐上了一辆高速并正在不断加速的列车,却不知驶向何方。这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来心生恐惧的根本缘由,因为我们失去了未来的确定性,也就是说,失去了对未来的把握。人类外在的能力在以几何级数增长,快接近把胡思乱想变为现实的程度了,而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并没有改观甚至更甚,对权力的欲望也没有改变,这就是可怕之处。
我们只看到科技对人类带来的便利与好处,漠视甚至忘记它带来的破坏性。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恰恰与两次工业革命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科技进步带来了人类的大灾难。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只有益处而没有坏处的事物,从来都是利害平衡的。目前,国家主义在强化,导致竞争加剧,更加促使了科技主义甚嚣尘上,地球几成丛林社会。
这个社会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就要确立规则,做到有序发展。
姚: 在您的散文中多次出现“流浪”这个词,如在《灵地西藏》:“流浪,对于人生来说,时时能让你保持一份对生命的清醒意识,不会被俗世的生活蒙蔽了眼睛”,真实细腻地表现了一种浪迹天涯的情怀。从您的经历中看得出来您也是“不安分”的人,是什么促使您踏上了一次次奇妙的“流浪之旅”?
熊: 这其实也是本能,是人的生命意识。“流浪”是生命的本质。我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我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世界在你面前不断地打开……你走了多远,你的世界就有多大。另外,深刻体认到了个体生命的限度,人生短暂,只有几十年。虽然人生的时间没法延长,但我的体验可以丰富,这样就相当于经历了好几个人生,个体的生命也相当于延长了。
流浪不是生活中通常意义的流浪,是在人生与生命层级上来说的。生命就是一次大流浪。为什么用“流浪”而不说“旅行”?“旅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流浪”是我在大地上的一种漫游。即便旅行,我一般也不愿意看资料与介绍,喜欢保持旅程的陌生感、神秘感。
我的写作也拒绝计划性的东西,信马由缰。动笔写的时候,会写成什么样子,我只有朦胧的意识,只是感觉,后面能写什么我并不完全知道,要是全清楚了,创造的快乐就失去了。它就像一团光,我只是朝那个方向走过去。
有的人说我写的是“历史散文”“大散文”,我既接受又不接受。接受是因为我写的散文以这一类型题材居多。写散文要有深邃的眼光,看到深厚的时间。深厚的时间就是历史文化。一个作家写现实生活若没有历史的眼光,对历史把握不好,那他对现实的认识也不会深刻。我的历史文化散文跟其他人不同,我是从现实里遭遇到的。譬如我写迁徙,根本无从计划,都是偶然遭遇上的,事情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是从过去一直延伸到了今天。写过一些迁徙的散文,这些年我才有意识地关心个体生命的迁徙。今年将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迁徙的散文集《一寄河山——大地上的迁徙》,正是一个个个体的迁徙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迁徙。
姚: 刚才您多次提到“生命”这个词,从您的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您觉得生命最重要的内核是什么?
熊: 生命最重要的方式是死与生,是成长与衰老,这既是形式也是内容。生命的内核是生命意识,而它的底色就是如何面对死亡。生死造就了生命的实在与虚幻,造就了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贱、好与恶等精神现象,一切意义都与生死相关。从生物角度来讲,生命是一个精密的系统。但生命又不是物理的生理的,她还有更捉摸不透的东西,意识、灵魂、精神、情感、意志……它们虽看不到,却在你的身体里。生命还有广阔的社会内涵,跟现实、经历、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
你说这些有没有进入内核?好像还没有。如果要进入生命的内核,可能要从宗教上来找,例如世界是怎样创造的,当然包含生命是怎样创造的,于是指向上帝。如果从人的生命意义来讲,我觉得个人的价值应该从人类来找。为什么人老了会喜欢寻根问祖?因为他在人的传宗接代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单个的东西很容易消失,但从“类”的层面来讲,它的意义就得到了保证。个体的基因、生命密码能够传承给下一代,文化能夠积累,所发生的事情成为历史,那意义就呈现了。
能够传承的叫文化,不能够传承就不能叫文化。物质不能传承意义,而文化能够。意义应该在历史的时间中寻找,离开了时间,意义就不存在。我们今天的人如果能创造繁荣的文化,就会对后人有意义。我们怀念唐代,不会怀念唐代的物质,物质只对他们自己身体的享乐有意义,对民族有益对历史有益的是唐代的文化。我们欣赏唐代诗歌,知道李白、杜甫、白居易。唐代的伟大在于它的精神气象,在于它的精神与境界。我们矢志以求的就是精神有所寄托,超越生命,活出意义。注重物质的人看不到生命的意义,也认识不到文化、文学的意义。
姚: 在您的文章中曾经说到过“《连尔居》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天马行空的魔幻作品来读”,“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我并非不能虚构,而是不敢也不想虚构。我要在这里重现他们所经历所看到所制造的灾难现场”。请问在创作中您是如何实现这种纪实和魔幻、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平衡?
熊: 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魔幻。看不到生活中的魔幻不是一个好作家。我来自洞庭湖,那里有浓厚的楚文化。楚文化应先是巫鬼文化。屈原是我们的源头,他天马行空的瑰丽精神气象,就是把魔幻当现实来写,或者说把现实与魔幻混淆。这是他浓郁的浪漫情怀的体现。这里面当然也有很深的地域文化色彩。《招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继承了民间的艺术。在民间,敬鬼神是很魔幻的,也是很现实的生活。人死了本身就是一件很魔幻的事。
不能不说生命是神奇的、神秘的。我曾有过一些奇特的体验。我一个人爬珠峰的时候,遇到过雪崩、塌方。当我陷入绝境时,我看见了珠峰上面漫山遍野都是人。身为一个现代人,我知道这是幻觉。但我睁眼闭眼反复三次,仍然看到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穿藏袍,站在石头后面朝我默默凝望。
我在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时,遇到了大塌方,我们只能拼命往山上爬。山上没有路,为了逃命,数千米高的喜马拉雅山脉,我又爬上了一座山顶。又饿又累,几近虚脱。我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这时候,突然听到了狗叫声。居然门巴族人居住在山顶!居然看见一个人在寨口的石头上向我招手。他是我们的向导。这个门巴族向导在大塌方前因为劳累拒绝同行,要在峡谷里的帐篷休息一晚,现在却突然出现在山顶的寨子里。西藏之行,这种大难不死的情况太多了,以至于我认为自己是死不了的人,感觉有神灵护佑。回来后我就写了《西藏的感动》,全是亲身经历。
我的细节为什么不虚构?像《己卯年雨雪》这种民族大灾难的题材,日本兵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需要真实,不能瞎编,否则授人以口实,失去了力量。在这里,真实才有力量。但人物和情节是可以虚构的。
姚: 我们知道您在创作《己卯年雨雪》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田野调查,力求将更真实的细节呈现出来。之前您也提到我们中国强调现实主义,但对现实的理解又比较肤浅,在您心里,什么是好的现实主义小说?
熊: 小说虽然是虚构的艺术,但却一个细节也不能失真,生活的逻辑一条也不能乱。真善美,真是基础性的。凡严肃对待小说创作的人,必然要深入生活。对待真实的历史,便是田野调查。
深入生活好,还是田野调查也好,不要误解为只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需要。任何艺术创作方法都是需要的。现在,我们对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也很肤浅。只盯着眼前的生活,将它“主义”化,看到一栋楼,就写这栋楼,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森林是什么?它是远方,是环境,是时间后面的历史。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写的是星期六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一部长篇小说就写一天。但是星期六这一天只不过是一个时间平台,小说的结构、切口。小说本身是有历史纵深感的。现实主义并不等于缺乏历史感,因为历史感的存在,现实才更加深刻。现实主义也并非要与魔幻绝缘,荒诞感、魔幻感恰恰是对现实最深切的一种体验。
姚: 1991年您出版了个人的第一本书,也是第一本诗集——《三只眼睛》,时隔近二十年,再次出版新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近二十年过去了,您在诗歌创作理念、对诗歌的看法上有了哪些新的变化?
熊: 变化是很大的。大学以前我没有接触过诗歌,也没有想到要去做个诗人。写诗首先对我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冲动。18岁那年的春天,我写了第一首诗。后来一边写诗一边读诗,去图书馆借古体诗词,到书店买的却是新诗集。开始写诗是以我手写我心,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再后来看国外的诗。那个年代,普希金、雪莱、拜伦、济慈等诗人的作品很受欢迎。在国内就是朦胧诗。之后,西方现代诗蜂拥而来,现代派诗歌对我影响极大。但那种现代性体验我们是没有的,就是一种模仿、学习,写作有玄思的成分。我认为那个时期的诗歌成就不大,但是学习了西方现代派技巧性的东西,那种训练是有效的。
那时候诗人并没有自己的思想,体验也很肤浅。我曾写过宇宙诗,想象人类脱离了地球,回望地球就是一个小小的泥丸,那是人类童年的摇篮,然后作为人类的后代,站在浩渺的宇宙来怀念地球。那种乡愁是宇宙乡愁。那种抒情是想象的抒情。我写《十二月·性土地·我们》(十二月是指时间,性土地指空间,我们指人类),即天地人,抽象的哲学式的诗。想不到这首诗不久前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文版引用部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先锋诗歌,注意到了我这首诗。诗选入了《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但这些诗我都没有收录到诗集里。
我也写古体诗。新诗的风格最初受古体诗影响大。编辑说,这样的诗不现代、太传统了。那时不现代就是落伍。后来我的诗比较前卫、先锋,受现代派的影响很大。那时候西方现代思想很时髦,它不是我们的思想,是一种时尚。现代派诗歌让我们以西方的眼光来看世界,感受世界,大大开拓了诗人们的思想与视野,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推到顶礼膜拜的地步。甚至倒过来蔑视自己民族的诗歌艺术。这是深刻的教训。但至今还无太大改观。
我的诗歌创作,工作之后,随着经历的丰富,语言表达的锤炼,慢慢成熟,现代感不再是来自思想与概念,而是来自生活。特别是来广东之后,广东的务实精神把我的空想、不切实际的东西统统挤压走了,人不再虚荣,变得实实在在,返璞归真。但这种务实的文化自然偏于物质,是与诗很隔膜的,诗变得没有意义。诗人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自然我的诗写得少了。但当我再拿起笔来的时候,一定是我自己的需要,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至少诗歌写作对我自己是有意义的,我离不开它。也证明了我本质上是个诗人,并非一种青春期的行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写的诗都丢进抽屉,毫无发表的欲望。这样的写作姿态自然会影响诗歌的面目。
我发现我诗歌的现代性不再是写作出来的。因为我的生活变得“现代”,人与人的冷漠,以邻为壑,人性的异化,物质生活的疯狂,人主体性的丧失,人的价值遭到否定,人像是符号……这些都在生活中出现了。我有一首写空中飞行的诗《共同经历》,这是生活中寻常的一景:我在飞机上,地面看飞机是一个小点,飞机看地面是一个模型。我周围有音乐、有人,但是,我从城市上空飞过,下面的人不知道我的状态,我们却同处一个时空,彼此大不相同。我飞行中的生活,与别人的生活是一种无感的穿越。这是现代生活的一个象征,同处一个时空,生活却并不相干并不相同,彼此无法沟通、理解。这样的生活对诗歌表现形式也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我写作追求一种特别与新穎。
现在我的思想又发生了很大改变。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归传统。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出国访问交流,外国同行无人不说李白、杜甫的伟大。除了李白、杜甫几乎就没有他人了。看看我们自己,早已把我们伟大的诗歌传统不当一回事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全盘西方,天皇发现大和民族的传统岌岌可危,于是回归传统。知识分子从盲目崇洋开始回归东洋自己的趣味,于是产生了新式的表达,形成了现代大和民族文学。
如果我们不从几千年的表达经验里来透视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会将自己的生活狭窄化。古人面对生活的苍凉意蕴,比先锋的叙述更能唤起我们潜意识深处的共鸣。
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他对中国文人提出了恳切的忠告:请尊重中国自己的传统!他看到西方的物质思想正在征服东方的精神生活,正在使得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点消失殆尽,世界正在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
1920年,罗素来华讲学,1922年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他认为中国走的路必须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其中之一就是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的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
的确,东西方是不同的文明类型,中国的“易”和“道”是生命哲学,注重直觉、感受和顿悟,是内视的参验法,是万物一体观照下的哲学。老庄哲学充满生命的灵性与智慧,参透天地万物的灵机变幻。而西方向外寻求显性的认知,擅长怀疑实证,注重形式规则与物质文化,缺少空性智慧,只知道“有”不懂得“无”,不懂得万物相生相克,导致物欲膨胀,器物不能循环利用,危及地球生态。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成为推手,亚非拉许多民族的原生态文化被摧毁了。
但处在东西方之间的中东、西亚坚持了自己的伊斯兰文明。更早接触西方并被英国殖民了近两个世纪的印度坚持了自己的文明。地处东亚的中华文明,显然是世界上更高级的文明,但现在我们还有多少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我们曾发生过疯狂的自我否定,搞过历史虚无主义。而一个文化自信都没有的民族又谈何希望?
其实,中国的诗歌是世界上最独特、最奇妙的语言艺术,它的抒情性、生活化、贴近人的心灵、充满悟性,等等,汉字天然地与诗歌结缘,仿佛为诗歌而生。诗歌要跳跃、诗歌要模糊、诗歌要朦胧、诗歌要想象的空间、诗歌要代入、诗歌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汉字做得最好,充满了魔力。中国成为诗歌的国度,有诗教传家的传统是有道理的。而西方语言强烈的逻辑性,定语、从句一个接一个,一定要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它擅长思辨,擅长交代、叙事,只能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诗歌艺术。
诗歌讲境界,产生广阔而超拔的联想和丰盈的意义,能把你最神性的体验激发。中国诗歌能从最浅显、最日常之处做到。其生活化的特点,使得几岁儿童都能背诵,甚至理解。而它丰澹的内涵,八十岁的老翁读起来都会感怀不已。哪怕是一个简单的画面,涵盖的信息都是丰富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描绘大自然的景象,却指向生命的轮回、时序的更替、生与死……简单的两句话写出了太多太多的言外之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在写景,但人生的况味深蕴其中。我们以禅入诗,追求禅境、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自然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中国人的天地观不是以概念而是以诗得以生动体现的。它是天地灵性呈现,以文字复活。
新诗一百年,我们几乎是一边倒地投入西方,我们没有继承,没有立在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上,这是无根之木。不久前,中国在西方组织了一个大型油画展,是国家最高规格的展览,把我们最优秀的油画作品都拿出去了。西方的名家几乎倾巢而出,他们看完之后都很感慨,有一个共同的感想,就是中国的油画确实进步很大,了不起!但有一句话却非常刺激:你们终于画得像我们了。
同样的道理,具有中华民族气派,鲜明的中国特征,能够代表黄皮肤、代表东方、代表中华文明的诗歌在哪里?还得回到唐诗宋词!它一看就是中国人独创的诗歌。新诗有我们民族的气息吗?能一眼看出是中国诗人创作的吗?这个问题如果不好好反思,中国诗歌走不出一条成功的路。
我最近写赋,写赋是我向传统致敬的一个方式。我的诗歌创作也将有意向传统靠拢,譬如《这是背对你的方向》最后一句 “这一天如此漫长,朝如青丝暮成雪”,直接化用了古诗。向传统靠拢当然不是回到古体诗词,是要把中国诗歌的神韵、精神、哲学与审美方式、趣味、经验等代入现代诗,是在传统上创新,是创造性的传承。日本比中国现代化,但大和民族的文化却十分浓郁。我们抛弃传统是舍本求末,学得再好也是西方第二,最终会被后人抛弃。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印度尼赫鲁大学的学者墨普德跟我说,你们为什么只邀请西方的学者?亚洲只请了我一个,你们想脱亚入欧吗?世界上有一个美国已经足矣,你们还想做第二个美国吗?你们是中国,请别忘了自己亚洲国家的身份。你们身在亚洲做不了西方国家。这也反映出我们并没有真正自信。
姚: 近来,您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在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埃及、约旦、匈牙利、英国等国翻译出版,受到国外读者的喜爱。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郝慕天在翻译您的《己卯年雨雪》时说:“我一边翻译一边哭,我翻译莫言的小说时也曾这样,熊育群的小说是一样的,写得非常非常感人!感觉好深好深!”意大利作家、汉学家、翻译家费沃里·皮克在《为何选译〈西藏的感动〉》一文中写道:“这部作品具有很高的精神价值。熊育群在《西藏的感动》中创造了一个迷人的世界,富有人类学和考古学内涵,作家的人类悲悯情怀渗透于字里行间,通过非常感人的故事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温暖,并使读者体验到了纯正的美感。”您能得到国外专家的肯定非常难得,可喜可贺!但是,也不可否认,目前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还是不算很大, 与欧美等国家之间还有较大距离。从您自身的经验来看,您认为中国的文学作品要跨出国门、走向世界,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熊: 走出国门,牵涉到世界性和民族性问题,也牵涉到题材与视野。国外读者现在对中国比以前更加关注了,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较好的时期。有人说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性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国外读者读中国文学作品首先是想通过作品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社会与生活,了解中国人与文化。没有中国特点没有中国烙印、本民族特点不鲜明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
但是民族的东西要与世界接轨,要有普适性,要有世界性因素。譬如,德国汉学家郝慕天,她刚拿到我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时,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写中国那么遥远的一个小镇,事情也是很久以前的,凭什么德国人要有兴趣?第二个是从她个人角度来说的,她讨厌战争,连战争题材的书她都不感兴趣。
但是,我的小说写的是人,是人的悲剧,一对中国恋人与一对日本恋人之间的悲剧。悲剧的后面是战争,但战争的后面还是人。从人的悲剧反思战争、揭示战争本质性的东西,这就不只是抗日战争,而是所有的战争。我写的虽然是过去的战争,着眼的却是人类还将发生的战争,是世界和平。这就跟发生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关系不大。两对恋人间发生的美好爱情,也正是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美好爱情,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时间,也不分地域,都以感情之纯美而打动人心。
能够引起翻译家的强烈共鸣,我认为与我处理抗日战争题材的方式也有关系。“抗日战争”看名字就知道这是抵抗的、被动的,也是站在本民族立场看这一场战争的,是民族的、被侵略的、受害者的视角,是以日本为敌,是写中国人民怎么顽强抵抗,不屈不挠,日本人怎样魔鬼不如。这当然没有错,事实就是如此!但这种写法只是发泄,是受害者的倾诉、控诉,是对侵略者的仇恨书写。抗战题材小说之所以难以走出国门,问题就在这里,除了受害者,共同的民族记忆,民族的仇恨,外人谁对你的民族仇恨有兴趣?
首先,抗日战争是中日两个国家的战争,是中日战争,这样的视角具有客观属性。其次,日本人也是人,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人。我把日本人当人来写,写他们怎么从人变成魔鬼。通过人物命运的改变,写到人性,写到战争发动的过程,其中的逻辑,战争背后的东西,这个过程刻画得惊心动魄,要写出战争的本质,写出战争如何异化人。
这一切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特别是军国主义与政府的所作所为,值得人类警惕。现在,有的国家仍在叫嚣战争,航空母舰动不动就開到人家家门口。这是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这就是世界性的因素。我是超越了民族的立场,站在人类的、普遍性的、客观的立场,带着一颗悲悯的心来写的。
这样的写作,当年侵华的日本鬼子看了也深为震动,他们来营田墓地祭祀、谢罪。有评论家评论《己卯年雨雪》体现了民族精神上的成熟。所谓精神的成熟,就是不再只是仇恨,而是能够客观看待,能够看到悲剧背后的东西。失去客观性,不能客观对待,民族精神就不能称得上是成熟的。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