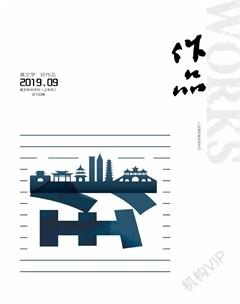遭遇来的小说(创作谈)
我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写散文则是我到了广东工作后开始的。这一转变缘由我人生轨迹的改变。而写小说却是我积累了十多年的主动作为。中篇小说《无巢》是《小说选刊》约稿,约定我写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长篇小说《连尔居》是受我一篇散文的启发,在一种冲动之下开始创作。《己卯年雨雪》则是遭遇来的小说。
有一天,我在网上无意中发现“长沙会战”,那时知道它的人非常少。汨罗江防线就是我家门前的河,这仗就在我家门口打的!这让我非常吃惊。那时,亲历者有的还健在,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营田惨案”。但谁也说不清了,连死伤人数都说法不一。也许还能找到营田惨案的幸存者?于是,我找了一个朋友,他组织起人马,我们开始了一场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
收集资料与田野调查的过程是对真相的叩问与挖掘,其次是思考与酝酿的过程、发现的过程。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产生了把它写出来的强烈冲动,但如何写一个惨案、一场战争?作为小说,这是一个写了几十年的老题材,很平常。战争是我最不熟悉的东西,它离我很遥远。若不是遇到了自己家乡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我不会去写这个题材。但走近事发现场,特别是亲历者的指认,让我开始有了切身的感受。
当我写到五万字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往下写了。这时候才发现写好这个题材远没有这么简单。我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感觉,觉得写不出来了。这五万字中有些不错的内容,丢了可惜,但它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我便从中挑了一万字出来,做了一些修改,这便是2006年4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天的十二条河流》。想不到这篇文章反响很大,还引起了争议,说它几不像。一些人把它当作我散文的代表作。这让我觉得不能随便就丢弃了。
我的困难很多,一是不熟悉中华民国时期的生活;二是对抗日战争特别是长沙会战了解十分有限。我把握不了吃不透的东西又如何能够独立思考,进而去感受、去发现、去表现?我的立场与情感又如何建立?
随着相关资料的获得,一点点的积累,就像搭积木似的,真相似乎在慢慢复原。譬如当年湘阴县县长谢宝树的《守土日记》中发现,那场战争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他拣重要的记录下来了。我在地摊上找到了《岳阳百年大事记》《岳阳文史》《湘阴文史资料》等旧书,还有收藏的朋友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写的《湖南会战》译稿等大量资料给了我,一位朋友从一个台湾将军那里要到了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印的《国军抗日战史专辑》。我又读陈存仁的《抗战时代生活史》《银元时代生活史》《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等,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
特别是有一天,我在大理的旧书店无意间发现了《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日本女人近滕富士之的档案材料,一个真实的日本人的内心世界令我感叹,她让我回到了常识——我们是一样的人。正是她引出了小说的女主角之一武田千鹤子。
这时候我认识到要写好这个题材不能缺少日本人,离不开日本人的视角,因為这是两个国家间的战争。而我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自己写自己,日本人几乎成了一个符号——魔鬼的代称。写魔鬼容易,写人变魔鬼就难了。但只有写好人变成魔鬼才有启示意义。中国战争题材的小说还不能与世界对话,寻思原因,我们受害者的意识太深,无法超越仇恨,对施害方又缺乏了解的意愿。要说战争中的人性,日本士兵更能提供丰富的例证。
日本女人近滕富士之让我想到,两对生活在各自国家的恋人,过着彼此相近又不同的生活,上学、恋爱、结婚,日常的起居、礼貌与情谊。本来毫不相干的人走到了一起,彼此产生了深仇大恨,都无法释怀,七十年过去了,这仇恨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这就是战争的逻辑。这是一种民族的仇恨,让每个人都不能幸免。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类的不智与理性精神的缺乏,把利益高高置于生命之上,这是一种自我践踏。我对战争的思考由此开始。
第二次创作,有了一对日本恋人。那时我没想到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你如何写好日本人,尤其是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与他们的生活。日本人的视角必定有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理解,他们自己认为的战争史与真实历史的区分,他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些牵涉到日本的历史、地理、文化、国民性、起居生活环境等,写好了这些,一场真实的立体的中日战争是能够浮现出来的。
这时期我开始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网野善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尾藤正英的《日本文化的历史》、奈良本辰也的《京都流年》、妹尾河童的《窥视工作间》等,看他们拍的电视剧《坂上之云》和众多电影,读日本作家田边圣子的《源氏物语》、川端康成的《雪国》、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柳美里的《声》等小说。
侵华日军的战地日记也开始出现了,大和民族是一个喜欢写日记的民族,我找到了《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还有太田毅《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小熊英二《活着回来的男人》,这些书有的是我从台湾找到的,有的是朋友惠赠,有的是民间抗战博物馆的高价影印件,它们对我帮助特别大,让我有如亲历。小说主角之一武田修宏立即获得了灵魂,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有了依据,特别是恶行细节我无一虚构,它们全部来自这些日军日记。
当然,光有书本是远远不够的。我第一次去日本是随团去的,不到十天。第三次投入写作,几乎是推倒重来,大约写到十四万字,感觉写日本人的生活仍然有些无力感,生活的细节仍然缺乏,没有日本人原型也让我感觉有些隔,于是我放下写作,从天津滨海国际写作营回来,第二次去了日本。
这次自由行将近一月,我不但找到了侵华士兵的家,找到了昭和时期生活的真实环境,还找到了千鹤子的原型,再次投入创作时就顺利多了,几乎是一气呵成的。
但最后一稿写得非常苦,反复地修改,估计有二十多遍,一方面是一些地方不太满意,另一方面恰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不断有新的史料出现,改得自己都想吐了,到后来,只要一打开电脑我就忍不住要去改,都变成习惯了。那年春节去台湾买了几本有关的书,我还有修改的冲动。可以说,这是我写得最苦的一部书,把头发都写白了不少。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面对这样一个巨大又残酷的事实,我觉得虚构的小说特别没有力量,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越来越偏爱非虚构的东西,小说面对现实正在失去它的力量。我尝试了一条虚构与非虚构结合的路子,那就是细节、大的事件、背景、环境力求真实,但人物与故事可以虚构,人物能够找到原型的我尽力寻找。我希望读者可以根据小说内容去与现实世界对应,甚至寻访小说主人生活与走过的地方。我自己写作时就沿着小说主人的行动轨迹行走过了。小说因此拥有一股真实的气息,它能够对现实发言,就像一个人站到了大地上,它是能够发力的。
我没想到这个题材深入下去十分恐怖,承受力差的人可能会被击倒,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就自杀了。男人可能要坚强一些。我越来越绝望。绝望不是来自那些血腥的场面,而是人性。我从这一场战争中看清楚了人性,這种绝望是巨大无边的,有时一个人忍不住哭泣,全身发冷,非常抑郁。我在进入一个地狱一样的世界。那么巨大深广的灾难与伤痛让我哭泣,主人公悲惨的命运让我哭泣。我明白了以前我们把“希望”这个词挂在嘴上,是多么轻飘的想法。这个世界希望其实非常渺茫,写作中,我是因为绝望才去追求希望,人世间没有希望,人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我们必须要制造出希望来。是绝望让希望显得珍贵,是绝望催生了希望。
在完成《己卯年雨雪》创作之后,我看世界的眼光也变了,我感到害怕,有一种力量似乎人类还不能控制,这在我小说中追问战争灾难的责任时,竟然追究得十分困难,跳过了那么多的人,很多人都自我原谅了。正如战争机器的发动,有那么多必然与偶然的因素交织成一团,有时让人辨识真相都很难,如同一千个人来凌迟一个人,到底是谁杀死了他?这其中人性的恶更令人心寒,我时时感觉到寒意,我能理解张纯如的自杀。几千年来,社会变化如此巨大,人性却一点没有变化。人类只有自己筑墙自我设限自我警戒,建立重重机制,困住心中的兽性,也许才能够得救。
我的小说采取了第一人称视角,因为伤害人最深的莫过于心灵的创伤,第一人称便于进入人的内心世界。但这个第一人称有所改变,只是以第一人称的感觉来写,因为我还得跳出来,事件成因、背景等更宏观的世界需要交代。
如果不是见证了亲历者内心的痛苦,如果不是对这场战争有新的发现与认识,如果没有超越,如果找不到好的形式,想要写好一部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写了漫长的战争史,同时也写了人对于自由世界最高的向往——道家的逍遥。它们恰恰成为人类生存的两极,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消解。中国文人有两种典型的人生选择——入世与出世,如同道家阴阳两极世界,本身内含有对世界的认识与态度。这种人生选择跟儒与道对应,都拥有自己行为的理论依据。当战争来临,这两种人生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极端,更凸显出儒道两种本土传统文化的对比。特别是小说中的左太乙把道家的人生态度推向了一种极致,以此来表达他对人对世界极端的失望心情,这更能表现战争的野蛮、生命的荒凉,这是一种生命控诉!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与左太平所代表的儒家相互排斥的人生态度,你会发现都是对的。恰如太极的阴阳世界,是一种对立统一。
千鹤子能够活下来,正是中华文明儒家与道家文化救了她,儒道在与野蛮对峙时显现了文明的高度:良知与正义超越了仇恨与冷血的杀戮,人道情怀超越了种族与国界。一场战争的胜利绝不仅仅是冷血杀戮的结果,一定有文明感召的力量。
小说写道家文化,本身也贯穿了道家的精神与风骨,它如云中之笛,有如天籁,这才是生命的境界,是超越生死的大悲咒大悲悯。写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大题材,一定要看到文化。这是最初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也是道家精神让战争小说有了魔幻色彩。
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出版三年,目前已有德语、俄语、英语完成翻译正在出版,签订翻译出版合同的还有意大利、匈牙利、日本等语种。作为抗战小说引起国际文坛关注算得上非常迅速。国内发行量一路攀升,出现了盗版。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郝慕天在翻译《己卯年雨雪》时说:“我一边翻译一边哭,我翻译莫言的小说时也曾这样,熊育群的小说是一样的,写得非常非常感人!感觉很深很深!”
作品走出国门是每个作家所追求的。这样的结果也是我追求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让日本人看到这场真实的战争,让他们知道真相,所以我一定要写得客观。其次,一方面我觉得要有民族性,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另一方面,民族的东西要与世界接轨,要有普适性,要有世界性因素。德国汉学家郝慕天曾问过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写中国那么遥远的一个小镇,事情也是很久以前的,凭什么德国人要有兴趣?第二个是从她个人角度来说的,她讨厌战争,连战争题材的书她都不感兴趣。
这样的问题对我并不存在。《己卯年雨雪》写的是人,是人的悲剧,一对中国恋人与一对日本恋人之间的悲剧。悲剧的后面是战争,但战争的后面还是人。从人的悲剧反思战争、揭示战争本质性的东西,这就不只是抗日战争,而是所有的战争。我写的虽然是过去的战争,着眼的却是人类还将发生的战争,是世界和平。这就跟发生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关系不大。两对恋人间发生的美好爱情,也正是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美好爱情,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时间,也不分地域,都以感情之纯美而打动人心。
我的回答是请她看两章。她一边哭一边翻译时,给我打来了电话,情难自抑。
这样的小说,当年侵华的日本鬼子看了也深为震动。有亲历者给我写信,说小说真实的情景勾起了当年的记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岁月。有日军遗孀写文章,说小说里的武田修宏与她的丈夫神似,仿佛他的灵魂到了这本书中。小林宽澄是当年的侵华日本兵,他被俘参加了八路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这位日本老八路被中国政府请到了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习近平主席的授勋。他前来参加《己卯年雨雪》故事发生地湖南湘阴的和平祭活动时,已是九十七岁高龄。小说中发生的惨案让他十分不安,老人不让人搀扶,一个人爬上长长的台阶,向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敬礼、鞠躬,他绕着纪念塔,边走边哭。在营田惨案百骨塔祭祀会上,他致辞时几度哽咽。在长沙会战纪念馆,老人献花、敬礼、鞠躬、下跪……看到纪念馆陈列的日本兵用过的东西,他说:“羞羞。”在中日战争老兵、营田惨案幸存者及后人恳谈会上,他跟中国抗战老兵拥抱,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老人家不久前在日本去世,那是他最后一次中国之行。这是战争双方士兵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走到一起,共同反省这一场战争。
有评论家认为《己卯年雨雪》体现了民族精神上的成熟。所谓精神的成熟,就是不再只是仇恨,而是能够客观看待,能够看到悲剧背后的东西。失去客观性,不能客观对待,民族精神就不能称得上成熟。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