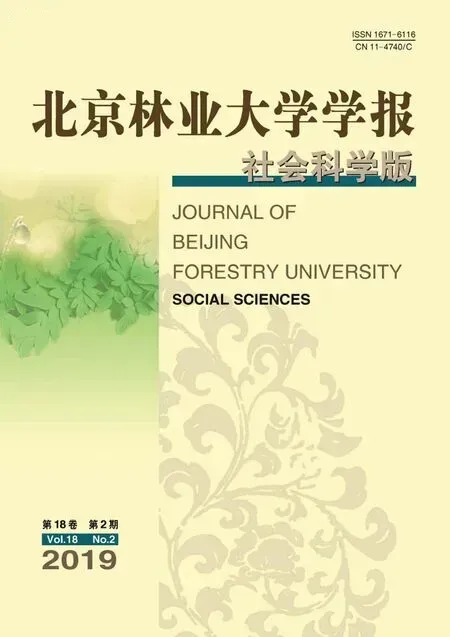气候小说的兴起及其理论维度
李家銮, 韦清琦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 2.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3.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一、气候小说兴起的背景
工业革命以来的生态灾难,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雾都伦敦的空气污染、苏联切尔诺贝利和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及国内的沙尘暴和雾霾。另外一些则不容易为人所直观地感受到,比如周期性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臭氧层空洞、全球气候变暖等,它们往往覆盖巨大的地域,越出多国的国界,并且横跨很长的时间,超过多代人的寿命。这些时间与空间规模超乎一般想象的现象,只有通过它们所造成的具体的、局部的结果才能为人所知。比如普通人可能知道白色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但是一般不会想到白色垃圾已经在太平洋上形成了面积6倍于英国的“第八大陆”,并正在造成大洋深处的海洋生物生存危机。这种时空规模超乎一般想象的现象被美国生态哲学家蒂莫西·莫顿称为“超级物”(hyperobject),语义范畴上不仅指物体(object),还包括事件(event)和现象(phenomenon)。莫顿2010年在《生态思想》(TheEcologicalThought)一书中提出“超级物”的概念,并用比喻的语言断言式地指出超级物的持久性和重大影响:“超级物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会腐烂的……超级物不仅在地球上烧一个大洞,也在你的头脑上烧一个大洞。”[1]紧接着在2013年,他又以这一概念为标题出版了新书《超级物:世界末日之后的哲学与生态》(Hyperobjects-PhilosophyandEcologyaftertheEndoftheWorld),列出了超级物的5大特性[2]:①黏性(viscosity),粘附于物体之上,影响无处不在;②非本地性(nonlocality),存在不限于一地;③时间弯曲性(temporal undulation),超越一般时空,时间不再固定,开始“弯曲”(借用自现代物理学的说法);④相性(phasing),观察者需要站在更高维度上才能理解超级物(“相性”借用自现代物理学);⑤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涉及多个物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物体之间的一种状态和属性(仿用自拉康哲学的主体间性)。
从莫顿给出的定义和特性看,气候变化属于典型的超级物。气候变化的时空规模远超一般事件,人类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局部的、具体的、短暂的天气变化,但是难以感受到全球性的、整体的、长远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也完全符合超级物的5大特性:它超出一般时空(时间弯曲性),不局限于某一地区(非本地性),深刻影响整个地球及各种生物(黏性),并通过其他物体和现象呈现出来(物体间性),只有跳脱到更高的逻辑层次才能理解其全貌(相性)。在人类所习惯的时间尺度上,缓慢的气候变化过程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无动于衷的麻木感,由此造成了许多对气候变化的误解、怀疑甚至否认。比如美国社会中历来存在气候变化怀疑论(climate change skepticism)和气候变化否定论(climate change denial),前任参议员汤姆·科伯恩等国会议员多次阻挠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的法案通过,石油资本及右翼智囊团发起的反气候变化运动(climate change counter-movement)影响了众多美国民众。2017年6月1日,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保护美国就业为由,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严重损害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
在此背景下,展示气候变化及其成因和危害,鼓励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行动,就成为整个知识界的责任之一。但是过往的事实表明,讲究事实和逻辑严谨性的科学在展示气候变化方面有其不足之处。首先,许多民众仍不具备理解气候变化的科学素养。比如,科学一般只做趋势性的气候预测,但是这种严谨性却被许多怀疑论者视为是一种漏洞,他们认为科学无法证明气候变化客观存在。其次,科学惯于使用的统计数据、方程式、图表等表现手段往往是中性的,甚至是学究式的,难以给人直观的强烈感官冲击,使人们直观地想象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从而激发行动上的改变。比如,科学能预测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但是难以让人们真切地想象海平面上升后淹没沿海城市的巨大破坏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苦难。文学艺术在展示全球气候变化上至少是科学的一种有益补充。气候小说(Climate Fiction)或气候变化小说(Climate Change Fiction),英文简称Cli-Fi,就是生态文学表现全球气候变化的最新尝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环境科学家莎拉·珀金斯-柯克帕特里克就认为气候小说“可能鼓励读者改变他们的日常行为”,并“传递一个重要信息,一个希望的信息,即与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做斗争永远都犹未为晚”[3]。早在21世纪初,气候小说、气候变化小说等概念就已经被提出来,比如美国著名生态批评理论家斯科特·斯洛维克2008年就著文分析了气候变化小说[4]。2013年美国记者丹·布鲁姆正式提出Cli-Fi这一凝练的英文名称,从构词法上很明显地模仿了Sci-Fi(Scientific Fiction,即科幻小说)一词。气候小说早年被视为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但是现在这一领域的大多学者专注研究气候小说的独有特点,主张将其视为与科幻小说并列的一个小说门类。比如,美国作家丽贝卡·图胡斯-杜布罗2013年就直接以《气候小说:一个体裁的诞生》(Cli-Fi:BirthofaGenre)为标题论述了气候小说的特点。美国生态批评家斯蒂芬妮·乐米那杰也认为气候小说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随着气候变化在20世纪末日渐显现,众多体裁开始自觉地谈论真实的或者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灭绝问题。气候小说(Cli-Fi)就是其中最流行的一种。”[5]
二、气候小说的成就
自从2013年Cli-Fi这一英文缩写被提出来并正式进入文学批评界之后,主张将气候小说视为一个新的文学体裁的文学批评家们就致力于为其寻根并编撰年谱。马修·施耐德-迈尔森的《气候变化小说》(ClimateChangeFiction,2017)、亚当·特雷克斯勒和艾德琳·约翰逊-普特拉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inLiteratureandLiteraryCriticism,2011)、《人类纪小说:气候变化时代的小说》(AnthropoceneFictions:theNovelinaTimeofClimateChange,2015)等文章和著作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气候小说的发展历程。许多经典作品也被重新从气候小说的角度进行解读,并被划分到气候小说的书单之内。
气候小说的定义可宽可窄,但凡包含气候变化元素的小说都可以宽泛地被视为是气候小说,但是严格地说,则“只有有意识地、明确地涉及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的文本”[6]才能被归于气候小说之列。按此严格的定义,21世纪之前的许多涉及气候变化主题或元素的科幻小说只能算作施耐德-迈尔森所称的“原型气候小说(proto-cli-fi)”[6]。早至20世纪60年代,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的主题就开始出现在科幻小说中,英国科幻小说家J. G. 巴拉德的《神秘来风》(TheWindfromNowhere,1961)、《淹没的世界》(TheDrownedWorld,1962)和《燃烧的世界》(TheBurningWorld,1964)就探索了未来世界的多重可能性。在前两部中,气候变化均由自然现象引起而非人类造成,《神秘来风》中的强风不知原由,《淹没的世界》中的全球气候变暖及海平面上升则由地球本身引起;只有《燃烧的世界》中的干旱是由人类排放工业废水造成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奥克塔维娅·巴特勒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借用了气候科学研究中的部分预测,加上科幻小说式的情节设置,开始对未来世界做出更加现实化的预测,并探讨了人类对于气候剧变的应对之策。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巴特勒的《播种者的寓言》(ParableoftheSower,1993)及其续集《有才能者的寓言》(ParableoftheTalents,1998),故事设定于由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之后地球发生生态崩溃的21世纪20年代,记叙了女主人公奥莱米娜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自我成长与寻求人类救赎的历程。同时期将气候变化设定为人为原因引起的小说还有大卫·布林的《地球》(Earth,1990)和布鲁斯·斯特林的《恶劣天气》(HeavyWeather,1994)等。但是这些“原型气候小说”中的气候变化往往很大程度上具有较多的科幻和猜测成分,与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全球气候变化出入较大,所以学界一般并不认为气候小说正式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
进入21世纪,人为原因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日渐为大众所接受,同时也兴起了多种形式的气候变化怀疑论和否定论。在面对大众的气候变化科普遭受阻力,并且未能引发人们实际行为改变的事实前,公共知识界开始期待文学艺术在普及气候变化知识、激发行为改变方面的“独到作用”。比如罗伯特·麦克法兰在英国《卫报》(TheGuardian)上发文质问:“关于气候变化的文学在哪里?对于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的文学创作性回应在哪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1世纪初气候小说正式诞生,涌现出了一大批明确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作品。美国科幻小说作家金·史丹利·罗宾逊在2004年至2007年间发表了《资本中的科学》(ScienceintheCapital)三部曲,包括《雨的四十种征兆》(FortySignsofRain,2004)、《五十度以下》(FiftyDegreesBelow,2005)和《六十天计时》(SixtyDaysandCounting,2007),以暴风雨和严寒的极端气候场景设定,力图唤起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真切感受。有“加拿大文学女王”之称的阿特伍德也参与进来,她的《羚羊与秧鸡》(OryxandCrake,2003)及其续篇《洪水之年》(TheYearoftheFlood,2009)和《马德亚当》(MaddAddam,2013)组成的“马德亚当”三部曲,描绘了一个后末世(post-Apocalyptic)世界,其中包含“无水的洪灾”等诸多气候变化的象征和隐喻,所以也被视为是气候小说作品。保罗·巴奇加卢皮的《曼谷的发条女孩》(TheWindupGirl,2009)和《拆船厂》(ShipBreaker,2010)则将场景设定于第三世界和社会底层,探讨了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同时期的气候小说作品还有科马克·麦卡锡的《路》(TheRoad,2006)、珍妮特·温特森的《石神》(TheStoneGods,2007)、克莱夫·卡斯勒的《极地漂流》(ArcticDrift,2008)、詹姆斯·霍华德·库斯勒的《手工世界》(WorldMadebyHand,2008)、萨斯·罗伊德的《碳日记2015》(TheCarbonDiaries:2015,2009)、罗伯特·查尔斯·威尔逊的《朱利安·康斯托克:一个22世纪美国的故事》(JulianComstock:AStoryof22nd-CenturyAmerica,2009)和马塞尔·泰鲁的《极北》(FarNorth,2009)等。特别是卡斯勒的《极地漂流》十分畅销,说明这一时期的读者群体开始接受这一新兴的小说形式。由于大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生态灾难有了基本共识,“这些作品不再把天气系统和人类命运的突变作为一种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将其描绘成迫在眉睫触手可及的问题”[6],主要着眼点在于激发人们在消费观等实际生活方式上的转变。
气候小说的真正爆发还是2010年之后的事情。丹·布鲁姆在2013年总结提出了Cli-Fi这一英文缩写,紧接着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以《时下正热:气候变化创造了一种文学体裁吗?》(SoHotRightNow:HasClimateChangeCreatedaNewLiteraryGenre?)为题报道了气候小说这一新兴的小说形式。《卫报》和《纽约时报》等欧美主要媒体都跟进了报道,使得气候小说这一概念逐渐为大众所知。读者群的扩大也促使更多作家加入到气候小说写作的行列,气候小说作品的数量因而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美国文学阅读网站goodreads以“Cli-Fi:气候变化小说”(Cli-Fi: Climate Change Fiction)为主题列出了196部近年的气候小说作品,足见气候小说势头之盛。阿特伍德2013年完成了“马德亚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马德亚当》,该三部曲正在被改编为电视剧,可以预见其影响将会更加广泛。罗宾逊2017年也推出了新作《纽约2140》(NewYork2140),将214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之后大部被淹没的纽约描绘成一片汪洋泽国,探讨了人类在气候灾难之后的新环境中的生存策略以及其中涉及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杰夫·范德米尔的《遗落的南境》(TheSouthernReach)三部曲包括《湮灭》(Annihilation,2014)、《当权者》(Authority,2014)和《接纳》(Acceptance,2014),以科幻小说的手法设定了一个生态灾害区,以诸多象征探讨了人类在生态变异之后的生存问题。这一时期的气候小说作品还有伊恩·麦克尤恩的《追日》(Solar,2010)、西蒙·罗瑟的《引爆点》(TippingPoint,2010)、芭芭拉·金索夫的《逃逸行为》(FlightBehavior,2012)、皮特·赫勒的《天狼星》(TheDogStars,2012)、纳撒尼尔·里奇的《末日来临》(OddsAgainstTomorrow,2013)、明迪·麦金尼斯的《一滴不剩》(NotADropToDrink,2013)和《一捧尘土》(InaHandfulofDust,2014)、芬兰女作家艾米·伊塔兰塔的《水的记忆》(MemoryofWater,2014)、扬妮克·索拉夫的《洋流》(TheCurrent,2014)、J. L.莫林的《自然的忏悔》(Nature’sConfession,2015)、克莱尔·维耶·沃特金斯的《金牌柑橘》(GoldFameCitrus,2015)、詹姆斯·布拉德利的《分支》(Clade,2015)、玛格丽特·博伊森的成人童话《爱丽丝,妙妙猫和气候变化》(Alice,theZetaCatandClimateChange,2016)、亚伦·蒂尔的《永恒先生》(Mr.Eternity,2016)和雪儿·蒂马琳的《偷骨髓者》(TheMarrowThieves,2017)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以气候变化和生态灾难为主题编撰的小说集,比如马克·马丁编撰,阿特伍德和巴奇加卢皮等知名作家参与创作的小说集《我和熊在一起:来自被破坏的星球的短篇故事》(I’mwiththeBears:ShortStoriesfromaDamagedPlanet,2011),以及约翰·约瑟夫·亚当斯编撰,收集了阿特伍德、罗宾逊和巴奇加卢皮等气候小说名家作品的《世界之大:气候小说的长篇小说选集》(LoosedupontheWorld:TheSagaAnthologyofClimateFiction,2015)。
气候变化也引起了中国作家的注意,但是中国气候小说的发展节奏与欧美不同,总体而言尚未形成与欧美气候小说同等的声势。诸多中国小说作品都包含气候及气候变化的因素,比如王晋康的《沙漠蚯蚓》(2007)设定于温室效应造成的干燥气候加剧,中亚地区沙漠扩大的背景;刘慈欣的《流浪地球》(2008)则以太阳即将毁灭、地球气候剧变为背景,讲述了人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三体》三部曲(2006、2008、2010)则以“三体”世界的气候灾难为隐喻,促使读者反思地球上的气候变化及应对之道;邢立达的《御龙记:史前闯入者》(2018)则描述了恐龙时代截然不同的气候,启发读者思考当下的气候变化。但是以上文所述的严格定义能称为气候小说的作品则凤毛麟角,其中吴显奎的《勇士号冲向台风》(1986)直接以气候灾难为主题,讲述了中国科学家利用探测器来控制台风的故事,获得了1986年首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刘慈欣的《混沌蝴蝶》(1999)讲述了一个南斯拉夫的气候学家试图利用气候上的“蝴蝶效应”拯救国家的故事;刘兴诗的《喜马拉雅狂想》(2012)则设想了23世纪由地球板块运动引发的气候灾难,讲述了人类试图通过打通喜马拉雅山脉来改变气候灾难的故事。
气候小说正在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阶段,迄今为止所涵盖的主题大致可以归纳为3大类:末日预言、出路探索和生态政治。几乎所有的气候小说都涉及末日预言这一主题,因为气候变化这一气候小说的母题本身就是一个影响全人类的“超级物”。所以大部分气候小说都将场景设定为某种气候灾难发生过程中或之后的世界,通过这一种具体的气候灾难来展现气候变化这个“超级物”的一个侧面,往往描绘出一幅反乌托邦的景象,充满悲观的预言色彩和对当下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早期气候小说的科幻小说色彩浓重,时间往往设定于久远的未来,设想的气候灾难往往属于宏大叙事,所以给读者的感官震撼有余,时间紧迫感则不足。比如发表于1962年的《淹没的世界》时间设定于2145年,将伦敦设想为热带气候,其中的全球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也不是人类造成的,所以读者可能惊异于作者的想象力,但是难以将小说场景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稍晚的气候小说则往往将时间设定为与成书时间比较接近的未来,其中的气候变化也往往由人类造成,但是仍然以宏大叙事居多。比如约翰·巴恩斯的《飓风之母》(MotherofStorms,1994)描绘了21世纪初核试验释放的包合物(clathrate compounds)引发的超级飓风,飓风造成地球上10亿多人死亡,最终人类利用自己的科技,引来冥王星的卫星上的冰,降低了地球表面的温度,以此制服了飓风。这种人类利用自己的科技克服自然的或人为的气候灾难的气候小说,虽然能引发读者的震撼感,但是在激发人类行为改变方面可能适得其反,读者可能感叹于人类科技的先进而认为继续当下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安全可行的。中国的《沙漠蚯蚓》和《喜马拉雅狂想》等气候小说也在此类。近年的气候小说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改进,将宏大叙事切换为局部的具体的叙事,将叙事重点放在灾难后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对于人类当前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比如《纽约2140》对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的纽约的景象着墨不多,重点关注纽约人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其中笔法细腻的生活场景描述反而更能激发读者与当前生活的联系。
将气候小说与一般科幻小说分开的正是基于“末日预言”的反思生态政治和人类出路的出路探索主题。当然,不同作家做设想的方式是不同的,比如《播种者的寓言》就十分关注宗教在气候灾难之后的作用,主人公试图建立一套新的信仰体系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曼谷的发条女孩》则将场景设定于石油资源耗尽的23世纪,设想人们如何在没有化石能源的情况下生存,作者设想的这种没有化石能源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正是解决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钥匙。气候小说家所设想的出路当然不能代替气候科学研究及其他硬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气候小说更多的不是寻求一种科学式的解决方案,而是更加注重分析人类造成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生态灾难的哲学和思想根由。可以说气候小说中对人类出路的探索是硬科学研究的有益补充,甚至可以说气候小说探索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终极出路。
气候变化对各国、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不一致,所以这一议题本来就是政治博弈、各利益集团勾心斗角的平台,这一点反映在气候小说中就是生态政治主题。首先是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气候变化怀疑论、否定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宣传战。以石油资本为代表的大产业资本、保守派、右翼智囊团因为自身的利益和信仰经常质疑、否定气候变化的存在或者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迈克尔·克赖顿2004年的科技惊悚小说《恐惧状态》(StateofFear),作者通过故事情节、诸多脚注和附录,传达了气候变化是“生态恐怖分子”(eco-terrorists)捏造的这一惊人观点,被马修·施耐德-迈尔森称为是气候小说中的“害群之马”。但是正是这样一部小说,曾经占据亚马逊网站销量第一和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二,销量达几百万册,可见美国对气候变化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不在少数。虽然从主题看,这部小说仍然算是气候小说,但是立场与其他所有的气候小说截然相反。与之相对应的是环境科学家、生态批评家、环保主义者、自由派等组成的阵营,几乎所有的气候小说家都属于这一阵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并激发人们在实际行为上的改变。许多气候小说就直接以主人公在两种观念的拉扯之间的成长为主题,比如《逃逸行为》中的主人公出身的社区和她的宗教信仰都极端保守并否定气候变化,但是通过个人学习和研究,她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另外,虽然造成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往往是受气候变化危害最小的上层有产阶级,但是责任最小的底层贫民、少数族裔、女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却往往最大,这一现象可以归结为“气候不公”(climate injustice)。不少气候小说涉及对气候不公及相关的种族问题和文化反思,比如《偷骨髓者》就深刻地反思了加拿大主流白人文化和原住民文化,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小说中以做梦的能力为隐喻——白人丧失了做梦的能力,只有土著民族(加拿大称为first nations)才保留着这一能力,反思了白人文化对地球生态的破坏以及地球生态对人类的反作用。
三、气候小说的理论维度
气候小说的兴起引起了教育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国际上众多高校开设了气候小说相关课程,比如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爱达荷大学和俄勒冈大学等均开设了关于气候小说的本科课程、研究生课程或者暑期课程。文学批评界自气候小说诞生起就开始关注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迄今为止已经有众多学者发表了有关气候小说的论述,包括斯科特·斯洛维克、格里塔·加德、格雷格·加勒德、艾琳·詹姆斯、安东尼娅·梅纳特、马修·施耐德-迈尔森、亚当·特雷克斯勒、E. 安·卡普兰、雷蒙德·玛维兹、杰森·摩尔等。《牛津研究百科全书》也收录了气候小说的词条。
教育界和文学批评界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气候小说的理论维度进行了梳理。可以说气候小说是一种开放的小说样式,气候小说家也在其中广泛地使用了许多传统的文学手法,所以可以笼统地断言,一切传统的文学批评手法都可以用于解读气候小说。但是从气候小说关注的焦点主题及其迄今表现出的特点而言,可以从三大特别突出的理论维度来解读气候小说,即生态批评、世界主义和女性主义。首先,气候小说的生态批评维度是不言而喻的。气候小说因全球气候变化而起,描绘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分析气候变化的成因,探索人类在气候变化后的出路,部分气候小说还能从灾难叙事中跳脱出来,批判化石能源依赖和消费主义等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反思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以及其中涉及的政治和生态不公等问题。所以很多生态批评家把气候小说放在人类纪(anthropocene)的概念中进行考察,比如在《人类纪小说:气候变化时代的小说》中,亚当·特雷克斯勒就从人类史的角度分析了气候小说的起源,以及气候小说与科学、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杰森·摩尔则从资本纪(capitalocene)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气候变化和气候小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也是气候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气候小说所描绘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灾难影响的是全世界的人类和其他所有物种,批判的也是当下全人类共同的消费主义文化以及全球化推动下的工业化浪潮,探寻的人类出路也是全人类甚至包括其他物种在内的所有生物的出路。根据王宁的概括,“世界主义的基本意思是,所有人类的成员,不管其种族及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一个大的社群,因此,世界主义十分接近当今人们对全球化话语的建构,根据这一构想,所有的人都分享一些超越了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和权利”[7]。本质上,全人类组成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生态的角度甚至可以说,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整个地球组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批评的基本观点就是人类同属于一个地球,并且与其他物种分享地球的生存资源,反对人类对自然以及其他物种的压迫与剥削。气候无国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是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也威胁着其他物种的生存。所以从诞生的背景和创作的内容看,气候小说天然就具有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的倾向,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提醒决策者及公众对气候变化做出正确应对。美国生态批评家厄休拉·K·海斯将生态世界主义定义为“将个体和群体视为由人类和非人类的物种共同组成的地球‘想象的共同体’的一部分的一种尝试”[8]。也有学者认为,气候小说的角色往往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对全人类和全物种的关怀和生态主义的主张是跨越国界的,挑战了西方主流的二元对立思想[9]。比如,《逃逸行为》展现了主人公从局限于本地和本社群的思维方式到生态世界主义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最终宣扬的是这种“人和非人物种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生态世界主义理念。
气候问题中的世界主义维度体现为各国政府主导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方面的努力,具体到气候变化问题可以称为气候治理(climate governance)。关于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治理议题中涉及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马修·格拉斯的《最后通牒》(Ultimatum,2009)就详细地“记录”了2032年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磋商过程,展现了其中的政治角力。罗宾逊的《资本中的科学》三部曲则反映了美国内部关于气候变化的决策过程——其中的主要情节就是全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领导和科学家的讨论和决策,其中不乏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在现实中,国际社会通过了《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国际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安排,这些国际共识主要聚焦于节能减排,延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进度。在气候小说中,小说家则敢于设想更为激进的气候工程(climate engineering)手段,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比如,查尔斯·谢菲尔德的《黑夜之间》(BetweentheStrokesofNight,1985)就设想了在全球气候变化引发人类生存危机的将来,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以及产业资本资助各种研究,以改变人类和其他物种的新陈代谢机制,或者建造绕地球自转的生态基地,但是最终人类毁灭于核大战。在《飓风之母》中,巨形风暴由人类造成,最终又由人类的科技平息,但是人类付出了至少10亿人生命的代价。在法国科幻小说家雅克·洛布和让-马克·罗谢特的《雪国列车》(LeTransperceneige,1982)以及2013年的改编电影《雪国列车》(Snowpiercer)中,人类使用气候工程的方法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失败,反而造成了全球气温骤降,人类重新进入冰河时期,地球生命几乎全部灭绝。可以说,气候小说总体上是对人类的科技持怀疑态度的,一方面反思人类依赖科技和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怀疑人类的科技是否足以及时安全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小说中也包含着女性主义的理论维度。在女性主义特别是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当下的生态危机不单是人类造成的,而是与男权制共生共存的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比如玛丽·菲茨杰拉德就以《气候变化是一个女性主义议题》(ClimateChangeisaFeministIssue)为题在《卫报》发文阐述了气候变化与女性的紧密联系。所以气候小说不仅反思人类的生活方式对地球生态的影响,也更深层次地反思其中的男权思想。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诸多气候小说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女性,而被批判的反面角色往往是固守传统生活方式的男性。比如,在《湮灭》中,最后一次前往生态禁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探险队员全是女性,之前由男性队员进行的探险全部失败,队员不是失踪就是自杀,身患癌症或者精神错乱,这一对比隐喻性地展现了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独到作用。同时,生态女性主义不只关注女性,而是关注所有被压迫的对象,包括少数族裔、底层民众、非人类的物种等。比如在《偷骨髓者》中,只有加拿大本地土著才有做梦的能力,而白人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所以该小说既是主人公逃离生态灾难的旅程,也是两种文明方式在大的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较量。
当然也并非所有气候小说都符合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部分气候小说仍然专注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反思并没有融合女性主义的维度。对这一小部分气候小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是持批判态度的,比如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加德做了严厉批判,她分析了“未能挑战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物种主义和性别原教旨主义的气候变化叙事作品”,指出它们往往是“由男性作家创作的”,是“非女性主义的”甚至是“反女性主义的、性别主义的”[10]。不论某一部具体的气候小说作品是否符合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笼统来说,从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对气候小说进行解读毫无疑问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