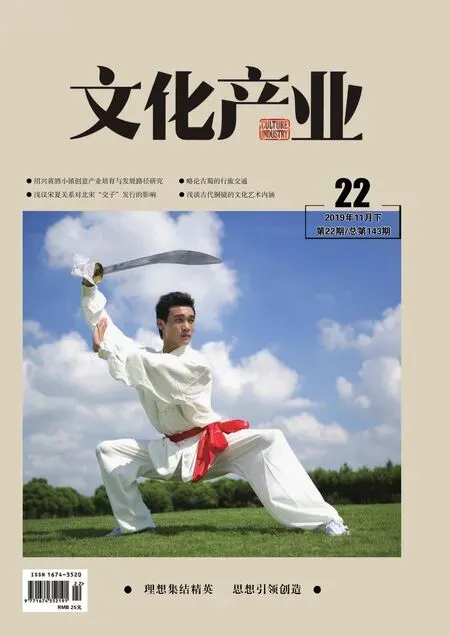对《长生殿》李杨爱情的现代审视
◎蒋郁葱
(北海职业学院 广西 北海 536000)
清代洪昇的剧本《长生殿》在艺术表现上取得了极高成就,并在戏曲史上赢得了“千百年来曲中巨擘”的美誉。获得这么高评价的原因各有说法,但在其以俱佳的曲辞与音律、并茂的文情与声情,表现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的态度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对于唐明皇李隆基和杨玉环这两个历史人物,其真实的两性关系或者说两人的爱情生活是否如各种传说或各种文献,也包括《长生殿》所记载的那样,本文不做考证。
我很同意这种看法:在一切艺术品里,作者意图中的世界和作品实现出来的世界,或者说作者的愿望和实践,是有区分的。在此,我只从作品出发,探索洪昇《长生殿》中“情”的内涵。
一、剧本故事透视
洪昇以其超越前人的文学表现才能特别是结构故事和运用语言的才能,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有着复杂心理过程的爱情故事,要透视这个故事,剧本本身应该最能说明问题。
作者在剧本开头即宣称了自己对“情”的态度:
《满江红》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共南北,两心哪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然悭,无情耳。感金石,回天地。召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
结合剧情和剧本中不断透露的观点,对以上这段开头分解成如下几点来理解:
洪昇对“今古情场”即凡间的情场表示了深切的怀疑甚至否定,而到天上实现“终成连理”的前提须“精诚不散”。何谓“精诚”?从剧本来看,是李杨二人的“悔”。
两情应当生死与共,无缘皆因无情,有情又生烦恼。情不独存于两性,臣忠子孝,亦由情至。
借太真外传谱新词,目的或原因是“情”。联系整个剧情分析后发现,作者所说的“情”,不独指爱情,还有更多的内涵,比如君臣之情、亲子之情。这就表明,爱情不仅仅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它必定牵扯到社会、伦理、道德、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等意识形态。李杨故事启示了“爱情变动不居,且不可能长久”。虽说无情可转换成有情,但长久保持和延续,只可能在虚幻的天上。因此,作者浓墨重彩地描述李杨分分合合,并最终把他们送上了天宫之后,自相矛盾地唱出了:“《永团圆》神仙本是多情种,蓬山远,有情通。情根历劫无生死,看到底终相共。尘缘倥偬,忉利有天情更永。不比凡间梦,悲欢和哄,恩与爱总成空。跳出痴迷洞,割段相思鞚。金枷脱,玉锁松。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

[清]吴辅卿《长生殿》立轴
二、对李杨爱情的现代审视
按现代人对两性关系的理解:爱情应建立在彼此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但也并不排除生物基础。反过来说,爱情不是一种单纯的性关系,它同时具有高级的情感包括心理的、美感的和道德的成分。而心理、美感、道德,在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形成条件和不同表现,稳定性因素和不稳定性因素同时存在。所以,“什么样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这个问题,并没有一定的答案。
按现代两性关系解读的基本原则,一口咬定《长生殿》李杨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爱情,这是没有理解“爱情”的不可定义性,是脱离文本实际的纯主观判断。抓住李杨关系中权利地位、年龄差距等不放,来审判两个主人公的爱情——一个贵为天子,一个国色天资,必定得出其关系不过是权力与美色的相互利用,而非精神人格上的相互吸引或互补的论断,这种看法无疑是缺乏科学依据和主观片面的,但《长生殿》本身情节上的牵强和不合人情逻辑,确实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没有人会怀疑《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因为他们之间没有门第的差异,也不是建立在“性感”基础上(就姿色而言,薛宝钗显然比林黛玉更具吸引力)。两人之所以第一次见面就有似曾相识之感,是由于审美心理和文化心理积淀的缘故,是“前生注定”。没有世俗动机,宝黛爱情自然是崇高而值得称颂和同情的,《长生殿》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关系,则缺乏这样的交代,两人产生爱情的基础不符合现代价值标准。如写两人定情时,虽反复咏唱“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两主角表现得非常坚贞,但这份“情”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剧本只透露了一句:妃子世胄名家、德容兼备,这只是李隆基对杨妃家庭出身和基本面貌的认可。那么杨妃爱李隆基的又是什么呢?剧本没说,却只反复强调“君恩”——一个爱另一个“德容兼备”,另一个却只是对这一个“感恩戴德”,也就是说,两人在长期接触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价值观念和性格气质的彼此认同,无怪乎有人说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了。
《情爱论》作者瓦西列夫中认为:爱情的结构是生物——社会的特殊结构,所以人的生命的本能只有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能表现出来,人是用意识的宏伟和优美来补充本能的力量的[1]。从李杨爱情的发展来看,李杨关系也有一个从生物因素占多到社会因素占多的进步过程。李隆基贵为天子,后宫无数佳丽,要使这样一个帝王钟情于一个女子确实很难。但第2出中,唐明皇以金钗钿盒之信物与杨玉环定情,双方都表现得非常真挚,二人山盟海誓:“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接着第4出描写两人爱情生活的穷奢极欲,爱情之火熊熊燃烧。遗憾的是,很快,李隆基就不能坚持下去了,滥情本性开始暴露,又施爱于他人。作为帝王,他显然无法理解爱情的排他性。李隆基不但放纵自己的肉欲,还谴责杨贵妃的嫉妒心,不高兴了索性将其谪出宫去。从这点看,李隆基感情中肉欲的成分明显多于精神的爱恋。而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在男女爱情关系中,男性更容易“见异思迁”,女性更容易走向痴情。于是女方不理解男方感情欲望的兔起鹘落,男方厌烦女方由爱生妒的自私狭隘,两个人的关系陷入不平衡也无法平衡的泥沼。要打破这种不平衡,或者将之调整到彼此能接受的程度,得靠双方各自作出让步和努力,即所谓“用意识的宏伟和优美来补充本能的力量”。《长生殿》对此虽有一些情节上的交代,使得两人感情关系的发展并非毫无逻辑,只可惜这叙述过程太简单,心理描绘笔墨粗浅,缺乏幽微和细致的美感,从而显得苍白无力[2]。
剧本前一部分写实,写出了李杨悲剧的必然结果,以此表明爱情的虚幻;后一部分写幻,鼓吹区别于世俗人间的天上的爱情,来证明“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的可能。李杨二人共经历了三次离合,而使两人关系发生质的飞跃或者精神层面的提高的,是马嵬之变。此前,两人已各自作了心理调整并建立和稳固了爱情关系,但马嵬之变使情缘突然中断。紧接着,唐明皇失佳人之后的痛苦显得很真挚,杨贵妃的“悔”也显得更诚恳,情感性质变化之快,让读者感到突兀。但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因为通常在死亡面前,在与所爱的人离别后,爱情会变得纯洁,甚至比之前更坚定。
为了情缘,李杨可谓吃尽苦头,生死离别。在实际生活中,对死者而言一切都不再有存在的意义,生前没有把握好的东西死后更不会拥有。洪昇袭白居易《长恨歌》幻想之力,亦将两主角送入天庭,但他并没有像白氏那样,把理想的爱情寄意于天庭,这正是洪昇的创新之处,显示其对爱情更独到、更本质的理解。
首先,李杨爱情总是“合”时不及“离”时真切深沉。这意味着爱情本身固有的虚幻性——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了才知可贵,杨贵妃死亡的现实加剧了唐明皇的悔恨。因此,《长生殿》后部分极写李杨忏悔之情,客观上起到了劝导的作用——要使爱情永生,得时时检点自己的所作所为,否则可能乐极生悲,错失良缘。
其次,作者一再表述人间爱情的短暂和不可靠。然而在把李杨送入忉利天重圆后,又发出了“双星作合,生忉利天,情缘总归虚幻”的喟叹,这岂不意味着李杨天上复合也不过是一场幻梦?既然人间天上都没有爱情,那么哪里有呢?“不比凡间梦,悲欢和哄,恩与爱总成空。”一个“空”字成为最终答案。
费尽心机所求证的“情”,最终以“空”作结,这大概就是戏剧家洪昇从佛学中得来的最终感悟[3]。
三、结语
我们审视当代无数爱情故事会发现,许多爱情原本就是自相矛盾的,《长生殿》也正是一部自相矛盾却能透视人性本质的作品。这基于作者自身人格的矛盾。在屡次的失意中,洪昇艰难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和创作之路,一方面有对自由和深情的向往,另一方面又对功名心存希冀。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爱情,虽然跟政治血肉相连,但毕竟不似民间小儿女,无需经过从禁锢到超越的艰难过程。《长生殿》能把李杨这两个特殊身份的人的爱情写得如此缠绵悱恻,已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力,这也是个体追求情爱,肯定人欲,讴歌情痴,赞赏情趣的表现,体现了与时代主流迥异的审美精神[4]。
行文至此,想起现代作家三毛的一句话:爱情有若佛家的禅,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是错。将这话作《长生殿》“爱情”的注脚,倒也贴切。
- 文化产业的其它文章
- 浅议宋夏关系对北宋“交子”发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