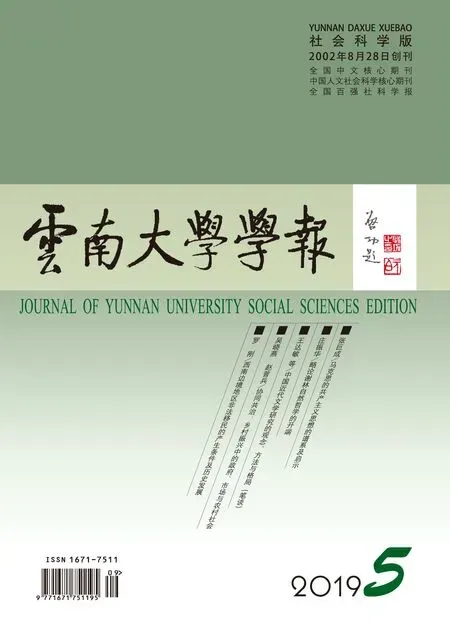查尔斯·泰勒的脱嵌理论及其影响
陈志伟
[广州大学,广州 510006]
嵌入(embedding)与脱嵌(disembedding)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核心概念。嵌入意味着自我认同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想象、宇宙想象,三者之间组成相对稳定的结构;脱嵌意味着自我认同的转型,意味着社会想象与宇宙想象的重构。在讨论大脱嵌(the great disembedding)的时候,泰勒说道:“社会重构也朝向个体组成”“社会生活的新式自我理解的成长和加固,这种自我理解赋予了个体以前所未有的地位”。(1)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46.大脱嵌意味着人们的自我认同、社会想象和宇宙想象的巨大转型。现代性自我的形成本身是同大脱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个体性的自我是大脱嵌的产物。在大脱嵌之前,人嵌入到特定的社会和宇宙之中,自我只不过是大存在链(great chain of being)中的一环,自我被它规定和赋予意义;在大脱嵌之后,自我理解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自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大存在链的一个环节,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我是价值和意义的来源,自我规定世界而非单纯地被世界所规定。总之,在大脱嵌之后,现代性的自我开始逐渐形成。大脱嵌带来了自我、社会和宇宙的巨大转型,带来了意义深远的现代性效应。一般认为,大脱嵌是西方近五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它与现代社会的形成同步。但是,其实早在轴心时期,就已经隐含着了大脱嵌的最初的源头。本文也将聚焦于对最初源头的探讨,从根源处把握大脱嵌。嵌入是脱嵌的逻辑前提,大脱嵌所说的无非是从嵌入到脱嵌的转变过程。下面,我们就顺着“嵌入—脱嵌”的思路来展开我们的探讨。
一、“嵌入—脱嵌”与自我认同
在自我认同中,“嵌入”与“脱嵌”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从嵌入到脱嵌的转变,意味着自我认同的转型,意味着自我理解的不同模式。泰勒认为,我们的自我认同总是在一定的“背景框架”之中展开的,人不可能完全的脱离于“背景框架”而理解自身。从一定意义上说,泰勒所持有的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先验整体论”理论。在泰勒看来,人不可避免地处于一个共同体之中,不可避免的使用着语言,“自我只会存在于我所说的‘对话网络’中”。(2)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6.共同体之中的人通过语言,在对话中理解了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从而获得了自我认同。也就是说,对社会的嵌入是自我认同之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完全的脱嵌。“大脱嵌”意味着自我认同的一次巨大转型。转型之后的自我,依旧生活在社会之中,依旧使用语言,依旧具有“背景框架”。脱离了嵌入是不可能具有自我认同的,无嵌入则无“自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脱嵌”的不可能。我们的背景框架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在某些特殊时期,这种变化可以是非常剧烈的,以至于自我从之前的框架中脱离开来,而进入到一个非常不同的新框架之中。这一过程,泰勒就称之为“大脱嵌”。“大脱嵌”并不意味着人不再需要嵌入,它意味着嵌入的方式以及所嵌入的背景框架发生了巨大的转型,框架日益成为内在性的框架,“现代人生活于一种内在的框架中”。(3)张容南:《查尔斯·泰勒对世俗时代精神状况的剖析与反思》,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正是通过这样的大脱嵌,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才得以最终形成。个人主义本身是大脱嵌的产物,对于脱嵌之前的人来说,个人主义是非常陌生的东西。无脱嵌则无“个人”。总之,人的自我理解以嵌入为前提,人的自我理解的转型则以脱嵌为前提,嵌入与脱嵌同自我认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大脱嵌所涉及的不同方面。
二、“嵌入—脱嵌”的两个方面:社会想象与宇宙想象的不同模式
(一)社会想象的不同模式:对社会的嵌入与脱嵌
泰勒在考察人们对于社会的嵌入与脱嵌的时候,主要是从“社会想象”入手的。社会想象意味着“使得想象成为可能的,对于社会的普遍的理解”。(4)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23.社会想象指的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集体想象,它区别于反思性的理论探讨,而是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
泰勒通过对早期宗教的考察,发现了社会嵌入的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不可分割性。对于迷魅时期的人们来说,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是不可分的,二者混而为一,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生活经验。其次,早期宗教的社会嵌入是一种集体性的嵌入。早期宗教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宗教仪式、宗教行为的完成依赖于全体社会的集体参与。当然,这并不否认在宗教仪式当中,不同的成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至关重要的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共同参与,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一个宗教仪式得以可能。迷魅时期人们的社会嵌入,只能是一种集体性的嵌入。最后,早期宗教的社会嵌入具有层级性。嵌入只能是集体的嵌入,但是集体当中的不同能动者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这些特殊角色的背后,是当时的人们所默认的特殊的意义背景框架。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一个层级性的“大存在链条” (great chain of being),不同的存在者居于不同的层级,且受到整体性的存在链条的规定。自我不可能跳出这种存在链条,不可能脱离社会而成为一个“个体”。
然而,脱嵌之后的现代“世俗性”社会,却提供了一种包含着众多选项的可能的信仰空间。根据泰勒的理论,而这种可供选择的空间是世俗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只有在脱嵌之后的世俗社会中,才可能具有这样的空间。对于嵌入性的社会来说,多个信仰的选项是无法想象的,不信更是不可能的。宗教构成了自我的认同的基础,赋予了“我是我”的基本身份,脱离宗教,则无法理解自我。与之不同,在脱嵌之后,人们的身份认同不再依赖于宗教,宗教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宗教成为了众多选项中的一项,“世俗性则越来越成为一个默认选项”。(5)张容南:《查尔斯·泰勒对世俗时代精神状况的剖析与反思》,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社会的想象图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不再建构在宗教之上,而是有其他的根基。社会想象的转型同时也意味着人们的自我想象的转型。自我逐渐脱嵌于宗教,个体性自我逐渐形成。个体性,意味着自我的身份认同的巨大变迁。在嵌入性社会中,个体的独立存在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脱离这个集体。在脱嵌之后的社会中,个体性自我才第一次变得可能。原子主义式的自我其实是脱嵌日益加深的结果。在脱嵌之后,社会也从一个有层级的社会,逐渐的变为一个扁平的社会。社会由地位平等的个人所组成,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存在等级上的差异。总之,在经历了大脱嵌之后,人们的社会想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理解社会的背景框架已经完全不同。新的社会建立在个体性之上,而非以特定的宗教信仰为根基。
(二)宇宙想象的不同模式:对宇宙的嵌入与脱嵌
大脱嵌不单单意味着社会想象模式的变更,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想象模式的变更,泰勒称之为宇宙到寰宇的转型(shift from cosmos to universe)。泰勒说道:“从前我们生活在‘宇宙’中,而现在我们则被包含在‘寰宇’中。”(6)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59.这里的“从前”指的是在“大脱嵌”之前的迷魅时代,那时候人们生活在宇宙之中,并且深深的嵌入到宇宙之中;而现在的时代则是“大脱嵌”之后的祛魅时代,现代人已经经历了对宇宙的脱嵌的过程,他们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同于古代人的世界,“将宇宙感知为一个有意义的秩序,这已经被颠覆了”。(7)Andrew O’Shea, Selfhood and Sacrifice: René Girard and Charles Taylor on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 p.211.大脱嵌之后的现代人已经不再生活于“宇宙”之中,而是处在“寰宇”之中,人们已经从宇宙的宏大秩序当中抽身出来。泰勒说道:“从宇宙中分解出来,意味着人类主体不再被理解为宏大的、赋予意义的秩序的构成性因素。”(8)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93.
泰勒赋予“宇宙”以丰富的含义:宇宙是充满了神灵、鬼魅和魔力的世界;宇宙是有限的世界;宇宙是静态的世界;宇宙是有层级的世界等等。从宇宙到寰宇的转型则意味着从迷魅的世界到祛魅的世界、从有限的世界到无限的世界、从静态的世界到演化的世界、从有层级的世界到平等的世界的转变。
生活于宇宙中的人们,是深深地嵌入到宇宙之中的。这种“嵌入”是一种活生生的经验,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宇宙中充满了各种神秘的“影响力”,不但神灵、鬼魔可以具有这样的影响力,甚至一些非人格的物体,如圣物,也可以具有“影响力”。这些影响力或善或恶,弥漫在整个宇宙之中。人就生活在这些影响力交织而成的力量场之中,人无法摆脱它们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被它们所渗透。泰勒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这个时期的自我称之为“可渗透的自我”。自我嵌入到宇宙的大存在链条之中,或者说,自我本身就是大存在链条的一个环节,自我不可能脱离它而存在。宇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神圣的存在,其本身就充满意义。人嵌入到社会之中,社会嵌入到宇宙之中,神则位于宇宙之内。对于早期宗教的信徒来说,宇宙是神圣的存在,神灵就在宇宙之中。也正是因为如此,宇宙才具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作用于人的结果就是人对宇宙的不可避免的嵌入。而且,这种嵌入性是一种集体的嵌入,自我必须要在一个社会之中才能够应对宇宙中的神灵等,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身份认同。对于早期宗教时期的人来说,内在心灵与外在的世界之间尚没有明显的界限,“内在化”的进程尚未开始。人的心灵与宇宙之间是贯通在一起的,宇宙中的神灵、鬼魔乃至圣物等,都可以通过其“影响力”而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的心灵。对于迷魅时期的人来说,不但心灵与世界之间并无明显的内外区分,身体与精神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宇宙中弥漫着的影响力可以同时作用于人的身体和精神。例如,早期宗教的人可以凭借着“充上力”的圣物而“净化”自己的心灵,从而让身体上的疾病获得医治。
总而言之,早期宗教时期的宇宙,具有层层的嵌入性的解构:人嵌入于社会,社会嵌入于宇宙,宇宙中则包含着神灵与魔力。这种嵌入性的结构意味着宇宙是一个贯通的整体,人、神灵与万物之间彼此相连。这种特殊的宇宙想象模式同社会想象的模式、自我想象的模式紧密的关联在一起。古代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特殊的背景框架之中,并通过这种框架赋予其生活以意义。例如,在古人看来,干旱的时候,通过集体的仪式向神灵祈雨是非常有意义的行为。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古人的这种向神灵祈求降雨的行为变得难以理解,现代人倾向于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降雨的现象。这说明,现代人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同于古代人的世界了,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再生活于“宇宙”(cosmos)之中而是生活在“寰宇”(universe)之内。现代人在内在的心灵与外在的世界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泰勒说道:“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观念或者情感考虑为‘内在于’我们之中,而把这些精神状态所关联的世界上的客体当成是‘外在的’。”(9)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11.世界当中不再有神灵与魔力,即便有,它们也无法轻易地侵入到内在性的心灵之中。伴随着鬼神的在世界中的退场,意义也从世界转移到了心灵之中。大脱嵌之后的世界已经是祛魅的世界,世界已经被“中立化”,世界变成了自我之外的“客观”对象。世界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自然规律,而人一旦掌握了这些自然规律就可以掌控这个世界。从嵌入性的宇宙到脱嵌性的寰宇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以及对自身的理解方式。
三、脱嵌的最初源头及其引发的效应
(一)轴心时期的宗教所隐含的脱嵌源头
对于早期宗教时期的人来说,人嵌入社会,而社会则嵌入到宇宙,神则居于宇宙之中,泰勒说道:“我们以这种方式深深的嵌入到社会中,随之也深深的嵌入到宇宙之中。”(10)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55.因此,神与人是相互贯通的,人可以在宇宙当中经验到神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早期宗教那里,神与人同处一个宇宙,人可以时时感受到神的在场。
但是,到了轴心时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泰勒接受了雅斯贝斯的理论,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之中,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希伯来先知的出现,重塑了宗教形态,新的宗教得以产生,泰勒称之为轴心时期的宗教或者高级宗教。对于这些高级宗教来说,它们具有明显不同于早期宗教的特征。在西方,这种新特征尤其以犹太教—基督教的“无中生有”的观念为代表。上帝是从无中创造了世界,而上帝本身显然是超越于作为其创造物的世界的。创造者从根本上高于被造物,超出于被造物,而这也就意味着“将上帝从宇宙之中分离出来,并置于宇宙之上”。(11)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2.由此,轴心时期的宗教打破了早期宗教的固有的嵌入链条。上帝作为首要的脱嵌者而存在,上帝超出于宇宙之外。当然,按照基督教神学的理论,上帝一方面具有超越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内在性,上帝在超越于宇宙的同时又内在于宇宙。但是,如果我们从存在论上来考虑,上帝的存在地位显然从根本上区别于宇宙的存在地位。基督教的上帝内在于宇宙与早期宗教的鬼神内在于宇宙,是完全不同的存在论图景。在基督教那里,上帝存在于宇宙之先,超出于宇宙之外;而在早期宗教那里,鬼神只能在宇宙之中存在,而不可能超脱于宇宙之外。
因此,在轴心时代,出现了上帝与宇宙的脱嵌,而随着上帝与宇宙脱嵌,随之而来的是此世与天国的脱嵌。在轴心时期的宗教中,这种“超越性”开始重新塑造人们的世界想象图景。存在着一个我们暂时生活于其中的可朽的世界,还存在着可以永远生活于其中的永恒的世界。同天国的永恒幸福比起来,此世的福祉就显得并不是最重要的了。这也就意味着,人间之善、人间的福祉受到了质疑,进而,其背后的社会与宇宙的秩序也受到了质疑。
一方面,不同世界之间相互脱嵌,即此世脱嵌于天国;另一方面,不同的善之间相互脱嵌,即人间的善脱嵌于“至善”。泰勒认为,不单基督教是这样的,柏拉图的“理念”、中国的“天”、佛教的“涅槃”(需要指出的是,在笔者看来,泰勒对佛家与儒家的理解未必准确,但他对西方传统的把握还是非常精准的)都标识着一种超出人间之善的至善维度。至善的超越性意味着它在宇宙之上或者宇宙之外,泰勒说道:“现在超越性或许是指宇宙之上或者宇宙之外。”(12)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2.在泰勒看来,宇宙与善之间相互关联,宇宙的脱嵌同时也必然意味着善的脱嵌。在轴心时期,一种全新的超越性的维度得以确立。相对于早期宗教,人们对善的理解方式、对宇宙的想象图景,都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
“大脱嵌”在轴心时期就已经开始发挥其作用,虽然它远未完成。随着大脱嵌的初步展开,人们对待善恶的态度和宇宙的态度也开始发生着变化。对于早期宗教时期的人来说,宇宙之中弥漫着神灵、鬼魔和它们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或善或恶,自我作为可渗透的自我,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影响。人们虽然可以借助于集体性的宗教仪式来祈求人间福祉,但是神灵的意图有善有恶,对人们的影响也有好有坏。泰勒说道:“这并非是说一切都以追求人类的繁荣昌盛为最终目的,神灵也可能有其他的目的,有时候有些神灵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有害的影响。”(13)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58.神灵并不总是善待人们,恶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对于他们来说,善恶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绝对的、超越的善。早期宗教时期的人们对宇宙秩序、社会秩序所采取的基本的态度就是顺从与接受。但对于高级宗教时期的人来说,“它不再是万物秩序的组成部分,不再应该原样接受,而是必须要对恶有所作为”。(14)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3.按照基督教的理论,万物都是全善的上帝的创造物,因此,恶在本体论上不再是必要的,恶成了“不完美”“善的缺乏”。既然恶不再是万物秩序的必然的组成部分,人也因此无须再忍受恶。同样,人们对社会和宇宙的态度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例如,早期宗教时期的人们会祈求宇宙之中的神灵,以获取人间的福祉,而高级宗教时期的人们则会祈求宇宙之外的上帝,以便脱离人间、进入天国,享受天国永恒的喜乐。
轴心时期的从早期宗教到高级宗教的转型,为大脱嵌敞开了大门。虽然它并未立刻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早期宗教的特征依旧以改良的形式存在于轴心时期的世界之中,但是它为大脱嵌带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空间和前景。在轴心时期,人与旧有的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之间开始有了裂痕。随着超越性的全新维度的出现,此世的福祉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人们开始追求此世之外的超越之善。这种追求不再像早期宗教时期那样必然地依赖于集体,人甚至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而求得。由此,个体性的可能空间得以敞开。社会的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出世的”“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社会团体,如僧团、修道会等等,他们所追求的是更高的维度。
(二)轴心时期的脱嵌所引发的效应:个人主义的崛起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轴心时代高级宗教的兴起,确实为大脱嵌敞开了可能性的空间,但这仅仅是最为初步的脱嵌,大脱嵌远未完成。作为大脱嵌之最终结果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规训的世俗社会、机械式的客观宇宙还远未到来。轴心时期的高级宗教隐含着大脱嵌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还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完全展现自身。早期宗教的自我、社会和宇宙的想象模式依旧以各种方式保留在轴心时期的现实社会之中。轴心时期的高级宗教隐含着平信徒与修士、此世与天国、人间福祉与更高的善之间的张力,但是,在现实社会的层面,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等级互补的关系。例如,随着高级宗教的出现,逐渐产生特殊的修士阶层。对于修士来说,其所追求的并非此世之善,而是永恒的天国之善。这些少数的精英处于世界的边缘,他们试图超脱于此世的社会和宇宙,试图从旧有的大存在链条之中抽身出来,泰勒甚至认为他们带来了“特定形式的宗教个人主义”。(15)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54-155.但是,这种脱嵌是不完全的。这些精英或许有了“个人主义”的意识,但是当时的社会、世界依旧是嵌入性的,而且这种嵌入性尤其表现为“互补性”。例如,平信徒和修士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关系。平信徒并不像修士那样专注于天国之善,他们依旧渴求此世的人间之善,并通过给修士做奉献的方式来祈求上帝护佑他们的人间福祉。因此,当时的社会依旧是嵌入性的社会,脱嵌尚未完成。但是,这并不否认在基督教中蕴含着的脱嵌的逻辑。《圣经》中的一些章节就号召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庭,脱离旧有的社会纽带,成为天国的子民。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人应该遵循神圣的要求而非此世的要求,其中蕴含的逻辑是:人应该脱离既有的团体,作为“个人”来响应上帝的召唤。与早期宗教不同,基督教中的这些思想隐含着一种全新的自我认同模式——作为个人的自我。
在泰勒看来,个人主义并非是现成地存在在那里的。个人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自我认同模式,而这种自我认同模式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产生的,它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想象和宇宙想象。对于早期宗教时期的人来说,“个人”是无法想象的,对于当代的人来说,“个人”则是自然而然的。之所以会有这样巨大差异,是因为意义背景框架发生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正是通过从嵌入到脱嵌的转变才得以完成的。
轴心时期的宗教为个人主义敞开了可能性的空间。在随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基督教中所蕴含着的这种脱嵌的逻辑开始逐步地显现。不单单是修士们具有了个人意识,整个的社会成员也开始逐渐把自身理解为“个人”,其中关键性的环节有“宗教改革”“自然神论”“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等等。泰勒说道:“大脱嵌的最后阶段大部分由基督教提供动力。”(16)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8.但是,泰勒也敏锐地觉察到脱嵌所带来的“败坏”。基督教之中蕴含着脱嵌的源头、蕴含着个人主义的逻辑,但其最终的指向是超越于此世的天国,而不是人间的福祉。基督教反对旧有的嵌入,倡导脱嵌,从而让人们摆脱此世,不再是世人。但是,“它不知如何就变成了非常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世人终究胜利了”。(17)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8.世人的最终胜利,也就是大脱嵌的最终完成。人类从信仰时代进入到了世俗时代,“世俗时代从根本上区别于信仰时代”,(18)Florian Zemmin, Colin Jager, and Guido Vanheeswijck edited, Working with A Secular Ag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harles Taylor’s Master Narrative,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6, p.28.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起源于轴心时期高级宗教的脱嵌效应,最终应用到了宗教自身上面。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推进,超越性的维度逐渐被人们所抛弃,“世俗的现代性非常反对超越性,并以此在它的人类概念的周边建立了一道隔离线”。(19)Andrew O’Shea, Selfhood and Sacrifice: René Girard and Charles Taylor on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 p.240.伴随着超越性的退场,宗教在西方现代社会中日渐式微,“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对宗教非常的不友好,进而否认渴望超越性的固有力量”。(20)Andrew O’Shea, Selfhood and Sacrifice: René Girard and Charles Taylor on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 p.256.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变成了众多选项中的一个,而不再是唯一的选项,“随着个人化、实用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参与的漫长趋势的结束,宗教仅仅成了一个选择的问题。”(21)Germn McKenzie, Interpreting Charles Taylor’s Social Theory on Religion and Seculariz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p.120.伴随着宗教逐渐退场、世俗化日益加深,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得以最终确立,“个人原子化趋势不断增强,社会正逐步变为孤独个体的功利性结合,共同体所蕴涵的意义感和认同感在慢慢消失”。(22)韩升:《自由主义视野的表达与批判——查尔斯·泰勒的共同体概念》,载《 哲学动态》2009年第4期。
总之,从轴心时期的最初源头开始,脱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宗教改革、自然神论、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等等),才最终得以完成。现代人的自我认同、社会想象以及世界想象,都是在大脱嵌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些认同模式最终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积淀在我们的意义背景框架之中,以至于我们“日用而不知”,成为了我们理解自我、社会和世界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正如麦肯齐(McKenzie)对泰勒的评论:“在他看来,它包括‘背景理解’,这种背景理解是沉默的,前反思的,嵌入到所有的典型故事、想象和意识形态之中,形成了一种传统或者公共的记忆。这种共同的理解,帮助我们得以知道自我、社会中的角色和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意义,并且通过实践而表达出来。”(23)Germn McKenzie, Interpreting Charles Taylor’s Social Theory on Religion and Secularization:A Comparative Study,p.113.从轴心时期而来的大脱嵌,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带来了个人主义的崛起,促进了现代性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