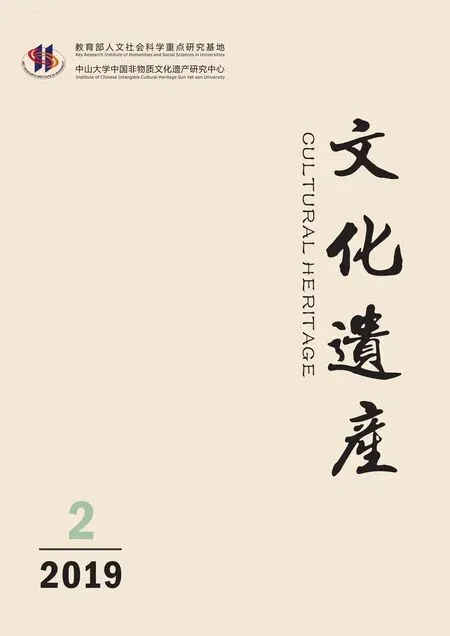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共同体*
宋俊华
一、引 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适应人类非遗保护需要而兴起的。
从2001年我国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3年后更名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不久,国内一些高校就开始建立非遗研究机构并酝酿建立相关学科,如2002年中山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相继建立了非遗研究机构,同年 10月,中央美术学院还举办了“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会上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注]乔晓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学教育》,《集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拉开高校非遗学科建设的序幕。
2003、2004年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正式入选广东省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标志着非遗研究正式成为我国高校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006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名单,中山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以下简称“非遗学”)二级学科名列其中,标志着非遗学在高校研究生教育序列被正式确认。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相继在民族学、美术学、艺术学等学科下开设了非遗方向的研究生专业。
2006年11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重庆文理学院设立工作站,并召开了“首届高校文化遗产学学科专业建设研讨会筹备会”,会上中山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四川大学、南京艺术学院、重庆文理学院等高校学者共同倡议举办高校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研讨会,以推动非遗学发展。2008年4月4-7日,重庆文理学院主办了“中国高校首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10年5月1日,苏州大学主办了“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吴论坛暨中国高校第二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11年8月2-3日,中山大学主办了“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暨第三届中国高校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15年、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分别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中文系、晋中学院晋中文化生态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了3次非遗学科建设会议。这些研讨会的召开,大大推动了非遗学科建设的发展。
十多年来,围绕非遗学的学科理论、课程设置等问题,各高校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产生了一批优秀成果,为非遗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2017年非遗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笔者曾阐述了非遗学科建设面临的三个问题:1.非遗学是“研究之学”还是“学科之学”?2.非遗学是“补缺之学”还是“独立之学”?3.非遗学如何走向独立?笔者认为,非遗学必须且只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学”,才是有意义的[注]2017年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中文系联合主办“2017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研讨会暨全国高校非遗保护研究联盟会议”,会上笔者做了《关于非遗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的发言。。非遗学科要独立,就要遵循学科独立的基本规律:既要有知识体系(对象、范式)的独立,又要有体制(学科专业、人员编制)的独立,而实现二者独立的关键就是要构建非遗学科共同体。
二、什么是非遗学科共同体?
学术界一般认为, 共同体(Community)(或译为社区)概念源于德国古典社会学家裴迪南· 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他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11schaft )中指出,共同体(Gemeinschaft,或译为礼俗社会)是比社会(Gese11schaft,或译为法理社会)更为理想的群体关系类型 ,“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 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众性的, 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 从出生之时起, 就休戚与共, 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注][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53页。显然,滕尼斯的共同体是指一种前工业时代的,导源于人的本质意志的,以血缘、地缘和文化等为纽带的人类结合体。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共同体概念几经转型和发展,已成为具有地域性社会组织、共同情感和互动关系等特征的更为广泛的概念。1955年希勒里(G.A.Hillery)在《共同体定义:共识的领域》统计的共同体定义有94种,1971年贝尔(C.Bell)和纽柏(H.New by )统计的共同体定义为98种,到了1981 年, 美籍华裔社会学者杨庆堃统计的共同体定义则多达140 多种。在这些定义中,共同体通常被描述为两种类型,一是地域性类型(如村庄、邻里、城市、社区等地域性社会组织), 二是关系性类型(如种族、宗教团体、社团等社会关系与共同情感)[注]李慧凤、蔡旭昶:《“共同体”概念的演变、应用与公民社会》,《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地域性类型共同体以腾尼斯所讲的地缘文化为基础,强调了地域性社会组织是共同体概念的核心,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美国芝加哥学派帕克(R.Park)和我国费孝通等为代表。帕克认为,“被接受的共同体,本质特征包括:一是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二是这些人口不同程度地完全扎根于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 三是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注]Robert Ezra Park : Human Ecology(原文发表于The American of Sociology,62 (July):1-15),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受帕克影响,费孝通把美国芝加哥学派所用共同体概念Community翻译为“社区”,即指我国社会基于地缘关系,在特定“地域”范围内活动形成的人类结合体。
关系性类型共同体以腾尼斯所讲的共同的、密切的人群关系为重点,强调共同情感和互动关系是共同体概念的核心,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涂尔干(Emile Durkheim , 一译“迪尔凯姆”)、韦伯(Max Weber )、鲍曼(Zygmunt Bauman)等为代表。涂尔干在1893 年发表的《社会分工论》中使用“机械团结”来表述他的共同体概念。他认为“机械团结”代表集体类型,是“个人不带任何中介地直接系属于社会”,而与之相对的“有机团结”则代表了个人人格, 即“个人之所以依赖于社会,是因为它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注][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7年,第89页。。在共同体社会中个人属于集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观念远远超过了成员自身的观念,个性没有张扬的机会。马克斯·韦伯则将“共同体”概念运用得更为宽泛, 包括家族共同体、邻里共同体、人种共同体等[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3-135页 。。鲍曼认为,“共同体”这个概念传递的是一种充满温馨的良好感觉(feeling),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注][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随着社会发展,后来的学者也把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也运用于共同体研究,使得共同体从上述学者所讲的传统封闭的、依附性、排他性关系结合体,发展为内生于现代社会关系的契约结合体。
本文认同关系型共同体的说法,共同体本质是一种基于互动关系的人群结合体。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人群,有不同的互动关系,就会有不同的共同体。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在界定非遗概念时,也用了“共同体”的概念,非遗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其中“社区”就是指“共同体”,即非遗项目持有人或传承人所组成的共同体,与腾尼斯所讲的传统社会共同体有内在关系,是特定群体的血缘、地缘、业缘、族缘等关系的反映,非遗项目是共同体存续的重要的符号。
与基于特定非遗项目的共同体相似,非遗学科共同体也是基于一个共同对象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但与滕尼斯等所讲的传统共同体不同,它不是基于传统封闭的、依附性的、排他性的地缘、血缘、族缘或某种信仰、情感的共同体,而是建立在现代的、自由选择的、平等的、互利的契约性共同体,是以非遗学科为共同追求的,具有明确学科归属和学科意识的科学共同体。非遗学科共同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具有明确的学科归属和学科意识。非遗学科共同体成员主张把非遗保护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发展,有明确的学科归属和学科意识,以确保参与者开展学科研究的独立性和系统性。
其二,具有强烈持续的学科责任感和使命感。非遗学科共同体成员在传承和保护非遗上有共识,有强烈的愿望,愿为学科独立而主动、持续性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其三,具有平等性和互利性。非遗学科共同体成员平等地开展学科案例和积累理论研究,基于互利原则约定了共同的规范和标准。
其四,认可文化中间人的身份定位。非遗学科共同体成员,有的是某个非遗项目的传承者,有的是某个行业的管理者,有的是来自传统学科的学者,在进入非遗学科共同体后,都会以普遍意义上的(非特指的)非遗传承和保护为使命,是非遗传承、保护与非遗对外传播的居间人,是非遗社区与外部沟通的桥梁。
三、构建非遗学科共同体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构建非遗学科共同体面临的机遇
所以,从国际国内环境来看,构建非遗学科共同体正在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
第一,较为完备的非遗保护法规制度和体制机制,既为非遗保护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又为构建非遗学科共同体创造了法制和体制条件。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6年4月生效),是各缔约国开展非遗保护的国际准则。截至2018年5月,已有178个国家加入了这个公约。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或核可的《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等有关非遗保护的国际文件,为非遗学科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基本准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评审非遗名录过程中,所建立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机制,为构建国际非遗学科共同体搭建了机制性平台。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各地非遗保护条例为主导以非遗保护政策为辅的较为完整的非遗保护法规政策体系。同时也建成了国家、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区(县)等四级非遗保护管理和实施体制机制。这些法规、政策和体制机制,充分保障了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持续有序开展,也为我国建立非遗学科共同体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第二,我国非遗资源十分丰富,保护传承活跃。
我国历史悠久,传统积淀深厚,是个非遗资源大国。2010年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一次全国非遗普查结果,全国非遗资源数量达87万项。截至2018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类非遗名录项目共有40项,总数世界第一。此外,我国还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项目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目前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1372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068人。
吉尔布雷斯的操作步骤是标准化管理的典型,后来有人将其的砌砖动作研究归纳为科学管理构成的4个要素(或原则):“(1)发展真正的科学;(2)科学地挑选员工;(3)工人的科学培训和发展;(4)管理者与工人之间是亲密的、友好的合作关系”。
我国在非遗保护传承上措施得力,成效显著,非遗传承十分活跃。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17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仅2017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共举办了2000 多项大中型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线上线下观众超过1 亿人次。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有579场生动多样的演出活动送进326个基层社区。2017年全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2466 个, 从业人员17235 人。全年全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举办演出50178 场,增长19.0%,观众4558 万人次,增长16.8%;举办民俗活动15133 次,增长3.9%,观众6211 万人次,增长34.5%[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05/t20180531_833078.html。
第三,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人才需求旺盛。
非遗保护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从业者需要具备多方的素质和才能。非遗传承人、非遗管理者、非遗传播者、非遗研究者等都是非遗保护迫切需要的人才。因此,近十多年来,我国针对不同非遗人才的培训层出不穷,有针对非遗管理干部的培训、传播人才的培训,还有专门针对传承人群的培训。仅2017年,文化和旅游部就指导78 所高校实施了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举办研培班196 期。但我国各级非遗管理部门、保护单位和各类高校在非遗保护人才方面的缺口仍然十分庞大。
第四,相关学科参与热情高,为构建非遗学科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支持。
非遗保护工作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缔约国政府主导的。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的科学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缔约国政府都吸收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此外,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缔约国政府对非遗保护名录评审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科学者被吸引到了非遗保护领域中来。我国各级政府在非遗保护中,建立了各级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与我国非遗名录的十大类别相适应,吸收了文学、民俗学、艺术学、历史学、人类学、医学、科技史等学科专家的参与。这些学科专家的介入,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各自学科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经验,大大促进了非遗学科的发展,也推动了非遗学科共同体的建设。
(二)构建非遗学科共同体面对的挑战
非遗学既是一个源于并直接服务非遗保护实践需要的应用学科,又是与相关传统学科融合发展的交叉学科。在非遗学科共同体建设上,当前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第一,学科时间短,基础薄弱。非遗概念正式提出才十多年时间。相对其他学科,非遗学仍然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这对构建非遗学共同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学科范式尚未真正确立。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范式。非遗学以非遗传承和保护为研究对象,但非遗又多从属于不同的传统学科,如传统音乐类非遗项目,既是非遗学的对象,又是音乐学的对象。对象的交叉,会导致学科边界的模糊,一些非遗研究者对非遗研究仍受制于传统学科的范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非遗学自身范式的发展。没有独立范式的学科,就很难有独立的学科共同体。
第三,参与者有热情,但自信心不够,持续度低。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对非遗保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科和学者开始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有的参与非遗项目的申报、评审工作,有的参与政府的咨询工作,有的参与非遗项目的开发利用工作,有的参与非遗项目的教育或传播工作,各种有关非遗保护的研究机构、刊物、论文、著作、研讨会不断出现,非遗保护成为过去十多年里学术界关注度很高的话题之一。许多高校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或方向,开展学历学位教育,有许多本科生、研究生以非遗保护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但从历年非遗保护研究的论文、著作情况来看,参与者多数以自己所从学科视角介入非遗保护研究,把非遗保护作为自己所属学科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一个旁证,很少把非遗作为自己专业方向来发展,这就造成了许多参与非遗保护研究者,往往对非遗保护研究缺乏持续的投入和关注,学科建设也因此而难以深入。
第四,非遗学体制性独立有待推进。一个学科的独立,取决于学科共同体的独立意识,也受制于学科体制的独立性。目前,我国许多高校都在开设非遗课程或研究生培养,但非遗学尚未纳入教育部正式本科学科目录,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非遗学的独立发展。另外,大多数高校的非遗研究机构,不是独立的实体机构,没有独立的人员编制,而是作为传统学科的一个分支而存在,这使得从事非遗学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学科归属感,忠诚度比较低。这种体制性问题,是制约非遗学科共同体建设的突出问题。
四、构建非遗学科共同体的原则和对策
(一)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客观性原则。客观、真实是学术研究的核心原则,也是非遗学科共同体建设的首要原则。目前,非遗学科建设尚在发展初期,要防范“以用代学、急用而学”的急功近利式思维,要秉持客观、真实立场,坚持以学为本的发展道路。
第二,坚持独立性原则。学科独立是学术专业化发展的要求,也是非遗学科共同建设的基本依据。非遗学科共同体要有自己独立的专业化标准、身份资格、研究内容、行为规范和活动范式。从本质上讲,所谓“学(discipline)”就是标明、划定、保持乃至开拓学科专业化边界、范围和研究范式的一套学术行为规则,以“学”相称实际上代表和反映的是一个学科是否具有和遵循一套成其为学科的边界与规则。
构建非遗学科共同体,要坚持学科独立性原则:1.明确非遗学科的专业定位。非遗学是与物质文化遗产学相对的学科,是对文化与遗产特殊形态的反映,是对人类文化与遗产普遍共性与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多样性遗产形态类型研究。只有这样,才足以把非遗学与文化学、遗产学等其他学科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确立自己安身立命的学术依托和专业空间。其二,明确非遗学的对象定位。非遗兼有文化类型与遗产类型的意义,非遗学科必须从文化类型与遗产类型角度为自己的对象定位。黄文山说:“殊相的摹述,不会满足严格的科学追求,因为社会科学所要了解的,不是文化现象的‘唯一性’,而是它的重演性。……科学的或真实的比较方法的第一个步骤是客观的文化个案的研究,第二个步骤便是文化的历年的类型的建立”[注]黄文山:《文化学的方法》,《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6页。。从形态看,非遗是文化类型中的代际文化(观念文化)和遗产类型中精神遗产,本质是人类代际之间传承的精神文化,体现为口传、身授、意会等形式传承的文化。相对于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而言,非遗具有代际性;相对于物质遗产而言,非遗具有主观性、观念性,且在传承方式上以口传、身授、意会等精神交流为特征。非遗学研究对象由其特有的存在、传承与时间属性决定,与其他学科具有明晰的边界。其三,明确非遗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定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以《关于人类文化多样性宣言》和尊重各种国际人权文件为前提的。人权平等与文化多样性是非遗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人类从诞生至今,对自身经历了由自然本体到神灵本体再到人类本体的认识过程,对人权也经历了从自然控制到人权神授再到人权平等的认识阶段。人本和人权平等的理论,不仅把人从自然和神权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且在观念上赋予了人人平等的权利,当然包括选择、创造、传承和享用文化的权利。人权平等既是文化平等的基础,又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人权平等和文化多样性要求非遗学在学科理念上,要以人为本,以非遗传承者为本,研究要从传承者那里来,到传承者那里去,从传承者的生产、生活和思想中探索非遗现象的内在规律,并把这种规律的认识反馈到传承者那里去,促使传承者及其文化的自我存续。这种理念决定了非遗学科与传统学科在学术动机上的边界,同时也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差异。其四,明确非遗学科学者“入伍进队”的学科知识结构、专业修养、学术平台和专业身份,突出非遗学科共同体的特定学科团队文化、利益诉求和共生场景,改变非物遗研究鱼龙混杂、浅层次重复的现状,确立非遗学的学科品性。其五,明确非遗学科建设的专业标准和行为规则,创新非遗学的研究职能、内容和方法,强化非遗学运作的专业性、创新性,提升专业形象。
第三,坚持系统性原则,强化非遗学科的系统本位。“文化个案研究的目的,本来想把时间性和地方性的类型建立起来,然后建造非时间性和非地方性的类型,再依据这些类型来说明某种文化的结构之产生及其互相关系。”[注]黄文山:《文化学的方法》,第59页。非遗学科目的,就是建构非遗的普遍性类型或模式。也就说,非遗学科理论知识是系统化的信息,它不仅直接反映出非遗的即时形态,而且力图按照其本来结构层次与序列来反映非遗的类型或模式,以避免因时空限制和主观偏见对非遗系统合理结构的误读。
因此,从非遗复杂多样的形态与眼花缭乱的个案研究中,梳理出非遗学的基本模式与框架,是非遗学科的迫切要求。其一,选择最具有整合力和包容性的基本学科模式,为非遗学提供有机系统的学科模版。鉴于非遗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和具有活态性等特点,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非遗现象与属性的,应该是非遗形态学。以人类客体生命自发、自动的生存、展示和演化与人类主体生命自觉能动地共生、竞争为前提,以人类个体、群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创造、展示、享用和传承非遗为主线,以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结合而成的非遗形态与类型为对象,以科学还原、类比为基础整合多视角的方法体系为治学方法,建构非遗生态学。其二,以非遗生态学的元模版为学科生命本质与基础依托,以非遗形态学为学科整体轮廓和实体骨架,以非遗实践活动的基本结构因素为划分标准、规则和方法,建立与非遗研究的学科形态结构系统、非遗存在结构系统、非遗理论结构系统、非遗话语文本结构系统等对应同构的非遗学科体系。这种学科、存在、理论和文本的高度对应、同构和有机排列组合,相互衔接、依存、制约、融合与转化,就形成了学科因子结构匹配、功能因果关系确定、整体系统严谨、和谐、开放和生动的非遗学科体系。
(二)基本对策
第一,要加大非遗学科共同体宣传,营造氛围。非遗学科共同体的建设,是基于共同学科理念的实践过程。而共同的学科理念的形成,则依赖于具体的学科实践。建立专门的非遗学网站、微信公众号或APP,编辑出版专门的非遗学期刊和出版物,持续性举办非遗学研讨会,是现阶段营造非遗学氛围,培养非遗学科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第二,加强文献和案例研究,夯实学科共同体的基础。非遗学科共同体的建设,是以共同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非遗学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就要加大对非遗保护方面的文献和案例积累,要建立非遗学的文献资源数据库、保护案例数据库。这些基础研究,是学科共同体对非遗学对象现象的认知实践,也是非遗学共同体意识,学科范式得以建立的基础。
第三,完善学科理论,促使学科共同体的范式性独立。非遗学科共同体建设,是以共同的学科范式和规则为前提的。非遗学要加大学科理论问题的研究,要加大学科理论平台的建设,包括学术机构平台、期刊平台、研讨会平台的建设,通过协同攻关,解决非遗学的重大理论问题。
第四,推动联盟建设,推动学科共同体的体制性独立。非遗学科共同体既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又是一个实体的共同体。非遗学科共同体建设要通过各种方式,促使从非体制性共同体向体制性共同体的转换。一方面要加大各高校和各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盟,推动非实体性的学科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大非遗学自身建设,促使非遗学的独立发展,从而推动各高校、研究机构的脱虚就实发展,促使非遗学科共同体的实体化转换化。
五、结语
非遗学科共同体构建是一项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的工作。
非遗学科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既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又符合科学发展规律。保护非遗,推动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需求,非遗学科就是为了解决保护非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设,也是为人类社会发展而设。交叉学科是传统学科在专业精细化基础上的新的发展趋势和要求,非遗学科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它打破了传统学科对象条状模式,转而从横向角度对学科对象进行划分,体现了传统学科的革新要求。
构建非遗学科共同体,是社会和科学发展的产物,是实现非遗学科独立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