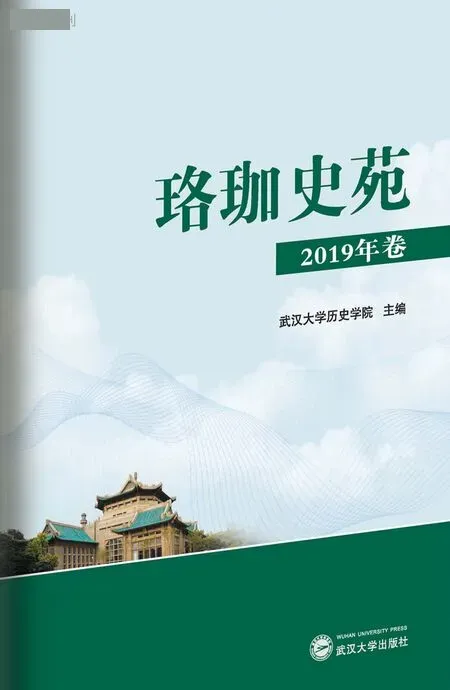从“伯夷谏武王”的后世解读看儒家文化的自我完善
全狄伟
一、引 言
一般而言,一种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或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或是出于自身学说体系完善的需要,都会不断地演变。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即是一种文化的自我完善、自我修复与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能力强的文化能长时间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主流,而缺乏自我完善能力的文化则会逐渐被时代所遗忘,所淘汰。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能长期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它通过注疏的形式使得后世的学者能够不断地对之前的各种思想学说(其中或是一些先贤语录或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作出新的适应时代的解释。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所体现的实际上就是儒家文化在注疏中的自我完善。一般而言,越具有争议的事件越有注疏的必要,也越具有自我完善的必要。下面笔者就借助一个在历史上有着重大争议的事件即伯夷谏武王事件,来看看儒家文化是如何自我完善的。①近些年,关于伯夷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也取得了较多成果。如针对伯夷形象的研究,有葛炜:«春秋战国伯夷形象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王建华:«伯夷叔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陕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针对伯夷事迹的研究有刘家钰:«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辨»«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叶罕云:«伯夷“义不食周粟”原因探析»,«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同时也有将«伯夷列传»作为文本的专门性研究,如单少杰:«‹伯夷列传›中的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占晓勇:«读‹史记•伯夷列传›»,«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1期。但是对于“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的研究和解读仍涉及较少,笔者此文也是在探讨儒家文化自我完善的同时,试图借着文化的自我完善这一视角重新梳理后世对于“伯夷谏武王”的解读,以期有助于充实对伯夷的研究和认识。
在儒家文化中,先秦的伯夷和武王都可以称得上是贤人乃至于圣人,孔子称赞伯夷是“古之贤人也”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页。,称其“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5页。。孟子则称伯夷是“圣之清者也”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40页。。而武王更是儒家心目中的圣王,武王伐纣也被儒家视为顺天应人,吊民伐罪的壮举。但是同样作为儒家心目中圣人的两人却在武王伐纣这一行为上产生了激烈的思想冲突,这就是后世有名的“伯夷谏武王”的事件。
二、“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的记载与传播
最早记载“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经过的并非是儒家的经典文献,而是作为道家思想代表的«庄子»。
在«庄子»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谓道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下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①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杂篇«让王»第二十八,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14页。
在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伯夷指责武王伐纣是推乱以易暴,同时为了表现自己对周的新政权的不认同而饿死首阳山下。在这一段记载中,虽然部分情节如武王派周公慰问,并想要给伯夷叔齐封官和流传到后世的“伯夷谏武王”事件有所出入,但是基本的要素可以说已经是大致具备了。从这一段记载也可以看到伯夷与武王之间激烈的思想冲突。这种冲突显然易于使人质疑“伯夷”与“武王”是否真的都有资格作为儒家口中的圣人。
而之后进一步详细记载这一事件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的«伯夷列传»中有如下记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①«史记»卷61«伯夷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69页。
拿这段文字与«庄子»中的记载对比,可以发现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难怪会有学者产生«庄子»中的文字出自秦汉人之手的想法。②对于«庄子»中的这段文字,张恒寿老先生在他的«庄子新探»中认为这是“秦汉人抄袭«吕氏春秋»而成的文字”,应当是伪作,也有许多学者持这样的看法。如果说这是伪作的话那么“伯夷谏武王”这一故事的形成就应当从战国推到秦汉了。但这似乎也从侧面说明了“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的确是从秦汉以后开始广为流传的。同下文提到的«伯夷列传»的广为传播不谋而合。然而两相对比也可以看到«史记»中的记载更为简洁,伯夷对于武王的批评也更有针对性。在«史记»这段记载中伯夷指责武王主要有两点一是“父死不葬”,二是“以臣伐君”,这两点都体现了伯夷与武王之间激烈的思想矛盾,而之后的武王不听劝谏,伯夷饿死首阳山下,更是加重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伴随着«史记»一书在后世的广泛流传,«伯夷列传»中所记载的这段首尾连贯、生动详细的“伯夷谏武王”事件也开始在后世广为流传,伯夷与武王的矛盾也因此愈演愈烈。
那么除了«庄子»和«史记»中的记载以外,在儒家经典文献中是否会有涉及这一事件的蛛丝马迹呢?虽然儒家经典文献中没有具体提及这一事件的经过,但是从孔孟评价伯夷的言论中似乎还是能看到这一事件的蛛丝马迹。孔子曾经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9页。,那么伯夷为了什么而不肯降志,其中是不是有不仕武王,从而不降其志的可能呢?孟子也曾说过伯夷“非其君不事”,“治则进,乱则退”,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86页。这是不是指的也是伯夷不愿为武王效力而选择归隐呢?虽然从孔孟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言论中不大易于窥透个中所指,但是的确他们的这些言论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似乎孔孟二贤也都了解这一事件,只不过并未明指罢了。①可以说这种暗指还是给了儒家文化自我回旋的余地,增添了后世学者几分疑古的勇气,使得后世的儒家学者更敢于去否定和修正这一事件。学者们对这一事件的否定会在下文中进一步谈及。
于是随着«庄子»和«史记»中的明指以及孔孟言论中的暗含,“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在后世流传愈来愈广,伯夷与武王的矛盾也愈来愈重。为何同作为儒家心目中圣人的两人会有如此大矛盾?以及在儒家歌颂武王伐纣的同时如何去理解同样作为圣人的伯夷对这一事件的激烈反对?这都呼唤着后世儒家学者做出相应的解释。这种解释既是对伯夷与武王之间矛盾的调和,也是对伯夷与武王形象的充实和完善,同时更是儒家文化内部的一次自我调适。
通过梳理后世儒家学者有关“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的相关言论,可以看到后世的儒家学者为了调和伯夷与武王之间的矛盾做了诸多努力,这些努力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对事件记载本身的否定和修正;一是在接受“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的基础上,在评价和解读中进行调和。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学者们所做的第一类努力。
三、在事件记载上进行否定与修正
伯夷与武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来源于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可以说若没有这一事件,这两位圣人间就不会有冲突。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从这事件本身入手,质疑这事件的真实性进而否定这一事件。而伯夷谏武王的具体情节并未出现在儒家经典文献中,而是出现在«庄子»«史记»等书中,这也更增添了后世学者的疑古勇气,兴起了专门针对这一事件的疑古思潮。这一思潮在宋代蔚然成风,宋代的诸多学者纷纷开始质疑汉人笔下的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记载的可靠性。
首先便是这事件本身是否存在。
宋代的一些学者认为所谓的“伯夷谏武王”只是出自«庄子»和«史记»诸书的编造,这一事件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王安石所写的«伯夷»一文就是这种观点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①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3«伯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4页。王安石认为孔孟都没提到“伯夷谏武王”,从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开始,“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才开始传播开来。接着王安石提到了伯夷与姜太公都曾经想去文王处养老,认为这说明了伯夷与姜太公一样都是反对纣王,拥护文王的,因此从情理上说伯夷不应当有之后的叩马谏武王之举。王安石进而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伯夷没有等到武王伐纣应当就死了,不然他也会像姜太公一样出来辅佐武王。在王安石提出这一假说时,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是否定了«史记»中的记载,构建了一个更符合其自身理想的伯夷形象。虽然王安石的这一假说也受到了许多质疑,但是他对«史记»记载的否定则是得到了诸多学者的支持。如北宋的谢景平就认为所谓的伯夷谏武王是“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无信也”,“其初盖出庄周空无事实,其后司马迁作«史记»列传,韩愈作«颂»,事传三人而空言成实”。②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第17«伯夷叔齐庙记»,«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4页a。吕希哲也在他的«吕氏杂记»中称“伯夷叔齐叩马谏武王伐纣,不听,不食周粟,此庄周寓言也”③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页。。这一思想也影响到了宋以后的学者,如明代的季本认为“«史记»载其(伯夷)谏伐事亦非也”,“今叩马而欲沮其事,将使武王收兵而还乎,此又迂儒不解事之见也”。④季本:«说理会编»卷6«实践二•让国»,«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4页a。清代的崔述在«考信录»中也认为伯夷谏武王是出自“«庄子»及«吕氏春秋»”附会,“太史公习闻其说,不察其妄而误采之”。⑤崔述:«考信录•丰镐考信录»卷8«伯夷叔齐»,«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3页a。
还有一些学者并未完全否定«史记»的记载,而是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正。如宋代的二程针对学生“伯夷叩马谏武王,义不食周粟有诸”的提问时,指出“叩马则不可知,非武王诚有之也。……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禄,非饿而不食也。至如«史记»所载谏词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语”①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8,«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59页a。。可见二程认为«史记»所提到的“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是应当确实存在的,但是«史记»所记载的伯夷的劝谏言论则是有问题的,因为武王伐纣时距离文王去世已经相隔一段时间了,伯夷不可能去指责武王“父死不葬”,同时伯夷在劝谏失败后,也并非像«史记»所记载的那样绝食而死,伯夷不食周粟只是不愿意出来做官。可见二程主要在“父死不葬”和“不食周粟”这两点上对史记的记载进行了修正。由于二程在后世的学术影响力,二程的这些观点也被后世的诸多学者继承。如宋人黄震在«黄氏日抄»中称“伯夷父死不葬之语与武王十一年代纣事,皆驰然汉人旧说。以武王上继文王受命之九年为十一年故云尔”②黄震:«黄氏日抄»卷46«读史•列传»,«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7页a。。元人陈师凯也称“孟津之会,文王之葬久矣。故知扣马之谏,必无此事也”③陈师凯:«书蔡传旁通»卷4上«泰誓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a。。而在不食周粟这一事上,宋代的刘敞也认为“所谓不食其粟者,言致为臣而去,不在廪饩之例。是乃所谓为饿也。安得采薇之事乎?”④刘敞:«公是集»卷49«周二贤赞»,«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页a。明代的方弘静也称“不食周粟,不食其禄也”⑤方弘静:«千一录»卷2«经解二»,«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7页b。。
孝是儒家伦理道德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有关“父死不葬”这条记载的修正可以说是为了使武王的行为更符合儒家的孝道,进而完善武王的圣人形象。而有关“不食周粟”这一条的解释也是为了使伯夷的行为显得不那么极端,营造一个更符合儒家理想的伯夷形象。除完善这两位圣人形象的作用之外,这些记载的修正也有助于缓和武王和伯夷间的思想冲突,使得两人的对立显得不是那么激烈。
总而言之,无论是对伯夷谏武王事迹的否定还是修正,其起因都是对«史记»«庄子»诸书记载的质疑。之所以从宋代开始学者纷纷质疑这些记载,一方面的确是因为这些记载在某些方面显得语焉不详,前后矛盾,显得不那么可靠,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记载都是“孔子、孟子之所不言”①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第17«伯夷叔齐庙记»,«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4页a。,即不符合儒家理想中的伯夷和武王形象。这些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记载加重了这两位圣人间的思想矛盾,使得后世的学者不得不对他们加以修正。这些修正的目的就是要把伯夷和武王塑造成符合儒家思想体系的圣人形象,来应对«庄子»«史记»诸书“伯夷谏武王”记载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此来完善自身的文化。而纵观这些修正的言论,也可以很好地看到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在儒家文化自我完善中的作用。
然而由于伯夷与武王毕竟与宋乃至宋以后的学者时代相隔太过遥远,单纯去质疑其中的某些记载总难免会显得证据不足,而且缺乏说服力。因此相比于去质疑记载本身,后世学者在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上所做的更多的努力是对伯夷行为的解释。如何能在肯定伯夷行为的同时无损于武王的形象成为后世学者着力的重点。而这种解释则将很好地体现儒家学者们所具有的思辨能力在儒家文化自我完善中的作用。
四、在评价与解读中进行调和
评价伯夷谏武王行为实际上主要是探讨伯夷的动机,即考虑伯夷站出来劝阻武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然后在此之上讨论伯夷这一行为的意义。
在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中,武王的态度是伐纣,而伯夷所作的是以君臣之道劝阻武王伐纣,反对“以臣伐君”。那么武王和伯夷这两位圣人这么做,各自的意图是什么呢?他们两者真的是针锋相对的吗?后世的学者开始了调和两者的努力。
(一)“武王周公尽其变,伯夷叔齐守其常”
在这些调和的言论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南宋的陈普提出的“武王周公尽其变,伯夷叔齐守其常”①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11«谊利道功»,«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a。。在这句话中陈普提出了“变”和“常”这两个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在儒家文化中“变”指的是权变,变通,是孟子所提出的援溺之意,就是对一些特殊的情况要特殊对待,懂得变通。而“常”指的是儒家文化要求人们所恪守的伦理纲常,这种伦理纲常除非是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不然是不能随便违背的。由此也可见陈普认为武王作为一个有德之人来讨伐当时极端荒淫无道的纣,虽然违背了君臣之道,但是却能够解民倒悬,顺天应人,是极端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体现的是儒家文化的变。而伯夷之所以会以君臣之道劝谏武王,出发点则是想要恪守作为儒家文化的“常”。陈普的这一言论并非前无古人。在陈普之前的朱熹就曾表达过“武王处一世之大权,二子(伯夷叔齐)守万世之大经,各一义也”②朱熹:«小学集注»卷4«内篇»,«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6页a。这样的观点,实质上也是从变和常来区分武王和伯夷。而陈普之后的明人王廷相和蔡清也在各自的文集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可以说后也有来者。如王廷相在«慎言»中称“伯夷大舜常道也,武王周公变也”③王廷相:«慎言»卷13«鲁两生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6页。,蔡清在«四书蒙引»中称“伯夷叔齐可与立者,武王周公可与权者”④蔡清:«四书蒙引»卷6,«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2页 a。。陈普以及这些古人和来者的言论将武王和伯夷的行为贴上了“变”与“常”的标签,而“变”与“常”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体两面,两者可以说是互不冲突,甚至是互补的。于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武王伐纣和伯夷劝阻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互不冲突,乃至互补的,就像施德操所说的“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①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页a。。通过这些学者的解读也可以看到,他们想做的就是把伯夷与武王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以儒家的价值评判标准来消解一些异端的价值评价,进而缓解伯夷与武王之间的冲突。这是儒家学者在完善自身文化中的一个比较高明的技巧。那么武王所实行的“变”和伯夷所坚持的“常”各自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学者们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武王救“天下之民”,伯夷“救万世之民”
在北宋王开祖的«儒志编»中有这样一段话:
纣之残贼天下,仁人之心危若缀旒。然太公相武王,惟恐天下一日不得武王也,思救天下之民也如此。伯夷自谋曰:“武王之佐有若旦望,有若君奭南宫适,有若散宜生虢叔,居其左右前后,不少我也。吾亦何为哉?吾其救万世之民乎?”于是非武王而去之。武王犹非,况不至武王乎?其救万世之民也如此。故去就于周者异,所以救民者同,是二老之心一也。②王开祖:«儒志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页a。
这段话认为太公望辅佐武王伐纣是为了救天下之民,是功在当时,而伯夷谏武王是为了救万世之民,是功在万世。这种以当时和后世来区分武王和伯夷作用的观点,可以说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伯夷和武王各自行为的目的。
那么为什么谏武王能起到救万世之民,功在后世的作用呢?王开祖的一句“武王犹非,况不至武王乎”似乎透露出了答案。可见伯夷针对的是那些“不至武王”的人。那么“不至武王”的人是哪些人呢?北宋的范浚在评论伯夷时曾说,“臣伐君盖甚逆之道,使君非纣不当伐也,臣非武王不可伐也。后世有乱贼之臣必将曰:‘武王圣人也而伐纣,当年无一人非之者,是则臣伐君乃圣人之教。’其于篡夺窃取将多有之。故于武王杖钺指商之初,叩马陈谏,以明君臣之分”①范浚:«香溪集»卷9,«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3页b。,南宋的罗泌也认为“天下之大义惟君臣尔。今以君为无道而伐之,则后世乱臣贼子将群起而效矣。故伯夷不敢以武王而废天下之大义,于是叩武王,而告之以伐君非忠”②罗泌:«路史•发挥»卷2«论伊尹»,«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4页b。。可见,这些“不至武王”的人,就是那些没有武王的德行却试图模仿武王的行为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伯夷谏武王就是想通过“明万世君臣之伦”③方回:«桐江续集»卷35«钓台书院清风堂记»,«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5页a。,“死守君臣之义”④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3«讲义•易»,«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b。来震慑后世的乱臣贼子,使他们不敢轻易背弃君臣之道,使后世不要出现“无君”的局面,从而“救后世之民”。这样的论断将伯夷的矛头由武王转向了后世的乱臣贼子,在肯定伯夷谏武王价值的同时,缓和了伯夷与武王间的矛盾,可谓一举两得,是一支调和伯夷与武王矛盾的强有力的论调。
(三)武王行君道,伯夷行臣道
除了以“变”和“常”,“救天下之民”和“救万世之民”来区分武王与伯夷的行为外,还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武王行君道、伯夷行臣道。如明代的湛若水在评价“伯夷谏武王”时曾说“武王君道主于救民,伯夷臣道主于明义,故皆得称曰仁”⑤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23,«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35页b。。在湛若水眼中武王通过伐纣救民行君道,伯夷通过谏武王明君臣之义行臣道,两者都符合儒家对于圣人的标准。实际上前文所提到的“明万世君臣之伦”,“死守君臣之义”这样的评价也已经隐约地表达了伯夷行臣道的观点。这样的言论也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如明宣宗朱瞻基在他的«五伦书»中就把伯夷列入臣道下的忠义类。①朱瞻基:«五伦书»卷33«臣道十•善行•忠义上»,«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页a。统治者和学者如此强调伯夷与武王在君道和臣道上的差别,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两者的思想是互补的,并不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想要把伯夷塑造成臣子的典范,乃至于忠臣的典范,使得后世的臣子愿意像伯夷一样恪守君臣之道。而将武王塑造成为君主的典范,目的则是为了强化君主的地位。在君道和臣道的话语逻辑下,伯夷和武王各行其是,各取所需,两人的圣人形象不但没有因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被削弱,反而被加强了。
前文指出了针对调和伯夷与武王矛盾的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实际上这三个观点是互为因果,三位一体的。臣道的核心是明义,明义就要恪守君臣之道,就要“守其常”,而君道的核心是救民,在当时那个纣王无道、民不聊生的时代,救民就不得不以臣伐君,不得不尽其变。尽其变是为了救天下之民,解民倒悬,使当时不至于出现“无君”的局面,而守其常则是为了救万世之民,使后世的乱臣贼子不敢轻易以臣伐君,也不至于出现“无君”的局面。虽然在武王伐纣时,武王与伯夷实际上都是臣,但是在当时乃至后世人的心目中显然武王比纣王更具有做君主的资格,所以也就不自觉地将武王伐纣也作为一个君主的本分,成为君道的一部分了。而伯夷的这种劝谏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死守君臣之义”的臣道行为。君道和臣道成为划分伯夷与武王的一个重大标准,也成为解读伯夷谏武王行为的一个新的出发点。
五、小 结
通过对“伯夷谏武王”后世解读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后世儒家学者在调和伯夷与武王矛盾,完善自身文化中的努力。而纵观这些调和伯夷与武王的言论,可以看到后世许多学者在解读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时已经不自觉地将伯夷视为守节之臣的代表,而将武王视为开国之君的代表。伯夷与武王的矛盾也被他们当作开国之君和守节之臣的矛盾来处理。在朝代鼎革之际,开国之君与那些死守君臣之道坚持不为新政权效力的守节之臣可以说一直是矛盾重重、冲突频发的。开国之君更愿意去用那些不守君臣之道的臣子来帮助自己夺取政权,而当自身政权稳固后,又要清理和否定这一批不守君臣之道的“有功之臣”,反过来褒奖那些曾和自己冲突频发的死守君臣之道的“逆臣”。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几千多年来的一种政治逻辑。而对于伯夷与武王的调和实际上也是从这一逻辑出发的,通过肯定武王来肯定后世的开国君主,通过褒奖伯夷来肯定后世的守节忠臣。可以说这一政治逻辑是解读伯夷谏武王这一行为的思想土壤,而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的不断宣传也更巩固了这一政治逻辑,丰富了这一土壤,有时甚至会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服务。①如明代的士大夫在尝试为建文忠臣平反时就经常以历史上武王与夷齐的故事来隐喻明成祖与建文诸忠的关系,这样既能肯定成祖的行为如武王安天下,又能够赞扬忠臣之义,从而有利地推动平反进行。显然“伯夷谏武王”事件成为平反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而“伯夷谏武王”事件的解读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政治意图(有关建文平反事可参看吴德义:«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可见,后世学者在解读“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时,赋予了其更多的现实意义,将伯夷和武王的形象塑造得更符合儒家标准,成为儒家理想中臣和君的典范,而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也渐渐地获得了符合儒家价值判断标准的解释。可以说一开始学者们解读“伯夷谏武王”是为了解决儒家学说内在的思想矛盾,是为了解决历史问题,而之后一些学者在引用和解读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时,他所想要解决的已经是一些现实的问题了。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到,“伯夷谏武王”这一事件的产生和传播既是对儒家文化内在逻辑的一种挑战,同时也不失为促使儒家文化发展完善的一大推动力。通过对“伯夷谏武王”后世解读的梳理,我们可以体会到儒家文化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学者们会自发地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去完善自身文化,其中既有对原始记载的考订与修正,又有对原始记载的新的解释阐发,既体现了扎实的考证能力,又彰显了卓越的思辨力。这一完善过程既是一个整理总结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既是为了解决历史问题,也是为了应对现实需要。儒家文化的这种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正是其在很长时间内能符合统治者需要、能保持生机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