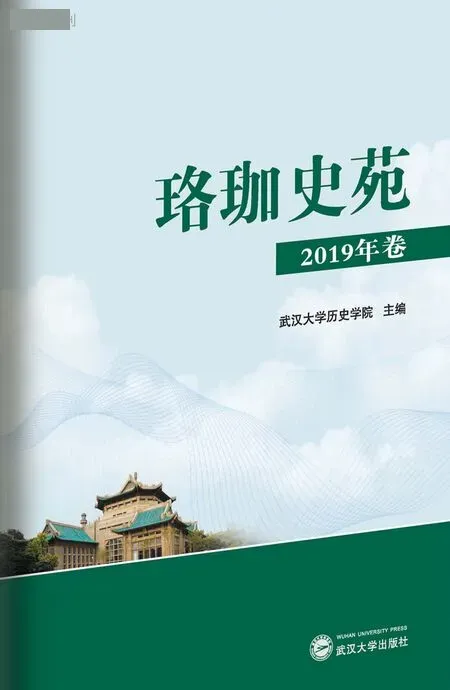放马滩秦简«丹»篇是志怪小说吗?
王 谦
新材料的出现往往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但应用新材料的前提是正确定义其在相关学科中的价值与意义。从这点来说,一个合适的文献定位是应用新材料的起点。自放马滩秦简«丹»篇出土,许多研究者都把它作为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随着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称«泰原»)的公布,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这样的争议体现出如何定义«丹»篇与志怪小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放马滩秦简«丹»篇以及北大秦牍«泰原»为考察中心,结合前贤的研究,旨在说明放马滩秦简«丹»篇尚不足以称为志怪小说,只能算是其滥觞。
一、学界对«丹»篇文献性质的认定过程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几支简记载了一个叫丹的人死而复生的离奇故事,该篇的命名在经历了“墓主记”、“志怪故事”、“邸丞谒御史书”等称呼后,学界目前多称为«丹»篇。其事如下(释文均采用宽式):
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
大梁人王里□□曰丹,□今七年,丹刺伤人垣离里中,因自刺殹,□之于市。三日,葬之垣离南门外。三年,丹而复生。丹所以得复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论其舍人掌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狐穴掘出丹,立墓上,三日,因与司命史公孙强北之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盈四年,乃闻犬吠鸡鸣而人食。其状类缢、少眉、墨,四肢不用。
丹言曰:死者不欲多衣;死人以白茅为富,其鬼贱于它而富。
丹言:祠墓者毋敢哭,哭,鬼去惊走;已,收餟而之,如此,鬼终身不食殹。
丹言:祠者必谨扫除,毋以□□祠所,毋以羹沃餟上,鬼弗食殹。①参考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第43页;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丹›篇校注»,简帛网,2012年7月31日,http://www.bsm.org.cn/;黄杰:«放马滩秦简‹丹›篇与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研究»,«人文论丛»2013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页。
此类离奇复生之故事多见于我国古代的志怪小说。所谓志怪小说,是指专记鬼神灵异的小说文体,其故事内容多源于神话传说、方术学说以及地理博物知识。②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此种文体萌芽于战国,成熟于两汉,盛行于魏晋。③陈文新:«论志怪三体»,«学术论坛»1995年第6期,第70页。志怪小说按照内容特征可分为“搜神”体、“博物”体和“拾遗”体三类。④关于志怪小说的分类,这里采用陈文新在«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中的划分方法,其他学者对志怪小说类型的划分可参考: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2页。“搜神”体以仙、鬼、怪形象为核心,广泛采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其代表为干宝编撰的«搜神记»;“博物”体源于先秦的地理学和博物学,多记“远方珍异”,其代表为张华编撰的«博物志»;“拾遗”体则融合杂传、“搜神”体、“博物”体等因素,专记仙境、仙品和仙人,其代表为王嘉编撰的«拾遗记»。①陈文新:«论志怪三体»,«学术论坛»1995年第6期,第70~74页;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由于«搜神记»卷15中记载了多则与«丹»篇类似的死而复生故事,因此,在学界关于«丹»篇文献性质的讨论中,«丹»篇“能否作为志怪小说”这一问题成为其中为人瞩目的焦点之一。从这场讨论入手,可以清晰地展现出«丹»篇从被定位为志怪小说,到这一定位被学界否定的全过程。关于«丹»篇的性质,前有“墓主记”“志怪故事”两说,后有“日书”“更易丧俗”和“丧葬文书”三说。现以此为线索回顾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并就相关细节展开分析。
«丹»篇最初被整理者命名为“墓主记”。整理者认为这一故事是M1墓主人自身经历的记录。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第31页;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第23页。最早指出其与后世志怪小说存在联系的是李学勤。李先生在1990年发表了«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一文,对简文的释文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和语译,并就其内容与«搜神记»中的复生故事进行了比较,认为简文在情节模式上同«搜神记»中的«贾偊»«李娥»等篇目相同,共同点都在于“故事中主人本不应死,被司命遣回人间,复活后讲述了死时在另一世界的种种见闻”,虽然情节不如«搜神记»中的故事曲折,但可以将其视为同类故事的滥觞。③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第46~47页。这一观点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继的许多研究者继承了李学勤的思路,进一步把«丹»篇作为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来看待。如200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天水放马滩秦简»一书,整理者就将«丹»篇的原定名由“墓主记”改为了“志怪故事”,并在内容提要中介绍道:“«志怪故事»被誉为我国最早的‘志怪小说’,在民间通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版,“内容提要”第1页。,已经明确地将«丹»篇文献的性质定义为志怪小说②很多论著也或早或晚采用了这一定位。如伏俊琏:«战国早期的志怪小说»,«光明日报»,2005年8月26日,第6版;唐海宏:«志怪小说‹墓主记›摭谈»,«甘肃高师学报»2012年第6期,第7~9页;丁丁:«秦简中的志怪故事与复生类志怪小说的渊源»,«戏剧之家»2014年第7期,第353~354页;蔡先金:«简帛文学研究»,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第590~595页。。
“志怪故事”说的失势是以北大秦牍«泰原»的公布为开端的。2012年李零发表«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一文,对北京大学收藏的一块大约为秦始皇时期的木牍进行介绍,并对其释文进行了注释、语译和简要的探讨。释文如下:
泰原有死者,三岁而复产,献之咸阳,言曰:
死人之所恶,解予死人衣。必令产见之,弗产见,鬼辄夺而入之少内。
女子死三岁而复嫁,后有死者,勿并其冢。
祭死人之冢,勿哭。须其已食乃哭之,不须其已食而哭之,鬼辄夺而入之厨。
祠,毋以酒与羹沃祭,而沃祭前,收死人,勿束缚。毋决其履,毋毁其器。令如其
产之卧殹,令其魄不得落思。
黄圈者,大菽殹,剺去其皮,置于土中,以为黄金之勉。③李零:«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文物»2012年第6期,第81页。
对比«丹»篇,可以发现两者在故事结构上几乎完全相同。它们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讲述主人公死而复生的过程,第二部分是通过复生者之口讲述死后世界的情况和丧葬祭祀宜忌。所不同的是,«丹»篇对于主人公死而复生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叙述,而«泰原»则对此一笔带过。由此,«泰原»一经公布,学界便一致认为其与«丹»篇属于同类性质的文献(为方便叙述,以下称这类文献为“«丹»类文献”),但同时又引起了对两篇文献是不是“志怪小说”的热议。如李零在«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文末就提出了«泰原»“是不是也是文学作品”这一问题供学界思考。事实上,李学勤之所以将«丹»篇看做志怪故事,主要是基于丹的复活过程与«搜神记»中部分复生故事相似,而«泰原»则有意省略了对主人公复生过程的叙述,反而将重点全部放在了介绍丧葬祭祀宜忌上,这使得许多学者认识到,在这类文献中,对人物复活过程的叙述可能只是一个杜撰的引子,之所以虚构一个死而复生的人物来阐述死后所见的鬼神之事,是为了取信于人。而第二部分——介绍丧葬祭祀宜忌才是这类文本的核心内容。①陈侃理:«秦简牍复生故事与移风易俗»,«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9~82页。正是鉴于此,学界近来大多放弃了把这类文献作为志怪小说看待,转而重新定义该类文献的性质。
实际上在«泰原»公布以前,孙占宇就提出«丹»篇并非“墓主记”,也不宜作为志怪小说看待,而属于«日书»中的一篇。其理由是,«丹»篇的内容与墓志、告地书等常见丧葬文书及编年记等记事类文书均存在明显差异,“墓主记”之类的作品应该是个纪实性的东西,而该篇所述丹死而复生的故事显然出于虚构,且后半部分大段关于死人喜好及祀鬼时注意事项的介绍,与丹的生平也没有太大关系。因此不宜将此文献视为记录墓主生平经历的“墓主记”。«丹»篇的核心内容是介绍鬼神的种种好恶以及敬奉鬼神的方法,与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内容相似,它应当是«日书»的一部分。而就作者意图及全篇内容来看,它也并不能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应该视为数术家言。②孙占宇:«放马滩秦简日书整理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82~185页;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46~49页。在«泰原»公布以后,通过与«丹»篇的对比,孙先生又重申了这一看法。①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丹›篇校注»,简帛网,2012年 7月 31日,http://www.bsm.org.cn/。陈侃理通过论述两篇故事中所见的丧葬习俗,认为这两篇文献是识字阶层有意创作或记录的,主要目的在于移风易俗,使当地的丧葬习俗逐渐偏离秦的旧有传统而转向东方六国文化的主流。而对于两篇文献是否为文学作品,陈先生认为«丹»篇可以视为志怪小说,«泰原»则不宜如此定位。«泰原»是这类文献中一个形态较原始、结构较单纯的文本,更能揭示这类文献的本质和主旨,所以从整体来看,不应该将这类文献视为文学作品。②陈侃理:«秦简牍复生故事与移风易俗»,«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2页。黄杰认为由于«丹»篇采用了邸丞向御史报告的官文书形式,因此这类文献不属于日书,而是由从事丧葬、祭祀事务的术士创作的丧葬文书,用于随葬死者,以文字的形式给死者一个心理安慰;而“‘志怪故事’的定位,从«泰原»看也难以成立”,因此也认为这类文献不是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持论与陈侃理相同。③黄杰:«放马滩秦简‹丹›篇与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研究»,«人文论丛»2013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456页。陈民镇认同黄杰对«丹»类文献的性质判断,并进一步指出,«丹»类文献在内容上确实与后世的志怪小说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在形式与功能两方面绝不相类。«丹»与«泰原»是秘不示人(很可能是“示鬼”之作)的私文书,它并不通行于社会,也难以划入“小说”的行列。但有一点它与后来的志怪故事倒是颇为相似,即均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也”。④陈民镇:«中国早期“小说”的文体特征与发生途径——来自简帛文献的启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第69~70页。陈民镇关于«丹»类文献“是不是志怪小说”的意见颇能代表目前学界的总体看法。
如果想要在古小说研究领域利用«丹»类文献,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文献的定位问题。目前学界对于«丹»类文献的定位稍显尴尬,没有形成共识性的意见:一方面,无法否定的是,«丹»类文献与«搜神记»等志怪小说中的死而复生类故事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这显示出它们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忽略,«丹»类文献在文本特征、创作宗旨、文体形式等方面与«搜神记»中的同类故事还存在不小的差别。对此,我们的意见是,可以在李学勤的基本判断的基础上稍加限定,认为“«丹»类文献是‘搜神’体志怪小说的滥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文献定位。
二、«丹»类文献是“搜神”体志怪小说的滥觞
“«丹»类文献是‘搜神’体志怪小说的滥觞”这一定义旨在明确其谱系归属,揭示其与后世志怪小说的承袭关系。
«丹»类文献近于“搜神”体志怪小说,将其与«搜神记»等作品中的复生故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情节模式和冥界观念上具有显著的关联性。
在情节模式上,正如前引李学勤所论,«丹»篇所记丹的复活过程与«搜神记»中许多死而复生的人,如“贾偊”“李娥”等极为相似,大致可以分为“主角死亡—经审复活—身体恢复—诉说死后见闻”四个阶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四个环节都要完全具备,只是情节的发展都基本遵循这一模式。亦有将死而复生的过程一笔带过,而重在描述死后见闻的作品,这类作品在结构上更接近于«泰原»。其中最相似的当为«搜神记»卷15«戴洋复生»:
戴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苏,说:“死时,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箓,给吏从幡麾,将上蓬莱、昆仑、积石、太室、庐、衡等山。既而遣归。”……①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3页。
再就故事情节中的部分细节而言,«丹»篇中亦有多处桥段被后世的复生故事沿用承袭。
第一,«丹»篇中丹得以复活的原因是其“未当死”①“未当死”李学勤认为意思是“罪不至死”,宋华强认为“未当死”指“阳寿未尽”,并且注意到这一点和«搜神记»中同类故事的相似性,可从。参看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第44页;宋华强:«放马滩秦简‹邸丞谒御史书›释读札记»,«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0~142页。,«搜神记»中所收录的多则故事,其主人公所得以死而复生的理由也恰恰是因其寿命未尽。如卷1«吴猛»中,吴猛认为已死的西安令干庆“数未尽”,故而帮助他复活。②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卷6«人死复生»中,汉平帝时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复活后,“自言见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当死。’”③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6,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页。卷15«颜畿»中,颜畿死而复生前曾附身在他人身上向家里人托话说自己“寿命未应死”。④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4~185页。“未当死”成为这类故事中人物得以死而复生的共同理由,这显示出后世的志怪小说与«丹»篇具有相同的思想背景和情节架构。
第二,丹得以复生是得益于方士的介入。简文说“犀武论其舍人掌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则丹的复活当归功于犀武手下的“舍人掌命者”,丹得以重生是他们依靠神秘手段与司命史沟通交涉的结果。所谓“舍人掌命者”,即“精通卜算人命并可与司命史沟通的术士”⑤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丹›篇校注»,简帛网,2012年 7月 31日,http://www.bsm.org.cn/。,方士的作用在这类复生故事中极其重要。前引«搜神记»卷1«吴猛»中,吴猛不仅认识到干庆“数未尽”,更是亲自为之“诉之于天”,这才帮助干庆死而复生。此事又见于«幽明录»卷5«干庆»,然详略不同。«幽明录»记述干庆于冥府“俄见吴君北面陈释,王遂敕脱械令归。所经官府皆见迎接吴君,而吴君与之抗礼,即不悉何神也”⑥刘义庆撰,郑晚晴辑校:«幽明录»卷5,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足见吴猛有往来阴阳两界的神通。关于吴猛的身份,«搜神记»称吴猛曾“遇至人丁义,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术大行”,«幽明录»更是直言他是术士。已死之人想要复生得依靠方士往来阴阳两界的神通,这一点出土的«丹»篇与后世的志怪小说也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复生者身体机能恢复的缓慢和艰难是«丹»篇中着墨较多的情节,这在后世志怪的同类故事中也有所继承。简文说丹复活后“盈四年,乃闻犬吠鸡鸣而人食。其状类缢、少眉、墨,四肢不用”,即丹四年后才得以听得到狗叫鸡鸣之声,才能够吃生人饭食,喉部有疤痕、眉毛稀少、面色黝黑,手脚僵硬,不听使唤。与此类似,在后世志怪小说中,部分作品也会有意“刁难”主角复活后的恢复过程。«搜神后记»卷4«徐玄方女»记载太守徐玄方女死四年后复活,“令婢四人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渐渐能开,口能咽粥,继而能语。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如常”①陶潜撰,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25页。,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才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②参考姜守诚:«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第一章«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考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页。。而前面提到的«搜神记»卷15«颜畿»一事则与丹恢复身体的过程更为相近。颜畿复活后“将护累月,饮食稍多,能开目视瞻,屈伸手足,不与人相当。不能言语,饮食所须,托之以梦。如此者十余年。家人疲于供护,不复得操事。含乃弃绝人事,躬亲侍养,以知名州党。后更衰劣,卒复还死焉”③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4~185页。。颜畿复活后终其一生也没有将身体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生时“服药太多”,伤了五脏;另一方面则是作者要努力刻画复生者恢复健康的困难。更加可堪玩味的是,颜畿复活后“屈伸手足,不与人相当”这一点与丹“四肢不用”可谓“同病相怜”。由上可见,此类故事在流传演化过程中依旧沿用着许多共同的情节。
冥界观念反映出古人对于人死后所去往的世界的看法,这种看法主要体现在对鬼的认识上。«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46,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88页。«尸子»云:“鬼者,归也。故古者谓死人为归人。”②尸佼著,黄曙辉点校:«尸子»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人死为鬼,称死人为归人,反映出古人理解的死亡只是生命在阳间的终结,而人在阴间则可以作为“鬼”继续生活下去。然而死生异路,鬼和人毕竟是本质有别的两种生命形态,因此人鬼之间的差异、鬼不同于人的特征是志怪故事中喜欢着重渲染的部分。«丹»类文献注重对丧葬祭祀宜忌的揭示,但这种揭示却是站在鬼的角度思考的,依旧体现着鬼的社会规则、风俗喜好与人不同这一点。而从«丹»和«泰原»反映的“冥界观念”来看,许多内容都清楚地呈现在了后世志怪小说的相关情节中。
第一,决定人生死神祇是司命。人死为鬼,人何时才会死、能否死而复生则由司命决定,这是从«丹»篇到后世的志怪小说一以贯之的信仰观念。司命之神掌管人的寿夭,这种信仰在先秦就已经十分流行。大司命之名目前最早见于春秋晚期齐国青铜器洹子孟姜壶铭文,传世文献中对此也多有记载。③关于先秦两汉司命信仰的演变,可参考杜正胜:«祖先、天神与生命的关系»中“早期的司命神祇”一节,收入«从眉寿到长生——医疗文化与中国古代生命观»“祝祷篇”,三民书局(台湾)2006年版,第191~202页;姜守诚:«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中的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第162~164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至乐»中庄子对骷髅所说的一番话:“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④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十八«至乐»,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19页。这里直接点明了司命可使死人复生这一点。在«丹»篇中,丹得以顺利复活得力于“司命史公孙强”,关于司命史公孙强是人还是神,学界尚未有定论,①李学勤认为司命是神名,司命史是司命的下属官员,自然也是神。雍际春也认同此说,认为司命史是“主寿之神司命的下属”。有些学者则认为司命史公孙强是人,如李零认为公孙强是犀武手下“舍人掌命者”之一;孙占宇认为“司命史公孙强当为人而非神,盖是公孙强欲自神其说而假托为司命神之属官”;姜守诚认为公孙强是有通灵本领的巫师方士之流,类似于后世的“灵媒”。见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第44页;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李零:«秦简的定名与分类附录: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今移简6于简7后)»,«简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丹›篇校注»,简帛网,2012年7月31日,http://www.bsm.org.cn/;姜守诚:«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中的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第163~164页。诸家意见,即便认为公孙强是人,也承认他是方士之流的人物,当时人相信这类人有可以沟通司命的能力,类似于前文所举的吴猛。他们可以与司命之神沟通,这与司命神决定人之寿夭的观念并不冲突。然而这里反映出的,司命可以使死人复活的观念和庄子说的一番话并无二致。在后世的志怪小说中,除去李学勤举出的«搜神记»卷15中的«贾文合»«李娥»之外,«列异传»中«蔡支»②曹丕:«列异传»,收入曹丕等撰,郑学弢校注:«列异传等五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5页。、«幽明录»卷4«易脚»③刘义庆撰,郑晚晴辑校:«幽明录»卷4,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等故事也都属于司命使死者再生的类型。或许需要提及的是,魏晋以来志怪小说中透露出的司命信仰,似乎与前代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司命只能决定人的“命”,却不能决定人的“运”,而在魏晋的志怪故事里,司命不仅执掌人的生死,还能够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贫富穷通。④见«搜神记»卷10«张车子»,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3页。«幽明录»卷2«冢上紫气»,刘义庆撰,郑晚晴辑注:«幽明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命”和“运”都被囊括在司命的手中,这时的司命才真正称得上是人命运的主宰。
第二,黄豆在冥界可以作为金钱使用。«泰原»提道:“死人所贵黄圈。黄圈以当金,黍粟以当钱,白菅以当。”句中言明黄圈可以当做黄金使用,并在文末交代“黄圈者,大菽殹,剺去其皮,置于土中,以为黄金之勉”,李零指出黄圈指的是“大豆黄卷”,“是用大豆发出的黄色豆芽”。①李零:«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文物»2012年第6期,第82页。这样的观念也见于东汉灵帝时期的张叔敬朱书陶缶镇墓文:“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②陈直:«汉张叔敬朱书陶瓶与张角黄金教的关系»,收入氏著«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页。黄豆可以用于地下官府缴纳赋税,这也反映出黄豆在地府充当金钱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对于志怪小说也有所影响。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尸穸»中记载了一则故事,南阳人苏调的女儿死去三年后得以复生,她在回忆冥界生活时说:“赤小豆、黄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无复作苦。”③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集卷13,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4页。此句本来颇难理解,因为没有上下文参证,读者无法知悉赤小豆和黄豆究竟有何妙用,竟能使已死之人在地府之中少受磨难。但是联系到«泰原»以及东汉陶缶的镇墓文,我们便可清楚地了解到赤小豆和黄豆是古人观念中阴间的金钱,它们是财富的象征,可以使地下世界的人免于劳役。④参考姜守诚:«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第六章«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体现的冥界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06页。出土的«泰原»竟成为解读«酉阳杂俎»中这则故事的关键注脚,这揭示出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
第三,复生之人的婚姻关系认定。已死之人复生之后,对其婚姻关系也要重新加以认定。尤其是女子,若其死后复活再嫁,那么生前嫁的丈夫是否还与之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呢?«泰原»有一条说“女子死三岁而复嫁,后有死者,勿并其冢”,此句有诸多解释⑤诸家解释可参雍淑凤:«北大藏秦牍‹泰原有死者›断句、语译、阐释商榷»,«古籍研究»2017年第1期,第198~199页。,但是诸家所说有一点则为共识,那就是对于已死的女子来说,她若另嫁他人(死后在地府改嫁或者复活后改嫁),就不能与原来的丈夫合葬在一起。这其实是借合葬谈论婚姻,表达对于已死之人或者复生之人婚姻关系的看法。当一个女子死后,她与生前丈夫的婚姻关系也已经解除,因此就不宜与其合葬。而在她改嫁后,则应该将其认定为再嫁丈夫的合法妻子。①参考姜守诚:«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第六章«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体现的冥界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303页。这样的故事在«搜神记»卷15中收录有两则。在«王道平»中,秦始皇时期与父喻青梅竹马的王道平外出从军,父喻父母遂将其嫁给刘祥,三年后她抑郁而亡。王道平回乡后得知此事,悲痛中前往父喻墓前拜祭,父喻魂自墓出,告诉他自己可以复活,复活后两人结为夫妇。刘祥得知此事后向官府申诉,最终官府判决“断归王道平为妻”②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179页。;另一则故事见于«河间郡男女»,«王道平»即以此为蓝本,因此故事基本相似,唯所言时代不同(河间男女之事发生在晋武帝时期)③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9页。。«搜神记»中的这两则故事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其实也是如何认定复生女子改嫁时的婚姻关系,而且最终的结论——女子应认定为再嫁丈夫的妻子,与«泰原»透露出的观念不谋而合,因此不能不说这两者间存在着紧密的思想关联。
“«丹»类文献是‘搜神’体志怪小说的滥觞”这一定位还旨在表明,«丹»类文献与成熟的志怪小说尚存在较大的差异,只能视为“搜神”体志怪小说中复生类故事的早期形态。
将«丹»类文献与«搜神记»这样的志怪经典相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许多学者都不再把«丹»类文献作为志怪作品来看待。由前文对«丹»类文献学术前史的回顾,可以将原因总结如下:其一,«丹»类文献的核心内容是揭示丧葬祭祀宜忌,而不是为了讲述一个死而复生的故事,叙事在文献内容中不占主要地位。其二,«丹»类文献具有实用性。从创作目的来说是为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是为了表达文学意象。其三,«丹»类文献采用了官文书的形式,与后世的志怪小说在形式上差别较大。以下则围绕这三点为中心,进一步论述«丹»类文献与成熟的“搜神”体志怪小说的差异。
第一,从内容特征上来看,“搜神”体志怪小说重在叙事,而«丹»类文献重在传达知识。
从文体的基本特征来看,“搜神”体志怪小说以叙事为宗。以«搜神记»为例,在目录分类上,«搜神记»曾长期被划入史部而非子部。«搜神记»在«隋书•经籍志»以及«旧唐书•经籍志»中,都属于史部中的杂传,刘知幾也认为其属于史书类的杂记。直到«新唐书•艺文志»才将«搜神记»划入子部小说家类①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诸子以议论为宗,而史部以叙事为宗,将«搜神记»等作品划归史部,说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叙事是其基本特征所在。出土的两则复生故事中,«丹»篇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丹死而复生的全过程,而后半部分则是借助丹之口向人们透露鬼在墓祀方面的喜好,其实质是为了说明鬼的习性与社会规则,传达对鬼的一些认识。而«泰原»对于主人公复生过程的忽略,更加让我们相信对鬼的关注才是这类文献的核心内容。此外,“搜神”体志怪小说以叙事为宗,还表现在其叙述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丹»类文献则以讨论鬼神的习性为中心。即便是情节模式相近的故事在这一点上的区别也很明显。试以前举«戴洋复生»为例,这则故事也是对复生过程一句带过,而主要内容在于戴洋复生后的叙述。这种内容结构和«泰原»是一致的。对比两个故事中人物叙述的内容,戴洋复生后讲述了一番自己死后在天界见闻:“死时,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箓,给吏从幡麾,将上蓬莱、昆仑、积石、太室、庐、衡等山,既而遣归。”作者显然意在借戴洋之口展示出仙界领域的广阔宏大和仙人的生活的自由超脱,但这种情境的展开是以戴洋游历仙境为线索的,记述的内容也是戴洋死后经历的一部分,人物活动依旧是叙事的主体内容。«泰原»在这部分内容的处理上则抹去了人物的痕迹,只是用条文的形式分条对鬼的好恶进行归纳,旨在揭示出鬼有异于人的某些特征。这些无疑显示了叙事在«丹»类文献中处于次要地位,而传达关于鬼的知识才是此类文本的主要特征。
第二,从创作目的来看,魏晋志怪乃是为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而«丹»类文献则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生活。
鲁迅提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在古小说研究领域是一个经典的命题②近来学界对于这一命题是否成立进行了新的思考。见刘勇强主持:«“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对吗?»,«光明日报»,2016年4月28日,第16版;陈文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不能成立»,«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第26~37页;程国赋:«“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刍议»,«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第38~50页;吴怀东:«鲁迅“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说补论——基于学术史的讨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第51~58页。,而这一命题的提出则是为了与魏晋志怪“非有意为小说”进行区别。魏晋志怪“非有意为小说”并不是说这类小说的创作者没有写作目的,而是指时人“没有把它当做文学体裁的一种来对待”。③王枝忠:«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第74页。其创作目的,鲁迅总结为“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而根据作者身份的不同又可以具体分为两类:教徒“意在自神其教”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文人多为“传鬼神明因果”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总而言之,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创作并不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顶多算是教徒的宗教宣传或者文人的消闲之作。
«丹»类文献对丧葬宜忌的关注和强调,使得研究者对其写作目的做出种种猜测(详见前文学术前史梳理)。虽然见解各异,但研究者们无疑都指出了«丹»类文献的产生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为人们提供某种生活中的指导。可见,«丹»类文献本质上是一种生活中的实用性文本,它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紧密。这样的特征,反映出这类文本很可能是从方术文献改造而来的。所谓方术,是“数术”和“方技”的合称,它们是古代与宇宙万物和人体健康有关的两门学问。①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98页。方术来源古老,春秋战国特别是秦汉以来逐渐兴盛发达,后世多以“方术”指星算占卜、医药养生之学。②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21~425页。方术书籍在汉代颇为流行,«汉书•艺文志»曾对西汉时期的国家藏书做出分类介绍,将当时的典籍分为六大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方术类书籍独占两席,其繁盛可想而知。但方术书籍后多散佚,留存下来的仅为少数,所幸由于出土发现,不少方术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其中就包括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甲乙两种«日书»。«日书»甲种«诘»篇记载了制服鬼怪的种种方法,其中提到“鬼之所恶,彼屈卧箕坐,连行踦立”③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简文是说鬼所厌恶的,是踡曲而卧,两腿分开而坐,鱼贯相随而行,单足而立这几种姿势。④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347页。这条简文的句式和内容都与«泰原»极其相似。“鬼之所恶”的表达方式,也见于«泰原»:“死人之所恶,解予死人衣。必令产见之,弗产见,鬼辄夺而入之少内。”而强调鬼对于某种姿态的好恶,在«泰原»中也有所写照:“收死人,勿束缚。毋决其履,毋毁其器。令如其产之卧殹,令其魄不得落思。”这是说“收殓尸体时,不要加以捆绑,不要扯裂死者所穿的鞋履,不要毁坏随葬的器具,应让尸体保持生时的卧姿,务必使死者的形魄不被束缚住”⑤姜守诚:«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考释»,«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第160~161页。。鬼厌恶“屈卧”与泰原复生者声称的要保持死者生时的“卧殹”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从«泰原»与«诘»篇的这种相似性出发,«丹»和«泰原»文中借复生者之口所揭示的内容,很可能是直接从«诘»这类方术文本中移植过来的,«丹»类文献是从方术之书增饰而来的结果。或许是方士为了使民众相信其学说,因此才虚构出丹之类的人物,借助他们死而复生的经历来使自己的说辞取信于人。抑或方士出于宣传的目的,为使自己的厌胜之术易于流传而别出心裁将日书条文改造成一则前后连贯的复生故事。无论如何,«丹»类文献都体现出了方术文献的特征,而方术类文献“很多是实用手册和教科书式的东西”①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00页。,这类书籍的产生是用于服务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创作目的上与魏晋志怪大相径庭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从文体形式上来看,“搜神”体志怪源出于史传,与杂史杂传最为相近,而«丹»类文献则近于文书。
“搜神”体志怪小说取名多用“传”或“记”,表明其作者力求以撰写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来写作志怪作品。但因其“体制不经”“真虚莫测”②“体制不经”“真虚莫测”本是«隋书•经籍志»对杂史的评价,李剑国指出,这同样也是杂传的两个基本特点。见李剑国:«序»;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页。,无法与正史共享“纪传”之名,故«隋书•经籍志»将其归于杂传。小说作品归入杂传,反映出小说与杂史杂传两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这一现象也令历代目录学家很难将其区别分类,«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杂史类引郑樵语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5«经籍二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8页上栏。,«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三»也说:“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④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二十七册,«子部•小说家类三»,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68页。。有学者指出,小说与杂史杂传的区别主要表现为题材选择和叙事方式两方面:就题材选择来说,述怪语异之“志怪”,载录各类历史人物琐闻佚事之“杂录”“杂事”“琐语”,记述人间奇人、奇情、奇事之“传奇”往往被视为小说;就叙事方式来说,叙事曲折细致,文辞华艳的作品属于小说。⑤谭帆、王庆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略论»,吴承学、何诗海编:«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可见,小说乃是史乘之支流,其文体标准是从与杂史杂传的比较中总结出来的,有了这样的标准,小说才得以与杂史杂传划出界限,并在目录分类里从杂史杂传中独立出来“自立门户”,重新回到子部的旧传统下。需要强调的是,在很长的时间段内,这类小说作品都是被当做杂史杂传来看待的,而杂史杂传也是在与正史的比较中分化独立出来的。程千帆曾将杂传与正史的区别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正史史传“以整体史实为对象”,“着眼史实所关,而定其去取”;杂传“专以传主一人为对象”,取资标准与史传有异。其二,史传为全书的一部分,人物事迹,“必赖互见”;杂传“以单行为主”,传主以及有关人物的事迹都会叙述。其三,正史人物的褒贬多秉承«春秋»的评价标准;杂传则杂以“虚妄之说,恩怨之情”。①程千帆:«闲堂文薮»,«程千帆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正因存在这样的差异,杂史杂传才被冠以“杂”字,而杂史杂传(包括被«隋书•经籍志»视为杂传的部分小说)与正史同列于史部,都采用纪传体来组织人物事迹,则显示出在文体形式上的一致性。
«丹»类文献从形式上看属于行政文书。«丹»篇中的“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透露了这是一份由邸丞上呈给御史的文书。②战国秦汉时期的官文书包括诏书、律令、案例、簿籍、契券、符传、公函等等形式,«丹»和«泰原»应属近于公函。关于秦汉时期的文书,参考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6~47、64~71、199页。而«泰原»中复生者被“献之咸阳”,也让我们推测此人被带到首都咸阳,交由政府人员处置,然后才有了这份记录,其性质也和行政文书相差不远。但陈侃理认为«丹»类文献并非真正的行政文书,而是有意模仿这种形式,其目的是借用这种官方化的“包装”来增加内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③陈侃理:«秦简牍复生故事与移风易俗»,«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文书属于档案的一种,档案的特点在于它的“记录性”,“它往往非常强调时间、地点、人物和谈话内容的准确性”④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9页。。«泰原»显示出这类文献关于时间、地点、人物的信息很不清晰,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文书,而是有意采用了文书形式,不妨依照话本小说中命名“拟话本”的方式称这类文献为“拟文书”,这样的形式与近于史传的«搜神记»等志怪小说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从学术界否定«丹»类文献是志怪小说的理由出发,把«丹»类文献同“搜神”体志怪小说进行比较,来说明«丹»类文献与魏晋志怪小说在形式内容、文体规范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志怪小说。然而,将其放入自身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量,与时代比较接近且同为出土文献的«汲冢琐语»相比①战国时期的准志怪小说除了«汲冢琐语»外,«山海经»也是一大代表,但«山海经»与“博物”体志怪小说更接近,因此本文不予讨论。,«丹»类文献能否被视为“准志怪小说”呢?以下就此问题展开辨析。
«汲冢琐语»本名“琐语”,西晋时期被人发现于汲郡汲县的一座古墓之中,所以又称«汲冢琐语»,属于战国初期到中期的作品。内容方面,«晋书•束晳传»称其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所谓“卜梦妖怪”,又可细分为“记卜筮之灵验”“记梦验”“记妖详”和“记其他预言吉凶的故事”四大类。②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2~94页。«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其归于杂史,但由于所记之事以志怪故事为基本内容,大多荒诞不经,因此明代胡应麟认为应该将其归于小说。胡氏«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四»云:“«琐语»之书,大抵如后世夷坚、齐谐之类,非杂记商、周逸事者也。”③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乙部»卷16«史书占毕四»,上海书店2009年版,第160页。«二酉缀遗中»称其为“古今小说之祖”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己部»卷36«二酉缀遗中»,上海书店2009年版,第362页。,后«四库全书总目»也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当代学者多将«汲冢琐语»定义为“准志怪小说”,主要原因是由于其脱胎于史书,还带有比较浓重的史书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在:其一,其作者“熟悉夏殷以来历史和掌故”,很可能是三家分晋前后的晋国史官或魏国史官。其二,其内容多取材于历史,“历史成分和虚幻成分杂糅,故事是虚幻化了的历史故事或历史化了的虚幻故事”。其三,其叙事继承史传传统,“记事首尾完整而精炼简洁,着重写人物言行,颇能表达人物特定情绪和形象特征”。其四,其形式采用史体体例,“按国别记事、以‘春秋’命题”,类似«国语»。其五,其文字简单质朴,近于«左传»。①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9~97页。小说是史乘之支流,«汲冢琐语»则体现了从史书到志怪小说的一种过渡状态,即一方面保留了大量史书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体现着小说的旨趣。相比«汲冢琐语»,«丹»类文献与志怪小说的距离还比较远。主要表现在,«汲冢琐语»中的志怪故事已经相当成熟,«丹»类文献中的志怪故事却并不成熟,它们改造自方术文献,不太重视叙事,且以文书自居,无意向子、史靠拢。其方术知识与复生故事相杂糅,体现出了从方术文献到志怪小说过渡的特点,应该说,从«丹»类文献中的故事发展到成熟的志怪故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将«丹»类文献视为“准志怪小说”显得有些“操之过急”,而将其定义为“‘搜神’体志怪小说的滥觞”则比较恰当。过去陈梦家针对«汲冢琐语»曾说:“«琐语»实为小说之滥觞也。”②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8页。当时«丹»篇和«泰原»尚未发现,这一论断无可厚非,但当两篇文献发现后,“小说之滥觞”显然更适合这两篇秦简牍作品的定位。
三、结 论
放马滩秦简«丹»篇的性质问题比较复杂,原因在于从这类文献身上可以看到许多其他文献的影子。从目的上说,它们最主要的作用是传达有关鬼神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很可能是直接从方术文献移植而来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丹»类文献具有某种实用性,实用性恰恰正是方术书籍所具有的特征,«丹»类文献呈现出的实用性特点,是它直接源出于方术文献的结果。从文体上说,它们有意地借助了文书的体裁。文书和史传一样,都是要求客观纪实的文体,这样的文体规范可以为内容提供一种形式上的真实性,掩盖虚构的事实,从而便于取信于人。从源流来说,«丹»类文献表现出从方术文献向志怪小说过渡的特点,它们是方术文献之流,同时也是志怪小说之源。就其与志怪小说的关系来说,由于两者在情节模式、冥界观念等方面存在相似性,同时又在内容特征、创作目的、文体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性,认为它们是志怪小说“尚欠火候”,最多只能算是“搜神”体志怪小说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