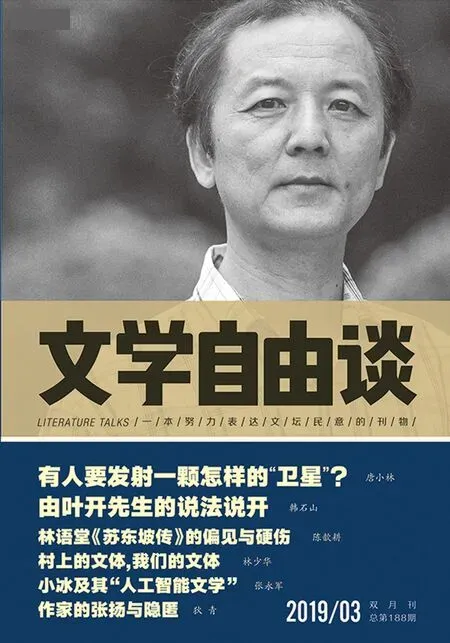影响我一生的三本书(外二章)
□王泽群
我出身于书香世家,十二岁上便罹了家难,一折腾就是二十二年,书,却从未离手。就是眼睛失明的那十年间,只要有些视力了,总会找书读,抓书读。读书以明理,审世以哲思。人,也就在不知不觉间进步着呢……
我读书极“滥”,抓到手的书,古今中外,五杂六味,诗词歌赋,小说戏曲……几乎都读。大多是通读,偶尔会细读。最认真读过的是《资本论》。荒原大漠,“文革”动乱,在戈壁“造河”,孤寂无聊。枕边恰有一套领导赠予的《资本论》,于是便“下定决心”“鼓足干劲”地读了起来,且读得有滋有味——这是题外话。
有一次与读书极多的好友苇子说起读书,我表扬她读书又多又快,且能总结出极好的文章。苇子很受用,但仍然谦虚地请教我:“你都读些什么书?”我说,我读的书很杂,很乱,但影响我的只有三本书,且都不是中国书。苇子有些吃惊,再问:“哪三本书?”我答:《牛虻》教我知道,一个人在心灵受到极大创伤后,该如何坚强;《红与黑》告诉我,尽管人世炎凉,你却只需抱定自己的目标,义无反顾,趔趄前行;《约翰·克里斯朵夫》则让我懂得了“圆融”二字,当一个人真正地走过、看过、见过,且心身俱是伤痕,他就会真正懂得自己该如何活在世上,活在当下,该珍惜些什么,该摒弃些什么了。
二十一岁远在高原大漠,母亲自戕后我双目失明,自己写下:“相信命运,绝不屈服。努力奋斗,永远微笑。”
五十六岁一切安定,我再撰座右铭:“一杯清酒,两肩闲云。万里襟怀,千年野史。”
三十五年间,一半儿是山一半儿是海,一半儿是汗一半儿是泪,一半儿是苦一半儿是痛,一半儿是血一半儿是花……这三本世界名著却一直在我的箧中,枕边,心上,不离不弃,煜光永照。
“文革”时有人说过“要学会用书,用报”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这本书
总以为,心底里鼓胀起来的起伏跌宕、排山倒海、缱绻缠绵、魂牵梦萦、倾心倾肝、哀痛哀伤的爱之诗意,滴到纸上,就是血。
古往今来的《诗经》、《离骚》、唐诗、宋词、元曲、新诗、散文诗,最能打动人心、被千年传诵的,是写爱情的那些篇什。凡是读书人,都有自己喜欢、记得结实的绝句,不需我在这里罗皂的。
当然,也有长风万里、大江东去、挑灯看剑、金戈铁马、卷起千堆雪……但那是英雄心曲,唱得豪壮,却与芸芸众生无关。君不见,中国各地、各民族的各种民谣,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唱爱情的。“食色,性也”。爱情,是人类本真的生命重要元素之一。
编辑这本《中国当代爱情散文诗金典》(以下简称《金典》),缘于我对“散文诗”这一总被文学大雅之堂“无视”的体裁的注视。
散文诗是和白话文几乎同时诞生的。有了白话文,就有了散文诗。第一个写新诗的是胡适,第一个写散文诗的是沈尹默。然而,新诗乍起,便云涌风狂,出现了一批巨匠,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等等,他们的诗集也一本一本被读者选出且喜爱。散文诗却没有。只有鲁迅的一册《野草》。幸亏是鲁迅,否则,《野草》怕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诗仍然很强势,涌现了一批以歌颂为主流意识的诗人,如闻捷、公刘、郭小川、贺敬之、李瑛等;散文诗仍然没有。仅有的、一直在操作散文诗的郭风、柯蓝,也无法与新诗的“著名诗人”们比肩。
改革开放之后却不同了,以耿林莽、许淇、李耕、王尔碑四位老将领衔的一大批散文诗人,为中国文坛奉献出大量的散文诗作品。这个羽量级的文体,在诗人们的努力、探索与开拓中,承载了重量级的内容,关乎历史、哲学、战争、人生、红尘、情感等等的方方面面。
以文学的视角审视,当下的散文诗创作,已不逊于新诗,甚至有了一定的超越。散文诗的年选本也已多至五六种就是证明。何况这些选本的选家,因为艺术观念与认知感觉的不同,使得这些选本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相映成辉,水准颇高。
收入《金典》的一百三十三位散文诗人的作品,就算是挂一漏万、贝海遗珠,仍然可以感觉到她基本涵盖了当今中国爱情散文诗的创作。《金典》中既有老诗人们对爱情、婚姻、承诺的深厚感悟,也有年轻的无名作者充满激情的对于人生、命运、萌动的淋漓高歌,更有一些娴熟操练了散文诗多年的中坚力量,大气磅礴地唱出了上古、人间、神话、传说,乃至于生命对于情爱的刻骨感觉。《金典》中的许多作品,对于散文诗这一独特文体的修辞、遣句、架构、折叠,都有着自己大胆的求索与开拓。
这是一本不错的书。
友人诘:何以是一百三十三?
吾笑答:一百三十三是素数。世界上许多发现、发明、奇迹、奇葩,都是素数。
是为序。
(本文系《中国当代爱情散文诗金典》之代序)
奇才阿正
阿正不大给我微信的。
我们是挚友,但也是那种“君子之交,淡淡如水”的挚友,更是那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挚友。
所以,他发了一个微信,说他的《上山——阿正文集》要出版了,让我“义不容辞”地给他写点儿什么,我也就“义不容辞”地回了四个字:义不容辞。
阿正的大名是:张永正。但是,阿正也好,张永正也好,估计没有多少人能够知道他,或是记住他的。
倘若我说,记不记得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访,北京大学以“国礼”的规格,送给他一幅铜版腐蚀肖像画?把克林顿刻画得惟妙惟肖的铜版腐蚀画作者,就是阿正。
用阿正自己的话说:出了点儿事。
与阿正相识在青岛人最可自豪的崂山清幽幽的山间。
喝了酒,在注满“崂山矿泉水”的泳池里游了泳,聊了半宿的天,睡了个囫囵觉。第二天,我们准备去访一位朋友。简单的行李都拎在手里了,阿正突然说:“它还在这儿。”就匆匆地出了门。
我挺纳闷:这伙计,干什么去了?“它”是谁啊?
还没等我寻思出个ABC,阿正笑嘻嘻地回来了,手里拿着个挺精致的球型铁笼子,笼子里面是一个青青的大蝈蝈。
我一下子就对这位张永正同志有了极大的好感!——五十多岁的人啦,童心未泯呢。
这样的朋友,值得交。
我们拜访的这位朋友是个“恋物癖”。
恋物癖,不是收藏家,却是比收藏家更“收藏”的一种收藏。
进了他“借用”的家,我大吃一惊,也大开眼界——庭院不大,却幽雅,摆满了现代装修剩下的砖瓦和不知道年代的瓦当;房子不新,却讲究,虽是农民房,但加了一个正正方方的玻璃门廊,这就不俗了;门窗却不是农家的原装样式,且一看就知道,非常结实,我估计是防偷防盗吧。
进了门,满满当当的全堆满了“物”,大到钢琴,小到茶盅,中到佛像,就连做饭的家什,锅碗铲勺,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这主儿,莫非什么都喜欢,都收藏?我是真惊了!
这朋友是阿正的发小,也是职业钢琴教授。他的弟子,在国家级的艺术团体里工作的不少,有些甚至都已成了“大师”;他甚至开过弟子们的专题演奏会,据说,社会反响还很不错呢。说起这些,他很得意,但他更得意的是自讽自嘲他的恋物之愚蠢,交易之失策。这就有些意思了。简言之,那就是他常常用一头牛,换了一头驴;然后用驴,换了一只羊;用羊,换了一条狗……三换两换,最后换成了一只小老鼠——居然还是个死的,只能做标本。
朋友讲得栩栩如生,有声有色,我听得哈哈大笑,捧腹喊痛。而阿正作证:他说得都是实话,是真实的故事。当年,朋友就用刚刚做的崭新的穿了没几天的皮大衣,换了阿正年节前买的一束刚刚时兴、朋友从没见过的塑料花儿。
就是这样一位主儿,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仅在崂山,他就“借家”了三处农民房,全都收拾得有板有眼有模有样,全都堆满了他的各种“物”的财富。仅我们进的这套民房里,三间屋除了杂七杂八的东西物件,就放了三架钢琴,且都用金丝绒毯盖着;至于那些佛像、木雕、茶具、珠串、艺术品,以我这凡人俗眼估量,都该是很有红尘价值呢。
我在房间里看到了阿正为他作的素描头像,对照他本人,实在是太像太传神了,我对阿正的这种本事,又陡添几分敬意。朋友却指着一件似匾似中堂的相框——里面是五个大字,写得还不错——问我:“看见这题字了吗?”我应了。他再说:“您念念。”客随主便,我就念了:“梁柏梧自题。”朋友问:“懂了吗?”我懵懂,且诧异,没作声。这朋友指着自己的鼻子尖说:“我的大号,梁柏梧。梁柏梧,两百五呀。我就是个‘两百五’!”
我猛省。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酒罢返程。我以作家的敏感说道:阿正,你的这位朋友,这个梁柏梧,写篇小说——当然得是中篇——肯定出彩。
阿正应道:我对他最了解啦。我来写。
我一楞。心里暗忖:你这个伙计,写小说?小说是那么好写的么?
但我没说。因为我知道,阿正是个奇才。他玩什么都能玩出个花样来。且拭目以待。
我说阿正是个奇才,绝无任何奉承之意。
“文革”失学,他无师自通,拉起了小提琴,且进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好像还坐了首席。有一次访朋友,公司客厅里放了一架钢琴,守着钢琴教授朋友,阿正弹了一曲,那手法,那旋律,甚是娴熟,曲子也好听。我是个“乐盲”,问他:“这是谁的作品?”阿正很随意地一笑,说:“胡弹,我的即兴创作。”
我大讶!
阿正长得很端正,很男人,一双眼睛后面,还有一双眼睛——虽然总是和善地、笑嘻嘻地看着你,但偶尔一闪,就是狡黠与不屑了。他的智慧与思想,不同凡人。
在文化宫工作的时候,他搞了许多“第一”——
他策划和组织了青岛市第一次“够级”大赛,掀起了青岛人发明的“够级”扑克的一个小小热潮;
他策划和组织了“全国第一”的有外国朋友参加的外语歌曲大赛,还出了磁带和歌曲集;
还有“青岛第一”的群众歌咏比赛,等等。
他不光给克林顿做了铜版腐蚀肖像画,萨马兰奇、吴仪、澳大利亚的霍克、日本的村山富士,以及两院的院士、文化名人等等,他也都受邀为他们做过画。被画的人,个个都非常满意,十分满意。
至于他和小培自驾游,绕着金鸡形的边境线走了数万公里,恐怕也是个“全国第一”。
现在该说说他这本《上山》了。这本书也是个“第一”。
笔耕墨海里蹉跎五十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文集”。
把中短篇小说(十五万字)、纪实文学(十万字)、彩印文字(三万字),以及为世界政要作的像,国内游走的、域外掠影的照片,钢笔画、油画,小提琴的叙事曲等等,全装在一个“筐子”里,除了张永正同志想得出,做得到,其他人就是想了,恐怕也做不到!谁有他这份儿才气?
这“筐子”里的东西,除了“小提琴叙事曲”,我都见过,特别是文字的东西(我指的是“小说”),我打压了他许多次。他是灵机一动,想起来了,就写了小说的。只有生活准备,没有文学准备,但他是个奇才,出手就有高度,从不荒腔走板。但人太有才了不免就有些“卖弄”,卖弄文采和思想。写小说最忌讳的恰恰是这一点。
他的小说处女作,写梁柏梧的,大概有三万字吧,他径直投给了《收获》。我听后又是一惊!“兄弟,你老哥操弄笔墨营生多年啦,小说也写了上百篇了,长篇、中篇、短篇、微型,甚至百字小说,被选中的多啦——《小说选刊》都选过我的中篇做头题——但我从来也没敢给《收获》投过稿子。我视《收获》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就您?一出手就是《收获》?尽管你奇才,你‘横溢’,我可不信你一下子就‘收获’了。”
想是这么想了,我却声色不动,静待结果。果然,他碰了壁。
所以,他的小说写一篇,我就批一篇,认为不行,需要改,需要朴实下来,平和下来,普通下来,纯净下来……他喏喏,但眼中常常闪出另一双“眼睛”。我装作不知,继续批判指点。他的优点是不管服不服,还是都听进去了;他的缺点是不管服不服,该改的我改了,您说不行,我不听,我也不服,我自己找个地儿寄了!几番折腾,居然,人家就通知他“用了”,还都是不错的、有级别的刊物。
这就让我无话可说了。除了祝贺,还是祝贺。
这个“野路子”的阿正,有赏识他的“野路子”的编辑。所以,我说他真是有才。有奇才。
到了《上山》,我读过后,只好说:“我真的不敢说你这篇小说写得怎么样了。盖因它极有激情,极有生活,文笔也相当不错。但你这写法,我不好说了。这样吧,你按你的意思去做。该是谁,就是谁了。”
果然,不久有他的微信:编辑通知,用了。
这就是阿正。张永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