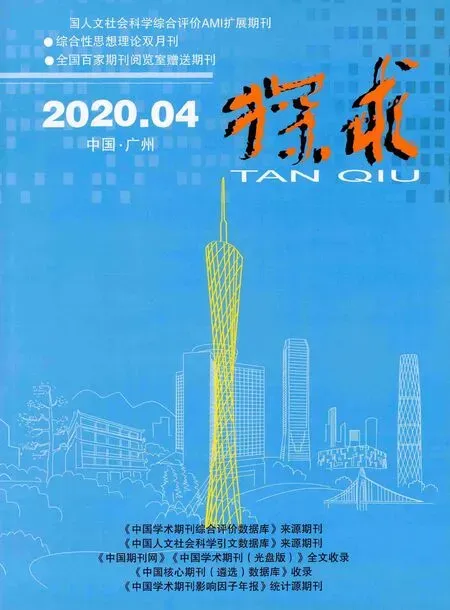生态安全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探究
□ 黄克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生态安全,把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之中,强调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是确保总体国家安全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家赖以持续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生态安全型社会”[1]。2019 年2 月颁布实施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将“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确定为大湾区合作六项基本原则之一,提出要建设“生态安全、环境优美、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美丽湾区”[2]。提出上述目标,一方面,既是加强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需要,也是大湾区建设生态安全型社会,顺应大湾区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城市扩张发展,大湾区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出现下降趋势,生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需要通过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优化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为大湾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支撑。
一、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是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屋建瓴,适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4]。明确将生态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之中,这是在准确判断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部署,对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建设生态安全型社会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生态安全的提出过程与发展完善
“生态安全”一词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 年代末,包括生态安全在内的新安全观逐渐超越了传统安全观,认为对安全的威胁并非只来自军事战争,生态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个人人身安全的重大因素[5]。2000年11月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正式提出“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2014 年4 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态安全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2015 年7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①,其相关核心指导思想就是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我国生态安全。2016 年10 月颁布的《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总体形成,国家生态安全得到保障”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之一[6]。2017 年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1],并阐明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7]。2020年6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提出,宁夏要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8]。
综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已成为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生态安全观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与生态安全相关的一系列制度的不断完善,生态安全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为建设美丽中国夯实了基础。
(二)生态安全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
生态安全是一个复杂问题,它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通常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生态系统自身是否安全,即其自身结构是否受到破坏,功能是否健全;二是指生态系统对于人类是否安全,即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9]。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应避免因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的威胁。另一方面,要避免因生态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引起暴力冲突,对区域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10]。
生态安全具有多重特征。一是整体性。局部生态环境的破坏可能引发全局生态问题,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深刻影响。全球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相互贯通的大系统,即使局部生态环境遭破坏也会导致全球性的灾害,出现气候异常、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土地荒漠化等环境问题并最终威胁地球的生存。二是综合性。生态安全是全部生态安全要素即森林、海洋、草原和农田等生命系统以及大气、水源和能源等矿产资源环境系统安全性的综合,而不仅是指其单个要素的安全性。这表明生态安全涉及到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因素,生态安全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三是长期性。生态环境的治理具有长期性和高代价性的特征,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人们历史性活动破坏的结果,因此其治理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0]。
(三)生态安全的构成要素与实践要求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安全的构成主要分为:一是按构成体系划分,生态安全体系主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包括生态系统、生态景观、生态功能区、陆海生态等安全,也包括水、土地、大气、生物等方面的安全)和人类生态安全(包括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安全)。二是按空间构成划分,生态安全包括区域生态安全、国家生态安全和全球生态安全等不同要素。三是从生态系统角度分析,生态风险与生态安全是衡量生态系统存在状态的主要因素。生态风险指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遭受不可逆损害乃至覆灭的可能等。化解生态风险,有助于实现生态安全。
综上,从分析生态安全的内涵特征及体系架构等方面来看,在当下我国生态安全建设实践中,应把主要目标集中于受到潜在威胁的、生态风险较高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要积极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以确保国家的生态安全和总体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等方面已有良好的开端:一是开展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工程。截至2019 年底,已建立自然保护区2750 个,总面积达到147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5%。二是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生态保护红线应用于全国生态管理的国家。截至2019 年底,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我国陆域国土面积的25%,覆盖所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三是筑牢重点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包括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内蒙古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甘肃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实验区等,上述区域(集中在西北西南)是构建我国陆地生态安全屏障的“主战场”。与陆地相比,我国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比较滞后。如国家公园作为一种新的生态保护形式和制度,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示,目前已在三江源、大熊猫、祁连山等10 个陆地区域开展试点工作,但尚无海洋类国家公园试点,国家亟须探索海洋类国家公园建设的经验,以弥补我国海洋国家公园的空白。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在这方面已开始谋篇布局。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近年来粤港澳全面开展珠江口生态修复整治工作,做好建立珠江口国家海洋公园的准备工作,设立跨境生态修复和自然保护协调机制,等等。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已成为当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二、筑牢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是践行生态安全观的生动写照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加强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安全环境优美的美丽湾区是重要的举措与目标之一。为此,必须认真践行生态安全观,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筑牢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安全屏障,优化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举措。从生态学角度分析,生态屏障是指处于过渡地带,经过人工改良的具有明确保护与防御对象的复合生态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空间跨度,在空间上呈封闭或半封闭分布,能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促进区域生态安全,优化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则是由生态基础体系所占据的物理空间及地理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11]。生态屏障与生态安全关系紧密,生态屏障是生态安全的保障,生态安全是生态屏障建设的目标。生态屏障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生态安全。优化生态安全格局必须践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理念(该理念是指处于特定的区域,具有保护功能的生态安全系统的理念)。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珠三角9 市)认真践行生态安全观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搞好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优化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等方面已初见成效。
(一)健全完善政策法规,以区域规划引领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在保障区域环境安全方面,2004 年12 月,国家建设部与广东省共同编制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年)》,将珠三角区域内生态环境、城镇、产业与重大基础设施地区划分为九类政策区,不同分区实施不同的空间管控,强调保护区域发展的生态“底线”,构筑珠三角网络型的生态结构[12]。2005 年2 月实施的《珠江三角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4—2020年)》提出建设生态环境安全格局,要求红线调控,优化区域空间布局;绿线提升,引导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蓝线建设,保障区域环境安全[13]。2014 年11 月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生态安全体系一体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要依托林地、水系、山脉等要素,组合、串联和扩大各类绿色生态空间,构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森林绿地体系[14]。
在建立粤港澳环境合作的体制机制方面,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和相关专项性环境规划和环境协议的相继推出,粤港澳三地间的环保合作全面开启。在空气质量管理、跨界河流治理、珠江口水质管理、东江水质保护等环保领域的合作正持续深入开展并取得实效[15]。如深港联合治理界河——深圳河,该河河口断面曾是广东9 个不达标国考断面之一,水质长期劣于地表水Ⅴ类标准。从1995 年开始,深港联合启动深圳河治理工程并取得良好成效。近年来,深圳河河口断面水质连续达到地表水Ⅴ类,2020 年1-5 月,深圳河口水质达到地表水IV 类标准,为1982 年有监测数据以来的最好水平[16]。澳门自2008 年起每年举办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促进泛珠三角地区与国际市场间的环保商业、技术及信息交流;澳门现已与广东及香港形成环保交流合作常态机制,参与了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共同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17]。
(二)建设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与绿道网,筑牢大湾区绿色生态安全屏障
在森林绿化方面,广东是全国绿化第一省,2013年广东便在全国首次提出建设国家森林城市群的概念,明确提出在珠三角率先建成中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群,这是广东先行先试、科学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世界级城市群的有益尝试和探索。2012 年至2016 年,广东围绕森林生态体系建设,设立各级森林公园1351 处,占全省国土面积的6.8%,森林公园数量跃居全国首位。2017 实施的《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建设规划(2016—2025 年)》提出要重点加快推进珠三角森林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努力构筑稳固的珠三角森林生态安全屏障。2008年广州率先建成广东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拉开了珠三角森林城市建设序幕。从2014 年至2018 年,惠州、东莞、珠海、肇庆、佛山、江门、深圳、中山也相继创建成功,至此,珠三角9 市如期实现“国家森林城市”全覆盖,2019 年森林覆盖率达52%,接近热带雨林国家巴西水平[18]。
在绿道网建设方面,2010 年广东在全国率先出台绿道网建设规划,并在广州增城开我国绿道建设的先河。2010—2019 年,珠三角已建成绿道超过1万公里(广东省1.8万公里),森林公园 482 个,基本实现“300 米见园,500 米见绿”,“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雏形初现[19]。绿道网建设有效地改善了大湾区生态环境,为推进大湾区全面建设构建了生态安全新格局。
(三)打造水清滩净美丽湾区,筑牢大湾区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
自2012 年国家启动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活动以来,广东有位于大湾区的珠海横琴、深圳大鹏及惠州获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上述示范区为建设美丽大湾区夯实了基础。2016 年12 月,《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为主线,以维护广东沿海海岸带生态系统稳定性为基础,优化海洋生态安全格局。2018 年1 月,《广东省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提出要以推动大湾区绿色发展为目标,加强大湾区自然岸线保护,以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作为刚性约束,开展“美丽海湾”“美丽海岸”“美丽海岛”等污染整治和生态修复行动,构建“蓝色海湾”保护屏障体系,打造水清滩净美丽湾区,筑牢大湾区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20]。
与全球三大知名湾区的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不同,即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地域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香港、澳门、广州与深圳四大中心城市并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广州是政治文化中心、深圳是科技创新中心,这种城市竞合关系让大湾区更有活力。从上文所提及的,近年来粤港澳三地在生态安全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就可见一斑。但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特殊格局,也使粤港澳三地环境治理必备的资源和信息未能充分实现互通共享,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和标准难以统一,继而导致大气质量改善、跨界污染治理(大气、水、垃圾等方面)、近岸海域保护等跨行政区环境问题改善的效果不佳[21]。在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区域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深度不够。自然资源资产欠账较多,生态系统较为脆弱,部分近海海域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距离粤港澳大湾区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追求仍有不小差距。基于此,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成为建设生态安全、环境优美大湾区的必然要求。
三、按照大湾区地理区域划分层次因地制宜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是我国“两屏三带”②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南方丘陵山地带和海岸带),在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从地理区域划分层次来看,可把大湾区分成核心层、协同层(中间层)和辐射层(外围层):“核心层”指临近珠江口岸线各行政区划的总和,包括广东珠三角9 市及港澳地区(即粤港澳大湾区,与大珠三角地域范围接近);“协同层”指环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是广东省除了珠三角9 市外的粤东西北地区,是大湾区城市群的直接腹地;“辐射层”主要指泛珠三角经济区(不含粤港澳)及中国内陆区域,是大湾区的广阔腹地。以上述地理区域划分层次并结合大湾区实施分区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
(一)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强珠江流域生态保护,筑牢大湾区“辐射层”的生态安全屏障
珠江是我国水流量第二大河流(年径流量3492 多亿立方米),境内第三长河流,流域涉及滇黔桂粤湘赣等六省区及港澳地区,面积约45.37 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约1.25 亿,在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珠江流域(尤其是中上游)是泛珠三角经济区的主要区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层及广阔腹地,做好珠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对促进西南、华南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当前,珠江流域面临珠江源区生态环境脆弱,云贵高原湖泊水污染及石漠化问题突出,南岭山脉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基于此,应抓紧开展顶层设计,参照国家已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的做法,及早谋划将珠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22],全力支持滇桂黔湘赣等省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外围地带的生态安全屏障。
一是建立珠江流域生态综合补偿制度,将珠江干流和各级支流(包括西江、东江、北江、武江、郁江等)的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中,并给予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从国家层面健全珠江流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纵向、横向”双向补偿[23],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合作、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建立粤桂、粤湘、粤赣等省区之间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关系,支持滇桂黔等省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二是按照《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将珠江源区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纳入国家山水林田湖草修复试点。三是筑牢作为我国南方丘陵山地带重要组成部分的南岭生态屏障,加强粤桂湘赣合作,做好南岭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确保大湾区水安全,筑牢大湾区北部生态安全屏障。
(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粤北生态发展区,筑牢大湾区“协同层”的生态安全屏障
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广东区域发展格局“一核一带一区”(即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发展区)的新思路,其中的“一区”指建设粤北生态发展区(包括韶关、清远、梅州、河源、云浮5市)。粤北地区位于我国南方丘陵地带的核心区,森林覆盖率高达73%,山地丘陵面积占81%,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广东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有效发挥粤北生态发展区生态保障的主体功能,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建设粤北生态特别保护区,打造大湾区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
为此,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成为粤北绿色发展的首要任务。一要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以创建南岭国家公园(广东省第一个国家公园)为主要目标,在保护效果、体制机制上对标最高最好最优。围绕东江、北江水源涵养区和南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两大核心功能提升,将该区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力争高标准、高水平打造集中连片、规模较大(3000 平方公里以上)的粤北生态特别保护区(以南岭国家公园为核心),助力大湾区建设。二要抓住南岭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成功入选国家试点项目的契机,实施南岭山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开展矿山治理及土壤修复,对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资源实施强制性保护,努力将粤北(以韶关、清远为中心)南岭生态屏障打造成“山青、水秀、林美、田良、湖净、草碧”的生命共同体。三要构建粤北生态发展区的生态廊道,严格控制南岭山区的开发强度,禁止可能威胁该地区生态系统稳定、生态功能正常发挥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源开发活动。四要从保护提升粤北山区生态系统的角度,健全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重点推动大湾区与粤北生态发展区建立东江、北江流域上下游“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并适当提高流域生态补偿标准[24]。
(三)以建设生态安全美丽大湾区为重点,筑牢大湾区“核心层”的生态安全屏障
粤港澳大湾区在地域分布上基本与大珠三角地域相吻合,因此,构建大湾区核心层生态安全屏障,可按照《规划纲要》《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珠江三角洲地区生态安全体系一体化规划》《广东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等规划文件,在大珠三角的架构下,制定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
1、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优化大湾区生态功能区布局
《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2]。大湾区处于珠江与太平洋交接地带,既是我国陆海统筹的核心区、蓝色国土绿色发展的标杆和试验田,也是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区的划分要以自然生态边界为准,而不受行政区划因素的影响。为此,要将大湾区内的绿地、林地、耕地、湿地等整体性划入生态功能区保护范围,通盘纳入大湾区的生态空间规划体系。
根据大湾区城市发展定位和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打破大湾区内外地域限制,推进大湾区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可借鉴大珠三角“一屏、一带、两廊、五核”的具体规划[14],构建大湾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一屏”即大湾区(核心层)的陆地生态安全屏障。大湾区的西部、北部、东部多分布大型山脉形成天然的生态屏障,包括肇庆的鼎湖山、江门的天露山、广州东北部的青云山(余脉)及九连山(余脉)、惠州的罗浮山及南昆山等,该区域主要构筑大湾区陆域连绵山体生态屏障,发挥生态防护功能,起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一带”指南部沿海生态防护带(即大湾区海岸线生态安全屏障)。以大湾区南部近海水域、三大海湾或河口(中部的环珠江口、东边的大亚湾、西边的大广海湾)、海岸山地屏障和近海岛屿为主体,包括珠江口河口、万山群岛、川山群岛、大亚湾—惠东稔平半岛和香港大屿山岛等,主要建设抵御海洋灾害的近海生态防护带、近海生物高质量栖息带,形成大湾区海陆能流、物流交换的纽带。“两廊”即珠江水系蓝网生态廊道和道路绿网生态廊道,主要以东江、西江干流为中心,串联沿江的丘陵、农田、防护绿带和道路绿网等。以绿道与碧道(大湾区都市型碧道)③等形式构建珠江口东西两岸重要的生态廊道,形成生态隔离带,起到有效加强生态隔离带与大湾区各区域绿核之间、各自然“斑块”之间生态联系的作用。“五核”即五大区域性生态绿核④,指由分布于大湾区内部或城市之间的山体和绿色生态开敞空间构成,是大湾区城市群的生态过渡区域。
2、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大湾区生态红线管制
根据《规划纲要》的要求,大湾区要“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加强珠三角周边山地、丘陵及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建设北部连绵山体森林生态屏障”[2]。生态红线是指在尊重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保护生态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划定的基本生态控制线[25]。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支撑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实施最为严格的管控措施,不断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26]。要加强对大湾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的保护力度,实行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切实维护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同时,要划定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将区域内重要河口、重要滨海湿地、重要砂质岸线、重点旅游区、自然景观和红树林等区域划定为海洋生态红线区,分区分类指导红线管控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丰富的海岸线生态资源,需要加强开发与管理。基于此,《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强海岸线保护与管控,强化岸线资源保护和自然属性维护,建立健全海岸线动态监测机制。强化近岸海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推进重要海洋自然保护区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与管理。”[2]
粤港澳三地要加强协作,划定海洋生态红线区,要将大湾区内的林地、城市绿地、农用地、水域和湿地等纳入生态用地管理范畴,明确用地规模、强化用途管理,设定生态建设指标;明确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
3.深化环珠江口的合作治理,筑牢大湾区海岸带生态屏障
环珠江口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的主要区域之一,粤港澳三地要联合制定环珠江口湾区环境整治方案、环珠江口水源地与珠江河口岸线保护规划。以申报建设珠江口国家海洋公园为契机,建设河口自然保护区,实施珠江河口滩涂湿地生态系统恢复工作。环珠江口湾区是大湾区滩涂湿地的主要分布区,为此,《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湿地保护修复,全面保护区域内国际和国家重要湿地,开展滨海湿地跨境联合保护”[2]。具体而言,要严格保护好大湾区海岸带红树林,构建功能完备的大湾区湿地公园体系,主要包括珠海的横琴国家湿地公园和淇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深圳的福田红树林公园和华侨城湿地公园,广州的南沙国家湿地公园和海珠国家湿地公园,香港湿地公园和米埔自然保护区,澳门的“湿地保护区”(如芒洲和二井湾红树林湿地公园)等,通过上述湿地公园建设,串联大湾区绿色海岸带并打通深港、珠澳跨界绿道,实现大湾区生态休闲廊道的互连互通,筑牢大湾区海岸带生态屏障。
深化粤港澳三地环珠江口的合作治理,还必须加强对珠江河口区域水资源、水环境及涉水项目的管理合作,重点整治珠江东、西两岸污染,规范入河(海)排污口设置。实施东江、西江及珠三角河网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保障大湾区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要加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和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实现从西江向大湾区东部地区引水,解决大湾区东部(尤其是广州、深圳、东莞)生活生产缺水问题,并为香港提供应急备用水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面崛起和长期发展提供水资源的万全保障[27]。同时,还必须按照《广东万里碧道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要求,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珠江流域的系统性来整体地谋篇布局大湾区的碧道建设,将东江干流、西江干流、北江干流和珠三角网河区骨干水道作为碧道建设的重点区域,抓好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深圳两市的“千里碧道”建设,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注 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风险的预警和防控,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②“两屏三带”:指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土地带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以其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撑,以点状分布的国家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③ 都市型碧道: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建设湾区岭南宜居魅力水网。空间范围主要为珠三角9 市。湾区碧道将重点解决区域河流水网水体黑臭、水生态损害、水域空间侵占等突出问题,注重推进治水、治城、治产相结合,打造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建设魅力湾区、彰显岭南水乡特色,构建绿色生态水网和都市亲水空间。
④“五核”:包括广州帽峰山—白云区区域绿核、佛山—云浮之间的皂幕山—基塘湿地区域绿核、江门古兜山—中山五桂山—珠海凤凰山区域绿核、东莞—深圳之间的大岭山—羊台山—塘朗山区域绿核和深—惠之间的清林径—白云嶂区域绿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