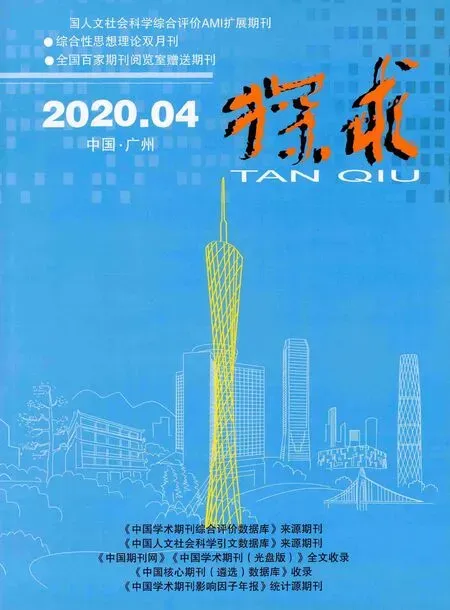以人观诗与以诗观人
——《观人学与中国传统诗学批评体系的建构》评介
□ 李舜臣
“文学是人学”,虽说是西方文论的产物,亦可通于中国的传统文论。古人已有“诗如其人”(陈师道《答秦觏书》)、“人即是诗,诗即是人”(杜浚《与范仲闇》)、“人外无诗,诗外无人”(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等言说,举凡中国诗学的本体论(“言志”与“抒情”)、重要范畴(神韵、形神、风骨)、批评方法(知人论世、品第批评),莫不是从“人”出发并围绕“人”而展开的。因此钱锺书先生指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人化或生命化”,蒲震元明确称为“人化批评”,吴承学称为“生命之喻”。
不过,所谓“人化批评”“生命之喻”,仍侧重于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表现策略,似不足以揭示问题的全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万伟成教授踵继前贤,别开蹊径,引入和运用中国传统“观人学”的原理和方法,提出“观人诗学”这一新说,从新的维度还原和建构中国特色的诗学批评体系。早在2005 年,万伟成教授便用纯正的文言撰有《观人诗学》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论者以为“是一部独特的文言诗学奇著”(李克和、陈恩维《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重构——评万伟成〈观人诗学〉》,《中国韵文学刊》2007 年第3期)。但他仍不断求索,力拓新境,新近又推出了《观人学与中国传统诗学批评体系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以下简称《建构》)。两部著作前后相距十四年,既有沿革承续,更有创新发展。如果说旧著保留了传统诗学评点式的特色,那么新著则思虑缜密,转精入微,从“范畴、术语”“批评内容”“思维方式”“批评方法”“批评形态”等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揭示出观人学对中国诗学批评的影响,逐步树立起“观人诗学”体系。
坦率地说,最初接触万伟成提出的“观人诗学”,内心颇有疑虑。因为这种冠之“××诗学”“××美学”等理论话语,大量充斥于时下的学界,似乎任何一种主题、方法、视角、现象都可拔升至“诗学”“美学”的高度,细究之下,却有名无实、耸人耳目者实在不少,令人产生“审美疲劳”。然而,捧读万伟成的《建构》,像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角镜”,既可聚焦于传统诗学的内核,也可广泛地观测到广阔而斑斓的图景,原有的疑虑顿时冰释。“观人学”,是通过观人形神而预知健康、祸福、休咎,在数千年的演变中产生了大量的图籍,逐渐成为中国固有的一门学问。1931年,邵祖平先生即撰有《观人学》一书,从学科史上确立了它的存在。遗憾的是,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观人学被认为迷信而遭到遗弃。但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然渗透于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朝廷的选才委官、中医的观神望气、民间的求神问卜等等,无不与之相关。万教授以严谨求实的心态,从大文化背景中考察观人学的源流,疏浚其向诗学批评渗透的历史脉络。他以为,观人学对诗学批评的影响,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发展,亦是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直觉领悟式”“浑融模糊”等思维方式之必然。他提出的“观人诗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契合中国诗学发展的本来面目,决非捕影跟风之举。
中国诗学究竟是否存在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石、形态如何?一般认为,中国诗学不同于西方诗学,不存在“有迹可循”的逻辑结构。这显然是以西方观念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论。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诗学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本体论、范畴论、风格论、方法论以及文本形态。古人或许从未明确其义界、内涵,但人们在使用这些范畴、观念、方法时,大多仍能遵循其基本义例,不会偏离得太远。这可以说是一种约定成俗的观念,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在“散金碎玉”的表象之下,中国诗学仍潜存着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体系。重构这一“潜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宏观地认识中国诗学的特色,而且也有利于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因此,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试图从那些“散金碎玉”式的话语、材料寻绎出中国诗学内在的逻辑理路。但往往具有相当的主观色彩,学者所持有的理论视角是成败的关键。依据不同的理论视角建构出来的体系,势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或走向“片面的深刻”。
万伟成从观人学的视角重审中国诗学批评,建构其体系,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自上古以来,古人即已形成了天、地、人“三才”的基本观念,以及“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思维方式。依照万伟成的认识,“观人学”影响下的诗学批评至少包涵两个层面:“以人喻诗”和“以诗观人”。这其中,既涉及传统诗学的思维方式、结构特征,又关联了批评本体、批评术语、批评内容、批评标准、批评方法、批评文体等层面。大量的材料表明,古人运用观人学进行诗学批评,绝非偶然兴到之举,在他们看似随意的评论背后实际隐藏着某种理论的自觉。万伟成的独到之处在于,以宏阔的理论视野,从多重关系的动态立体研究,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着力彰显中国诗学的特色。全书除“绪论”外,共有八章。第一章“观人学与诗学范畴或术语”,拈出“形神”“气韵”“英雄”“风骨”“贫富”等范畴,揭示出观人学术语在诗学中的投射;第二、三、四章分论“观人诗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包括道德、审美、才性、风格、人格、诗谶诸方面;第五章围绕意象批评、认知隐喻,探讨观人学对诗学批评思维方式的影响;第六章从“观”“相”“品”三方面,阐述观人学的方法论向诗学批评的渗透;第七章简论中西文论中“人喻诗学”之异同及现代转换等问题。全书构架逻辑严密,内容丰富,不枝不蔓,所论问题无不都是烛照于“观人学”这一视域之中。
重新建构古代某种文化体系,易流于“以今范古”之弊,即不顾历史的情境,套用今人观念衡评古人,从而偏离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万伟成所建构的观人诗学批评体系,努力祛除此种流弊,自觉遵循历史的规律,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例如,对“形神”“气韵”“风骨”等范畴的探讨,都先是找出其最早出处,从语义学寻绎其本义,概述其在观人学中的用法、涵义;然后以辩证的眼光揭示出这些从观人学“移植”到诗学中的范畴、方法、命题衍生出的新涵义、新术语。“观人学”与“诗学”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门类,诗学批评对“观人学”原理、方法、术语的借鉴,亦非简单的移植、照搬。万伟成也充分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很多地方都特别凸显这种差别,例如探讨“神气”这一范畴时,他指出,在相学、中医“神气”的要义是贵“神藏”,多少有些玄虚色彩;而诗学批评移用“神气”这一范畴,则往往落到诗之音节、字句、篇章等实处。
自“诗言志”开山浚源以来历代诗论家推阐词场,扬榷是非,创作了大量的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犹如一座座“矿山”,有的被挖掘、利用、再生,而有的仍隐而不彰,沉而不显。不同的研究视角,则如同一盏盏“探照灯”,往往能发现一些被人忽视的宝藏。万伟成从“观人学”的视角探究诗学批评,挖掘出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批评范畴和批评现象。例如,“贫寒气”“寒乞气”“富贵气”等术语,除相关文章略有所及外,很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探讨,但实际这类范畴大量出现在唐以后诗论中。万伟成敏锐地注意到它们的价值,指出观人学中的“贫”“富”概念原是指人物质之贫富与精神之穷达;用之于诗学,则诗论家通过诗歌批评“观诚”“考志”“观色”“揆德”,体现出儒家道德观念和“诗教”精神。这类范畴亦非孤立的存在,而与“诗穷而后工”“体格风神”等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对范畴的诗学意义就得到了凸显。又如,观人学中还有“英分”“雄分”这对术语,乃指观人时“察”气而生,气有阴、阳之分,人则有“英才”和“雄才”之分。魏晋南北朝人们开始将它们运用于诗学批评,并衍生出“英华”“英俊”“英骨”“自然英旨”和“沉雄”“雄浑”“雄健”等近百种概念。这些概念也很少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但在古代却被广泛地运用于才性批评以及风格批评中。观人学对传统诗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批评方法、内容、术语等方面,还影响到了诗歌批评的形态,这其中除了学界研究较为丰富的“名号”“并称”“点将体”“流别体”之外,万伟成还挖掘出“事数”“祖宗录”“谱牒批评体”“主客体”等批评文体,也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万伟成择取这些范畴、现象进行研究,决非钻牛角尖,或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力图挖掘出更多的理论资源。
毋庸置疑,古代“观人学”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邵祖平先生的《观人学》因追求科学性和严谨性,概不采入谶纬之说。“谶纬”虽不可尽信,但其神秘性往往最能引人兴趣,况且诗歌本身亦具有“感鬼神”“幽赞神明”之功能,因此,用谶纬学评诗衡人,大量地出现在“以资闲谈”的诗话之中,宋人阮阅《诗话总龟》卷三三、三四即有“诗谶门”,可见其影响之大。然而,这类批评很少为研究者所关注,印象中似乎只有吴承学先生《谣谶与诗谶》等文略有所及。万伟成不仅全面地探讨了“诗谶批评”产生的文化渊源,还深入地分析了它所具有的观人学、文学、诗论之属性。古人运用“诗谶批评”,不单通过评论诗歌来预示诗人的穷通、寿夭、祸福等命运,还经常对“诗言志”说、“真情”说、“知人论世”说、“诗歌的起承转合”说等命题进行神秘阐释。因此,“诗谶批评”虽具有宿命论的色彩,但这种神秘的诗学体验是中国诗学批评的特色之一,决不可轻易忽视。
万伟成在挖掘这些不被人注意的批评现象时,并不仅满足于“以古释古”,而是尽可能用当代的眼光对它们进行新的阐释和评价。他辩证地分析了“诗谶批评”对诗学体系建构正、负作用,指出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性内核,抛弃其神秘的外衣和不合时宜的禁忌与理论。同时,以观人学的视角审视传统诗学,一些传统的诗学命题便可获得新的阐释。譬如“诗言志”说,以前都以为最早出自《尚书·尧典》,但是因为《尚书》的编定时间难以考实,万教授审慎地以为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并将“诗言志”与“文王六征”的“考志”术联系起来,因此,“诗言志”顺理成章地承载“诗人关于人伦政教的志趣和怀抱”。从观人角度解释“诗言志”一开始即打上了浓厚的儒家诗教的色彩,也许更显合理。再如,学术界常论的“人化批评”“生命之喻”,往往多限于考察人体结构与艺术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万伟成则引入了“隐喻”理论和“认知语言学”,认为“以人喻诗”只是观人学影响诗学批评的初级形态,而实际上,古代诗论家“观人经验理论,用来阐释诗学原理、进行诗歌批评与诗学体系的建构的认知活动”“其批评方式也已经超越了譬喻的,演进为艺术直观生命的体悟”,从而进入到“人、诗合一”的高级形态。显然,这一结论较为以往的研究更为深刻。
总之,《建构》一书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辩证的眼光,挖掘出大量新的理论资源,为学界重审传统诗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堪称近年来古典诗学研究的力著之一。当然,该书亦非尽善尽美,仍存在一些可待完善的空间。例如,观人学对诗学的影响和渗透是全方位的,尚有一些较为重要的命题、现象尚未进入到作者的视野。像“习气”这一术语,大量地出现在唐宋以后的诗文评中,意涵非常丰富,既可指向作者、作品,有时也指向时代风格、地域、流派风格。又如,“观人诗学”,除观诗人的志向、道德、才性、风神、人格、命运之外,还可观人的身份。身份批评显然也是观人诗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应当予以充分地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