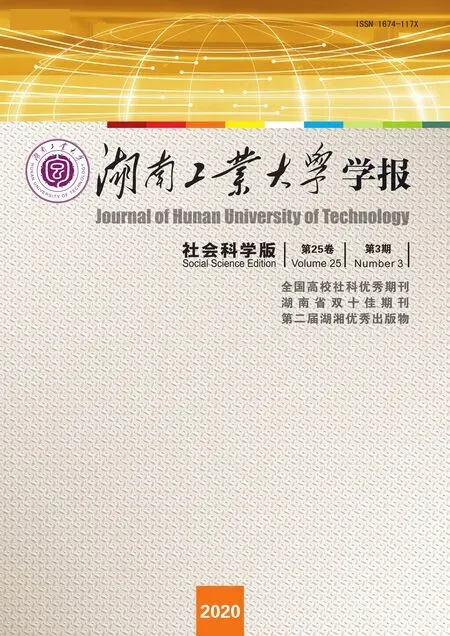论当代电影“文学性”之必要
——以周星驰“西游”电影为例
王柯入,韦 强
(1.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2.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电影与“文学性”的关系,曾是学界与电影界论争的热点。有人认为“文学性”是电影的主导,也有人认为“文学性”对于电影并不重要。在当代,电影越来越重视科技的运用,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电影的“文学性”不再重要。然而,通过对周星驰“西游”系列电影的分析可以发现,“文学性”之于当代电影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一 关于电影与“文学性”关系的论争
早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电影界就针对电影的“文学性”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讨论者认为,“文学性”之于电影,拥有主导的地位。著名导演张骏祥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指出:“戏剧和电影,是艺术……又是文学:戏剧文学和电影文学。”[1]3他认为电影应该“更多地重视影片的文学价值”[1]4。当时,持有类似观点者不在少数,张成珊《电影的文学性与特性》也指出:“电影是文学艺术的一种样式,它也应该遵循文学艺术总的规律,也就是说它应当具有文学价值。”[1]43他们都认为,“文学性”才是电影安身立命的根本。这种电影“文学至上”的观点虽然传统,但是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1 世纪。姜珉《论我国电影作品的文学性》说:“文学是电影的母体,足够的文学精神和品格是评价一部电影的重要标准。”[2]马兰萍则表达了对电影技术压制文学性的担忧:“在经济利益的追逐下,很多电影的文学性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技术……过多的重视技术必然导致电影作品在思想上的缺乏,对观众的审美观造成误导。”[3]夏曼丽《解构与重塑:电影艺术文学性研究》是近些年提倡电影“文学性”的代表:“电影艺术中文学性的存在是电影成为艺术的基点。”“当电影艺术文学性的消解成为趋势,电影艺术也将丧失其艺术的本质。”[4]可见进入21 世纪之后,“文学性”之于电影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仍然具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与“文学至上”观点针锋相对的是,一部分电影研究者和电影行业人士主张要突出电影的独立地位,使电影摆脱文学的主导。王忠全《“电影作为文学”异议》认为:“把电影归结为文学,置两种不同艺术的质的规定性于不顾——不能不说是对艺术历史本身的一个谬误。”[1]163陈墨《雾失楼台:电影的文学性与人文维度》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没有任何理由将电影当成文学或其他艺术的附庸。”[5]朱玛《论电影与电影文学的几个问题》虽然认为电影不能完全忽视文学性,但还是指出,“电影主要运用画面和声响,那怎么能说‘电影就是文学’呢?” 朱玛援引郑雪来的观点,认为文学性和戏剧性、绘画性、音乐性一样,都只是构成电影的一部分,文学性在电影中“比重有限,而且一经进入电影,这种‘文学性’也是经电影的肠胃消化过的,又发生了相当的,甚至是质的变化”[6]。这一派的观点,虽然并非完全否定电影的“文学性”,但很明显,其试图弱化“文学性”之于电影的意义,主张尽量剥离“文学性”与电影的关系。
“文学性”与电影关系之争,持续20 余年,始终未有明朗的结果,这主要是因为论争双方对争论的焦点——“文学性”的内涵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把电影“文学性”理解为电影文学,有的人理解为电影剧本,有的人理解为电影语言,这就导致争论者貌似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然而实际上只是自说自话。如此一来,自然难有统一结论。所以,首先还是应当明确电影“文学性”的内涵。笔者以为,电影固然不能与文学相等,但如果讨论电影的“文学性”,那么就可以把电影视为一部“小说”。一部优秀小说的核心要素无疑是精彩美妙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情节,那么以此来审视电影的“文学性”,语言、情节就是其核心要素;所以电影“文学性”的内涵,其实就体现在其电影语言上拥有文学感和艺术感、情节上拥有故事性和逻辑性上面。一部电影如果能够在语言、情节两个方面具备优秀的水平,那就意味着这部电影具有良好的“文学性”,而这对电影本身的质量也是一种提升和保证。所以,笔者认为,无论电影的科技、视效发展到什么程度,“文学性”依然是构成电影的核心要素。近些年,影坛大兴“西游”热,“西游”题材的电影层出不穷,而其中最为成功的当属周星驰的“西游”电影。周星驰的“西游”电影,较之其他“西游”电影,最大的优长之处就在于“文学性”。以周氏“西游”的文学性聚焦,恰恰可以证明,即便在科技、视效大行其道的当代,“文学性”之于电影仍有不容忽视之意义。
二 周星驰“西游”电影的语言艺术
从1994 年的《大话西游》,到2017 年的《西游·伏妖篇》,从主演到导演,再到监制,周星驰对于“西游”题材的热情持续了20 余年。而近些年,又恰逢“西游热”,“西游”题材的电影层出不穷。除了周氏的“西游”电影外,2014 年至今,有郑保瑞执导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和田晓鹏执导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3》等一系列“西游”电影上映。在这股“西游”电影热潮中,周星驰主导的两部“西游”电影《降魔篇》《伏妖篇》都能脱颖而出,获得佳绩。《降魔篇》2013年以12.4 亿元的票房当选年度票房冠军,《伏妖篇》票房更是高达16.6 亿元。与此同时,其他“西游”题材电影则黯然失色,《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票房为10.4 亿元,《大话西游3》更是只有惨淡3.6亿元,即便是2015 年以黑马姿态一鸣惊人的《大圣归来》,也仅收获9.5 亿元的票房。
周星驰 “西游”电影能够成功,往往被归结于周星驰本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然而事实上,其他“西游”电影虽然成绩不佳,但风格也是各有优长。《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大牌云集,而且拥有酷炫的特效和武打设计;《大话西游3》拥有“大话西游”的金字招牌;《大圣归来》的动画效果有口皆碑。所以说,仅凭“周星驰”这三个字,其电影就能从众多“西游”题材电影中胜出,是不可能的。周星驰的“西游”电影能够获得佳绩,主要还是因为其影片质量极高,其画面的视觉、情节的喜剧感之呈现都属上乘。最为重要的是,如果将周氏“西游”电影对比其他同题材作品,就不难发现,周氏作品有一个显著特色为其他作品所不具备,那就是其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周星驰的电影一向给人以夸张搞怪的“闹剧”印象,绝少有人将周氏电影与“文学性”联系起来。然而实际情况是,周氏电影虽并不以“文学性”为主要特色,但“文学性”却从来都是周氏电影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最简单的例子,周星驰的电影诞生了大量经典台词,而在其古装电影之中,台词语言的运用尤其出彩。周氏古装剧中的经典台词,形式上具有对仗、排比、押韵等古文文风,其内容则充满解构、滑稽、反讽的意味,因此其台词兼具古典文采与现代内涵。所以,周星驰电影中的“文学性”,其实一直是被低估的。而“西游”电影作为其古装电影的一个分支,“文学性”一向充满亮点,《大话西游》中“爱你一万年”的经典台词至今流传不衰,周星驰亲自监导的两部“西游”电影,“文学性”也是促成其优于其他“西游”电影的重要因素。本文所论析的“文学性”,主要分为语言和情节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构成了“文学性”的基本内涵。而周氏“西游”在“文学性”上的优长,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没有精彩的语言就不会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此类推,电影“文学性”的命脉也在语言。周氏“西游”电影在“文学性”上优于其他“西游”电影,首先就体现在语言方面。“大话西游”之所以被奉为经典,高超的语言艺术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层出不穷,除了“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这两句公认的传世经典,包括“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原来那个女孩子在我心里留下了一滴眼泪,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当时她是多么的伤心”等台词也是共鸣性极强,甚至成为流行语。“大话西游”不仅颠覆了“西游”故事原有的呈现方式,其对于传统华语电影语言体系也是一次革新。它构建了一套自成一派的语言体系,正是这种独树一帜的语言体系,使得《大话西游》体现出极强的“文学性”。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在现代文学的语境之下,并非语言具有一定程度的文言色彩,就等于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西游”作为脱胎于古典名著的电影,能够使用一定的文言台词,自然会提升作品的文学品格,同时也让电影语言与题材更为契合。这一点,《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做得最好,其中不少独白和台词都具有文言色彩,显得颇为典雅。但是,这种语言表达,只能算是一种“规矩”,却无法构成亮点。因为这种文言的表达,是一种程序性、陈规性的设计,是对传统语言模式进行的套用,它本身虽然比那些随意化、口语化甚至口水化的台词显示出更高的文学水准和文化修养,但它更像是一篇规规矩矩的“公文”,文笔上非常标准,甚至无懈可击,但是如果以文学视角观照,却缺乏个性、灵性与特性。因此,仅仅使用文言句式对语言进行铺陈,并不能体现太高的“文学性”。通过《大话西游》,我们不难发现,具有高“文学性”的语言体系,往往具有四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哲理性。例如至尊宝与刘镇伟饰演的强盗“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的对话,两个人连续问多个“需要吗?”强调了这个看似普通却蕴含一定哲理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因此这句发人思考、具有哲理意味的台词,更容易为观众记住并传播。第二,语言具有幽默感。幽默感是最能体现语言智慧性、精彩度的要素,也是最能够调动观众情绪的语言要素。《大话西游》作为一部喜剧,自然不乏幽默感极强的台词。例如唐僧劝化妖怪的台词:“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只要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这句台词的幽默感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化用了国骂“他妈的”,一是利用了“人妖”这个词的特殊含义。这种台词的格调并不算高,但以幽默感衡量,却是一句成功的台词。第三,台词蕴含着打动人心、激起共鸣的情感。《大话西游》之所以最初在大学生群体之中流行,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对爱情的表现与思考,正契合处于恋爱年纪的大学生们的情感心理。而其中最容易激荡内心的,就是那些极富情感性的台词,至尊宝“爱你一万年”就是其中代表。除此之外,包括“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你的良心告诉我你最爱的人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女人。……你我都要相信这都是天意,也就是传说中的缘分。”等台词都是能够以其情感内涵打动观众的台词。这些台词打动人心的情感效果,源于极为讲究的语言组织。“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本身富有韵律与意境,而“我睡不着”“你也睡不着”“天意”“缘分”都具有对称修辞的成分,它们都是通过语言修辞来烘托出爱情的场景想象与情感传达。这些台词即便脱离影像画面,单纯作为小说语言,也一样具有同等的情感效力,具有极高的审美含量。第四个,语言的异文化。所谓异文化,是指语言在新的语境中,因为陌生化、新奇化以及语言内涵本身的异变,从而产生的新的语言效果。《大话西游》中,唐僧的台词多使用异文化的语言,从而产生了极强的喜剧效果。例如唐僧在劝告孙悟空不要乱扔月光宝盒时说:“月光宝盒是宝物,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要是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污染环境”“小朋友”都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汉语的词汇,将其套用到唐僧口中,就产生了异文化的喜剧效果。这些现代汉语异文化到古代人物和神话人物身上,喜剧效果十分强烈。异文化语言也不只是创造喜剧效果,它还能制造惹人深思的效果。原本平常的语言,如果设置在特定的语境中,有可能产生远远超过语言内涵本身的想象张力和思考空间。例如《大话西游》结局,至尊宝和紫霞看着远去的孙悟空,说:“你看,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哎。”这句话独立来看,只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比喻句,但是当其出现在《大话西游》的结局时刻,结合整部电影的剧情发展,就使得观众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联想。有的人认为这句话来源于周星驰自己的真实经历,有的人认为它表现了男人一生的无奈,有的人认为这是电影对于人之爱情的总结,如此等等。总之,语言的异文化可以让原本平常的语言产生诙谐幽默、引人深思的效果,是语言“文学性”的重要特点之一。《大话西游》通过具有异文化、幽默感、情感性、哲理性特点的台词,使其语言体系体现了极强的“文学性”。到了自己导演《降魔篇》《伏妖篇》时,周星驰依然延续了其对“文学性”的追求,特别注意台词的雕琢和锻造,因此,虽然这两部电影的“文学性”逊色于《大话西游》,但是较之近年来其他“西游”电影,其文学性还是明显要高出一筹。
作为一部定位为喜剧的电影,周星驰在《降魔篇》中,有意识地使用文字游戏制造喜剧效果,如孙悟空假装忏悔时说“大日如来真经真是好,真是妙,真是呱呱叫”,空虚公子出场时的自我介绍“我是空虚公子,不是肾虚”。这些语言都算不上特别高明的文字游戏,但却可以看出周星驰在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文学性。而《大话西游》中哲理性、情感性、异文性的“文学性”语言在《降魔篇》中也都有体现。例如其中最为经典的台词“有过痛苦,才知道众生真正的痛苦;有过执着,才能放下执着;有过牵挂,了无牵挂”,不仅文采斐然,而且极富哲理。异文化的语言,在《降魔篇》也有出现,如唐僧告知村民道长杀错了妖怪时所说的:“它只是一条古氏鱼,生性驯良,性格积极乐观,人品相当的不错。”“性格乐观”“人品不错”都是现代词汇被异文到了神话语境中的结果。
在《伏妖篇》中,周星驰延续了对文学性的追求。猪八戒大战蜘蛛精时的台词“(蜘蛛精)我是蜘蛛;我也是只猪!”以及“你越反抗,我越强壮”都是利用谐音和文字游戏营造的喜剧桥段,其格调依然不高,但也体现了周星驰追求文学性的用心。而《伏妖篇》在文学性和语言性的整体水准上,比《降魔篇》更为出色,经典台词也更多。其最为经典的台词,是小倩临终前所言:“世上最难过的关,是情关。”此句台词无论是表达的情感还是语言本身的美感,都是极富文学性的。此片中,周氏常用的语言异文,仍然出现过多次。例如唐僧敲打孙悟空时自夸自己的本领:“为师一个打一百个几十个,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我低调我不说。”“低调”是近些年流行起来的现代词汇,它在当今网络传媒的异文下已经从一个褒义词变成反讽意味的词,而《伏妖篇》又将其融入了“西游”故事中,使其通过异文产生出一定喜剧效果。又如唐僧与孙悟空发生争吵,沙僧说:“走的最长的路,就是师父的套路。这招以退为进,在适当的时候下跪认错,可以收买人心,师父看着傻,其实他是危机管理学的高手。”“套路”“危机管理学”都是典型的现代词汇,被周星驰驾轻就熟地运用到了“西游”电影中,从而成为全片最具笑点的台词之一。
所以从语言水平来说,周氏“西游”电影比其他“西游”题材电影高出一筹。《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虽然尝试台词古雅化,但最终给人平淡如水之感,缺乏亮点;《大话西游3》尝试延续前两部的后现代语言风格,但弄巧成拙,没有任何给人印象深刻的语言或台词;《三打白骨精》由小沈阳出演猪八戒,本意即为发挥东北演员语言包袱能力强的特点,从而加强片子的喜剧感和语言性,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其并未呈现出任何语言亮点;至于其他“西游”题材,语言艺术皆乏善可陈。
三 周星驰“西游”电影的情节构建
关于“文学性”,除了语言要素之外,另外一个关联因素是情节。叙事体裁的文学作品,一定需要有一个情节完整、逻辑清晰的故事。一部作品如果情节支离破碎、逻辑不清甚至有违常理,那么自然难以称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电影也是如此,如果把电影理解为一部影像“叙事文学”,那么其“文学性”的高低也取决于情节构建的水平如何。周氏“西游”电影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虽然从内容来说,它们是对《西游记》的重构、颠覆、戏说,完全背离原著的故事情节,但是它们却能借助原著的人物,构建出一套情节完整、逻辑清楚的新故事体系。《大话西游》的两部作品,看似荒诞不经,其实逻辑清楚、主题鲜明。影片的结构以孙悟空顿悟人间情欲、决心立地成佛的脉络为主线。上部《月光宝盒》以至尊宝对白晶晶产生爱情为主要情节,但实际上却是为下部《仙履奇缘》做衬托,为至尊宝陷入对紫霞仙子的爱恋埋下伏笔。下部《仙履奇缘》则讲述了至尊宝通过与紫霞仙子、白晶晶的爱情纠葛,最终看破红尘,从而悟道变回悟空的故事。该片看似无厘头,但其实头绪非常清楚。周星驰导演的《降魔篇》《伏妖篇》,同样非常在意情节的考究。《降魔篇》的主题与《大话西游》近似,只不过是看破红尘、一心向佛的主角从孙悟空变成了唐僧。故事推进以玄奘、段姑娘先后收降鱼妖、猪妖和孙悟空为故事主线,以玄奘和段姑娘的爱恨纠缠为情感脉络,在叙述唐僧收降三个徒弟经过的同时,把玄奘克服私欲、心求大爱的心路历程表现得非常清楚。而在设定猪妖和鱼妖两个形象时,《降魔篇》也非常注意逻辑:鱼妖在河边救小孩,却被村民误认为人贩打死,于是,他心生怨念,化为鱼妖;猪妖本来对妻子十分痴情,妻子却因其貌丑而和美男通奸并将其害死,猪妖这才积怨成妖。可见,鱼妖和猪妖都本性善良,只是因为受到了冤屈和不公,最终才积怨成魔,这就为他们后来能够洗心革面、皈依佛祖埋下了合理的逻辑伏笔,所以其情节推进很有逻辑和层次。《伏妖篇》在情节设计上,比《降魔篇》更具隐晦性,一路伏笔,层层推进,最终呈现出一个出乎观众意料的结局。它的情节主线,是唐僧师徒四人先后制伏了蜘蛛精、红孩儿、九头金雕等妖怪,但是它并不是简单地让妖怪先后登场,而是始终以玄奘与孙悟空的矛盾为轴线,最终引出一直隐藏为国师形象的妖怪九头金雕。所以从情节上看,《伏妖篇》比《降魔篇》更为高明。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从“文学性”角度讲,如果情节设计在故事完整的基础上,又能够暗含伏笔、隐没线索,给读者、观众以想象、推断、索隐的空间,那么它的文学性会更上一个层次。《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不朽的文学名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情节设计“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它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平铺直叙的传统,设下层层伏笔,让读者、学者玩味不尽、索隐不休,因此其文学性高出其他古典小说一筹。《伏妖篇》在情节伏笔的设计上,就体现了较高水平,并因此成为支撑其“文学性”的基础。《伏妖篇》最大的伏笔是,表面上,孙悟空和唐僧一路上矛盾重重,然而到了片尾,观众才知道,他们一路上其实都是假装矛盾,其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引出九头金雕这个幕后妖怪。所以,《伏妖篇》的伏笔设定,提升了影片情节水准。如果把“情节伏笔”作为“文学性”的参数,那么《伏妖篇》无疑值得加分。
周氏“西游”电影虽然从情节来说,完全脱离原著的故事设定,但是它借助原著的主要人物和其核心情节,自成一套情节完整、逻辑清楚的故事体系,这就让它如同一部拥有完善体系的小说一样,具有了较高的“文学性”。而难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恰恰成为当代国产电影,尤其是名著改编电影的一个通病。近些年改编自古代名著的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编创者想摆脱原著束缚,自成一套故事;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改编作品总体上并没有脱离原著框架,然而故事逻辑上却又与原著背离。这样,由于新的故事体系未能完整建立起来,情节安排自然给观众不伦不类之感。让观众观看完之后,既没有感受到编创者对原著的尊重,也没有感受到编创者自己的创造魅力,对于其情节发展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改编者最终也只能靠眼花缭乱的科技手段为苍白的情节遮羞。《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两部电影,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这两部电影都未能完全脱离原著的情节,然而又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但这种改编却导致其故事既丧失了原著的逻辑性,同时又未能呈现出一个新的令人满意的情节内容。《大闹天宫》保留了原著中悟空学艺、偷丹、官封弼马温等情节,但其故事的总体构建,却变为牛魔王造反天庭而利用孙悟空,孙悟空后来发现了牛魔王屠戮花果山的阴谋,最终大败牛魔王的情节构架。所以,整个故事其实并不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而是牛魔王大闹天宫,这就使得影片的逻辑基础发生了异变。《三打白骨精》的主体情节,延续了原著白骨精幻化成老妪等人物被悟空打死,从而导致悟空被唐僧驱赶的框架,但是改编者又加入了云海西国国王这个角色。正是这个角色的加入,成为拖累情节逻辑的绊脚石。比如在片中,当悟空发现海西国王残害儿童时,他只是警告国王,并未将国王杀死,唐僧也并未责怪悟空。然而之后的段落,悟空在集市识破白骨精变化的妇女和小孩,将他们打死,唐僧却非常愤怒,要赶走悟空。在原著中,唐僧赶走悟空的逻辑,是悟空前后三次杀死一家三口人,唐僧劝告三次无果,才决定赶走悟空。然而此片中,唐僧第二次见其杀人就要赶走他,本身逻辑就没有太强的说服力;片中插入悟空放生国王的情节,更加使得唐僧的暴怒不符合逻辑。
所以,评价一部改编自名著的电影,其核心要素并不在于电影本身是否完全尊重原著,而是在于电影本身是否具有令人信服、满意的故事体系。有的改编电影表面上对原著亦步亦趋,然而在将文字转化为影像时,却又情节和逻辑颠倒错乱,最终成为失败的改编。相反,有的电影虽然情节上完全与原著脱离,但由于其自身能形成完整体系,构建了独立于原著的“新故事”,那么这样的电影堪称成功的改编。电影从业者喜欢改编名著,主要看重的是名著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电影作为影像艺术,语言比重远不能和小说相比,因此电影对名著“文学性”的“复刻”,很大程度就体现在故事情节的营构上面。包括《大闹天宫》等在内的名著改编电影,说它们文学性不高,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语言缺乏文学性,更在于它们未能构建一个故事层面令人满意的情节体系,从而无法完成独立的故事构建。衡量电影的“文学性”,并不仅仅是看电影是否成功改编了小说,也可考察电影的情节是否可以改编为成熟的小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西游”电影失去了特效即失去了电影的生命,更遑论改编成为小说;相反,周星驰的“西游”电影则一定程度上具有改编成小说的可能性,其与其他“西游”电影文学性水平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20 世纪80 年代,电影“文学性”的讨论风行一时,然而新世纪以来,这样的讨论却越来越少。虽然也有零星的论文在讨论电影“文学性”,但和学界关于电影的论文总量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这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越来越弱,以至于开始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话题。21 世纪之后,电影的“文学性”也的确越来越被轻视。一方面,快餐文化、视像文化风靡之后,能够静心阅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从而导致文学失去了以往正统的文化地位,变成一种消费主义的商品附庸[7]。由于其本身生存状态岌岌可危,电影界对其的轻视也就非常正常了。另一方面,3D技术的横空出世,导致电影愈发朝着重视视觉效果方向发展,影片的画面美感、视觉特效成为票房高低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都导致文学性愈发被边缘化。但同时也可以看到,虽然近些年国产电影在技术、视效等方面进步巨大,尤其是很多大片斥重金请外国团队制造特效,使得影片视觉效果具备了和世界大片比肩的水平,然而国产电影的口碑却每况愈下,不仅知识界不满意,连普通观众都不满意。可见,视觉特效并不是决定影片质量的唯一标准,其正如朱国华《电影:文学的终结者?》所言:“无论是冈斯的《车轮》、布努埃尔的《一条安达鲁狗》,还是拉杜克本人摄制的《贝壳和僧侣》所演奏的‘视觉交响乐’是多么新奇,它们并未成为未来电影的大趋势。”[8]可见世界范围内,仅仅具有出色的特效还无法成为优质电影。如今,人们对国产大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故事讲述差、台词水平差等方面,其实一言蔽之就是“文学性”差。可见,文学性对于电影,仍然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星驰的“西游”系列电影,于技术和视效而言,并未优于《大闹天宫》等影片,它比其他“西游”电影高明的地方,就是其“文学性”高出一筹,这也是其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都优于其他“西游”电影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周星驰电影的好票房不是仅仅因为“周星驰”这块情怀招牌,更重要的原因是其电影的“文学性”独树一帜。事实证明,即便在3D 技术普及和视觉至上的当代,电影的文学性仍是电影非常重要的加分项,值得每一个电影工作者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