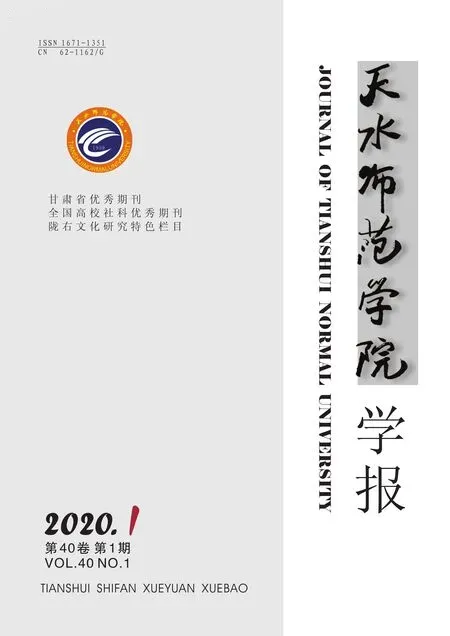从弥勒下生信仰看佛教的社会化
——以敦煌石窟唐代弥勒大像相关历史信息为中心
马 德
(敦煌研究院,甘肃 敦煌 736200)
一、弥勒信仰的“出世”与“入世”
弥勒信仰以弥勒菩萨为信奉对象,在印度出现较早,如《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五、《贤劫经》卷七《佛兴立品》等,皆以弥勒为未来出现之第一佛;《阿毗昙八犍度论》卷二十七亦记当来弥勒成佛之事。弥勒造像在印度出现也比较早,据《名僧传抄·法盛传》载,佛灭度后480年(公元前后),呵利难陀罗汉上升兜率天绘弥勒之像,至忧长国(佛国记之陀历国)东北,造牛头栴檀弥勒大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灵运传》载,那烂陀寺供有弥勒像;《大唐西域记》卷七、卷八亦载战主国都城西北之伽蓝供奉弥勒像;摩揭陀国佛陀成道之菩提树东方有精舍,以白银铸十余尺高之弥勒像。
中国关于弥勒信仰之译经,自西晋竺法护开始,先后有鸠摩罗什、沮渠京声、菩提流支、义净、菩提流志等共译出十余种译本,可归纳为“上生”“下生”“本愿”三系统。东晋时,弥勒信仰逐渐盛行,亦据经文教义分为上生、下生二派:上生信仰现今于兜率天说法之弥勒菩萨,而欲往生兜率天;下生信仰,相信弥勒将来下生此世界时,于龙华树下三会说法以救渡众生,而自己亦能生此世界,于龙华树下听受说法而成佛,故有龙华三会之说。上生信仰者,始有道安(314~385),据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所载,前秦苻坚遣使西域,携回弥勒结珠像等,道安开席讲法时,常罗列尊像。继有戴颙,据《法苑珠林》(卷十六)记载,东晋戴颙依据梦告,造立弥勒像,后安置于会稽龙华寺,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安置的弥勒佛像。道安之后,弥勒信仰逐渐普及,到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即成为后来的弥勒净土信仰,佛教史籍《法苑珠林》《名僧传抄》等记载丰富。至唐代,玄奘、窥基亦宏扬兜率上生信仰,而成为法相宗之传统。而下生信仰亦甚为普及,《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载:刘宋明帝撰《龙华誓愿文》,周颙作《京师诸邑造弥勒三会记》,齐竟陵文宣王作《龙华会记》,南岳慧思作《立誓愿文》,皆倡弥勒下生阎浮提之说;又据《名僧传抄》载,南朝刘宋元嘉九年(公元432年),法祥建弥勒精舍;唐代则天武后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命法朗等伪作《大云经》,谓武后系弥勒下生;五代时有布袋和尚更被传为弥勒化身。
由于弥勒信仰之普及,历史上的弥勒造像,多不胜数。南北朝时代,南齐建武年间,僧护曾发愿于剡县石城山雕凿千尺弥勒像,然愿未果而入寂,后由僧佑于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完成,历时30年才全部雕成,为江南早期石窟造像代表作。世称三世石佛、剡县大佛,即今新昌石城山大佛寺石佛,位于新昌县城西三里南明山中,石座高2.4米,像高13.2米;佛像高大巍峨、气势磅礴,南朝文学家刘勰誉之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旷代之鸿作”,后世称之为“江南第一大佛”。又据传说,石城山大佛寺创始于东晋永和初年(公元345年),故又有“石城古刹”之称。北魏献文帝时(466~471),凿造大同云冈第13窟弥勒洞,安置16米高之倚像,迁都洛阳后,又造龙门石窟,内有太和、景明、永平等年间所造之大小弥勒佛像数百尊。此外,山东历城黄石崖、千佛山亦有许多北朝所造弥勒像。至唐代,所造四川乐山大佛为世界第一大佛。位于甘肃省永靖县西南方向的小积石山中的炳灵寺石窟,以保存中国石窟最早纪年题记而闻名于世,始建于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之后,历代多有修建,直至明代;其中第171窟佛龛内造上半身依山石雕、下半身泥塑、通高27米的弥勒大像,建造于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宋、元、明、清历代均有修缮,佛顶原有七层阁楼建筑,后毁于战乱。另外,甘肃省甘谷县大像山的弥勒大佛,坐落于高约200米的崖壁间,是全国相对地面高度最高的大佛,整个身躯为半圆雕,高23.3米,宽10.2米,为石胎泥塑;经传,石胎雕于北魏时期,泥妆塑于盛唐年间。
相较之下,敦煌石窟的创建比新昌、云冈、龙门都要早,十六国、北朝时期就造有为数不少的弥勒菩萨造像,如著名的莫高窟第275窟交脚弥勒等;但北朝时代的造像似乎多表现为弥勒上生的内容。唐代建造了两尊弥勒大像,即今第96窟北大像和第130窟南大像。北大像建于武则天时期(又称武周时代,为唐朝的插曲),南大像建于开元时代①原文见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及敦煌遗书P.3720.。
另一方面,据历代史书所载,民众藉弥勒下生信仰,曲解经文,聚众叛乱者亦不少。隋代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宋子贤自称弥勒出世,聚众叛乱,袭击炀帝鸾驾而被捕。又陕西扶风人向海明亦自称弥勒出生,号召谋反。唐代开元(713~755)初年,贝州(河北)王怀古自称新佛(解作弥勒佛),举事被捕。唐僖宗(873~888)时,弥勒教徒于西蜀地方扩展势力,组织弥勒会。北宋仁宗(1022~1063)时,贝州之王则率领弥勒教徒叛乱。南宋及元代之白莲教亦混入弥勒教,假藉弥勒下生之名谋反,迄至明、清时代,尚流行于各地。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敦煌遗书的记载中还有更早的,即敦煌研究院藏北魏兴安三年的《大慈如来告身》,就是藉弥勒之名聚众起事的广告,也伪托是弥勒下生②敦煌研究院藏敦煌遗书DY.007号。。
从国内多处中古的弥勒造像看,很明显地都展示出弥勒下生信仰。弥勒上生信仰多为佛教僧团内部之信仰,而弥勒下生信仰则深入到民间,深入到基层社会。如果从佛教的入世和出世观来看,二者正是佛教的出世与入世的两种信仰观。
以往在敦煌佛教的研究中,对敦煌弥勒信仰问题,多以壁画为主,谈及敦煌弥勒造像者较少。例如,在敦煌石窟唐代《弥勒经变》壁画中一些关于细节的描写,特别是对未来的描写,非常生动丰富,艺术水平更是美妙绝伦。实际上,弥勒大像才是真正表现弥勒信仰的标志,展示弥勒信仰的主体,更应该得到关注。
二、敦煌唐代弥勒大像的历史信息
(一)莫高窟北大像(第96窟,通高34米)
1.唐武周时初建
据《莫高窟记》记载,北大像是延载二年(即证圣元年,公元695年)由灵隐禅师与居士阴祖所建,兹录如下:
莫高窟记
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年中,有沙门乐僔,仗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覆于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可有五百余龛。又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卅尺;又开元年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开皇年中僧善喜造讲堂。从初凿窟至大历三年戊申即四百四年,又至今大唐庚午即四百九十六年。
时咸通六年正月十五日记[1]42
2.晚唐重修
敦煌遗书P.2762《张淮深碑》记:
(前略)爰因搜练之暇,善业遍修,处处施功,笔述难尽:乃见宕泉北大像,建立多年,栋梁摧毁,若非大力所制,诸下孰敢能为?退故朽之摧残,葺昤珑之新样。于是杍匠治材而朴属斤,郢人兴役以施功:先竖四墙,后随缔构。曳其栿檩,凭八股之车卖轳;上墼运泥,斡双轮于霞际。旧阁乃重飞四级,靡称金身;新增而横敞五层,高低得所。玉豪扬采,与旭日而连晖;结脊双鵄,对危峰而争耸。[1]301
张淮深这次重修北大像的时间在唐代乾符元年到中和五年(874~885)之间,主要是将窟前瞻四层楼阁增建为五层,使之更为雄伟壮观。现窟内东壁门北露出晚唐壁画,当为张淮深重建时所绘制。这次重修活动没有提及“窟家”,纯属官府举措,说明原建窟主阴祖已无后人在敦煌。
3.宋初重修
宋代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与其妻浔阳翟氏避暑莫高窟,因见北大像窟檐“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撑木损折”,发愿修复。这次重建只拆换了下两层撑木,窟檐仍为五层。据敦煌遗书CH.00207《曹元忠与翟氏重修北大像记》记载:
大宋乾德四年(966年)岁次丙寅五月九日,敕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托西大王曹元忠,与敕授凉国夫人浔阳翟氏,因为斋月,届此仙岩,(中略)遂睹北大像弥勒,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材木损折,大王、夫人见斯颓毁,便乃虔告焚香,诱谕都僧统大师,兼及僧俗、官吏,心意一决,更无二三,不经旬时,缔构已毕。梁栋则谷中采取,总是早岁枯干;椽柃乃从城斫来,并仗信心檀越。工人供备,实是丰盈,饭似积山,酒如江海。可谓时平道泰,俗富人安,尽因明主以陶熔,皆由仁君而造化。(中略)凉国夫人翟氏自手造食,供备工人。其月廿一、廿二两日换柱,材木损折较多,不堪安置。至廿三日下手拆。大王、夫人于南谷住。至廿四日拆了,夜间大王、夫人从南谷回来。至廿五日便缚绷阁、上材木、缔构;六月二日功毕;四日入城。助修勾当:应管内外都僧统辨正大师紫赐钢惠、释门僧正愿启、释门僧正信力、都头知子弟虞侯索幸恩;一十二寺每寺僧十二人;木匠五十六人,泥匠十人。其工匠官家供备食饭;师僧三日供食,已后当寺供给。[1]143-144
此文亦未及北大像之原建“窟家”,而由官府与僧团联合重修。据窟内现存壁画痕迹及后来试发掘的铺地花砖,这次重修在维修完楼阁后还对窟内外的壁画进行了重绘(目前所能看到的大底层的通道内的壁画痕迹,及现第三层暴露出来的壁画颜料痕迹即是宋代初年的壁画),并在底层地面全部铺上八辨莲花图案的地砖。由于文书的主要内容是为来莫高窟避暑的曹氏夫妇歌功颂德,所以文中透露出曹氏夫妇离开时,整个重修工程似乎还没有完结。另外,虽然是维修窟前土木建筑,但势必会影响窟内大佛塑像及四壁壁画的损伤而进行补修补绘。而所有这一切,包括这项工程的全部收尾,写于工程收尾之前的这份文书没有丝毫反映。
在第96窟窟内底部的地面上,紧贴西壁凿建的连接南北两壁的通道从大佛佛座底下穿过,中间大佛之腿部还凿有两孔作供礼拜者采光的明窗;此通道原凿建与大佛初造为同时期,因为道壁上也暴露出与窟内各壁同样的数层各时代的壁画痕迹,其中最明显者为两端入口处内顶上的宋代火焰纹与云纹壁画,与莫高窟第25等窟的壁画几乎为出自同一人之手,是典型的曹氏中晚期(宋初)壁画。莫高窟第96窟前底层殿堂地面与窟内地面所铺设的八瓣莲花花砖,与窟内壁画一道,为公元966年重修北大像的“二期工程”,其时当在曹元忠夫妇离开莫高窟后不久。
4.清末重修
据立于1906年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千碑记》记载:“丁酉(公元1897年)之岁,邑人戴君奉钰倡首续修,聚众善之赀力,营艰大之工程;左提右挈,其运意为独挚矣!始构大雄之殿,继兴大士之宫,畴昔荒刹萧索,不蔽风雨;今则洞宇峥嵘,观瞻辄资景仰。苟非竭诚补葺,即阅五六年,殊难告厥蒇功。”这里记载的戴奉钰所建似乎没有成功。1936年《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记:“大佛一尊,余身尽山,高十八丈。年久山圮,法相暴露。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商民戴奉钰建未成。”所载相同。然从由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所拍“北大像”窟外的五层楼照片看,似乎又是在唐代改建的五层基础上所为,即光绪二十四年戴奉钰所建。但与崖面上留下的遗迹相比较,清代所建五层楼阁的规模远比唐代要小。
5.民国重修
据《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载: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928~1935),敦煌“德兴恒”商主刘骥德,敦煌乡绅士民张盘铭和莫高窟主持喇嘛易昌恕等人,“集合官绅农商各界,发愿重修”,“起民国戊辰至乙亥,八易春秋,用金一万二千余元”,改五层为九层,“而工程巩固,巍峨壮观”,同时曾对“北大像”全身妆銮。重建峻工后,九层飞檐倚山而立,兽鸱栿脊,风铎悬鸣;栏槛宫阙,层廊迭垒,巍峨绮丽,殊为壮观,但其规模仍依清代楼阁。
(二)莫高窟南大像(第130窟,通高28米)
1.初建
前述《莫高窟记》云“开元年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晚于此半个多世纪的P.3721《瓜沙史事系年》记“开元九年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发心造南大像弥勒高一百廿尺”。由此可知,南大像之始建当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20世纪60年代曾在该窟顶部壁画地仗与崖体之夹缝间发现书写有“开元十三年”题记的发愿文幡一条,证明该窟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之后不久开始壁画的绘制。根据甬道北壁所绘晋昌郡太守乐廷瑰供养像可推知,该窟的建成时间当在唐代设置晋昌郡的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间。[2]204-205由此可见,第130窟南大像从开凿到最后完成,经过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同北大像一样,南大像的建成,是莫高窟营造史上的又一伟大创举,也是开元、天宝时期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象征。
开元时期造弥勒大像者不止莫高窟一处,榆林窟第6窟高达24.7米的弥勒大佛也建造于开元年间,但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现存面貌为清代重修所致。而以其巍峨雄伟的气势闻名中外的世界第一大佛的四川乐山石刻弥勒坐像的建造,有比较可信的史料记载。乐山大佛地处四川省乐山市东,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合的凌云山上,依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凿造的一尊弥勒坐像,与乐山城隔江相望。青衣江、大渡河于凌云山下汇集为岷江,据传当年水灾频繁,为害甚烈。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凌云寺僧释海通为减杀水势,造福民众而发起募集人力物力修凿的。海通禅师圆寂以后,工程被迫停止,多年后,先后由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和韦皋续建,至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竣工。前后历时90年,耗资数以亿贯。可见乐山弥勒大像的建造具有明显的社会目的和意义。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发髻有1021个,耳长6.72米,鼻长5.33米,眼长3.3米,肩宽24米,手的中指长8.3米,脚背宽9米,长11米,比起曾号称世界最大的阿富巴米羊大佛(高53米)还要高出18米,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之称。
有人据莫高窟北大像的相关信息认为,既然北大像是为武则天造像,那么开元时期的莫高窟南大像就是为唐玄宗李隆基造像了。这种说法纯属主观臆断,因为没有任何记载能说明南大像是为唐玄宗李隆基造像,前述乐山大佛的建造已经说明了问题。唐玄宗执政初的开元二年(公元713年),连颁五道诏令阻碍和禁止佛教的发展;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于花萼楼召释道二教论议后才开始崇佛,之后于开元二十三、四年(公元735年、公元736年)亲注《金刚经》颁行天下普令宣讲;开元二十六年“敕天下诸州立龙兴、开元二寺”;第二年颁诏令天下僧道遇国忌日就龙兴寺开道散斋,千秋节(玄宗生日)就开元寺祝寿;这样,开元寺实际上成了全国民众为李隆基个人祝寿的“道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敕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以金铜铸帝身及天尊各一躯,送开元观及开元寺”。[3]天尊即元始天尊,为道教三清之首,送入开元观顺理成章;而“帝身”无疑为玄宗自身,入开元寺者非此莫属。敦煌于唐代不仅建造了龙兴、开元二寺,而且开元寺的玄宗“圣容”“御座”一直到一百多年后,经历了吐蕃统治又重新归唐的乾符年间(874-879)还保存完好;当时唐僖宗派天使一行到敦煌授敕封后,在张淮深(尚书)的陪同下到开元寺:
尚书授敕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炖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于(余)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雕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洲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天使两两相看,一时垂泪,左右骖从,无不惨怆。[4]
这段描述十分感人。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敦煌的开元寺里,专门供有唐玄宗的“圣容”“御座”。因此,不可能再以弥勒大像为唐玄宗了。况且,莫高窟南大像及四川乐山大佛都兴建于开元初期和前期,当玄宗还在崇道抑佛时,弥勒大像的建造虽然不曾受到玄宗禁佛令的影响,但绝对不可能以玄宗为弥勒而造大佛。
2.吐蕃时期对南大像的重修
敦煌文书Дx.6065《乘恩等重修莫高窟弥勒像帖》全文如下:
(前缺)月廿一日,诸寺尊宿、教授、法律就灵图寺……高窟弥勒像。所要色、彩、麻、胶等物,仰……所要人工,仰诸寺尊宿、禅、律有徒弟者……其林木、白土,仰窟家供。亲赴窟检校大德:宋教授者梨二人李教授梨二人张阇梨二人唐梨一人索教授梨一人杜法律梨二人 康梨二人阴法律二人照法律二人英法律二人照律师二人宋律师二人法圆律师洪律师二人真法师哲法师严法师惠法师 张上座 应管窟头僧,除老病小者仰当寺排合五人为一蕃,从起首日至终,一蕃上五人,除本居窟者,终而复始。其法律大德应有名者,并限令今月廿四日夜窟头取齐。道光禅师、智超准上限须到窟头,并据一。 乘恩
据《宋高僧传》记载,乘恩为长安西明寺僧,天宝末年后避乱游居河西。但本文与敦煌文书P.3730、Дx2959等所记载之乘恩,活动于公元815年之后,二乘恩恐非一人。而本文书之成书及其所记重修莫高窟弥勒像之年代,据贴文中宋(正勤)教授阇梨(公元821年担任敦煌僧团之都教授)、洪律师(公元820年担任敦煌僧团都法律兼摄副教授)、徒弟法(S.1475《酉年(公元817年)曹茂晟遍麦契》云“保人男沙弥法年十八”)等人的活动年代,应在公元817年前后。帖文中之“窟家”应是莫高窟南大像130窟原建窟主马思忠之后人。这次重修主要是对窟前的土木结构的殿堂楼阁进行了整修,由马氏家族供应材料,敦煌僧团出人力。所以,Дa.6065《乘恩等重修莫高窟弥勒像帖》是公元817年前后,担任都教授的乘恩和尚组织敦煌僧团及窟主家族重修莫高窟130窟的帖文。这是目前所见有关大像重修的最早的记载,从时间上距初建时间仅60余年。这份文书为我们提供了莫高窟崖面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3.宋初曹宗寿时期的重修
曹氏时义这后期的曹宗寿时期,南大像经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包括窟内壁画的和窟前殿堂的重建。这次重修的痕迹至今依然有存,[2]210兹不赘。
(三)其他相关信息
敦煌莫高窟北大像(第96窟)所在崖体倾斜度大,虽然也可以开龛,但崖面高度不足,开龛的话会降低佛像本身的高度。另外,要是崖面进深太深,工程量大,且也不能保证崖顶的坚固性,因为佛像的高度不能改,所以只能在崖面上想办法。这样就有了弥勒像的头部及上半身先置于露天的设计。我们从上世纪初佛像暴露的照片上看,佛像头顶几与崖顶相齐。而四层楼阁为大像凿成后始建,实际上就是刚好将佛头罩在里面。后来改成五层,实际上是在第四层上面又加盖了一层,即今日九层楼之第8、9二层。但从建筑规模遗迹看,无论进深面宽,今天的九层楼还不及唐代四、五层楼的一半。
敦煌莫高窟南大像(第130窟)一开始就建在室内,崖壁上分为三层,除最上层在开凿时没有留下岩体甬道(可能是考虑到出渣)外,二层和底层的窟门都有比较长的甬道,而且在底屋甬道的南北两壁靠近顶部,还分别开有盛唐时期流行的敞口形佛龛,内一佛二菩萨组像,龛顶和左右后三壁都绘有壁画,而窟前木结构建筑一直为三层,现存顶层小型窟檐及底层规模庞大的唐宋殿堂遗址。
三、弥勒下生信仰的功利性与佛教的社会化
弥勒下生信仰,主题就是对未来美好世界和幸福生活的向往。但当这种信仰进入中国社会之后,却展示了其明显的社会功利性。
武周时所建的弥勒大像,人们总是把它和武则天联系到一起,认为是为迎合武则天皇帝而造。可能有点道理。因为敦煌莫高窟北大像的营造者(窟主)为敦煌阴祖,敦煌文书P.2625《敦煌名族志·阴氏》中有关于北大像建造者阴祖及其后人活动的简略记载:
(前略)阳(阴)祖,乡闾令望,州县轨仪,年八十四,板授秦州清水县令、上柱国。祖子守忠,唐任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又改授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凉州丽水府折冲都尉、摄本卫郎将、借鱼袋,仍充墨离军副使、上柱国。以父老请侍,孝诚恳切。蒙凉州都督郭元振判录奏:谋略克宣,勤劳久着,当王凉之西面,处四镇之东门。弹压山川,控御缓急,寇不敢犯,尘不得飞。将士有投醪之欢,吏人承狭纩之惠。防授既众,功效实多,利润倍深,孽课尤剩。赵充国之为将,省而成功;甘延寿之居边,惠而能利。长子修已,右卫勋,二府勋卫,材兼文武,蹈礼依仁,少习父风,乡闾挹以其干略,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岛军兵马。次子修义,见任文州平府别将。[5]111-112
这里将阴祖之子阴守忠与汉代名将赵充国相提并论,可见其功勋卓著。但守忠在武周初年还是一普通百姓,他曾于公元691年时向武则天献“祥瑞”,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祥瑞》条下记:
白狼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状称:白狼频到守忠庄边,见小儿及畜生皆不伤,其色如雪者。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云:‘王者,仁智明悊,即至;动准法度,则见。’又云:‘周宣王时白狼见犬戎服者。’天显陛下仁智明悊,动准法度,四夷宾服之征也。又见于阴守忠之庄边者,阴者,臣道,天告臣子并守忠于陛下也。”[5]19
看来,《敦煌名族志·阴氏》所记阴守忠官居“唐任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又改授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凉州丽水府折冲都尉、摄本卫郎将、借鱼袋,仍充墨离军副使、上柱国”的时间明确为唐,应当在李唐复国即公元705年之后;这里没有记载阴守忠在武周时期担任何职,但可以推知,公元691年阴守忠向武则天献祥瑞白狼后即得官职,此后不久(公元695年)其父即建造莫高窟北大像,这一切都是阴守忠及其家族为讨好武则天的功利行为。所以说,阴祖是为了武则天建造北大像。可能是因为在武周时的表演太过肉麻,所以李唐复国后即以服侍老父为名请辞官,恰好又逢郭元振保荐而继续留任唐朝。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年间(701~705),[2]204正是武周末及李唐复国交替时期;守忠得其保荐后又再建功业,以至于其父阴祖84高龄获得板授。这样看来,阴祖一家建造北大像的目的和动机就有点眉目了:守忠因献祥瑞白狼而得官,随之有阴祖建造北大像之举,这一切所展示的功利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守忠的二子在河西节度使时代(复唐之后)都顺利为将,为阴祖一家再显荣耀。虽如此,可能也是因为在武周时代包括献祥瑞、造弥勒大像等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一系列行为,阴祖一家在李唐复国后无法在敦煌立足,而随其子阴宁忠的重新出仕而举家东迁,蒙唐朝的板授高年制度在84岁时得到一个“秦州清水县令”的虚衔,加之其子守忠、孙修己修义等也为官河东,已经没有后代在敦煌。此后,北大像无“窟家”(即窟主)而由官府和僧团管理。
有种说法认为,至唐代后,由于阿弥陀经之译出,发愿往生西方净土者亦多,故弥勒信仰已不如以前盛行。这可能是从文献的一些不完整的记载中得出的结论;或者说,这只是就佛教内部而言,而忽视了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唐代的弥勒信仰并不比前代任何时候逊色,只是信仰形式发生了变化。如世界第一大佛四川乐山大佛就凿建于唐开元时代,甘肃永靖炳灵寺的弥勒大佛也是开元时期建造的,其时正值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期。历史证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期,正是弥勒信仰的极盛期,敦煌地区亦不例外。当然说到底,这种信仰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
弥勒信仰已成为社会需要,无论是早期的利用还是后来的崇敬,都是为了未来,但这种对未来的向往也明显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上至唐朝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如此。这也正是佛教社会化的具体体现。如果从佛教义理方面讲,敦煌弥勒大像的营建,属于弥勒下生信仰。在敦煌石窟众多的《弥勒经变》壁画中,弥勒下生来到人间,人间变成天堂,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这些经变画与弥勒大像相呼应,展示了全社会的弥勒信仰。
所以,笔者以为,中国社会的弥勒下生信仰,一直是带有功利性质的,是急功近利式的追求未来之世,与佛教教义相去甚远。如果说南北朝时期以来的弥勒造像,一直是在追求弥勒下生的太平盛世,那么武周时代有歌颂则天皇帝的意图,此后也是为了国泰民安。敦煌唐代的弥勒大像就是传递了这方面的历史信息。
中国的弥勒下生信仰固然有曲解佛教教义之嫌,但能够让佛教深入社会,直接进入民众生活,也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人间佛教之路,问题是需要正确的导向。弥勒下生是指弥勒佛降生人间,给人世间带来幸福和繁荣,这一点是不能伪托的。这也就是佛教一贯强调的“正信”。所以,弥勒信仰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大力倡导和奉行人间佛教,或者是社会化佛教的同时,一定要处理好“正信”,以免误入歧途。特别是弥勒信仰,更需要我们共同去维护这一片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