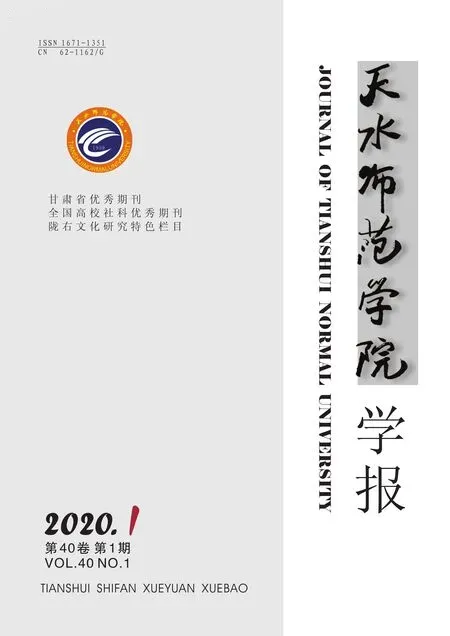敦煌人的特质及其人文启示
成兆文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一、敦煌人的来历
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自己强烈的地域特征,盖因人是有交往边界的群体性高等动物。作为中国最具精神含量的地名之主人,敦煌人的特殊性更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
谁是敦煌人?不就是生活在敦煌大地上的居民吗?仔细想,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除过和其他地方一样的规定性:敦煌人就是出生在敦煌的本地人,籍贯或者出生地在敦煌的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现代的敦煌人和古代的敦煌人是大不一样的。当敦煌从一个地名上升为文化概念时,敦煌人就不仅仅是限于时空坐标的简单描述,它隐含着文化流动的精神聚拢。
当代敦煌是一座非常具有精神归属感的城市。这一品性在泡沫般膨胀的现代城市中是非常罕见的。异乡感是现代人共同的宿命,缺乏精神归宿感,哪怕是宽房大舍,打拼经年,也难安心。这一点在敦煌是一个例外,敦煌是当今城市中最有精神归属感的地方之一,到了敦煌几乎每个人觉得这座城市与自己有关,都有为敦煌做些什么的心理冲动。20世纪伊始,从敦煌藏经洞发现之日起,来敦煌的人就络绎不绝,这个队伍日渐壮大,许多文化艺术家在敦煌一待就是几十年。
三百年前,清王朝雍正四年(1726)的移民政策,肇造了近现代的敦煌人。[1]103就山川形貌来说,敦煌除过没有海洋,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地形地貌,雪峰高山、草原绿野、森林农田、大漠戈壁、雅丹地貌、丹霞奇景、峡谷湍流、湿地丘陵、湖泊清泉,如此等等。文化的多样性更是敦煌的一大特点,汉唐如此,近世以来得以延续。敦煌三百年前的居民来源几乎涵盖了甘肃所有的州县,这就使得敦煌有了“小甘肃”的美称。[2]37-67敦煌后来还有多次移民,包括河南、上海、天津、山西、陕西的部分居民迁入,成为敦煌人的一部分。移民的多样性保持了近代以来敦煌人的多样性,多样性恰恰是古代敦煌精神的一种延续。那时候的移民之艰辛与生命之顽强超过现代人的想象。在敦煌悬泉置留下的汉代竹简上可以清楚看到,从敦煌到长安出差一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这还是官方支持下的公差。清朝和汉代的交通工具相差无几,拖家带口从甘肃各地赶来,尤其陇东南山大沟深,要靠双脚跨越莽莽戈壁,其艰辛程度难以想象。有人说,当时移民的只是生活艰辛的贫苦百姓,理由是富庶之家没有移民的愿望。这种说法有点绝对了,因为移民实边、开垦荒地是一项国家政策,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从历史上看,敦煌的辉煌与关内中原大族的迁入有关系,他们在战乱年代主动举家迁移,带来了中原成熟的文化因子,莫高窟的开凿可以累世坚持上千年,没有世宗大族是不可想象的。
五十六个州县的移民到了敦煌以后,在如何安置的问题上,当时的管理者也是颇费心思。黄河从甘肃省中间拐弯穿过,把陇上居民分为河西河东两部分。敦煌移民以党河水为界,河西人仍然被安置在党河以西,河东人居党河以东。地名当然是新的重置,那些古代很多著名的地名和水系几乎不见了,[3]295-337代之而起的是各州县的名称,但多样性予以保留。这样就有了三重效应:从小处说,熟人邻居形成了生活习惯、文化心理相互认同的生活方式,山河变了,而乡里乡亲依然如故,只不过把过去的州县乡亲变为生活的邻居。扩展一点讲,河东河西隔河相望,这是生活习俗相近者的聚拢,又以自然屏障为界,乡音彼此保留下来。河西河东在敦煌得以复制,村之外,还是缩小版的州县,多样性的统一,大致分为河东河西两块,也形成了各有特性的敦煌人。再扩展一点讲,整个敦煌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甘肃,民风民俗、乡音乡情都以村落的形式得以保留,无论甘肃何地的居民都可以在敦煌找到自己三百年前的乡亲。敦煌近世文化的包容性在居民的安置上得以彰显,这是对更加久远的古代敦煌开放包容精神的续写,令人心生敬仰。有历史感的文化人,都感念时任甘肃巡抚、川陕总督的岳钟琪,他主持移民敦煌的眼光和决定是对敦煌历史文脉的延续,他提出移民敦煌的两个原则是就近、懂农垦。这两个原则简练实用,历史证明效果很好,一则保证了敦煌人来源广泛,但多而不杂;二是移民大多数是高素质、懂种地技术的农民,避免了吸纳游手好闲之徒,这也深深影响了后世敦煌人的性格特点。有人就此总结过,敦煌的河西人生活相对拘谨精明,河东人则豪放直爽,这与河西先民过惯了农垦文明、自给自足、较为排外有关。笔者则更认为这是先民自身特质与敦煌本地地理人文共同作用的结果,陇东南的先民要到河西之西端安身立命,必然要带着开拓意识。除过方言对应性之外,他们自身迈向远方的第一步就带有豪迈之气。
二、敦煌人的基本特质
笼统说敦煌人,以下几个特质是最明显的。
一是淡定。敦煌人的淡定不仅仅是因为见多识广,小城市大舞台,还在于敦煌人在骨子里受到一种敦煌文化场的滋养,还在于对自己生活地域的满意与自豪,敦煌人对生长生活在敦煌的自豪感,是从骨子里带来的。
应时是敦煌人的第二个特质。应时于此有两层含义,一是敦煌人对现代化或者先进的生活方式熟悉,二是敦煌人喜欢学习,开阔眼界。古代敦煌人就不必说了,华戎交会,丝路明珠,是各种文化的集散地。经过一段时间沉寂后,百年前从莫高窟发现藏经洞起,敦煌再一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旅游业井喷式发展,给敦煌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各种经济的、文化的、信息的元素向敦煌积聚,敦煌人又投入了新的“开放”和“包容”的世界。敦煌市图书馆利用率很高,各种学术研讨会大咖云集,只要有讲演,敦煌人就争先恐后,生怕错过,敦煌人的文化品位自然就高起来。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敦煌的文化活动无论文艺演出还是文化展览,抑或是学术演讲,都是高水准的,因为举办者知道活动面对的不仅是敦煌本地,同时也在面对全世界。敦煌人在高质量的文化活动中锤炼了品性,提高了审美境界。因此,敦煌市人口不多,但敦煌研究院的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高尔泰、樊锦诗都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新一代传人常莎娜也是世界名人。
敦煌人的第三个特质是安逸。安逸是相对富足的另一个表现。在县域经济中,敦煌一直在甘肃省名列前茅。许多人以为敦煌地处沙漠边缘,是不毛之地,恰恰相反,仰赖祁连山的冰雪,党河水滋养着敦煌绿洲,还有疏勒河从远方缠绵而来,再有宕泉河等各种小溪,敦煌的绿洲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冲积扇形状,大河西流,南水北去,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地理常态大不一样。敦煌有着广阔的面积,虽然绿洲面积不大,仅仅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但有着肥沃的土壤和丰饶的物产,让敦煌人不愿意外出,大有“走遍世界各地,唯我敦煌美丽”的自豪。
敦煌人的第四个特质是古雅。敦煌人的古雅表现为三点,第一是对传统文化的狂热喜爱,第二是对仪式感的看重,第三是对文化传统的坚守。《晋书》中记载李暠说敦煌居民:“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4]113敦煌人自古有敦雅的特质。
敦煌人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消费从古至今都延续着一种激情,敦煌人对文化的热爱发自内心,几乎所有的人家都要挂中堂贴对联,崇文重教,蔚然成风。说起传统文化,很多敦煌人都能讲个滔滔不绝,从敦煌壁画到敦煌史地人物,从汉代长城到近代堡子文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曲子戏讲到敦煌舞蹈、敦煌建筑、敦煌打铁花,等等。敦煌人古雅的第二个表现是对仪式感的看重,婚丧嫁娶、待人接物都有各种礼数、各种仪式。孩子从出生、满月、百日岁到升学、工作和婚姻,都有各种各样的礼仪。敦煌人的礼节之多造就了幸福的烦恼,因为,乡里邻居、亲房亲戚,事无大小,都需要常去看看,难免应接不暇。
仪式感是礼仪的另一种表达,任何文化的载体都是仪式感,这在其他地方也不鲜见。正月初一、十五到雷音寺上头香,二月二社火舞龙钻龙,三月三到广场放风筝举办诗会,清明节携全家到亲人坟头上坟,四月八到莫高窟礼佛,五月五用党河边露水洗头,六月六到鸣沙山做沙疗,七月十五又一次去祖先亲人墓地上坟,八月十五在家里拜月,到月牙泉赏月,九月九看望有德老人,十月一一定要给逝去的亲人送寒衣,腊月的小年也更是甜言蜜语。这些中华节日的基本礼仪在其他地方,随着时间流逝和城市化进程,慢慢淡了,敦煌人却一直坚持下来,这也是古雅的第三个方面。
古雅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审美上的古典。飞天形象不但是敦煌艺术家的灵感源泉,也是敦煌人审美的自觉参照。飞天的形象深入人心,这自然成了敦煌女子的潜意识审美模型。作为飞天的后人,敦煌女子明媚优雅,骨子里渗透着一股古雅之气,眉宇间带着汉唐的气韵,表达情感深沉内敛又不失热烈奔放。
三、敦煌人特质的原因分析
敦煌人为何有这样的特质,至少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的敦煌是灿烂文化的代名词。自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以来,敦煌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历史名城。要了解敦煌的整个战略位置,必须要了解河西走廊。要了解河西走廊,就必须了解一座山海,即山的海洋——祁连山。在中国大陆的西北部,横亘着广袤的大漠,在大漠与内陆的连接处,就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青藏高原靠近西北的边缘,横亘着祁连山。祁连山绵延800多公里,但它的宽度却十分惊人,平均达200~300公里。在这个突然隆起的山海里,储蓄了亿万方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这就让祁连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水塔。有了祁连山,西北方的大漠与大陆之间出现了一大片肥沃而狭长的绿洲,这就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把西北大漠与西南青藏高原分隔开来,荒芜中突然有了勃勃生机,给了西北大陆一个稳定的粮仓和里进外出的大通道,还如同巨大的臂膀,把新疆揽在大陆的怀里。河西走廊上,汉王朝设置威武、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部边缘,也是祁连山与西部当金山的边缘,再往西就是广袤的库木塔格沙漠。得益于祁连山的恩赐,党河水和疏勒河水从雪山走来,南水北去,大河西流,在3万多平方公里的敦煌大地上,生发出了一片不到1500平方公里的绿洲,这是敦煌人赖以存身的基本条件。据史书记载,敦煌疏勒河曾经有发达的漕运,河上船只往来不绝,可见那时水量之丰。由此,敦煌的战略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它是河西走廊绿洲进入西部大漠最后一个重要的水源补给线。古今中外,文明都与水源地有关。阳关和玉门关就是扼守水源的重要关隘,谁守住了水源,谁就是文明的话语主导者,这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由此,拥有敦煌预示着往西可以睥睨西域,远出欧洲,向东则通联中原,联结长安。这也是敦煌作为地名出现后,被有眼光的汉代雄杰所看重的根本原因。军事要塞,不单纯是戍边拒敌,而且也是重要的经济重镇。有了人气,文化自然而来,商贾云集理所应当,各种信息汇聚激荡。
敦煌地处祖国内陆,现在看似偏远,在陆权时代,这里是交通要道。但从距离上看,毕竟远离经济政治中心,魏晋时期当中原王朝因为战乱陷入混乱礼崩乐坏的时候,以敦煌、武威为代表的河西五凉文化却在把华夏文明继续发扬光大。敦煌的文庙曾经会聚着许多学子,研习儒家经典,知书达礼,忠君报国情怀高涨。在文化发展史上这种现象叫“边缘崛起”,即远离战乱,反而可以把文明因子加以聚合创造。有人说,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大发明是隋唐科举制度,而这个制度的雏形则诞生于河西走廊的五凉文化。敦煌的地理位置遥远反而有利于文化因子的自然发酵、发生化学反应。
其二是特殊的资源禀赋。最新发现,敦煌及其河西走廊一带,在三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和敦煌附近新发现的史前旱峡古玉矿都证明,敦煌在很早以前就有文明的雏形。从史前看,敦煌是各种稀有经济资源的发端地,这里的大地上产出各类宝器玉石,这是古代价值的最高载体,象征着权力荣耀与审美标准。同时,敦煌还生产各类矿物质颜料,它是莫高窟壁画经久不衰的秘密。很多迹象表明,莫高窟壁画的大部分颜料产自敦煌本土,只有少数颜料来源于中亚细亚或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敦煌西土沟发现的古代铜渣,可知四千年前这里已经有了冶炼业。文化繁盛的背后是强大的经济支撑,敦煌为中原地区提供了稀缺资源。敦煌开始以玉石而著名,玉门著名就在于此,后来更是以丝绸之路重镇闻名。丝绸是轻质软黄金,其价值之高足以让古代来此的商贾发挥人力极限潜力,跨越大漠,通达中西。汉唐以来的敦煌资源富集,有些人文资产也化为后世的资源禀赋。在敦煌捡到几千年前的石器陶片很正常,在烽燧边随便可以捡到唐砖汉瓦。2014年6月,在丝绸之路——天山廊道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中有一个名词:敦煌悬泉置。三危山下的遗址旁,一个不起眼的土坑里,出土了三万多枚汉简,世界上最早的麻纸和最早的环保法,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最大的邮政站,再现了丝绸之路曾经的繁华。
其三是特殊的历史人文。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对敦煌的有效管理是从汉代开始的,敦煌的历史地位在唐代达到顶峰。敦煌遗留的文化遗存,除过明朝短暂的二百年断续之外,囊括了两千年来的文化历史。这就形成了巨大的敦煌文化场。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的汇聚地,更是中华文明各种思潮流派的竞技场,儒佛道竞相绽放,文史哲、音体美轮番精彩。生在敦煌的人自然受到文化的熏染。古代敦煌的地位,相当于当代的北上广、深港澳,曾有“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的说法。[4]文化是斩不断的场域,一旦历史被激活,就会实现过去与未来的共振。汉代以来各路英雄围绕敦煌建功立业,凿空西域的张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雄班超,文武双全的索靖、李暠,一代书法草圣张芝,丝路文化大使鸠摩罗什、法显、玄奘,以及重开丝路的张议潮、曹议金等文人雅士于此慨叹人生,英雄豪杰因斯建功立业。张大千曾痴迷敦煌壁画,在敦煌面壁三载,[6]8-9自后画风大变,声名更隆。常书鸿、段文杰等一代著名的绘画大师,之所以痴心不改,还在于敦煌本身具有的强大吸引力。艺术家一旦走进敦煌的历史文化,艺术的灵感被激活,大多数人就舍不得离开敦煌了。
历史人文活化在敦煌人的心目中,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发自内心,痴迷文化是敦煌人的表现,也是其基本特质。莫高窟在“文革”浩劫中能躲过一劫,除过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保护之外,还与敦煌人自发参与莫高窟的保护巡查有关。对历史遗迹的厚爱,在敦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否则,从汉代以来烽燧、洞窟壁画和塑像能够完整保存是不可想象的。
文化的自觉是敦煌文化得以创新传承的根本原因。相比较于世界其他文明交汇、文化碰撞之地,古代的敦煌人有一种主动把各种优秀文明因子、文化元素进行融合会通的自觉,莫高窟壁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历代敦煌文人艺术家都把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因子当作一项自觉的行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这个自觉性使得敦煌的文化包容性极为强烈,它也是敦煌精神的最珍贵的部分,对此问题的理论性抽象是著名学者范鹏先生提出敦煌哲学的初衷。[7]的确,敦煌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是敦大煌盛的形容词,更是一个代表活化历史的动词。
其四是特殊的地理气候。敦煌干旱少雨,年降雨量40多毫米(近年降水量多有增加),蒸发量2600毫米,后者是前者的65倍,被称为旱极。敦煌属于典型的沙漠气候,地处祖国内陆,可谓西部沙漠之城。如果没有这极为干燥的气候,莫高窟保存一千六百余年是不可想象的。敦煌夏季气温之高是远近闻名的,室外温度接近40度常见,2016年夏至,雅丹地表温度更是高达67摄氏度,鸡蛋随便就可以烫熟。
为了对抗干旱的风沙,敦煌人发明了各种生活的办法,开凿石窟是众多办法之一,古代只有坚硬的石头才能永恒。20世纪初,当道士王圆箓清理淤积在莫高窟的流沙后,发现很多一千多年前的壁画新艳如昨。敦煌古人就地取材,夹杂当地盛产的芦苇或者其他植物,夯土为墙,挡住了两千年的风沙。笔者在玉门关小方盘城和众多汉代烽燧前近距离观察,发现很多汉代墙体早已石化,其致密牢固程度不亚于现代水泥。因此,敦煌人的建筑颜色以大地黄为主,与大地融为一体,呈现着天人合一的生存之道。同时,敦煌的冬天也是出名的冷,塞外风一刮,气温便落到了零下二十度以下。围着柴火烤火,或者坐在热炕上打发时间,成为近代敦煌人的生活常态。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敦煌大地上留下了神奇遗产。鸣沙山除过不鼓自鸣的神奇现象之外,还有白天踩踏而下的大量沙粒,黄昏夜晚的风又会全部携带到山顶,重现刀削斧刻之状。月牙泉放在风景秀丽的江南不会显眼,但在沙漠里有一汪清泉,如同万年深情亮澈的眼睛注视着天空,这就极其罕见了。最富造化的当然是敦煌雅丹地貌,四百多平方公里戈壁大地上,雕凿出一座超级神幻城池,金字塔、狮身人面、比萨斜塔、金狮望月、孔雀开屏,甚至有汪洋大海中的千帆竞发,富有联想能力的学者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西游胜境,《西游记》中的各种场景各个仙佛妖怪形象在此得到了集中。很多人到雅丹有非常强烈的时空穿越感,有河北的驴友说:面对雅丹地貌,那亿万年时间的印痕凝聚与呈现,似乎见到了时光中的委屈与坚守,不由自主让我泪水长流,觉得此地才能够把自己的心灵安放。敦煌被一些人誉为爱情之都,除过些许浪漫的想象之外,更在于敦煌本身就充满奇迹。
四、敦煌人是历史场域与时代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
回到第一个问题,谁是敦煌人?
原始的敦煌人在史料上说是乌孙人、月氏人,随着匈奴人的崛起,他们西迁到中亚细亚去了,但留下的历史遗迹不多,没有形成文明的体系。至于“舜窜三苗于三危”的说法,[8]有人认为是西南少数民族被舜迁移到敦煌来,但距离太远,所以不太可能。随着敦煌旱峡古代玉矿的发现,大量的陶片和石器出土,让人们重新开始打量最早的敦煌人。汉代经营河西以来,有史可查的敦煌人来自陇东南及关中平原的望族,他们文武俱盛,怀揣家国热情,富有英雄情怀。早期以敦煌为代表的河西走廊成为中原文化的飞地,很重要的原因是先民们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著名学者郭瑀是秦州略阳大儒郭荷的弟子,就带动了河西整个儒风的盛烈。由于是华戎交汇处,这里的人口也是一个巨大的民族基因库,汉人、月氏、乌松、粟特、匈奴、回鹘、西夏、吐蕃、蒙古人等不一而足,都在这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西晋时候,投鞭断流的前秦皇帝苻坚曾经迁江汉中州的居民一万七千余户到敦煌,三国两晋时的敦煌人口曾达十一万之多。[4]119北魏时候,两万多敦煌工匠支援山西云冈石窟的修建,凿窟塑像当然是累世之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十代人,这些人自然变为山西人的一部分。张大千高价收购的莫高窟壁画粉本显示,当年的壁画汇聚了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莫高窟的石窟艺术一开凿就是上千年,这与敦煌的大家族绵延不绝息息相关,很难想象没有家族强大的经济支撑和情感绵延的事业何以延续如此久远。古代敦煌的索家、张家、曹家都是名门望族,先人实力庞大,后世也是英才辈出,这也让敦煌的文化形制不断传续。到了元代,统治者意识到了世宗大族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有意识把敦煌人向内地迁移。据史料记载,敦煌人回归东方,除过少数人以工匠之名的艺术流动外,大部分居于酒泉、张掖一带,确切说张掖高台一带。有几位敦煌学人对此问题感兴趣,专门到高台采访,便有人拿出家谱,说他们的祖先来自敦煌。西安市还残存有年代久远破败的敦煌庙。广东梅州、福建泉州还留下了敦煌人的不少遗迹,泉州有洪姓“燉煌衍派”等。这些地方共同的特征是都处在古代丝绸之路重镇上,可以推测商贾与文化的流动具有同向性。
许多来自陕西山西的游客很疑惑很好奇,说敦煌的口音怎么和他们的本地口音很像,甚至有论家认为敦煌口音就是陕西话。雍正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在微观上采取了文化相似相近原则,在宏观上也崇尚了河西归河西,河东归河东的大原则。这样就造成了敦煌的两种本地口音,河东的口音是以天水里秦州户为基础,大体相当于天水平凉庆阳陇东南口音;河西则以酒泉张掖为主,是典型的河西话。敦煌主要市区以天水里为中心,自然,陇东南话就成为敦煌人的主要口音。在过去农垦时期,敦煌的河西人与河东人相互揶揄,北地东地的人因为土地肥沃较为富有,常常笑话南地西地的敦煌人生活精打细算,后者则常常反讥前者实诚到了愚笨。甘肃的口音大体以华家岭为分界线,东边的口音与陕西口音极为接近,与西边河西口音迥异,一山成为文化的分界线,这个界限在敦煌变为一河。就此可以回应前面陕西人到敦煌有熟悉感的原因了:陇东南一带是秦文化的发祥地,严格意义上说,是陕西的口音像陇东南口音,陕西话与敦煌话都是陇东南话语体系的派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南三门峡的五千多人迁入敦煌,许多人由于想家或者不习惯干旱的气候跑回原籍去了,但留下了上千人,现在人口也有五六千了,他们也是地道的敦煌人。几乎同一时期,大批天津青年干部到了敦煌工作,后来娶妻生子,在敦煌工作生活几十年,大多融入了敦煌,许多成为敦煌文化的传承者。1990年代前后,敦煌市迎来了最后一批官方的移民,被安置在定西村及其周边,他们个个是种田的行家里手。也就是在此前后,月牙泉的水位急剧下降,引发了世人对敦煌生态问题的关注,后来大家取得了一致看法:敦煌的环境承载力是相当有限的,无法承受大量的农业移民,敦煌的居民数量才稳定下来。敦煌市周边还有六七千农场的耕耘者,他们几代人生活在敦煌,却没有敦煌的户口,2019年才高高兴兴登记入籍。一大批知青到过敦煌,1978年后,有的回上海等大城市了,也有的留在了敦煌,他们的后人从长相和待人接物都有一种海派的大气包容。远距离的交往不但是文化的碰撞激荡,而且有利于生理基因的优化。敦煌的女子贤惠吃苦,孝敬公婆是很出名的,还有大唐以来飘逸大气的美感,当然吸引了很多来敦煌的小伙子。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来敦煌做生意或发展事业的年轻人大多选择留在了敦煌,他们融入了敦煌,成为大敦煌人的一部分。
可以说,现代敦煌人的人文气质,实则是不同的历史场域和时代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包容性既有久远的历史传统,也有现代精神的介入。
五、广义上的敦煌人是受文化敦煌感召的聚集者
在漂泊的现代社会中,敦煌是一个罕见的具有家园感、安居感的地方。到了敦煌,行走的冲动就被历史的空气稀释了,诗与远方就在跟前。因此,那些常年待在敦煌的人,有一种精神的安顿感。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企业家带着奉献的情怀而来,在敦煌收获的不仅仅是企业的效益,更是一种他们自己说不明道不清的情怀。他们热爱敦煌,一言以蔽之,敦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敦煌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种精神图腾,对敦煌的热爱与付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与付出。
敦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精神的象征,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敦煌拥有几乎无限的疆域。许多人拿季羡林先生的断语解读敦煌,说敦煌是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没错,这是敦煌的世界文明意义,但敦煌首先是中华文明的集散地,这一点却被很多人忽略。敦煌是各种文化思潮各种文明因子的融合汇通地。因之,许多人到了敦煌有一种悠远的历史沧桑感。笔者原先以为敦煌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但随着接待国际友人,发现泰国、日本、韩国,甚至欧洲的国家,都对敦煌有一种说不清的痴迷,他们到了敦煌有一种说不上的亲近感。以本人的观察,作为世界文明的大观园,各种文化的基因库,敦煌的气息契合了古今中外所有人们隐蔽的文化记忆,他们到此地都感到亲切,都感到敦煌与自己有关。敦煌是与几乎每一位人有关的地方,尤其是文化人。
敦煌研究院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专家,他们把终生的心血献给了敦煌文化的研究,当然属于敦煌人。敦煌凡是有文化活动,不但本地的“外地人”都积极参加,而且全国的文化敦煌人都闻风而动。在敦煌,一个小小的文化学会或协会都可能吸引全国各地的文化名流参加,这在全国绝无仅有。
因此,海北天南的敦煌人不仅仅是籍贯上的敦煌人,不仅仅是敦煌人走出去成为世界人的一部分,不仅仅是那些在敦煌生活创业的敦煌人,更是一种被巨大的历史记忆唤醒和汇集的文化敦煌人。文化敦煌人具有广阔的甚至无限的地域,它最明显的特征是跨界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凡是有历史文化感的人,都有一种与敦煌有关的情感体验,敦煌这座城市,敦煌这个地方是与世界上几乎所有人有关的,它保存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记忆。文化本身是历史记忆的集中与升华,敦煌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每个人只要带着文化历史感来敦煌,都能感受到来自历史的温暖。大师宿儒、海外赤子带着朝圣的心情来敦煌,他们在玉门关阳关的大地上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伟大帝国昔日的伟岸身躯,他们更加懂得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之谜,他们也洞穿了未来这个民族的伟大前程。所有的心结在此被打开了,所有落于纸面飘忽的文化经典被敦煌的大地复活,他们获得了历史的馈赠,能量满满,感动满满。就此而言,敦煌更是一种精魂,一种精神,一种装满秘密的历史气息。
时代在变,敦煌人也在变。近代的敦煌人说到底是来自甘肃省各地的移民,他们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有着把距离踩在脚下的顽强生命力,但未必有深重的历史感。古代的敦煌对于近代以来的敦煌人是陌生的,但只要敦煌的文化场在,历史记忆与能量就会被复活。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吉川小一郎、奥登堡等一大批探险家或者掠夺者来了又去,陈寅恪当年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浩叹,反过来印证了敦煌的巨大魅力,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吸引了张大千、常书鸿这样一代艺术家们来敦煌,但随即敦煌仍然陷入了沉寂,普通的敦煌人仍然远在大漠边缘,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1979年前,敦煌人就是那些近世移民的后裔,他们在敦煌大地上劳作,出生成长并老去,他们自给自足,安逸古雅,很少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敦煌凭借历史的馈赠,超越了自然距离的阻隔,又一次变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越来越多的人到敦煌来旅游观光、艺术朝圣,莫高窟成为世界艺术家的圣殿。
世界变了,敦煌人背负历史的文化符号走进了最新文明的时代洪流中。打破了基于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敦煌人比方圆周边更加开放,敦煌人的特征也处在急剧嬗变当中,这实际上是敦煌自身的回归。回归不是时间的复古,而是借助历史的抛物线,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如果从文化角度广义上去看敦煌,敦煌就不再仅仅是拥有二十万居民的小城市了,而成为一切关心人类命运、打通时间界限者的精神故乡。正如欧洲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提到古希腊油然产生家园感一样,敦煌的精神温度实际上远远超越了地域,她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自然,敦煌人就不仅仅是那些守护敦煌大地的敦煌本土人,而是围绕敦煌产生所有文化情思的文化敦煌人。
严格意义上,敦煌人是那些具有强烈异乡感者,他们因为敦煌,找到了精神的返乡。